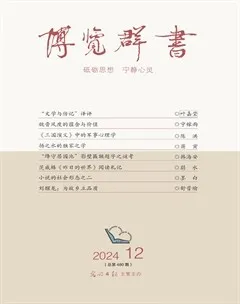藝術與詩意的交匯
2024年的夏天有些特別,隔三岔五會有一場雨降臨,濕熱的天氣以及一些地方橋塌路斷的消息還是讓人沒了外出寫生的念頭。多半時間在畫扇子,扇子雖小,但構圖不好把控,畢竟拿到手里的視覺效果和畫掛起來看的感覺大不相同,就嘗試畫一些簡單的構圖。
其實繪畫是一件快樂與痛苦并存的事情,這種“在瓦礫上跳舞”的日子也不好過,你根本不能痛快地放開了畫,我也不想重復別人更不愿重復自己,為了達到“大道至簡”的境界就得不斷地學習、思考,以求獲得更多的靈感。
偶爾看到《光明日報》主管主辦的《博覽群書》上葉嘉瑩先生評杜甫《秋興八首》:無論是技巧還是內容,都已經進入了一種更為精純的藝術境界。就內容而言,它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現實之情意,而是一種經過藝術化了的情意。就技巧來看,它有兩點,其一是句法的突破傳統,其二是意向的超越現實。“香稻啄馀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就邏輯與文法而論,此兩句實有鄰于不通之嫌,但如果把后五字當形容詞短語,來修飾前面的名詞“香稻”和“碧梧”,這樣就能渲染出記憶中香稻、碧梧一份豐美安適的意象。在傳統觀點中,杜甫是寫實派的詩人,但他的《秋興》其七“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乃是藉織女、石鯨表現一種空幻蒼茫飄搖動蕩的意象。重要的是杜詩的轉變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升華,這猶如繪畫到一定程度,你畫出的效果不一定是你能想到的,這也許就是藝術的魅力。
不知是在家久了少了大自然的供養,還是得了空調病,那些天總是乏力頭疼,精神不振時,聽我家先生說《章評新觀察》主編張永錄老師邀請我們去長安杜甫文化藝術館采風。因前段時間張老師給我寫過評論文章,對張永錄老師的學識、文筆以及寫作速度感觸很深,加之又是我欽佩的“詩圣”杜甫,所以對此行還是充滿了期待。
杜甫文化館建在杜曲是由于杜甫曾長期生活于此,“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原”表明杜甫曾居住在杜曲樊川。
車剛到文化館門口,就看見薛勇館長。據他介紹,文化館開館于杜甫逝世1251周年,即2021年初冬,他和哥哥薛平之所以在家里老宅上建館,也是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全面推進詩圣故里、花園杜曲建設,進一步發展文化建設,帶動鄉村振興。目前除了和文化名家們就杜甫的作品進行深度交流外,還和學校進行國學教育,比如讀詩、禮儀學習等活動,此外這里還是長安區青少年教育實踐基地。
薛館長介紹完文化館的情況后,張永錄老師又給大家介紹了一起參加活動的各位老師。有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王明星,書法家劉富科,西安市美術家協會監事長童登新,甘肅省文史館員安新龍,長安毛體書法家林彥等。王部長不愧是搞宣傳的,在幾位老師書法創作的時候,他又和薛館長聊起了文化館的后期發展,又書寫了習總書記說的“文明之水,潤物無聲”;85歲的劉富科老師精神矍鑠,除寫了“詩禮之家”四個大字外,還一字不落地書寫了毛澤東的《清平樂·六盤山》;長安花鳥畫家張小梅老師比較好學,看童登新老師畫了九個活靈活現的蝦,她也想學畫蝦,童老師又欣然給她畫了幅《知足常樂》圖;安新龍老師出手大方,除了給館里留了幅牡丹圖外,還給幾位老師贈畫交流,我們有幸也得到了安老師的水墨葡萄;李恩明老師畫了幅梅花迎春圖;林彥老師的書法頗得毛體神韻。
古長安少陵樊川唐詩之旅除了杜甫文化館外,還有杜甫廣場、杜公祠、杜牧紀念館、曲江唐詩古廊、李商隱文化藝術館等,這些都為古都長安的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文化滋養。在館里我們還見到了長安杜牧文化研究會行進館長,因下午還要去終南山下至相藝術空間觀看蔡小楓老師畫展,只能等下次有機會再去杜牧、李白等詩歌研究會館學習了。
蔡小楓老師我在多年前就從我家先生的文章中認識了他。此次展出的作品大部分以拓片配畫的形式出現,生活中的火龍果、蓮藕、大白菜、玉米還有貓、鴨子以及古人的計時神器滴漏都藝術化出現在作品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一幅黑白強烈對比的畫作,三只潔白的白鷺看著被淤泥包圍著的一朵朵出泥不染的荷花,神情寧靜,又似乎在思考著什么。
寫詩離不開生活,繪畫同樣也是在畫生活,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彩的世界,每個人所表達的也就不可能相同。但藝術又似乎是相通的,你聽不懂一首歌在唱什么,但那旋律又會讓你喜悅,讓你感動,抑或有想哭的感覺,其實只要你用心感受了,藝術就在你的身邊,就在你的生活中。
(作者系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女子書畫會副秘書長、陜西省婦女書畫協會副主席、陜西省美術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