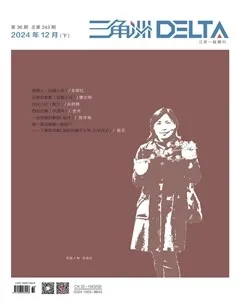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發(fā)展路徑及其必然趨勢(shì)
中國(guó)音樂(lè)史上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作為古代史與近現(xiàn)代音樂(lè)史的分割點(diǎn),自1840年之后,西方列強(qiáng)打開(kāi)了中國(guó)大門,在掠奪與侵略的同時(shí),也將文化藝術(shù)傳入中國(guó),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與外來(lái)音樂(lè)交織融合,大環(huán)境的影響促進(jìn)了本土音樂(lè)性質(zhì)發(fā)生較大的改變。政治運(yùn)動(dòng)層出不窮,西方觀念潛移默化,抗日救亡呼聲高漲,外來(lái)音樂(lè)家將中國(guó)音樂(lè)推向世界,中國(guó)音樂(lè)家遠(yuǎn)渡重洋將外來(lái)先進(jìn)音樂(lè)方法帶回中國(guó),以上種種,使得近現(xiàn)代音樂(lè)發(fā)展呈現(xiàn)出繽紛繁榮的局面,顯示出了與古代作品大不相同的音樂(lè)風(fēng)格。
縱觀歷史長(zhǎng)河,文化發(fā)展與觀念進(jìn)步必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過(guò)程,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的轉(zhuǎn)型由性質(zhì)到思想的改變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探索。自洋務(wù)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在“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觀念影響下,西方音樂(lè)逐漸進(jìn)入大眾視野。彼時(shí),國(guó)人對(duì)西方音樂(lè)文化大多仍持抵觸的看法,兩種文明在同一時(shí)空并存率先產(chǎn)生的是沖突與矛盾,而非新文化的發(fā)展。西方的音樂(lè)沖擊著中國(guó)的禮樂(lè)觀念,從排斥到慢慢接受,在中西音樂(lè)互相交織、沖撞以及摩擦的諸多矛盾罅隙中,音樂(lè)家們逐漸探究出正確的道路。
中國(guó)音樂(lè)史的轉(zhuǎn)型契機(jī)
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提出,促進(jìn)了以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為基石,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音樂(lè)的觀念誕生,此時(shí)期是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文化開(kāi)始覺(jué)醒的初步階段。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后,人們普遍認(rèn)同西方神韻,音樂(lè)思想帶有主觀意識(shí)。由于許多類似條件的催化,學(xué)堂樂(lè)歌文化誕生。大批的文化官員、音樂(lè)家赴日美等地學(xué)習(xí),歸國(guó)后將所學(xué)用于中國(guó)音樂(lè)教育的發(fā)展,在他們的努力下,文化交融出現(xiàn)了新的可能性。以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為代表人物,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學(xué)堂樂(lè)歌作品。他們將在日本留學(xué)時(shí)所學(xué)的音樂(lè)帶回了中國(guó),并靈活地運(yùn)用在學(xué)堂音樂(lè)的教授之中,使音樂(lè)課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視,逐漸成為素質(zhì)教育的重要課程。同時(shí),學(xué)堂樂(lè)歌也進(jìn)一步豐富了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的龐大載體,其成果為五四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中國(guó)現(xiàn)代音樂(lè)文化的深入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yàn)。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之后,音樂(lè)發(fā)展推進(jìn)到了一種精神層面。正如青主所講,人們逐漸接納,并把音樂(lè)藝術(shù)當(dāng)作是一種世界的藝術(shù)。與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不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不僅在音樂(lè)方法上學(xué)習(xí)外來(lái)知識(shí),更是開(kāi)始用辯證的眼光看待這一現(xiàn)象。對(duì)待異質(zhì)文化去蕪存菁,是人們觀念轉(zhuǎn)變的一大進(jìn)步,也是社會(huì)大背景驅(qū)使的必然結(jié)果。外來(lái)音樂(lè)家來(lái)華交流、多種比賽的舉行、專業(yè)音樂(lè)學(xué)校的建立,都促進(jìn)了音樂(lè)界的文化交流,促使藝術(shù)獲得更高的提升。此外,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史的發(fā)展始終游走于戰(zhàn)爭(zhēng)之中,盡管侵略者屢次三番試圖灌輸軟性文化動(dòng)搖國(guó)人意志,中國(guó)的音樂(lè)家與知識(shí)分子仍堅(jiān)守在文藝這片相對(duì)貧瘠的土壤上,在困難的環(huán)境中孕育出精美瑰麗的花朵。
本土音樂(lè)的改良與進(jìn)步
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史在改變的過(guò)程中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以及人們思想上的改觀,需從多方角度進(jìn)行研究。西方列強(qiáng)打開(kāi)中國(guó)國(guó)門對(duì)民族與百姓是極其沉重的破壞,外來(lái)文化的強(qiáng)勢(shì)入侵使國(guó)人在初始階段自亂陣腳,文化自卑與崇洋媚外思想接踵而至,不少音樂(lè)家提出全盤吸收外來(lái)物質(zhì),摒棄我國(guó)所有優(yōu)秀傳統(tǒng),極左和極右的思想觀念多年來(lái)反復(fù)困擾著音樂(lè)家的歌曲創(chuàng)作。在屢屢碰壁中,逐漸重拾文化自信,這是難能可貴的覺(jué)醒。大批音樂(lè)家推陳出新,將古老的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斷試錯(cuò),最終得以推理出最為合適的生長(zhǎng)道路。
在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歷程中,許多中國(guó)音樂(lè)家前仆后繼地為中國(guó)新音樂(lè)創(chuàng)作做出努力,他們從不同的層面出發(fā),豐富原有中國(guó)音樂(lè)的同時(shí),融入外來(lái)的創(chuàng)作技術(shù)及思想,為中國(guó)音樂(lè)開(kāi)辟了新的可能性。提出國(guó)樂(lè)改進(jìn)觀念的劉天華,將西方器樂(lè)演奏方式融入中國(guó)二胡的表演理念中,既保留了傳統(tǒng)特色,又在吐故納新的思考中總結(jié)出二胡演奏新的可行性,打造出了一條中西融合的新路徑;對(duì)近現(xiàn)代重奏作品有極高建樹(shù)的譚小麟先生,努力地?cái)[脫西方傳統(tǒng)音樂(lè)風(fēng)格的影響,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民族風(fēng)格與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旋律和聲材料與調(diào)性結(jié)構(gòu)自然地交織、融合在一起,在把握其師興德米特作曲技法體系的同時(shí),追求音樂(lè)鮮明的個(gè)性與深厚的民族風(fēng)格;近代音樂(lè)教育啟蒙先師蕭友梅先生,其聲樂(lè)作品《春江花月夜》以我國(guó)傳統(tǒng)大曲多段連綴的結(jié)構(gòu)創(chuàng)造一種完全有別于西方大型聲樂(lè)套曲的新風(fēng)格合唱套曲,雖然在和聲上他使用了西方一些大型作品所必需的轉(zhuǎn)調(diào)和調(diào)性布局,但細(xì)節(jié)部分仍體現(xiàn)了他獨(dú)創(chuàng)的新特點(diǎn),該首作品豐富了中國(guó)藝術(shù)歌曲的創(chuàng)作手法,有著非凡的創(chuàng)新意義。
以上諸例可見(jiàn),無(wú)論是從中國(guó)音樂(lè)的角度出發(fā)創(chuàng)作西方性質(zhì)的作品,還是從西方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中總結(jié)方法改進(jìn)中國(guó)的民族器樂(lè)演奏,中國(guó)音樂(lè)家們每一次的創(chuàng)作與思考,都飽含著對(duì)中國(guó)音樂(lè)求變、求新的不懈努力。
國(guó)外音樂(lè)家在華創(chuàng)作
中西音樂(lè)的交流融合,不只是西方的音樂(lè)單方面?zhèn)魅胫袊?guó),中國(guó)的傳統(tǒng)音樂(lè)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世界音樂(lè)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遠(yuǎn)道而來(lái)的西方音樂(lè)家為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如世界著名鋼琴家齊爾品訪華便是一個(gè)鮮明的例子,齊爾品的第一次遠(yuǎn)東之行旨在創(chuàng)作一部有完整意義的中國(guó)歌劇,為此,他還邀約文學(xué)家魯迅先生共同創(chuàng)作一部具有中華民族韻味的歌劇,雖然由于魯迅先生的病情,二人最終未能合作成功,但由此可見(jiàn),他對(duì)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的深深喜愛(ài);此外,他在上海國(guó)立音專開(kāi)辦的“征集有中國(guó)風(fēng)味的鋼琴曲大賽”,亦促進(jìn)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年輕音樂(lè)家的創(chuàng)作激情,打通了中國(guó)本土的音樂(lè)作品進(jìn)入世界音樂(lè)的路徑。再如阿甫夏洛穆夫,由于他長(zhǎng)期旅居中國(guó),對(duì)中國(guó)文化藝術(shù)有一定的理解,他將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與現(xiàn)代音樂(lè)巧妙地結(jié)合,創(chuàng)作出了許多以中國(guó)歷史故事為題材的音樂(lè)作品,他的音樂(lè)劇作品《孟姜女》便是這方面的重要體現(xiàn),從中可見(jiàn)他對(duì)中國(guó)戲曲改革的極大興趣;還有隨中國(guó)音樂(lè)家來(lái)到中國(guó)的外國(guó)音樂(lè)家,如青主的夫人華麗絲女士,她隨青主來(lái)到中國(guó),并在當(dāng)時(shí)的上海國(guó)立音專教習(xí)鋼琴和聲樂(lè),她利用教學(xué)之外的時(shí)間,學(xué)習(xí)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并創(chuàng)作了許多以中國(guó)古代詩(shī)歌為詞的藝術(shù)作品,如《浪淘沙》《桃花路》《易水是送別》等都是她這類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代表。
這些外來(lái)的音樂(lè)家來(lái)華,或?qū)⒆约罕緡?guó)的音樂(lè)帶進(jìn)了中國(guó),或吸收中國(guó)的音樂(lè)文化將其加以自己的理解創(chuàng)作為新的音樂(lè)作品。他們的舉動(dòng)加速了中國(guó)本土音樂(lè)走向世界的速度,他們?yōu)檎麄€(gè)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的創(chuàng)演、教學(xué)做出了一系列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xiàn)。
戰(zhàn)爭(zhēng)中孕育的時(shí)代音樂(lè)
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的發(fā)展之路,另一個(gè)不可忽略的重要路徑,是整個(gè)近現(xiàn)代中國(guó)音樂(lè)的發(fā)展始終伴隨的戰(zhàn)爭(zhēng)影響。在被外敵侵略的時(shí)期,救亡圖存的政治主題以及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始終貫穿于音樂(lè)作品之中。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抗日救國(guó)迫在眉睫,民族危亡喚醒了百姓的愛(ài)國(guó)熱情,這是全民投身救亡浪潮的時(shí)代,也是近代音樂(lè)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diǎn)。此時(shí)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緊扣時(shí)代主題,無(wú)產(chǎn)階級(jí)性質(zhì)的工農(nóng)歌曲和根據(jù)地歌曲的創(chuàng)作與傳唱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革命斗爭(zhēng)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救亡歌詠運(yùn)動(dòng)的開(kāi)展為抗日戰(zhàn)爭(zhēng)貢獻(xiàn)著重要的力量,以聶耳、冼星海等革命音樂(lè)家為代表人物,創(chuàng)作了層出不窮的群眾歌曲,為當(dāng)時(shí)的抗戰(zhàn)軍人帶去了昂揚(yáng)的斗志。
如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該音樂(lè)融合了合唱、獨(dú)唱等多種不同的形式,使得整個(gè)作品層次鮮明,表達(dá)情感豐富。其歌曲的八個(gè)不同樂(lè)章《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河之水天上來(lái)》《黃水謠》《河邊對(duì)口曲》《黃河怨》《保衛(wèi)黃河》《怒吼吧,黃河》一一為我們展現(xiàn)著黃河流域附近的不同的壯麗景色,其昂揚(yáng)的曲調(diào)、有力的歌詞無(wú)不激發(fā)著百姓心中的愛(ài)國(guó)熱情,推動(dòng)著廣大人民群眾投身于抗戰(zhàn)的隊(duì)伍之中,積極抵御外敵,頑強(qiáng)保衛(wèi)家園。再如張曙抗戰(zhàn)歌詠的《還我山河》,整首音樂(lè)節(jié)奏雄渾有力,用如同呼喊般的曲調(diào)歌頌著戰(zhàn)場(chǎng)上英勇殺敵、保家衛(wèi)國(guó)的將士們,歌詞鏗鏘有力地唱著“以我們的熱血澆自由的花朵,以今天的犧牲換萬(wàn)代的平和”,彰顯了那個(gè)年代的人民為家園甘灑熱血、無(wú)私奉獻(xiàn)的精神。歌曲與當(dāng)時(shí)人民百姓的心情緊密結(jié)合著,鼓舞著千萬(wàn)的人民群眾抗擊外來(lái)侵略者的斗爭(zhēng)意志。
諸如此類在戰(zhàn)火之中孕育的歌曲,皆反映著強(qiáng)烈的革命樂(lè)觀主義精神,他們不僅是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時(shí)代的強(qiáng)烈需求下,應(yīng)時(shí)而生的音樂(lè)藝術(shù)瑰寶。他們的出現(xiàn),一定意義上為當(dāng)時(shí)的群眾帶去心靈上的慰藉,亦為水深火熱之中的廣大人民指明了前進(jìn)的方向。
我們今天再去探究以上音樂(lè)的歷史進(jìn)程可以發(fā)現(xiàn),毋庸置疑的是,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發(fā)展每個(gè)階段的歷史演變都伴隨著諸多社會(huì)事件及政治事件的行進(jìn)。在這些事件中,總有伴隨時(shí)局應(yīng)時(shí)產(chǎn)生的音樂(lè)作品,他們以人民百姓喜聞樂(lè)見(jiàn)的傳統(tǒng)形式從古代社會(huì)自然流傳了下來(lái),又被接受外來(lái)音樂(lè)理念的音樂(lè)家以更新的形式融合創(chuàng)新出來(lái),而后順應(yīng)著時(shí)局的變化表露著人民百姓的心聲,這些音樂(lè)產(chǎn)物串聯(lián)起了時(shí)代發(fā)展的整個(gè)歷史軌跡,這是社會(huì)發(fā)展早已預(yù)知的結(jié)果。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錯(cuò)綜復(fù)雜的大環(huán)境趨勢(shì),而不單單是某個(gè)音樂(lè)家或者某個(gè)音樂(lè)作品的功績(jī)。故而,回顧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史的發(fā)展與轉(zhuǎn)變,會(huì)發(fā)現(xiàn)人物是音樂(lè)發(fā)展創(chuàng)作的催化劑,而社會(huì)事件、政治事件、制度更新、戰(zhàn)爭(zhēng)更迭等諸多原因都是其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原始動(dòng)機(jī)。
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的轉(zhuǎn)型,在諸多音樂(lè)家及人民群眾團(tuán)體的創(chuàng)作下得到極大蛻變,而政治的影響、西方的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更迭決定了近現(xiàn)代音樂(lè)的走向與最終形態(tài)。文化藝術(shù)的積攢使得后來(lái)者在回顧借鑒時(shí)有跡可循,溯源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從往昔經(jīng)驗(yàn)中得以不斷繼承、揚(yáng)棄、推廣。外來(lái)音樂(lè)使得我們更好地檢討自己的文化缺陷,以融合進(jìn)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如如今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踩在往日作品的創(chuàng)作肩膀之上,20世紀(jì)近現(xiàn)代的音樂(lè)作品也依托傳統(tǒng)的音樂(lè)文化、外來(lái)異質(zhì)文化和諸多社會(huì)原因得到更大的發(fā)展。
作者簡(jiǎn)介:
王妍妍,女,1999年5月生,漢族,哈爾濱音樂(lè)學(xué)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guó)近現(xiàn)代音樂(l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