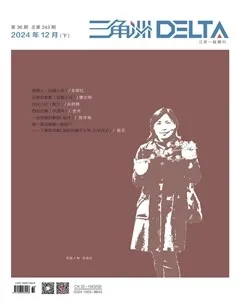微觀史學視域下分析《馬丁·蓋爾歸來》一書
以戴維斯及其代表作《馬丁·蓋爾歸來》為例,對其內容進行剖析的同時,讓我們從史學的角度考察這篇著作的絕妙之處。真假馬丁·蓋爾的出現打破了小村莊的平靜,富裕的農民馬丁·蓋爾狠心離開又突然歸來,后來他又與親戚爆發財產糾紛鬧上法庭,妻子迫于壓力竟然把他送上了審判席。就在這時,真正的馬丁·蓋爾居然出現了。作者戴維斯試圖通過講述這一離奇的冒名頂替故事,再現16世紀法國農民的經濟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從各方面刻畫他們豐富的生活細節。
法國農村社會歷史背景分析
一、人口狀況:農民階層分布
十六世紀的法國人口約有1500萬,是歐洲大國,巴黎有居民30萬,為歐洲最大的城市,但法國當時仍然是封建農業國。盡管農奴制早已廢除,但法國的農民依然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控制。同英國農民那種“自由且有尊嚴”的形象大不相同,法國農民在一生中要受到國王、封建主和教會的三重盤剝。如果再稍微遇到一點天災人禍,法國農民就很有可能失去他們的生命。
在大革命前,農民階層總體能分成三部分。其一,是善于參與市場投機和土地買賣的土地承包商和農場主;其二,是固著在土地上,有時也依靠小商品交換獲取收入的普通農民;其三,是依靠出賣體力、出售手工藝品等低級手段獲取財富的貧農,他們甚至可能沒有一塊棲身之地。
二、經濟發展狀況:資本主義
十五世紀末時,法蘭西開始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清除了中世紀的封建割據狀態,促進了經濟發展,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從而帶來階級結構的新變化。16—17世紀的法國,封建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仍是法國社會的經濟基礎。但是,十六世紀前法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農民階級保持了自己經濟的獨立性。法國農奴早在十二世紀就開始人身解放,到十五世紀末已成為在封建法權掩蓋下的小租佃者,他們享有相當程度的人身自由。
十六世紀前期,法國農村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已經開始,不過它與英國的方式不同,而是采取了國債制度和包稅制度的形式。由于十六世紀“價格革命”的發展使征收固定地租的封建貴族損失慘重,封建國家為了補償貴族的損失,便大量增加國稅。從1522年開始,法國政府發放有息公債券,資產階級于是購買公債,依靠高利貸獲取高額利潤。貨幣大量集中在少數大商人和包稅人之手,這就為法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生創造了前提。
三、階級關系變化:大工場
在法國封建社會末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仍然產生了資本主義因素。十六世紀,工業中的資本主義關系就已經萌發,只是因為封建制度的阻撓,所以拖到十八世紀下半期才成長起來。十六到十八世紀,商品貨幣發展,重商主義流行。
十六世紀時,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資本主義分散的工場手工業的萌芽在法國的農村出現。這種分散的工場手工業,主要集中在城市周圍的農村中。在城市里,則出現了比較發達的工場手工業形式。為了從對外貿易中獲得大量金銀而開辦王家工場的,但在客觀上,這些大工場卻成了后來法國大工場手工業的搖籃。
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封建勢力是要鞏固自己統治和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但法國封建政府開辦王家手工場的結果,卻增強了資本主義力量的發展,可見進步的資本主義一定要代替落后的封建制度這個客觀規律的作用。十七世紀時,法國農民中出現了財產分化現象、互相租地現象,以及寄生蟲階級分化現象。不過這種新型關系只是資本主義關系的萌芽形式,真正的富農農場或企業式的大農場在當時的法國農村中是罕見的。到了十八世紀,情況就不同了。農村中除了富農經濟外,還出現了一些資本主義大農場。
法國的資本原始積累也是跟剝奪農民有聯系的,但剝奪的主要方法不是英國式的圈地,而是租稅壓迫。沉重的租稅迫使無數農民典押和出賣土地,變成分成制租佃者、雇農和貧窮的流浪者,這些人構成了十六世紀開始出現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主要勞動力。
微觀史學下的《馬丁·蓋爾歸來》
一、十六世紀法國文學發展背景
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浪潮下,歐洲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弗朗索瓦一世是十六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國王,由于從小接受來自意大利的藝術熏陶,他對于意大利文藝復興非常喜愛,還將文藝復興的先進思想、藝術形式帶進德國,奠定了法國文藝復興的步伐,被稱為“法國第一位文藝復興式君主”。
文藝復興源于意大利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表現為對古希臘古羅馬的重新發現與熱情向往。文藝復興傳入法國后,為法國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的主要思潮。文藝復興運動充分肯定人的價值,重視人性,成為人們沖破中世紀的層層紗幕的有力號召。
與此同時,由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傳播到了法國。由于法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矛盾激烈,法國發生了多次宗教戰爭。1598年,亨利四世規定天主教為法國國教,內戰結束,法國成為首先對新教寬容并實現民族統一與宗教差異并存的國家。
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們對宇宙和世界有了新的認識。1455年,約翰內斯用活字印刷機第一次印刷了《圣經》,是西方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人,他的發明導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推動了西方科學和社會的發展。指南針的運用和造船技術的進步也促使了地理大發現。
二、戴維斯其人其書
戴維斯出生在美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母均為祖籍東歐的猶太人。在學習期間,戴維斯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早年的學習經驗對她早期的研究曾有不小的影響。從1963年至多倫多大學任教,至1977年離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總共有15年的時間,這無疑是她學術生涯中最關鍵的時期。在此期間,她在分析里昂檔案的基礎上,在歐美核心史學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頗有分量的社會文化史論文,這些論文奠定了她作為社會文化史學家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除了本篇著作外,其他的還有《檔案中的虛構》《邊緣女人》《騙子游歷記》等。
《馬丁·蓋爾歸來》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540年,在法國中南部一個名叫阿爾蒂加的山村里,一個名叫蓋爾的富裕農民離家出走,多年杳無音信。突然有一天“他”回來了,并與他的妻子貝特朗度過了幾年的幸福時光。然而,隨著“馬丁”與其叔父在經濟上的沖突加劇,在其叔父的威逼之下,“馬丁”的妻子將他告上了法庭,說他是冒名頂替者。正當他行將勝訴之際,真正的蓋爾歸來了,經過地方法院和圖盧茲高等法院的兩次審判之后,真相終于浮出水面,假馬丁受到了頗為嚴厲的懲罰。這個傳奇性的故事不僅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而且也引發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問題。妻子為什么要承認一個冒名頂替者為自己的丈夫,為什么又要告發他?這個家庭中的人際關系是怎樣的,這個故事反映了村民的哪些想法、愿望和感情?正是有了這樣一系列的問題,這個故事得以在法國長期流傳下來,1561年就有兩本書寫這個案件,其中一本還是參與審判此案的一個法官寫的。此后這個案件在法國常被提到,還引起熱烈討論。
如果我們可以將全書的第一至第九章視作故事的主體的話,那么這本書的導論、尾聲以及第十、十一和十二章就全然不是在講述這個故事本身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戴維斯想要達到的目的,顯然不可能是僅僅通過對于史料的爬梳將這個故事盡可能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故事背后,作者還希望能夠提供某種可能的歷史解釋。在1988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她點名撰寫此書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將這個故事置于16世紀法國村落生活和法律的價值和習慣之中,借助它們來理解這一故事的核心因素,并借助這一故事回過頭來討論他們——也就是說,將一個傳說轉化為歷史”。
這部著作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史學界的極大關注。后現代史學的倡導者安克斯密特則將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金滋堡的《奶酪與蛆蟲》和杜比的《布文的傳說》一道稱為“后現代歷史編摹學”的代表作。最重要的是,這三本書開啟了微觀歷史學的先河,成為微觀史學濫觴時期的三大典范之作。
微觀史學的現代性特征
一、總體史觀:微觀史學與年鑒學派
法國年鑒學派的著名史學家雷維爾認為,微觀史學的出現與流行是與學界對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主流社會史研究中宏觀分析法的不滿密切相關的。狹義上的微觀史學主要是與意大利史學家卡羅·金茲堡等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對于這一學派的方法,金茲堡與波尼等人認為年鑒派主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長時段的計量分析,會掩蓋與歪曲事實,他們處理的時段無法觸及對日常生存的問題。微觀史學將自身定義為“現實生活的科學”,以重構宏觀分析無法理解的“現實生活”為宗旨。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從學理上說,這種方法實際上是從社會網絡的角度把握個體,從個體的角度理解社會。
從以上的一些學者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微觀史學的發生和發展實際上既是對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第二代年鑒派的宏觀分析維度以及肖努為代表的計量史學方法的反動,也是這一思路在某種程度上的延續和發展。雷維爾進一步指出:“微觀史學讓史學家得以把握宏觀方法無法分析的社會行為和經驗及群體認同的形成過程。其實,這個研究策略的變化,史學家的策略不再是對抽象特征進行統計,而是將這些整合,連接在一起。”從雷維爾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微觀史學提醒人們,每個歷史行動者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不同層面的不同過程,這些層面包括最地方性的以及最全球性的層面,因此,在不同層面之間并沒有斷裂,更沒有沖突。
二、“一葉知秋”:微觀史家們的訴求
在談到《馬丁·蓋爾歸來》和《奶酪與蛆蟲》《蒙塔尤》這三部微觀史著作時,戴維斯曾一再強調:他們對16世紀鄉村社會的興趣,至少不亞于對他們所處理的故事本身的興趣,在研究方法上,他們追求的正是兩者相互補充的效果。從戴維斯和勒華拉杜里等人的“自說自話”中,我們不難看到,雖然微觀史家們將其研究的區域縮小到了一個極為有限的范圍甚至個人,但他們似乎都沒有放棄一種一葉知秋的抱負:總希望能夠從個別的事實中發現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信息。然而,我們怎么能知道他們所研究的個案能夠具有真正的典型性呢?金茲堡認為,格蘭第的“正常的例外”這一概念有兩重意思:其一,它指的是那些只是表面看起來屬于例外的人和事;其二,假如資料對下層階級的社會現實是系統的歪曲,那么一個真正例外的文獻較之一千種老套的文獻更有啟示。
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認識,我們不難看到,微觀史學的興起和發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宏觀研究以及宏大敘事的發動,但二者的關系似乎并非如此簡單。在縮小視閾的同時,微觀史家一方面既沒有放棄對于總體史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沒有丟下一葉知秋的抱負。因此,從這兩點上看來,微觀史學似乎并未脫離現代史學尤其是年鑒范式的軌道。可以說,它仍然具有十分強烈的現代史學特征。
綜上所述,這樣一種擺動于現代史學與后現代史學之間的狀態就是微觀史學的重要特征。
在本書中,戴維斯引導我們思考:16世紀法國農民實現社會流動和階層躍升的渴望為何如此強烈;在沒有指紋和照片的年代,一個人的身份是如何界定的;人際網絡起著怎樣的作用;新舊勢力的對抗、不同文化習俗的沖突、風云變幻的國際局勢如何攪動地方社會。
(作者單位:山東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