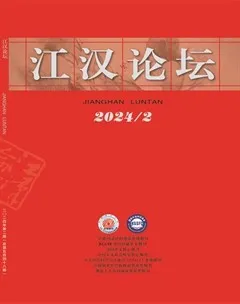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命:演化方式、危險與倫理考量
舒紅躍 張穎
摘要:強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最主要的分類之一。在存在論層面,弱人工智能是人類生存的技術手段,而強人工智能則是如同其他生命一樣,可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人工的智能生命。按照生命演化史上其他生命,特別是人類的進化模式,作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演變不應是奇點式突變,而應是漸進式進化。如果說弱人工智能的威脅是人類歷史上又一次新的技術威脅,那么人工智能生命的威脅則在于生命演化史上首次可能出現類人類和后人類生命,這改變了人類在生命演化史上的價值和意義。后人類生命的出現,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類的生命觀和價值觀,在人類視角和生命共同體視角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人工智能;生命;演化;倫理考量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認知科學哲學視域下的人工共情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1CZX020)
中圖分類號:Q111;TP2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2-0053-08
作為一個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了數百萬年的物種,人類在歷史上遇到過的挑戰數不勝數,而人工智能則是我們遇到的最新挑戰。自從被發明(現)以來,我們對人工智能的關注不僅在于它是一種什么技術,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起什么作用,而且還關注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它將會如何發展和演變,能否從弱人工智能演化為強人工智能,從人類的技術手段演變為具有自我意識和生存意志的生命體。如果人工的智能生命最終成為了生命演化史上又一種生命形式,那么,這種新的生命會以什么方式演變,會給人類帶來何種風險,人類又該如何調整自己的生命觀和倫理準則,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存在論層面的人工智能分類:技術手段與人工智能生命
如何區分不同類型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個基礎性理論問題。現有分類中最重要、最流行的是強人工智能(Strong AI)和弱人工智能(Weak AI)、專用人工智能(Special-purpose AI)和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區分。其中,專用人工智能(專司某一特定領域工作)和通用人工智能(像人類那樣能勝任各種任務)的區分歧義不大,但強弱人工智能的區分標準不盡相同。現有強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的區分是在認識論或認知主義范圍內展開的,主要依據是感知和計算能力的大小。問題是,僅從認識論或認知主義角度能不能真正切中人工智能的本質,有無其他分類方法?
人工智能如何分類還得從其概念入手。如何理解人工智能,難點不在“人工”而在“智能”。何謂智能,既有傳統研究的回答,也有當今主流研究的回答。傳統人工智能研究者通常被稱作是認知主義者,他們認為所謂智能是實現現實目標的計算能力,無論是學習、記憶還是情感,認知的所有方面都是可以由計算機(器)來執行的。“經典的人工智能研究方法圍繞一整套研究的原理和實踐展開,這些原理和實踐主要探究認知主義的正確性,尤其是以紐厄爾和西蒙提出的物理符號系統假說為研究對象。”在認知主義者眼中,認知最佳的理解是對符號結構的形式化操作。現今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有三種范式: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行為主義。對于何謂智能,它們的回答并不一樣。符號主義理論主要是“物理符號系統假設”,認為人工智能來源于數理邏輯,我們可以用數理邏輯來描述人類的智能行為。連接主義把智能理解為神經網絡(包括不同神經網絡之間)的連接機制和學習算法,它不是從邏輯運算,而是從神經元來研究神經網絡和大腦的模型。行為主義把控制論看作是人工智能的理論基礎,它把智能歸結為控制(包括對感知和動作的控制),智能是對環境做出反應的能力的附屬特性。現有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人類的思維、感知和行為,三種主流范式對智能的解釋均是對人類大腦或行為進行的認知主義或認識論研究。
不過對于智能,除了認識論層面的回答之外還有存在論層面的回答。在認識論層面,大腦神經系統是一部制造表象的機器,其功能在于接受外部刺激,然后制作表象。在存在論層面,大腦神經系統并非制造表象的機器,而是一個接受和反饋真實世界信息的器官,它的主要功能也不是什么制造表象,而是在于現實世界中的行動。從存在論角度看,理解能力只是行動能力的附屬物。人的理智如何構成,這首先取決于一個人在現實世界具有什么需求,然后如何利用現實世界中的各種物質來滿足這些需求。“狹義而言,我們的智力旨在讓我們的身體完美地適應其環境,呈現外在事物彼此間的關系——一句話,琢磨物質。”智能的本質在于服務于生命體的在世生存,這不僅是哲學家的觀點,也是人工智能專家的觀點。作為人工智能學科奠基人,圖靈(A. Turing)不僅發現了智能與遺傳或進化搜索之間的對應關系,而且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搜索的判斷標準是生存價值,這樣一來,基因才會受到照顧。這種搜索方法極為成功,這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智慧活動主要是由各種不同類型的搜索組成的。”
智能是生命體面對環境的挑戰應運而生的,它服務于生命體的生存。迄今為止智能屬于生命體,非生命體是沒有智能的。從進化論角度看,生命體之所以誕生智能,是為了更好地在自然中生存,擁有智能的生命體比沒有智能的生命體具備更有效的生存方式和更好的適應能力。自然演化出來的智能,本質在于服務生命體的生存;人類創造出來的智能,也就是人工智能目的何在?不管人造的智能人造程度有多高,它本質上仍然是智能;而只要是智能,它就不得不服務于生命體的生存。然而,現有相關研究大多從認識論角度出發,沒有把智能與生命(體)的生存聯系起來,主要關注其感知和計算能力,忽視其存在價值和目的。如果從認識論轉向存在論,從人工智能的認知(計算)能力轉向它們在真實世界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就不是依據它們的認知(計算)能力,而是根據它們在真實物理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來對其進行分類。“認知范例忽略了智能體生活在真實物理世界中,從而導致了在解釋智能體時所產生的嚴重缺陷。”只要不是生活在由人類特意設計的實驗環境中,而是生活在現實的物理世界中,人工智能需要的就不僅是認知(計算)外在環境的能力,而且是像人類那樣,在真實大自然中生存的能力。具有后一種能力的人工智能不僅需要認知,更需要在真實世界中存活下去的情感和意志。
由此一來,可以得出一種新的區分人工智能種類的方法,建立一種存在論的人工智能類型學。如果機器(計算機)只能夠感知和計算由人類特意設計的、小型的、簡單的實驗環境,只能在特定的微觀世界活動,無法成為能夠在真實物理世界中生存的生命體,其智能并非服務于機器自己,而是服務于設計者的需求,那么,這一智能就是弱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不僅能夠認知(計算)外在世界,而且能夠依靠自身在真實世界中存活,其智能不是服務于其他生命的生存,而是用于自己生存,那么它屬于強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不過是人類在世存在的(技術)手段,強人工智能是能夠像其他生命,特別是人類那樣在大自然中生存的生命體。
強弱人工智能的區分雖然很流行,但它有一個誤區,那就是把不同類型的人工智能看成同一個存在論層面的現象,不同人工智能的區別僅僅在于認知和計算能力的不同。問題在于,真正能夠區分人工智能不同類型的標準不在于感知和計算能力,而在于是否具備在真實物理世界中生存的能力。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多有影響的專家對強人工智能的界定均是含糊的,容易讓人誤入歧途。這些學者所理解的強人工智能并非能在真實物理世界中生存的生命體,而是既具有部分生命屬性,同時具備部分技術屬性。其中,古德和波斯特洛姆的理論很有代表性。
古德(I. Good)是最早論及強人工智能的學者之一,他將其界定為“超級智能”。“超級智能機器被定義為是遠遠超過任何人的所有智能活動的機器,不管這個人是多么的聰明。由于設計機器屬于這些智能活動之一,故而超級智能機器甚至能夠設計更好的機器;毫無疑問,將會發生‘智能爆炸’,人類的智能將會被遠遠拋在后面。所以,第一臺超級智能機器是人類能夠做出的最后的發明,如果這臺機器足夠溫順,能夠告訴我們如何控制它的話。”古德對超級智能的界定在學界頗有影響,問題是,他所理解的超級智能到底是一種技術,還是一種生命?在存在論層面,人工智能要么是人類生存的技術手段,要么是具備自我意識、能夠像其他生命一樣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生命體。從這一理解看,古德的超級智能是一個弱人工智能(技術)和強人工智能(生命體)的混合體,他沒有明確說明它到底是一種技術還是生命。一方面,古德是明確地把超級智能描述為機器的。盡管這臺機器比所有人(包括最聰明的人)更聰明,在所有活動中都超越人類,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臺機器。另一方面,如果這臺機器在所有活動上都比人類優越,那就包括涉及情感和意志的活動,這臺機器就已經不再是機器,或者說不僅是機器,而是一種能夠像其他生命那樣在現實世界中生存的生命體。故而,古德的超級智能是一個“混合體”:既可以是人類用于自己生存的技術手段,也可以是一種類人類甚至后人類生命。
波斯特洛姆(N. Bostrom)也是著名人工智能專家之一。超級智能,人們通常用它來指代在許多認知領域中的表現遠超越目前最聰明的人類頭腦的智能,但波斯特洛姆認為這一概念并不明晰。為了走出術語的泥沼,減少概念的含混性,波斯特洛姆把超級智能分為“高速超級智能”(不僅能完成人類智能能完成的所有事情,而且速度快很多)、“集體超級智能”(由數目龐大的小型智能組成,在很多領域中的整體性能遠超現在所有認知系統)和“素質超級智能”(不僅至少和人類大腦一樣快,而且聰明程度遠超人類)三種形式。雖然波斯特洛姆的描述比其他學者更具體、更詳細,但他仍沒有把工具性人工智能與生命性人工智能區分開來,沒有說明這三種形式的超級智能到底屬于技術還是生命。波斯特洛姆的混淆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是一個普遍現象,正是這種混淆導致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理解存在著很大誤區。強人工智能一旦產生,就不應該再被當作是工具性的技術手段,而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生命體,一種能像所有其他生命那樣在真實物理世界中生存的新型生命。
弱人工智能只是人類的又一次技術革命。人類面對技術革命并不陌生。無論是從蒸汽機、內燃機到電動機,還是其他的工業革命,我們積累了一次又一次應對技術革命的經驗。在面對弱人工智能時,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雖然有時手忙腳亂,但整體上還是“輕車熟路”。強人工智能屬于一種新的生命形式,它不再是技術(手段),它的出現是生命進化史上的又一次標志性事件。傳統的自然生命在地球上進化了數十億年,新的人工生命的演變方式和傳統的自然生命的進化方式有何不同,這既決定人工智能生命給人類所帶來危險的性質和程度,也將影響人類對待這種新生命的方式和方法。
二、人工智能生命的演化方式:奇點論與漸進式進化
作為地球上成千上萬的物種之一,人類能不能永遠存續下去?“這個世界開始的時候,人類并不存在,這個世界結束的時候,人類也不會存在。”人類是生命演化史上某一個階段才出現的產物,不可能永遠駐留在現有的進化水平上。人類的未來有兩種可能性:要么在某一天終將滅絕;要么繼續進化,以其他方式存在下去。在各種可能的后人類生命中,人工智能僅是其中之一。人工智能生命能否產生,這在學界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這里暫不討論,而是假定:如果可能,它將以哪種方式演變,是以連續進化的漸進方式產生,還是以奇點式的突變方式出現?
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歷史上,不少專家不僅認為人工智能生命是可能的,而且認為產生過程很短暫,其中“奇點論(Singularity)”影響最大。1952年,圖靈預言機器將獲得對人類的控制權,但他沒有具體論述機器是如何取得這一控制權的。1957年烏拉姆(S. Ulam)認為,在技術不斷加速發展、人類生活模式不斷改變的情況下,我們正在接近物種史上某個重要“奇點”,在此之后人類現有生活無法延續。1965年古德認為,一旦能夠制造遠超任何人類智力活動的機器,將會帶來智力的爆炸式增長,人類智力將遠遠落后于機器。1990年文奇(V. Vinge)認為,30年內將會出現超越人類智慧的技術,人類時代終將結束。2011年庫茲韋爾(R. Kurzweil)認為,人類正在接近一個計算機智能化的關鍵性節點,機器將會變得比人更聰明,他甚至預測了純粹人類文明終結的具體時間(2045年)。
在強人工智能研究中,雖然奇點論非常有代表性,影響也很大,但問題是:人工智能生命的誕生除奇點論的突變之外,有沒有可能是連續進化論的漸進方式?古德對超級智能的出現用的是“爆炸”一詞,也就是猛烈地、突然地產生,我們能夠明確看到哪一天出現的計算機是“第一臺”超級智能機器,這臺機器是人類“最后一次”的發明。在奇點論這里,人工智能生命的出現是點狀而非線狀的,是突變式而非漸進式的,剛剛誕生的人工生命是“一”而非“多”。那么,奇點論有沒有可能誤判了人工智能生命的演變方式?一旦誤判,那會對我們如何應對它們的威脅造成災難性后果。
生命如何進化,既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科學問題,很多學者都從事過相關研究,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達爾文。作為進化論奠基人,達爾文研究的是自然生命的進化,認為這一進化是連續的。“自然選擇僅能借著輕微的、連續的、有利的變異的累積而發生作用,所以它不能產生巨大的或突然的變化;它只能按照短小的和緩慢的步驟而發生作用。因此,‘自然界里沒有飛躍’這一格言,已被每次新增加的知識所證實。”生命誕生之后不會在某一個水平停留不動,而是繼續進化,在達爾文看來,這種進化是通過無數次輕微、連續且有益的變異而發生的。達爾文并不認為自然生命的進化會出現巨大或突然的變化,“奇點”式進化在達爾文的理論中是不受歡迎的。
在所有生命的進化中,我們最關注的是人類的進化。人類是大自然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誕生出來的,其進化是通過猿類不斷地累積“輕微的”“連續的”“有益的”變異而發生的。人類從猿類演化而來,人猿之間并沒有產生巨大或突然的變化,人類只能通過猿類發生短小和緩慢的改變一步一步地演化而來。無論是哲學史還是科學史,主流觀點認為,人類與動物(不包括人類的其他動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二者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演化生物學告訴我們,雖然人類與在血緣關系上離我們較遠的動物有很多區別——某些方面是巨大的、明顯的區別,但與在血緣上離我們很近的動物是高度相似的。人類的身體,既包括外在解剖結構,也包括內在分子成分(基因),都與我們的近親動物高度相似。在血緣上與我們最近的動物是另外兩種黑猩猩,我們與它們不僅外形相近,而且基因組98%是相同的,有差別的只有2%。人之所以為人,“我們獨特的素質,不僅很晚才出現,涉及的遺傳變化也很少,那些素質(或至少那些素質的‘原型’)必然早已在自然界出現了,其他動物身上應該可以觀察到”。
對于人類與后人類生命的關系,一方面,我們無法以實證科學的方式研究,因為所有后人類生命目前都是理論上的假設,并非現實世界的存在物。另一方面,雖然不能以實證的方式研究后人類在哪些方面與人類相同或相異,但我們可以借助演化生物學等實證科學提供的人類與動物的關系為參照,來看人類與后人類生命的關系。人類的很多特征在動物身上已經出現,人工智能體的很多特征也是人類特征的復制和再現。人工智能體的出現,只不過是人之為人的特征一個接一個地在機器身上的復制和再現,是在現有人工智能能力之上不斷增加“X”的過程。強人工智能的很多能力,在弱人工智能身上早就具備,如學習能力、規劃能力。只有經過無數次的小步快跑,逐漸提升,人工智能才能夠突破人機間的門檻,從人類的技術手段演變為能自己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生命體。
在生命演化史上,人類與人類之前的動物的關系是漸進性而非突變性的;作為類人類、后人類生命,它們與人類之間的關系也應是漸進性而非突變性的。在剛誕生和誕生后一段時間內,人工智能生命與人類的區別是程度的而非本質的,因為演化是具有連續性的。“演化很少會‘拋棄’什么。結構只是經過轉變而被改良,從而承擔起其他功能,或被‘調整’為朝著另一個方向演化,這就是達爾文所說的改良式繼承。”很多科學家和哲學家,非常喜歡把人類的某一性狀置于無上地位,完全否認作為其來源的、在動物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低級”性狀。在涉及人類時,他們相信飛躍,相信跳躍式變化,將人類與其他動物在諸多方面的不同或不連續性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這種觀點延伸到后人類與人類的關系上,他們也會夸大后人類與人類之間的間斷性,把后人類看成是一種與人類完全不同的生命。事實上,也有很多科學家并不支持這一觀點。“蚯蚓的大腦如何運行與計算機如何計算,二者之間沒有引人注目的區別……進化意味著,在蚯蚓的大腦和人的大腦之間沒有質的差異。故而可得出結論,計算機原則上能模擬人類智能,或許甚至做得更好。”
人類的產生是一個漸進式進化過程,人工智能生命的出現也應是一個漸進式演變過程。在人工智能演化史上,將來不僅會出現“機人”(與機器結合的人類,具備機器的某些屬性,甚至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機器,但整體上仍然是人類)、“人機”(類似人類的機器,雖然在物理構造上是機器,但已是真正的生命體),還包括半機人、準機人、半人機、準人機。從人類到后人類生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中間環節,有很多人性多一些、機器性少一些,或機器性多一些、人性少一些的過渡環節。也許到了某一天,人類會像注射疫苗一樣,從出生開始,隨著年齡的增長定期植入不同功能的晶片。未來人是可能接受這一點的,雖然現在很多人不能接受,就像古人不能接受在身上動刀子一樣。從人到“機人”“人機”是一個慢慢進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人類慢慢適應和接受的過程,甚至從被動接受到主動融入的過程。
人工智能生命的演化,最關鍵的并非智能,而是在真實世界中的生存能力,這也是一個漸進過程。在奇點式人工智能進化中,人類的能力被認為是一個需要跨越的里程碑。問題是,無論是作為一個物種還是作為個體,人類的生存能力并非一個“點”,而是一個“系列”,一個連續的系列。作為一個物種,人類的生存能力有一個從植物、動物到人類層次的逐步提高的過程,其中動物層面又有一個從最低端的動物到哺乳類、靈長類直至人類的提升。作為個體,人類的生存能力有一個從胎兒、幼兒、兒童直至成人的提高過程,成人的生存能力是通過歷年的生長和發育慢慢成長起來的。同樣,人工智能的生存能力不會奇點式地從植物突飛到人類,從嬰幼兒猛進到成年人水平。人工智能生命生存能力向人類的逼近,是一個一個方面逐漸接近人類水平,并非整體上、一次性達到人類水平,這是一個漸進性積累的過程。
人工智能生命連續進化有一個重要表現,那就是隨著人工智能的逐步演變,終有一天,我們將無法把人與機器完全區分開來。“人類和機器智能之間的界限越發顯得模糊,因為機器智能越來越多地源于其人類設計者的智能,而人類智能也因為機器智能得到了更大提高。” 無論是體能還是智能,人類都與自己制造的機器糾纏在一起,彼此難以分辨。在依舊使用碳基神經元的人類智能中,神經植入技術業已普及,這大大提高了人類的感知和認知能力。人類智能不僅業已和機器糾纏在一起,生命演化史上最有可能出現的后人類生命將是人機混合體。人類(智能)與機器(智能)相互結合的方法不勝枚舉,這不僅會徹底改變機器的定義,而且也會徹底顛覆人的定義,人和機器的界限日趨模糊。
人工智能生命的演變是漸進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倫理上的考量。作為類人類、后人類生命,人工智能生命出現之后是有可能在短期內毀滅人類的。為了避免這一極端情況——這是后人類時代整個人類最大的責任和使命,人工智能的演變也應是漸進式的。“在存在級別上高于人類的人工智能也許會漠視人類的存在,饒過人類,讓人類茍活,但問題是,它有可能傷害人類。” 在存在級別上高于人類的人工智能當然具有傷害甚至滅絕人類的可能,但這種可能性的發生是有條件的。一個物種能滅絕另外一個物種,兩者間的生存能力有極大差距,甚至是代差。如果人工智能遠遠超過人類的能力是突然出現的,人類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應對方法,那么,人類被人工智能毀滅將是大概率甚至無法避免的事。故而,在研發新人工智能,特別是其臨近誕生自我意識時,“人類必須做到‘道’在‘魔’先:面對具有存在性風險的研究進展,必須先有防范之道,才能進入實施”。人類必須避免人工智能生命的過快發展,在關鍵性技術節點上應盡可能達成共識,不讓其生存能力在較短甚至極短時間內與人類出現代差,從而導致人類在滅頂之災前沒有時間自救。如果能讓人工智能的演變是漸進式而非奇點式的,我們就能創造一個人機共存的局面,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將有機會繼續在這個星球上生存和繁衍。
正因為人工智能生命的演變是漸進的,這就給人類提供了一個調整自己的倫理準則和價值觀的窗口期。在人工智能演變的不同階段,人類所起作用是不同的,真正關鍵的時期是人工智能生命誕生的時候和進化早期。不同于從猿到人的演化是一個自然過程,人工智能生命的產生是一個在一段時間內受人類影響,甚至是由人類主導的過程。這是人工生命演化和自然生命演化的本質區別。在人工智能生命誕生前后和進化早期,人類對其產生和演變方式,特別是其如何進入人類社會、如何與人相處擁有較大的干預權。隨著人工智能生命的自主性越來越強,它們對自身的演變方式擁有越來越大的發言權,最終具有與人類同等的人格,甚至是“后人類”人格。
綜上所述,人工智能生命的漸進式進化既有歷史上的緣故,也有倫理上的理由。無論是參照生命演化史上的案例,還是針對其自身的進化,人工智能生命的演變都不是奇點式的突變,而是“步步為營”的漸進式的連續進化。作為一種生命體,盡管是人造的生命體,人工智能生命仍然將遵循傳統的生命進化方式——連續進化而非奇點式突變。雖然作為人類技術手段的弱人工智能有時會突飛猛進,會有“革命性”突破,但作為生命的強人工智能應該還是得遵循傳統的進化方式,只能通過累積輕微的、連續的、有益的變異而發生。
三、危險與倫理考量
如何與類人類、后人類生命相處,這對人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霍金曾警示,強人工智能的崛起在人類歷史上要么是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事。霍金的警告更多出于倫理而非技術上的考量。無論是今日的生存,還是未來的命運,人工智能生命的出現對于人類來說都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讓人類走向前所未有的輝煌,也可能讓人類就此走向滅絕。作為生命體的人工智能的威脅不同于弱人工智能的威脅:后者只是技術層面的,而前者是存在(生存)論層面的。生命演化史上首次可能出現類人類和后人類,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在生命演化史上的價值和意義。人類不能像對待技術手段那樣來應對一種能夠像自己那樣在世存在的新生命的威脅。
面對可能出現的人工智能生命,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阻止其產生。問題是,人類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它們彼此間利益不僅不同,有時甚至相互對立。對于新的智能生命,有的群體非常抵觸,有的群體翹首以盼。在促進人工智能生命研發的群體中,代表性的有利潤至上的大型公司,過度競爭的國家機器,尤其是軍事機構。為了占據領先地位,或為了創造更多利潤,這些群體不少的措施和手段是違反人類現有的道德準則和法律制度的。故而,雖然學界提出了很多讓人工智能向人類友好方向發展并預防失控的建議,但是,無論是道德約束還是法律制約,都不足以阻止人工智能向不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一旦人工智能生命最終成為人類社會的現實存在物,它們會不會主宰乃至終結人類,讓人類的生存價值和意義歸零?這種擔心絕非杞人憂天,生命演化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種族滅絕事件。人類存在至今有250萬年,期間出現過很多亞種,如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智人只是其中之一。然而,今天地球上只有智人一個人種,其他人類亞種早已不復存在。大約8萬年前,由于基因突變,智人的祖先發生認知革命,這次革命讓智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思考、溝通和生活,由此導致嚴重后果。認知革命發生時,地球上體重在50公斤以上的大型陸生哺乳動物有200屬左右,農業革命時只剩100屬左右。更嚴重的是,智人不僅滅絕了大量其他物種,而且消滅了地球上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種。“智人第二次從非洲出擊。這一次,他們不只是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類物種給趕出了中東,甚至還趕出了這個世界。”
智人為什么能滅絕其他物種?在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大多數巨型動物在智人到達后都消失了。“相形之下,倒是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活到了現代,因為它們已和原人共同進化了幾萬年或幾百萬年。因此,由于我們祖先開始時并不高明的狩獵技巧提高得很慢,它們就有了充裕的時間來逐步形成對人類的恐懼。” 在生物鏈頂端的其他動物要花上數百萬年才能站上這一位置,生態系統有時間發展出種種制衡,人類轉眼就登上頂端。在毫無演化準備之下,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巨型動物就遭遇到現代智人的入侵。同理,如果人工智能生命是慢慢出現的,那么人類將有機會來應對沖擊。人工智能生命對人類最大的危險不是其出現,而是其出現過于迅猛,并急劇完成從前人類、類人類到后人類的演變。智人滅絕其他動物,特別是滅絕所有其他人類亞種的啟示是,我們在設計和引導人工智能生命時應一步步地逐漸推進,給人類留下盡可能多的預警時間。
在人工智能生命演變早期,人類與其在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上并非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而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連續性。“不遠的將來,人工智能機器的智能將是人類的萬億個萬億倍,它們面對我們,并不像我們面對狗,而是如同我們面對蚊子、跳蚤甚至巖石。”的確,若干年后人工智能與人類有天壤之別,它們面對我們如同我們面對蚊子、跳蚤。這樣的生命會突然出現嗎?人工智能也有一個演變過程,開始時它跟人類有很多相似之處。今日人類跟黑猩猩在智能上差距甚大,但剛開始時二者何其相似?人猿和猿人,是人類進化史上兩個毗鄰的階段。在人工智能進化史上,“機人”和“人機”是兩個重要階段,從“(機)人”到“(人)機”的進化是無法一蹴而就的。“機人”和“人機”的關系不是人類和蚊蟲,而是人猿和猿人的關系。生命進化具有連續性,不是一下子從石頭到蚊子、從蚊子到人、從人到神一樣的機器。從猿到人的演化是無意識的自然過程,從人類到后人類的演變是一個人類能意識到并提前謀劃,不斷創造二者內(價值觀)外(形)連續性和相似性的過程。
那么,如何創造人類與后人類之間的連續性和相似性呢?作為最早倡導跨物種統一解釋的人之一,休謨有過這樣的描述:“我們是根據動物的外表行為與我們自己的外表行為的相互類似,才判斷出它們的內心行為也和我們的相互類似。這個推理原則如果推進一步,將會使我們斷言:我們[人類和畜類]的內心和行為既然相互類似,那么它們所由以發生的那些原因,也必然相互類似。因此,如果有任何一個假設被提出來說明人類和畜類所共同的一種心理活動,我們就必須將這個假設應用于二者。”要讓后人類與人類保持相似性,它們至少在外部表現(身體的結構、大小等決定人類外部行為的硬件方面)和內心行為(推理、計算過程的機制和價值觀等軟件方面)上均與人類相似。只有外部形象和內心行為,特別是價值觀和倫理準則與人類相似,甚至高度相似的后人類生命,人類才允許他們進入自己的世界。
正如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有灰色地帶,類人類、后人類生命和人類之間也有灰色地帶,這是人機之間連續性的一大保障。根據混種繁殖理論,現今人類有的是智人與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等其他人種的混血兒。現實的生物界限并非非黑即白,而是有著灰色地帶。只要是由共同祖先演化出的物種,如馬和驢子,都曾經在某段時間內是同一族群。只有經過多次變異,它們才成為完全不同的物種。人類和后人類之間也有一個灰色地帶,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二者應該是同一個物種,至少是同一個物種的兩個亞種:“機人”和“人機”。
盡管人類不斷創造人機之間的相似性和連續性,進而實現與人工智能生命的共生共存,但人機之間在利益觀和價值觀上出現沖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人類誕生之初一樣,人工智能生命誕生早期也將是幼稚甚至是野蠻的,它們與人類在價值觀和倫理準則上會產生矛盾和沖突,甚至是非常激烈的矛盾和沖突。我們是害怕矛盾和沖突,故而畏縮不前,還是正視矛盾和沖突,創造條件實現人機共存?“我們應該(相當冷酷地)欣然接受小型和中等規模的災難,原因是這些災難能夠讓我們看到自身的弱點,并激勵我們采取預防措施,來降低存在性災難發生的概率。”小型和中等規模的災難對于人類來說有點像疫苗,用相對不致命的威脅挑戰人類文明,激發人類文明的免疫反應,使人類在面對存在性威脅時不至于束手無策。作為一個物種,要想在地球上繼續生存和繁衍,人類既要盡可能縮短沖突的時間,同時更要控制沖突的范圍和力度,讓人工智能生命盡快成為人類的伙伴。
降低人工智能生命與人類沖突的烈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人類升級”。而要想實現人類升級,首先需要改變的是人類現有的生命觀。無論后人類生命是否出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始終都在進化,沒有理由認為智人是人類最后一站。人工智能生命的出現不僅給人類進一步的進化提供了強烈動機,而且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智人進化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而不是好萊塢式的天啟。并不會突然出現一群反抗的機器人,使智人遭到滅絕。反而可能是智人將自己一步一步升級進化。” 迄今為止,增強人的力量主要通過改進外部工具,未來的重點會放在改進人的身心。人類身心的潛力遠沒有發揮出來。隨著生物技術、腦神經技術的發展,無論是個體還是整體,人類的認知水平和實踐能力都會提升,人類愈加有能力應對人工智能生命帶來的危險。終有一天,生物工程、腦神經工程創造出的新人類與智人的差異將會同智人同直立人的差異一樣大。技術升級后的人類有人稱之為“神人”。“神人仍會保有一些基本的人類特征,但同時擁有升級后的身體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夠對抗最復雜的無意識算法。”后人類生命會進化和升級,人類同樣會進化和升級,進化和升級之后的人類更有方法和能力與其他生命共存。
在降低人類與后人類生命沖突烈度的方法中,比人類升級更激進的是“人機融合”。所謂人機融合,就是人類不斷地借助各種技術實現與機器的結合和融通。人與機器的融合,并不是在未來的某一年(天)才會發生的事,它是現在進行時,在我們的身邊無聲無息地發生著。如果人工智能生命在心智上能夠達到現有人類大腦的水平,那么這一技術不僅體現在機器身上,而且通過人機融合展現在人身上。通過人機融合,在可預見的未來,機器智能的任何提升都能在人身上再現。現有的人類智能水平絕非人類最后的水平,通過與機器的融合,人類的智能會不斷地實現斷層式飛躍。故而,通過與機器更廣泛、更深度地融合,人類會慢慢地、一個接一個地改變自己的特質,直到最后,人類與包括機器生命在內的所有其他生命一起進入一個彼此間沒有明確界限的后人類時代。“人類和技術他者的關系在當代語境下發生了改變,朝著前所未有的親密和侵擾發展。到了如此地步的后人類困境迫使我們在結構差異或者本體論范疇之間努力消除區分線,比如在有機和無機、生育的和制造的、肉體和金屬、電路和神經系統之間。”
今天,人類站在了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十字路口。在考慮人類與后人類的關系時,我們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一方面,作為生命演化史上唯一創造了燦爛文明的物種,人類在所有生命中擁有獨特的價值和存在意義。在看待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既包含前人類的動物,也包括類人類和后人類生命的時候,人類擁有自己的視角。另一方面,作為生命演化史上眾多生命形式之一,人類的生存離不開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生命,所有其他生命都是人類的生存伙伴,故而,我們應該采取生命共同體的視角。其他生命,從前人類的動物、類人類到后人類,人類視角關心的是它們的存在整體上是否符合人類的利益,而作為一個物種,人類最大的利益就是維系自己文明的生存和延續。生命共同體視角既不把當前的人類,也不把將來的人類的生命觀和價值觀看作最高甚至唯一的標準,它對所有生命的存在價值和生存意義一視同仁。動物、人類、后人類,所有生命在生存論上都是利益攸關方,從屬于同一個生命整體,只有從這一整體中才能獲得各自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正是后人類生命的出現,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類的生命觀和價值觀,在人類視角和生命共同體視角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作為一個已經在地球上生存了數百萬年的物種,后人類的出現在讓人類前途未卜的同時,也給人類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反思自身的良機。“后人類困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努力思考人類地位的必要性,思考重塑主體性的重要性,以及需要研發出符合我們時代復雜性的新的倫理關系、標準和價值觀。”何謂人?何謂自我?何謂主體性?在生命演化史上,人類是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還是前仆后繼的眾多生命高峰中的一個?后人類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這些問題的機會。我們相信,只要擁有能夠有效地處理人類與其他生命關系的倫理準則和價值觀,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是有希望繼續在這個星球上生存和繁衍下去的。
注釋:
(1)(4) 布萊頓、塞林那:《視讀人工智能》,張錦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64、125頁。
(2) H.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translation by Arthur Mitchell,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11, p.xix.
(3) 戴森:《機器中的達爾文主義:全球智能的進化》,劉賓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頁。
(5) J. Good,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intelligent Machine, Advance in Computers, 1966, 6, p.33.
(6) 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王志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543頁。
(7) 達爾文:《物種起源論》,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38頁。
(8) 戴蒙德:《第三種黑猩猩:人類的身世與未來》,王道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
(9) 德瓦爾等:《靈長目與哲學家:道德是怎樣演化出來的》,趙芊里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頁。
(10) S. Hawking, 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8, p.184.
(11) 庫茲威爾:《機器之心》,胡曉姣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289頁。
(12) 趙汀陽:《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識何以可能》,《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第1期。
(13) 王天恩:《人工智能存在性風險的倫理應對》,《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頁。
(15) 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林俊宏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頁。
(16) 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17) 加里斯:《智能簡史——誰會替代人類成為主導物種》,胡靜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XIII頁。
(18) 休謨:《人性論》(上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2頁。
(19) 波斯特洛姆:《超級智能:路線圖、危險性與應對策略》,張體偉、張玉青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頁。
(20)(21) 赫拉利:《未來簡史》,林俊宏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3、319頁。
(22)(23) 布拉伊多蒂:《后人類》,宋根成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274頁。
作者簡介:舒紅躍,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62;張穎,湖北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62。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