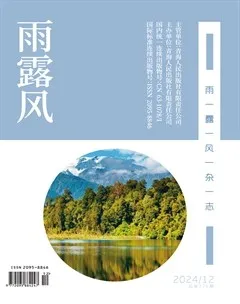試論《說文解字》之或體



重文是《說文解字》(后文簡稱《說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文類型眾多,其中以古文、籀文、或體三類重文數量最多。有關或體的性質、構成,鮮有學者進行探討,因而對《說文》或體進行探討仍有其必要性。下文通過對比或體與古文、籀文的關聯,對或體的來源及其構成進行綜合探析。
一、或體與古文、籀文
(一)古文類
古文,指的是《說文》中附于正篆字形之下標注為“古文”的文字形體。關于古文性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主張古文實際指的是周朝末年的文字;另一種觀點則主張古文應指春秋戰國時東方諸國的文字。古文究竟應該看作何時的文字,對此問題可從《說文解字·敘》中探尋。原文寫道:“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1]
古文絕于秦焚經書,秦統一后在全國推行的文字是秦國文字,被銷毀的書籍則是以東方諸國文字撰寫的書冊,可知古文指的并非周朝末年的文字。古文字形的來源包含三類情況。一是西漢時期魯恭王擴建宮室時于孔子舊宅發現的古文經書,可信程度高,因而其字形上應為春秋戰國時期的魯國文字。二源于西漢時張倉所獻《左傳》,張倉因戰功被分封于北平,舊為燕國故地,因而其所獻《左傳》有極大可能為燕國文字撰寫。三源于漢朝于各個郡國發現的青銅器皿。東漢時,全國行政區被劃分為105個郡國,其中大部分郡國位于戰國時東方諸國故地,則鼎上之字形亦多為戰國時東方諸國文字。另外,漢時以儒家為正統學派,學者極重儒家經文傳統,則許慎收錄古文時有很大可能繼承尊孔傳統而以孔子壁中經書為基礎,以張倉所獻書、各地青銅器銘文作為補充,總之,古文類重文的幾種來源皆與春秋戰國時期東方諸國緊密關聯,基本可認為許慎所錄的“前代古文”實為春秋戰國時期以魯國文字為主的東方諸國文字。
(二)籀文類
籀文,指的是《說文》中附于正篆字形之下標注為“籀文”的文字形體。西周晚期周宣王曾令太史籀作書,據此也有學者認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而王國維在《觀堂集林》卷七一文中提及“籀文”,并將之稱作“西土文字”[2],西土是指秦國,即將籀文看作秦國文字。籀文性質為何可參看許慎的《說文解字·敘》:“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據此可知,周宣王時曾命太史籀以大篆寫作十五篇文章,是一種與古文存在差異的字形。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也曾對文字形體進行改制,分別讓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三人作書時皆參照《史籀篇》之大篆。可見,秦文字實際受到西周籀文的影響,并在籀文基礎上加工整理,兩者間具有一脈相承之關聯。因而,籀文的實際所指應是西周晚期以及春秋戰國時秦國所使用的文字形體。
(三)或體類
或體與古文、籀文、漢時異體緊密關聯。黃侃先生《文字聲韻訓詁筆記》曾說,許慎將不能確認為古文籀文的字形另起新類而名之為“或體”[3]。此說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許慎所見出土材料有限的情況下,確實易產生部分字形難以確定的情況,這很可能是許慎另起“或體”一類重文的本意。此外漢時已有成熟的文字體系,因使用習慣、地域差異從而產生了相互區別的字形。因而可進一步指出,除黃侃先生所述尚不能定為古文籀文的字形外,還應包含當時廣泛使用的異體字形。基于對或體構成認識的差異,各家對或體的界定說法不一。其中“或從、或省”“亦又”兩類許慎皆未明確其來源而看作一字多形,學者幾乎皆將兩者納入或體,以此兩類為或體的基本形式。根據對《說文》古文籀文的分析,文獻之說實為以六國文字收錄之古文;秦刻石碑可確定為籀文字形,因而兩者無須納入或體,則或體應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明確為前代字形不含,二是古文獻字形不含。另外,還需特別指出的是俗體不含。
文獻之說是指許慎標明出處的一類重文,常見的來自《詩》《逸周書》等。這些文獻為西周至秦時之作,可能為當時許慎于各地所見之古籍,收錄的字形實為古文或籀文。馬敘倫先生曾論及文獻之說:“或字出于古書者,蓋為不知六書者所誤合。”[4]因而將古書之字納入或體,是一種不明六書的錯誤做法,或體不包含文獻之說類重文。通人之說的重文,常注明“杜林說”“楊雄說”等諸家。馬先生指出,重文中如楊雄等諸家之言可算是或體字的來源。西漢孝平時,征百人說文字未央廷中,其整理之文字則反映西漢時期文字形體,與《說文》字形相差不遠。因而通人之說可納為或體。秦刻石碑不含。秦刻石碑屬秦文字體系,實際可歸入籀文,因而不包括在或體中。最后指出,俗體不含于或體中。部分學者認為俗體應當作或體的一種,事實上,俗體是一種相對概念,指的是民間所用而傳播不廣的且與正體有別的字形。從許慎所注明重文出處情況來看,只有經過學者收錄或古代資料上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形體才會被收錄,民間使用的俗體不在收錄范圍內。王筠所述“或體無所謂正俗之分”[5],正是指《說文》所錄字形不包含俗體。因而,或體實際包含之字形即為當時所用較廣之異體以及漢朝前見之于各類出土材料而未能證實的文字形體。
二、或體性質及其劃分
(一)異體說
重文等于異體字是早期學界較為普遍的看法。最早將或體看作異體字的是王筠,認為“或體一字之異形也”,其后姚孝遂、蔣善國等學者皆將或體看作一個時期內存在的異體字。關于異體字也有不同看法,《現代漢語詞典》將異體字界定為“跟規定的正體字同音同義而寫法不同的字。”《辭海》將異體字界定為“與‘正體字’相對。與正體字音同義同而形體構造不同的字,即俗字、古文、或體之類。”《大辭海》將異體字界定為“音義相同而形體構造不同的字。”可見,上述皆認為異體字是同音同義的形體,并據此將包括或體、古文、籀文在內的重文皆稱作異體字。然將重文等同于異體卻存在矛盾,不妨先了解許慎是如何看待重文的。
1.許慎重文觀
許慎對重文的看法如何,這一點沒有直接說明,然通過許慎對重文所作體例劃分,或可知曉一二。許慎首先劃分出古文、籀文兩大類,從其來源特點考慮有兩大因素。一是根據時間差異將異形字與正篆區分出重文;二是根據地域差異將重文劃分為古文、籀文。可見,許慎同樣認識到文字異形的問題,并且將地域差異因素、時間差異因素皆納入考慮范圍,這是與今之“凡一字之異形即異體”更為細致的劃分方式。因而,在以形音義角度將或體當作異體字基礎上還應考慮時間、地域因素,對或體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
2.異體論
既然異體字為與正體音義皆同之字形,則同為異體的字形間音義皆存在關聯。而事實上,所謂異體字間也常出現意義并無關聯的字形。《說文》有字形“”,或體為“”,皆以“度”為聲符,而意義則不存在關聯性。也有字音不同的情況:逎,聲符為酉,王力先生定為余母幽部,或體聲符為酋,從母幽部,二者聲母不同部,韻部相同,字音相近,則不同于異體字“意義皆同”的描述。為了解決異體的這一矛盾,又將音近義同字形也作為異體,而意義存在差別的有待商榷,因而如何對或體分類也尚未明晰,暫且將或體看作異體字。
(二)異體分化說
也有學者指出包括或體在內的重文為異體字,但應進行細分。張標便不同意將重文與異體字看作相等關系[6],需要進一步分化。為了解決異體劃分而產生的矛盾,近年來,學者們對異體字理論進行深入探討。裘錫圭提出的廣義異體概念,認為異體還應包含音義不完全相同的字組,由此拓寬異體字內涵,解決異體劃分的字音矛盾,但這會使異體字范疇過于寬泛化。宋麗麗也認為異體字指因地域差異而產生的音義相同的字形,即將異體字限于某一共時階段進行辨析,與或體中的字形情況較為貼切。或體中的異體字應僅指于漢時出現,且音義皆同的字組[7],其可作為對或體的劃分標準,將三者區別開來才恰符合對或體字劃分的需求。據此,可知或體之中存在漢時異體、古文與籀文。古文、籀文與正篆具有時間差異。因而可作為古今關系看待,其中字形間音近而意義并無關聯,又可分為通假關系。
1.古今關系與異體字
或體的古今字與異體字應如何區分。古今字概念最早由鄭玄提及,《禮記·曲禮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鄭玄注“余”“予”為古今字。鄭玄是精通古文經學的大學問家,因而與許慎等古文經學者在文字理論上具有相承性。鄭玄之“古今字”一說不是突然出現的觀點,許慎將部分重文劃分為古文籀文,正是從時間差異進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今字觀雛形。鄭玄之說應是繼承許慎等人的文字觀加以補充說明并明確提出的。近人亦嘗試對古今字進行解釋。一般來看,同一個詞在不同時代用不同的字表示,前一個時代使用的字叫古字,后一個時代使用的字叫今字,便形成古今字。王力先生例舉“責”“債”,詳細地說明古今關系,與不同時期而表達相同意義的字是為古今關系看法一致。因而古今關系即可理解為表示同一字詞,而存在歷史先后差異的字形。確定字形間的古今關系后,可根據相承性、歷時關系兩種特性將或體中的古今字與異體字進行區分。首先古今字組具有相承性,其音義通常相似。古今字形的相承性體現在其變化中,一種是在古字的基礎上添加偏旁,另一種則是改變原有的偏旁。而無論是在古字的基礎上加偏旁,還是改變古字原有的偏旁,古字與今字皆有共同點,只有極少數古今字存在今字與古字字形不相似的情況。《說文》有或體字形作“”,與正篆“達”皆從“辵”,且聲符“羍”“大”音近,為改換聲符后仍音義皆相關的字組。其次古今關系具有歷時差異。西周晚期金文有字形作
“”,容庚《金文編》認為即“達”字,正篆字形作
“”,基本構件相同,可見其正篆是承金文之寫法的古字。或體作“”,僅見于漢時,則可知,“”應是漢時通過改換聲符才出現的字形。正篆“”與或體“”音義相近,且具有歷時先后之分,為古今異體字形關系。可見,《說文》確實存在或體與正篆實為古今關系的現象,可將這部分字形劃分為古今類異體。
2.通假關系與異體字
或體中存在“義符通用”現象,即改換形聲字形符而形成或體,然而并非所有改換的形符意義皆有關聯,有的或體與正篆間僅存在音近關系,這類或體顯然不能看作異體字。秦鳳鶴也關注到這一現象,指出重文不完全等同于異體字,其間還存在通假關系。[8]關于通假字的認識各家基本一致。宋麗麗也指出,通假字指同一時間內,漢字使用上的不規范現象,以讀音相同或相似而意義無關的字代替本字。張嚴勻認為通假字是某詞用字在共時階段本來應該寫成甲字卻寫成了乙字的情況。[9]則通假字應具備如下特點,一是通假字意義不存在關聯。二是通假字聲符應該相同相近。三是通假字間不存在歷時關系。常有將古字的沿用視作通假現象,如此便是錯解了其歷時層次的特點,引起了古今字與通假字概念的混淆。例如“逶”,正篆字形作
“”從辵委聲,意為彎曲綿延之貌。或體“”從蟲為聲,聲符“為”與“委”音近,形旁與正篆字形意義無關。兩者皆為漢時存有的字形,意義無關聯而以音近的“委為”作聲符,則此組正篆與或體實則為假借關系。由此可見,或體中確實存在與正篆為通假關系的字形。針對或體性質構成及其特點,本文對或體分類作如下標準:異體字,存在于漢時,且音義皆同的字組可當作純異體字。存在歷時關系,音義相關的字組可作為古今異體字。意義無關聯,僅音同音近的字組可作為通假異體字。
三、結語
《說文》各類重文間關系緊密。從文字來源看,古文是許慎收錄的春秋戰國東方諸國文字,籀文是周宣王時期至秦國使用的文字,或體則包括古文、籀文以及漢代的異體字形。從或體性質來看,將或體重文皆當作異體字是繼承王筠之觀點,其缺陷是沒有考慮字形發展變化的具體情況。因而根據文字發展的共時與歷時、形音義的區別,可將或體進一步劃分為純異體類、古今類異體、通假類異體三小類。通過將或體分化為三種不同類型,使得對《說文》或體重文的來源、構成的理解更加深入,達到對或體類重文進行區分的目的。
作者簡介:陶海江(1998—),男,土家族,貴州銅仁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字學。
注釋:
〔1〕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王國維.觀堂集林[M].北京:中華書局,1984.
〔3〕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M].北京:中國書店,1988.
〔5〕王筠.說文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87.
〔6〕張標.大徐本《說文》小篆或體初探[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1):1-8.
〔7〕宋麗麗.芻議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J].作文成功之路(上),2018(4):7.
〔8〕秦鳳鶴.《說文解字》異體字類型研究[J].中國文字學報,2014:189-200.
〔9〕張嚴勻.同源字與通假字的區別及其交叉關系[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9,38(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