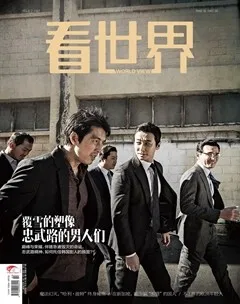滬港雙城鏡,時代繁花夢
王悅


電視劇《繁花》劇照
電視劇《繁花》與小說太不一樣了。
中國的電視觀眾可能從沒在熒幕上看過更改幅度如此之大的改編,但這種改編方式在王家衛是早有“前科”。
1994年上映的《東邪西毒》號稱改編自金庸的《射雕英雄傳》,但影片上映后,所有人發現電影情節與小說沒有任何關系,只留金庸起的人名了。
既然討論電視劇像不像小說已沒有意義,人們只好去爭論電視劇里的上海,究竟有多像1990年代的上海。以王家衛慢工出細活的嚴謹態度而論,劇中的上海可以說無一個地點無原型,無一件物品無來處。但不應忘記,王家衛并非是1990年代上海的親歷者,他對上海繁榮年代的精確還原本質上是一個香港移民對舊家園的想象。
王家衛5歲就離開了上海,對上海的感懷一次次在他的電影中得到抒發。這一次,王家衛把鏡頭轉向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在他的想象中,這一時期的上海生機勃勃,龍蛇混雜,有機會也有陷阱,一如他成長的1960年代的香港。
1990年代的上海人也一如1960年代的香港人,都是不確定年代的過客。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云散了。”1982年,美國哲學家馬歇爾·伯曼以馬克思的這句話為書名,寫下了他討論現代性的名著—《液態現代性》。在他看來,“現代性”的經驗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一種環境之中,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歷險,去獲得權力、快樂和成長,去改變我們自己和世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要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摧毀我們所知的一切,摧毀我們所表現出來的一切。”這也正是王家衛想要在電視劇《繁花》中傳達的體驗。
確定性的喪失,首先體現在剛剛開放的資本市場上。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阿寶借了好兄弟陶陶用來結婚的6000塊錢買股票,一個禮拜后虧了3000元。爺叔對懊惱不已的阿寶說:“紐約帝國大廈曉得伐?從底下跑到屋頂要一個鐘頭,從屋頂跳下來,只要8.8秒,這就是股票。想從股票上賺錢,先要學會輸。”
股票的漲跌可以決定人的命運,有的人一步登天,有的人一貧如洗。因為深圳股市擴容,投資人A先生的資金化為烏有,墜海輕生。阿寶卻在股市上賺到了第一桶金,搖身一變成為寶總,做起了外貿生意。
黃河路上飯店層層疊疊的霓虹燈,是90年代上海繁榮的象征,但這繁榮又不專屬于任何人。黃河路的客人喜新厭舊,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李李接手歇業的“金鳳凰”開張“至真園”,噱頭做足風頭出盡,黃河路上的老板娘人人眼紅。附近“金美林”的老板娘盧美林處處刁難至真園,最后黯然退場的卻是自家的飯店。
盧美林向李李求助遭拒,留下一句話給李李:“新店開張那天,就是你至真園走下坡路的那天。”李李雖不為所動,也不由得脊背一涼,更加堅定了要賣掉至真園的決心。
資本市場不只是將個人的財富卷入不確定的洪流,同時也動搖了人心,將不確定性注入最親密的關系中。1978年是改革開放元年,阿寶當時的女友雪芝家里來了香港的親戚,之后她就嫁去了香港。1987年雪芝剛剛離婚,短暫回到上海見阿寶。她說自己希望阿寶過得好,但是又怕看到阿寶過得比自己要好。
無形中,財富和地位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標準,友情和愛情在利益面前統統都要讓位。阿寶與四個女人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正是一個不確定時代人際關系的寫照。

阿寶與四個女人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正是一個不確定時代人際關系的寫照。
當都市喪失了確定性,在上海往來穿梭的所有人,都共享了“異鄉人”的經驗。王家衛的電影多聚焦于不確定時代里人與城市的關系。“異鄉人”是最常出現在鏡頭中的形象,有人遷徙到陌生城市成為異鄉人,也有人因為家鄉發生劇烈變化而被迫成為異鄉人。電視劇《繁花》中,這兩種形象兼而有之。
李李和強總都從深圳來到上海,他們維持著異鄉人的身份,把上海當作累積財富與名聲的賭場。他們并不想融入上海,而想成為制定規則的人。

電影《重慶森林》劇照
玲子和菱紅都是從日本打工返鄉的上海人,她們想要重新融入故鄉而不能。玲子決定求新求變,將日本料理的精神與傳統本幫菜結合,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夜東京”。菱紅也受到玲子感召,放棄了半死不活的精品店,遠赴北京打拼,重新做一個異鄉人。
實際上,王家衛鏡頭下1990年代的上海,可以視作1960年代的香港的鏡像。1990年代和1960年代分別是這兩座城市的喧騰時代。《阿飛正傳》的故事始于1960年,終于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于1962年,終于1966年。
1958年生于上海的王家衛,5歲就隨家人移居香港。60年代的香港有大批來自上海的移民,他們大多只是把這里當作臨時的避難所,絲毫不改精致講究的海派作風。王家衛一家人依然用上海話交流,母親每天穿旗袍,喜歡搓麻將牌,看西洋片。王家衛曾說,母親是戲癡,自己上午上學,母親中午便接他去看戲,一天看兩三場。
初來乍到的王家衛,既聽不懂廣東話,也不會說。兄弟姐妹仍居于上海,只能鴻雁傳書。王家衛在香港孤單長大,用懵懂細膩的少年心思咀嚼1960年代香港的滋味。在夜總會工作的父親回家就會向母子二人分享燈紅酒綠里男男女女的人生和遺憾。父母聊到的舞廳女郎、船員,以及小王家衛默默觀察的住隔壁出租屋的男侍、盼愛卻等不到回音的新加坡華僑,全都改頭換面出現在《阿飛正傳》中。
面對確定性的喪失,電視劇《繁花》中的角色往往訴諸回憶,反復咀嚼過去時光中的機緣巧合。從晦暗難明的當下看來,過去偶然的一次相遇都會蒙上一層命中注定的光暈。粉飾過往對于王家衛來說仿佛是宿命,這其中既蘊藏了向前看的動力,也暗含了拒絕現實的危險。
《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寫道:“那個時代已過去,屬于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耐人尋味的是,在電視劇《繁花》中,阿寶喜歡引用的普希金詩句與之恰成對照:“一切都終將過去,而那過去了的,都會成為美好的回憶。”前者是對1960年代香港的追懷,而后者是對1990年代上海的想象。
香港作家朗天曾經指出,王家衛電影的時空其實是被凝固了,觀眾所進入的只不過是極度風格化了的藝術時空,其中充塞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電視劇《繁花》用懷舊的音樂、仿90年代的場景和服裝、升格的鏡頭營造出的上海,同樣也是凝固的時空。王家衛沒有將1960年代的上海放進電視劇中,但這段歷史在金宇澄的小說中卻占去了不小的篇幅,貫穿了阿寶、小毛、滬生等人的成長階段。
王家衛固然架空了歷史,卻并未忘記歷史。在他的電影中,為當下賦予意義的是過去某一時刻對未來的承諾。在《阿飛正傳》中,在菲律賓的火車上臨死的旭仔對劉德華飾演的香港警察說“要記住的我永遠記得”;《2046》的創作則是緣起于中國政府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后所作的“50年不變”的承諾。

電影《花樣年華》劇照

電影《2046》劇照
1958年生于上海的王家衛,5歲就隨家人移居香港。
承諾的母題一直延續到電視劇《繁花》中。阿寶找爺叔學做生意成為寶總,他的初衷是1987年對雪芝的承諾。他要用10年的時間證明雪芝是錯的,自己會超過雪芝宣稱的賺錢速度。表面上兩人比的是富貴,暗地里較量的卻是感情。阿寶并非真的想要用10年的時間腰纏萬貫,他想用這個承諾維系與雪芝的關系。
沒想到,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寶總要做的承諾越來越多。寶總向汪小姐承諾,4年后她一定能當上科長;寶總也向玲子承諾,她會當上夜東京的老板娘。世事難料,汪小姐當不成科長,反而成了寶總的競爭對手。玲子的“夜東京”也丟掉了寶總的座位。而為了信守承諾,寶總不惜與盡心盡力幫他謀劃的爺叔作對,但每當承諾完成,寶總卻倒像是一個多余的人。
幫助服飾公司上市是寶總最后的承諾。成功上市后,服飾公司的蔡總卻勾結南國投的強總,將寶總踢出游戲。寶總變回了阿寶,旁觀者或許為之惋惜,而阿寶本人卻如釋重負,因為他終于完成了對所有人應有的承諾,而這一過程用了7年。
“摸著石頭過河”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名言,也是應對不確定未來的一種承諾。王家衛把這句承諾當作阿寶們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1994年,東方明珠電視塔落成;1997年,香港回歸。從當下回首,那個不確定的1990年代仿佛已經通過歷史的進程獲得了自身的確定性。對于王家衛自身來說,《春光乍泄》中的身份迷惘,《2046》中的無限悲涼也都在1990年代的上海找到了答案。
但對于身處復雜當下的我們來說,不確定恐怕仍然是恒常的經驗。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