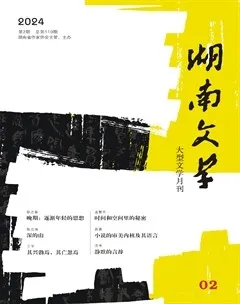警惕“地方性寫作”帶來的創作抑制
劉長華
“地方性寫作”這一命題在當下正以熱詞的身份在文壇、學界高視闊步。就詞源和思想背景而言,“地方性寫作”一語許是與域外學者吉爾茲所肇造的概念——“地方性知識”有著抹不去的淵源。依循這樣的精神系譜,“地方性寫作”其初衷和使命應是解構一元化和普遍主義寫作而來。其價值和意義毋庸饒舌,文學史上許多出類拔萃的作家確乎就是“地方性寫作”的典范。不過,悖論也就可能旋踵而至,當“地方性寫作”以席卷、覆蓋的姿態呈現時,其本身就將成為新的一元和獨尊。“地方性寫作”如果在批評家“不遺余力”地鼓吹下,在地方利益不斷地誘使甚至裹挾下,成為一種自覺得不能再自覺的行為時,作家就可能陷入畫“地”為牢的困境:文化人格標簽化,思想資源框條化,題材選擇單一化,藝術風格同質化……
“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宇宙和世界向來就不等同于空間,時間是從不缺席的。任何一個作家所生活的、所面對的世界都是由“地域”和“時域”所共同維系的,缺一不可,置于“時空隧道”面前亦不例外。“地方性寫作”這一詩學路徑的提出,本身就是基于特定而鮮明的時代語境。作家如果只是“目無全牛”地游刃于擇定的地域,將心智全部聚焦于“目”前地方性所蘊涵的社會情勢、人文氛圍、意象資源等,并形成一種總體性的、概念化的判斷和定位,并在這種判斷和定位上,運用所謂“挖井”理論,圍繞某個原點和圓點,心無旁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地窮盡下去。這樣的“地方性寫作”有可能敞開別樣的風景,令旁人無法企及。但他筆下的地域和空間,無論是有真實原型的還是心造“幻境”的,在時間河流的沖洗下,就不可能自我巋然,相應的判斷和定位就不能一勞永逸、冥頑不化。福克納的“南方小鎮”、魯迅的“魯鎮”、莫言的“高密縣”……都有開放的、多維的一面。明顯一例便是《故鄉》《社戲》中的“魯鎮”,它就有過溫熱可親的時段。否則,將有可能是作家的作繭自縛。
時間坐標系亦無非是由橫縱兩軸建構而成。“地方性寫作”的時間橫軸,就是將地域的力量幅面予以敞開、拓展。地方性相關的體驗、知識、景觀、人事等都被擱置在宏大的時代背景之下考察,比較性、個性化的質素才會獲得凸顯,“地方性”才會名副其實地成為“地方性”,所謂時代感、當下性的思想參照和藝術張力才會從中獲得充盈。不然,就將不免有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自話自說之嫌。時代性不僅指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現有情狀,更要放眼世界的形勢和趨勢。無論于“道”,還是于“器”都應如此。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是“地方性寫作”的另類表達,其中相關的民族神話、傳說書寫正與世界文明對工具理性的反思構成潛在而生動的對話,使得一塊塊古老的土地散發著時代的亮光。
時間縱軸就是將地域的精神絡脈予以拉伸。“新東北作家群”給人們在閱讀上所帶來的悵然與悲欣,其中的動能很大部分源自他們筆下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形象所自帶的歷史感。“東北老工業基地”作為“共和國長子”,曾幾何時頂戴了多少陽光燦爛的日子;當企業改制和職工下崗潮涌而至時,相關人們的內心海洋又將經受怎樣的潮汐翻滾……這樣的時間跨度自是蘊含著寫作上的富礦。冠以“新”字頭命名的“地方性寫作”,這似已從一開始,就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昭宣了與“老”“舊”歷史形態的比況為題中應有之義,只是策略的顯隱高低有區別而已。時間的流動性賦予作家所據之為寫作對象、寫作資源的地域,在“常”與“變”等難題和辯證關系上產生新的藝術彈性空間。
言及地方和地域,文化是其中無論如何繞不開的議題。作家的創作本身就承擔著文化展現、文化傳承、文化創新的責任。偉大作家是優秀文化的化身。與之同時,還有一個基本原理廣為人知,即新一代更優秀的文化被結晶出來,往往離不開兩種或多種文化的“雜交”。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碰撞、交融、裂變,就是“雜交”的路徑表達。過分強調“地方性寫作”作家的某一地域身份,甚至就是它的文化形象大使和代言人,顯然是一種文化近親繁殖的表現。長此以往,作家的創作生命力自然就會萎縮,“地方性寫作”所饋贈作家的某些固有優勢經“圈養”之后就可能慢慢消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說得很絕對:“在自己文化和歷史的懷抱中寫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寫作與地方》)“地方性寫作”的精神內核之一就在于它的“野蠻生長”。因此,“地方性寫作”注重作家地域文學的個性特色和核心競爭力,但在文化胸襟上也應不忘兼容并蓄、博采眾長。
“地方性寫作”作家的漫游姿態不可或缺。“到不了”和“回不去”是人們對文學空間的永恒想象之一,隸屬于人類的精神母題。“烏托邦”能棲息人的漂泊靈魂。其中的美學腔調既有纏綿悱惻,也有悲壯熱烈……不過,無論是“到不了”還是“回不去”,都暗含了相應主體與漫游這一行為實踐有著或遠或近的纏繞。漫游不僅僅只是抽象姿態的闡發,對于“地方性寫作”作家而言,更應是實實在在的心智結構之優化、文化血液的換氧。蘇軾作為古代文學史上“地方性寫作”色彩比較濃郁的作家,蜀地文化固然是他的精神底色之一,表現出任俠豪放的風神,但他更注重深入體驗和吸納因貶謫等原因而長時間蟄居地方的文化。“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那種掃卻平生不快的豁達、明麗之感,可視為巴蜀文化和以“寬容包蓄”為特征的南粵海洋文化相融匯的產物。這樣兩句看似平淡無奇的詩歌,卻能被代代傳唱,奉為經典。細加品味個中三昧,它的品格真不能讓人小覷。
根據“雜交”原理,文化交叉地帶所孕育出的作家就有與生俱來的優勢。從地方利益博弈格局和版圖來看,交叉地帶往往被人設為邊緣化的地位。但它的交叉,不僅意味著文化穿梭游歷時相對自由無礙,而且它更像熔爐,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激蕩得更頻仍。“雞鳴三省”所說的“鳴”就可能是“三省”的聲音。前些年里,學界所發明的“邊地文學”這一范疇就涵蓋了相干的精神意蘊。事實上,沈從文的《邊城》就沾溉了文化交叉地帶才有的汁液,它里面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情調,是融入了湘西核心區之外的常德、酉陽對“桃源夢想”的一往情深。生于、長于湘西本埠的蔡測海近年來的“地方性寫作”在這方面更是明確,他的寫作立足于湘、渝、鄂、貴諸省交壤、同異相生的武陵文化,值得大加關注。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有言:“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高致”與康德對審美時的心境——“靜觀”的基本看法有著對應的關系,這對“地方性寫作”同樣有著深刻啟示。一頭忘情地扎進“地方性寫作”中,在情感狀態上就可能表現出“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我愛這土地》),或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當然,這“恨”亦可能是“愛之深,恨之切”中的“恨”。但,不管如何,“炫富”“比爛”“賣慘”等都是偏離現代美學軌道的,與文學的現代性要求頗有差池。因此,“地方性寫作”在寫作心境和與這心境相匹配的技術層面上,要有“出乎其外”的自審意識,不能被偏至性的情感所捆綁。
人本主義創始人羅杰斯所提出的“共情”說,近些年來被漢語界引述較多,并在不少時候被偏正性地、名詞化地處理為“公共情感”。這樣的郢書燕說對于當下某些過于“私人化”的寫作卻是一劑良藥。“地方性寫作”當以為鑒。因為“地方性寫作”離不開一些諸如風土、人情、歷史等知識性與背景性東西的呈現和介紹,這對于相當多的“外面世界”的讀者來說,就有點“云山霧罩”,“不知所以然”。情感也許才是作者發給讀者最好的通行證。但私人性的情感太濃太厚,同樣是“御讀者于作品之外”。上世紀20年代臺靜農筆下的“冥婚”、蹇先艾筆下的“水葬”……與今天所言的“地方性寫作”深有交集,特殊文化事象固然令人耳目驚異,但“可憐天下父母心”和對愚昧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更能贏得時間。
與這種情感選擇直接相連的便是作家的視角看取問題。“地方性寫作”作家立足腳下、眼前、心中的那片“多情”的土地,“多情”就意味著應“多視角”。文學創作固然不是科學研究,難以以量化的冷靜和客觀描述與闡發自己的對象。但是,人文畛域也有“真理”之說,“地方性寫作”的“真理”就在于盡可能讓對象“祛蔽”,不管文本內敘述者視角如何變幻多姿。作家視角的單一化和模式化無疑就是遮蔽。“多視角”還應包括作家直接與所書寫的地域有實際性的距離。自不待言,這本身就可能是一種心理焦距,所以不少回憶性、回眸性視角固然很“深情”,但也很“真情”,它們不會以“深”去誤會“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些流散文學作家、族裔文學作家在“地方性寫作”上做得比較出色,正是因為他們在視角姿態上足夠地“出乎其外”。
“地方”與“時間”、“地方”與“文化”、“地方”與“距離”,是本文立論的三個維度,不一定言之成理,但套用一句一路流傳的網絡語——“你寫‘地方’就不能只是寫‘地方’。”這是真的。
責任編輯:羅小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