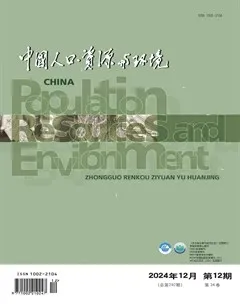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











摘要 在生態文明建設和推進共同富裕的雙重背景下,探索實施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是提升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關鍵。該研究在科學測度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和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基礎上,以山東省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為例,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檢驗了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①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發揮了顯著提升作用,在控制村級啞變量、補充其它控制變量、數據縮尾處理、更換因變量權重測算方式和使用工具變量后,該結論依然成立。②中介效應檢驗發現,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會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釋放家庭發展性消費支出和激發農戶內生致富動力,進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③異質性分析表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老一代、低收入水平和低學歷的弱勢農戶群體發展韌性的影響更為顯著,表現出“底層保障型”特征。④分維度來看,雖然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和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均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發揮了多維提升作用,但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作用要明顯優于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該研究的政策啟示是,在發展相對滯后的生態保護紅線區,需重視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在破解農戶家庭發展困境中的重要作用,關注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提升家庭發展韌性的異質性特征,適當降低生態補償政策的參與門檻,形成以“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為主,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為輔”的可持續發展機制,這對提升生態補償的政策效應具有啟迪意義。
關鍵詞 生態保護紅線區;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家庭發展韌性
中圖分類號 X32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12-0180-13 DOI:10. 12062/cpre. 20240706
隨著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中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脫貧地區農民生活得到持續改善。但是,絕對貧困在統計意義上的消失并不意味著反貧困事業的終結,當前城鄉間、農村區域間以及農村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情況與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尚有一定差距,農村生計系統的風險治理仍存在深層次的脆弱性問題亟待解決[1]。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維護區域生態安全底線的生態保護紅線區,由于受到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區域生態基礎和環境承載力等外部條件限制,當地農戶家庭普遍面臨生計選擇空間受限、可行能力缺失、內生動力不足等難題。為了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政府肩負著重要的責任[2]。因此,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逐漸成為了國家開展推進鄉村共同富裕工作的重點關注群體。近年來,在大國博弈、氣候變化和不斷推進的市場改革沖擊下,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生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面臨更嚴峻的風險和不確定性[3],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當地經濟發展和共同富裕進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其著力點就在于進一步化解生態脆弱地區農戶家庭內部脆弱性問題,推動農戶生計韌性穩定地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探尋提升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實現路徑,對于扎實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綜述
學界關于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發展韌性測度方法的研究。關于發展韌性的測度方法大致有兩種:第一種立足于家庭生命周期關注經濟狀態長期變化,借助計量經濟學方法估計福利函數條件期望和方差,進而實現將發展韌性量化為滿足某種福利標準的條件概率[4-5];第二種致力于構建多維韌性指標評價體系,并計算綜合指數衡量個體韌性水平,其中最典型的是由緩沖能力、自組織能力和學習能力構成的分析框架[6]。伴隨著思維范式的愈加深化,多維韌性評價指標體系因具備識別農戶家庭韌性多樣性、 長期性和成因復雜性等特征的潛力而得到廣泛應用[7-8]。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隨著韌性概念內涵的不斷擴充和深化,需對經典指標體系進行適當調整以更為恰當地反映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階段性和動態性特征[9]。二是關于韌性影響因素的探究。學者們從無條件現金轉移支付[10]、農業保險[11]、人力資本[12]、土地綜合整治[13]等角度較為全面地分析了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措施和路徑。在共同富裕和生態文明的雙重戰略疊加期,政府積極探索并實施了一系列多元化、多種類和綜合性的生態補償方式組合[14-15],為新時代如何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供了新的啟示。然而,現有研究多專注脫貧攻堅時期生態補償的福利效應[16-17],且主要從宏觀層面探討生態補償是否存在減貧效果[18-19],而正處在探索發展階段的多元化生態補償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可能產生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關注,尤其是缺少從微觀層面解析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與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關系的研究。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以“三區三線”劃定試點省份山東省為調研地區,利用課題組對山東省7縣(區)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在科學測度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和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基礎上,探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與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①在經典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結合農戶主體與外界沖擊相抗衡的過程,構建了涵蓋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3個維度的多維韌性評價指標體系,以更為恰當地反映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階段性和動態性特征。②中國處在加快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時期,文章圍繞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目標,探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對現有研究進行有益補充。
2 概念界定與研究假說
2. 1 概念界定
2. 1. 1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
在生態補償領域,“多元”可指補償主體、融資體系或補償方式的多元化[20]。本研究所探討的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為政府主導下的補償方式多元化。由劉格格等[14]的研究可知,生態補償方式的“多元”不僅體現在補償方式種類的多樣化,還需考慮不同類型補償方式補償力度的差異。基于此,為了科學測量農戶家庭獲得生態補償方式的多元化程度,研究進一步構建了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指數,該指數是將農戶獲得的生態補償方式在種類和補償力度兩方面綜合量化后的數值。其計算方法是用農戶家庭所獲得各類生態補償方式的補償額度除以生態補償總額后求平方和。此外,根據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課題組[21]、王金南等[22]和靳樂山[23]對生態補償方式的劃定標準,將生態補償方式劃分為資金補償、實物補償、技術補償和產業項目補償4種類型。其中,資金補償是指政府以補償金、補貼等轉移支付形式向農戶提供資金支持;實物補償是指政府向農戶提供農機具、勞力、住房等生產和生活要素;技術補償是指政府無償向農戶提供智力服務,例如管理組織模式的創新與推廣、生產技術的咨詢和培訓等;產業項目補償是指政府協助或主導受償地區發展新型綠色產業等產業發展,以及實施或推進生態環境修復項目等項目建設。同時,參考沈滿洪等[24]的分類標準,以不同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后續發展能力影響差異作為分類標準,將生態補償方式劃分為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和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其中,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包括資金補償和實物補償,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包括技術補償和產業項目補償。
2. 1. 2 家庭發展韌性
韌性(resilience,又譯作彈性、恢復力、復原力、抗逆力)在工程學、物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是一個具有可塑性的多元概念。近年來,韌性的概念內涵得到不斷擴充與深化,由最初表示恢復至初始狀態的能力[25],演變為受到外力干擾時保持自身狀態不變的能力[26],又逐步發展為強調受到干擾后自我調適、學習并提高抵御能力等更為廣泛的內涵[6,27]。慮及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生計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困境,本研究參考Speranza等[6]和Barrett等[27]對韌性的界定,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定義為在應對外部沖擊和干擾時,農戶所擁有的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通過吸收化解、自我調適、系統更新使家庭達到持續發展的良好狀態。其中,抵抗恢復能力是指農戶利用自身擁有的資源和權利維持生計穩定性的能力,可由人力、物質、金融、社會和自然5種生計資本表征。適應調節能力反映了農戶在穩定生計的同時通過接受各方援助和采取調節措施以適應新外部環境的能力,包括政府幫扶、親友協助和市場參與3個方面。學習創新能力體現了農戶憑借漸進式調節行為無法應對風險沖擊時,采取順應變化、技能革新、調整生計策略的能力,包括信息獲取、知識學習和創新轉型3個方面。3種能力分別對應農戶與外界干擾相抗衡的3個階段:第一階段,吸收化解。在較低的外部沖擊下,抵抗恢復能力通過吸收化解外部沖擊對家庭功能和結構產生的影響,從而保持原有平衡狀態的持續性。第二階段,適應調節。隨著外部沖擊力度逐漸增加,超越了抵抗恢復能力可以吸收化解的范圍,適應調節功能開啟并發揮增量調整的重要作用。第三階段,系統更新。當外部變化超過了適應調節能力范疇時,系統需要引入新狀態變量以達到持續發展的新平衡狀態(圖1)。
2. 2 研究假說
發展韌性的理論研究指出,家庭發展韌性的提高主要面臨兩個障礙因素:一是阻礙家庭持續發展的潛在結構性障礙[27];二是限制家庭向上流動傾向的主觀心理障礙[28]。勞動力、資金等稀缺資源的投資選擇是改變家庭潛在結構性障礙的重點,而激發家庭內生致富動力是減輕“福利依賴”“等靠要思想”等心理障礙的關鍵。因此,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可能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釋放發展性消費支出和激發內生致富動力等途徑緩解家庭結構性障礙和心理障礙,進而發揮提升家庭發展韌性的重要作用(圖2)。
2. 2. 1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勞動力就業結構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勞動力就業結構是指勞動就業人員在不同行業的分布比例,反映了農戶家庭勞動力由低收入傳統農業向高收入現代產業流轉的現實情況[19]。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優化不但加快了土地流轉速度、推動耕地利用轉型[29-30],還可以提高生產技術效率、促進農業技術進步[31-32],同時也影響了家庭收入結構和家庭積累能力[33],并最終在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助力增進共同富裕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理論上,在當地政府積極鼓勵企業綠色發展、休閑服務產業和更廣泛農村發展戰略的背景下,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可以起到優化農戶家庭勞動力就業結構的關鍵作用。隨著地方政府探索推進了技術補償、產業補償等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綠色農業、生態旅游、民宿產業以及配套的康養服務業、餐飲業等新型產業快速發展,改變了當地勞動力市場需求,增加了多樣化非農就業崗位供給[19]。此外,受限于最嚴格的生態環境治理約束,傳統農業行業較非農行業的收益差距逐漸凸顯。為增加生產要素的邊際回報率,當地農戶傾向于改變原有生產方式和生計策略選擇,逐漸調整勞動力等關鍵生產要素配置,促使家庭勞動力集中在優勢生產部門,進而優化了農戶家庭勞動力就業結構。因此,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可能會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2. 2. 2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發展性消費支出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發展性消費是指那些超越了基本生活所需的支出,體現了個體為提升生活質量和實現自我發展而投資的強度[34]。汪險生等[35]研究發現,發展性消費能預示生活質量的改善,即隨著發展性消費的邊際消費傾向逐漸提高,生活質量的提升趨勢會愈加顯著。事實上,伴隨著農戶在身體健康、技能培訓、休閑娛樂等方面發展性消費支出的逐步增加,不僅家庭成員的身體狀況、生存技能、能力素質等人力資本水平得到明顯提升,還滿足個體自我發展、自我實現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層次需求,進而實現從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3維度全面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可見,增加發展性消費支出是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從理論上講,影響農戶家庭消費行為的主要有“流動性約束”和“背景風險”兩大因素[36]。而多元生態補償方式不僅可以通過發放資金補償、提供就業崗位等途徑直接增加農戶家庭的轉移性收入,也可以通過改變農戶家庭生產力、生計方式及生計策略選擇等途徑間接提高農戶的創收能力,同時還能借助當地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刺激農戶家庭非農就業率持續增加,從而有效緩解了抑制農戶消費行為的“流動性約束”和“背景風險”,并釋放了農戶家庭的發展性消費潛力空間。因此,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可能會通過釋放發展性消費支出,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2. 2. 3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內生致富動力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動力源于個體對環境信息的感知偏好和綜合評價,以及接收與處理信息后形成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是產生個體行為的先決條件[37-38]。內生致富動力反映了農戶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生計決策的自主與理性,是滿足自身未來發展需求的行為驅動力。管睿等[39]指出,決定農戶發展的根本力量是內生動力,只有化外部推力為內部動力,調動農戶追求未來美好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保障家庭生計得以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進而發揮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重要作用。在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下,激發生態保護者和地方發展的內生動力是進行生態補償方式多元化設計的目標之一[17]。近年來,在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生態保護紅線區,生態補償方式逐漸由“單一輸血型”補償轉變為“多元造血型”補償。理論上,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激發農戶內生致富動力的核心就在于生態補償與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例如,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通過開展技能培訓、協助建立生態經濟產業等途徑,在保障生態安全和資源合理利用的同時,能夠兼顧當地農戶可行能力的發展和就業機會的供給,使得“扶智”與“扶志”充分結合,最終起到激發農戶內生致富動力的積極作用。因此,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可能會通過激發內生致富動力,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綜合上述分析,對生態保護紅線區內農戶而言,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會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釋放發展性消費支出和激發內生致富動力,進而提升其家庭發展韌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說。
H1:多元生態補償方式能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H2a:多元生態補償方式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H2b:多元生態補償方式通過釋放發展性消費支出,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H2c:多元生態補償方式通過激發內生致富動力,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3 研究設計
3. 1 數據來源
研究所采用數據來自課題組2022—2023年對“三區三線”劃定試點省份山東省7縣(區)的實地入戶調查。調查地點選擇東平縣、泰山區、墾利區、利津縣、鋼城區、費縣、無棣縣7 個生態保護紅線覆蓋面積較大的樣本縣(區)。所選7個樣本縣(區)分布在山東省的不同區域,東平縣位于魯西平原區,墾利區、利津縣和無棣縣位于魯北濱海平原區,泰山區和鋼城區位于魯中山地區,費縣位于魯南山地丘陵區。山東省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文化積淀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上呈現出“東北—西南”遞減趨勢,歷史文化涵蓋了泰山文化、黃河文化、孔孟文化等不同地域文化。在調查方法上,本研究采取多階段抽樣法,首先,依據生態保護紅線區劃定范圍和生態補償實施情況,在上述樣本縣(區)中隨機抽取1~3個樣本鄉鎮;之后,在當地政府相關負責人員帶領下,依據每個鎮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區社區數量和社區居民數量的多寡在每個鎮隨機選取40~60戶樣本農戶,開展相關問卷調查。調查方式為一對一訪談,問卷內容由課題組成員依據訪談情況如實填寫。調研結束后,為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對問卷進行篩選,剔除了存在離群值、缺失值的無效問卷,最終獲取有效問卷1 051份。
3. 2 模型構建
3. 2. 1 基準回歸模型
為厘清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本研究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3. 2. 2 中介效應模型
如何保障中介效應檢驗的科學可靠性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心理學的傳統3段式逐步檢驗法在經濟學領域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40],但是近期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在復雜社會科學的背景下因果問題尤為復雜,致使研究實踐的初衷和最終呈現效果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錯位[41]。對此,借鑒Aguinis等[42]和牛志偉等[43]構建4段式中介效應模型的做法,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來檢驗因果關系中的中介效應,具體模型設定如下所示:
3. 3 變量設置
3. 3. 1 因變量
本研究因變量為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采用多維發展韌性指數(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resilience index,簡稱MDRI)表征。結合前文概念界定并借鑒Speranza等[6]和Barrett等[27]的研究,家庭發展韌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包括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3個維度,多維發展韌性指數(MDRI)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此外,由于學界關于多維發展韌性指標權重賦值方法的選擇暫無統一定論,且目前為止尚未找到一種絕對優于等權重法的賦權方法,所以參考多數學者的處理方法,選擇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的等權重賦值法對指標進行賦權,家庭發展韌性指標的賦權結果見表1。
3. 3. 2 核心自變量
本研究核心自變量是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用來衡量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獲得生態補償方式的多元化程度。生態補償方式的多元化表現在補償種類的多樣化和補償額度的差異性兩個方面,故而需要將補償種類和補償額度同時納入測度模型進行計算。慮及4種生態補償方式均屬于政府轉移支付資金在實際使用過程中的多樣化表達形式,將農戶獲得的不同類型生態補償方式統一量化為資金,以實現不同生態補償方式補償額度之間的可比性和可加性。
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是現有文獻中常用來測度多元化程度的一種綜合指數[44],該指數數值反向反映多元化程度。慮及思維習慣,使用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測度農戶獲得生態補償方式的多元化程度,該指數數值越大,意味著多元化程度越高。4種生態補償方式補償額度和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3. 3. 3 中介變量
本研究中介變量為勞動力就業結構、發展性消費支出和內生致富動力。借鑒李玉山等[45]、李坦等[19]、尹志超等[36]的研究,將中介變量指標設置為:①勞動力就業結構指標的測算思路是求家庭總非農就業人數與總勞動力人數的比值;②發展性消費支出指標使用家庭人均設備用品、教育文娛、交通通信等消費支出來測度;③內生致富動力指標的測算思路是在問卷中設置對應問題“在下列選項中,您的家庭屬于哪一種生活狀態?”。
3. 3. 4 控制變量
慮及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問題,借鑒已有相關研究[10,46],選擇如下控制變量:①戶主的個體特征,包括戶主性別、戶主年齡、戶主婚姻狀況;②農戶的家庭特征,包括黨員戶、家庭成員規模、家庭撫養比;③農戶所在的區域特征,包括經濟增長。
3. 4 描述性統計分析
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見表2。結果顯示,首先,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指數的均值是0. 46,標準差為0. 15,極值區間是0. 10~0. 84,研究區域內農戶家庭發展韌性指標的最小值出現在無棣縣,最大值出現在利津縣,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距超過0. 74,表明生態保護紅線區不同農戶之間家庭發展韌性指數差異較大。本研究測算的多元生態補償方式變量均值為0. 31,標準差為0. 29。其中,接受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的農戶最多,均值為0. 91,相較之下,接受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的農戶偏少,均值為0. 40。考察樣本3個維度的中介變量中,勞動力就業結構指標的均值為0. 57,說明所選研究區域農戶非農就業率偏高,表明在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業發展受限的情況下,當地農戶傾向于改變原有生產方式和生計策略選擇,勞動力等關鍵生產要素配置逐漸由農業領域轉移到非農領域;發展性消費支出指標的均值為4 726. 07元,與2021年農村人均發展性消費支出6 541元相比處于較低水平,說明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關于發展性消費支出的消費意愿有待進一步提升;內生致富動力指標的均值為1. 34,有97. 62%的農戶具有較強的內生致富動力,僅有2. 38%的農戶選擇依靠政府幫扶生活,這意味著當地農戶自我發展意識總體而言處于較高水平。
4 實證分析結果
4. 1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
4. 1. 1 基準回歸結果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首先,為驗證前文假說H1,控制了戶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區域特征,并選擇OLS估計方法進行回歸,結果顯示核心自變量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0. 167 7,這表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有效提升了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且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每增加一單位標準差,預計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大約會提升32. 42%(0. 167 7×0. 29/0. 15)。對于估計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偽回歸問題,參考Günther等[47]的解決方法,將因變量“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由連續變量轉換為二分類變量,即因變量在均值(0. 46)以上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此外,由于轉化后的因變量為二分變量,所以重新選擇Probit模型驗證基準回歸結果,發現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的影響系數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值,仍支持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有效性,假說H1初步得證。
4. 1. 2 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進一步采取控制村級啞變量、增加其它控制變量、數據縮尾處理、更換因變量權重測算方式等策略進行穩健性檢驗,基準回歸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4。第一,控制村級啞變量。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調查涉及的樣本村莊較多,這些行政村整體呈現出較為分散的格局,零星分布在魯北、魯南、魯中和魯西的不同區域。慮及山東省內各村莊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積淀上存在的差異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控制了村級啞變量。第二,補充其他控制變量。由于政策執行力度會通過影響生態補償實施效果進而作用于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參考莫勇波等[48]的測度思路計算政策執行力指數,并將其納入基準回歸模型重新回歸。第三,數據縮尾處理。考慮到樣本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常值問題,進一步對所有變量進行1%的數據縮尾處理,并對處理后的樣本重新回歸以減少異常值對實證檢驗的干擾。第四,更換因變量權重測算方式。考慮到家庭發展韌性指標體系所選取的各項指標屬于并列關系,并且分析的指標之間存在一定關聯,因而重新采用CRITIC法賦權并核算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從4個回歸結果來看,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系數仍顯著為正,估計結果與前文結論保持一致。
4. 1. 3 內生性問題的討論
核心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由此產生內生性問題。這是因為,隨著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其參與生態治理的需求愈加迫切,進而可能對多元生態補償方式供給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采用工具變量法來緩解該問題。該方法可以分解為兩個主要步驟:第一,找到一個同時滿足相關性和排他性要求的工具變量;第二,將找到的工具變量帶入2SLS模型中,在第一階段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在第二階段比較基準回歸結果與重新回歸結果的一致性。關于工具變量的選擇,借鑒Ellis等[49]的研究,將工具變量設置為“社區平均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即通過剔除農戶個體后再計算社區內其他農戶的平均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于居住在同一社區的農戶,“同儕效應”導致其在生活環境、行為習慣、生計決策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工具變量“同一社區其他農戶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的均值”與農戶個體的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但是這一變量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卻不相關,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與外生性的基本條件。引入工具變量的2SLS 估計結果見表5。首先,Cragg-Donald Wald F 統計量大于10,Kleibergen-Paaprk LM 統計量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通過了弱工具變量檢驗和工具變量識別不足檢驗。其次,2SLS第一階段估計結果表明,選取的工具變量與和自變量多元生態補償方式之間呈顯著正相關,滿足相關性要求。2SLS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的系數仍顯著為正值,表明農戶獲得的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每增加一個單位,對應的家庭發展韌性會隨之提升30. 07%。這一結果進一步論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4. 2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機制檢驗
根據前文構建的4段式中介效應模型驗證假設H2,主要包括4個步驟:第一,通過模型(1)檢驗核心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如果核心自變量系數顯著,則總效應顯著;第二,通過模型(2)檢驗核心自變量對中介變量的影響,如果中介變量系數顯著,則需進行后續檢驗;第三,通過模型(3)和模型(4)檢驗中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如果中介變量系數顯著,則初步證明中介效應成立;第四,分別進行Sobel檢驗和Bootstrap(1 000次)抽樣檢驗,如果兩種檢驗均能通過,則再次證明中介效應成立。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見表6。其中,勞動力就業結構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列(1)—列(4)所示。首先,結果顯示核心自變量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支持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有效性。其次,列(2)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多元生態補償補償方式對中介變量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優化作用。隨后,列(3)—列(4)中介變量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值,初步證明中介效應的存在。最后,分別進行Sobel檢驗和Bootstrap(1 000次)抽樣檢驗,結果顯示Z 值統計量是5. 010,且在1%水平上顯著,置信度為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上述結果均表明勞動力就業結構的中介效應成立,即多元生態補償方式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從而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假說H2a得到驗證。此外,列(5)—列(8)和列(9)—列(12)分別是發展性消費支出和內生致富動力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同理可驗證多元補償方式可以通過釋放發展性消費支出和激發農戶內生致富動力進而起到提升家庭發展韌性的重要作用。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勞動力就業結構、發展性消費支出和內生致富動力在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和農戶家庭發展韌性之間發揮中介效應,假說H2a、H2b、H2c均成立。
4. 3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影響的異質性檢驗
為進一步揭示不同農戶群體從多元生態補償方式中獲益的異質性,本研究基于戶主年齡、人均收入水平和戶主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異開展異質性分析。第一,代際差異理論認為,不同世代群體因其出生時代、社會環境和生活經歷的不同,造就了有差異的價值觀、人生態度和行為方式。因此,由年齡產生的代際差異可能會影響到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作用,根據“戶主是否在1980年之前出生”將農戶家庭劃分為老一代農戶和新生代農戶兩個群體,并據此分析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不同代際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差異。第二,考慮到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戶家庭在家庭背景、可行能力、生計策略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等方面的較大差異可能產生明顯的家庭發展韌性差距,因此根據“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低于樣本均值”將農戶家庭劃分為低收入組和高收入組兩個群體,并據此分析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不同收入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差異。再次,由于戶主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可能造成其在生態認知、綠色技術采納、重大生計決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進而可能會拉大農戶群體之間的發展韌性差距,為此,根據“戶主受教育水平是否低于樣本均值”將農戶家庭劃分為低學歷組和高學歷組兩個群體,并據此分析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不同學歷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差異。
以戶主年齡、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戶主受教育水平作為分組標準,將樣本劃分為老一代組與新生代組、低收入組與高收入組、低學歷組與高學歷組后,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同時,進一步運用費舍爾組合檢驗法進行組間差異性檢驗,該方法通過“自抽樣法( Bootstrap) ”計算出“經驗P值”,并以此判斷分組回歸組間差異是否顯著。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影響的異質性分析結果見表7。首先,在年齡分組方面,兩組回歸系數的組間差異在5%顯著水平上通過了費舍爾組合檢驗,這說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于老一代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作用更強;其次,在收入分組方面,經驗P 值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作用在低收入群體中更為顯著。最后,在受教育水平分組方面,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系數均正向顯著,經驗P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盡管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不同分組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均產生了顯著提升作用,但是對低學歷組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作用要明顯高于對高學歷組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這是因為,老一代、低收入、低學歷的農戶往往面臨獲取發展機會難度大、擺脫相對貧困能力不足、增收渠道單一等困境,這類群體有更強的意愿通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來獲取穩定補貼、發展機會和提升勞動技能。因此,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這些弱勢農戶群體發展韌性的影響更為顯著,這說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具有“底層保障型”特征。
4. 4 進一步討論: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不同維度的影響差異
依據前文理論分析可知,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包含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3個維度,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可以劃分為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和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兩種類型。因此,為進一步探究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不同維度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研究進一步將核心自變量分別設置為“是否獲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和“是否獲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將因變量分別設置為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并采用OLS估計方法進行回歸。
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不同維度的影響結果見表8。結果顯示,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和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均能對農戶家庭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即二者均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發揮了多維提升作用。但是,不難發現,相較于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而言,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在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3個維度均發揮了更強的提升作用。究其原因,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是一種通過直接給予現金、生活或生產資料等途徑實現“授之以魚”的生態補償方式,雖然能產生立竿見影的幫扶效果,但是存在不可忽視的“救助缺陷”,難以保障政策效果的可持續性[26]。而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則是一種借助提供智力服務、產業或項目支持等途徑實現“授之以漁”的生態補償方式,能夠催生農戶的自我持續發展能力,幫助受償農戶逐漸減少對政府的物質依賴,憑借努力奮斗走向自力更生之路。因此,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提升作用總體要優于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
5 結論與啟示
5. 1 結論
本研究以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①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發揮顯著提升作用,這一作用主要通過優化勞動力就業結構、釋放家庭發展性消費支出和激發農戶內生致富動力等路徑實現。②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具有“底層保障型”特征,具體表現為對老一代、低收入水平和低學歷的弱勢農戶群體發展韌性的影響更為顯著。③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和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均對農戶家庭抵抗恢復能力、適應調節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產生了積極影響。總體上,相較于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而言,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發揮了更強的提升作用。
5. 2 政策啟示
基于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①在發展相對滯后的生態保護紅線區,需重視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在破解農戶家庭保護與發展困境中的重要作用。當前,生態保護紅線區生態補償實踐探索存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缺位、市場化補償手段應用性有限、對農戶可持續生計關注不足等問題。為此,各級政府未來可在整合現有生態補償政策的基礎上,開展生態綜合補償,大力推行林業碳匯交易、水權水質交易、生態產業化經營等市場化生態補償方式,建立全覆蓋、不重復、可銜接的生態補償體系。②關注多元生態補償方式提升家庭發展韌性的異質性特征,適度提高生態補償政策目標和工具的瞄準性。慮及目前生態補償存在一定的參與門檻,致使部分農戶不能參與其中而獲得經濟收益。而事實上,弱勢群體有更強的意愿通過多元生態補償方式來獲取穩定補貼、發展機會和勞動技能。因此,應通過適當降低生態補償政策的參與門檻,讓更多弱勢群體參與生態補償而獲益,以更好地發揮多元生態補償方式的底層保障功能。③逐步形成以“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為主,輸血型生態補償方式為輔”的可持續發展機制。重點協助和鼓勵地方政府實施多元化的造血型生態補償,不斷探索包括對口協作、異地開發、生態恢復項目、技能培訓、綠色產業等造血型生態補償方式,以期發揮等量補償額度的最大效益。
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生態補償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功能定位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緊密結合時代特征和基本國情,經歷了專注環境保護、兼顧環境保護與減貧、協同推進環境保護和共同富裕3個階段,為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當前中國正處在生態文明和共同富裕的雙重戰略疊加期,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指引下,生態補償作為促進生態資源富集區共同富裕的普惠機制,將致力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雙重戰略目標。鑒于此,本研究以生態保護紅線區農戶為例,重點探討了多元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有益借鑒的同時,仍存在一定不足和進一步研究空間:①研究樣本的局限性。由于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不同地區生態補償執行情況有所差異,盡管本研究選擇山東省生態保護紅線區作為研究區域有助于探索前沿理論,但結論的普適性仍需謹慎對待。未來研究還需要結合不同地區生態補償政策的異質性特征,利用實證分析方法驗證本研究所得結論的普適性。②研究視角的局限性。在生態補償領域,“多元”可指補償主體、融資體系或補償方式的多元化。因此,除本研究所關注的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外,未來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探究補償主體和融資體系的多元化。
參考文獻
[1] 楊文靜,孫迎聯. 我國反貧困治理與農戶生計轉型:歷史回顧與
改革前瞻[J]. 經濟學家,2022(5):97-106.
[2] 黃偉,王桂新. 綠色發展如何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
基于貴州省的數據分析[J].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40(1):77-83.
[3] 白云麗,曹月明,劉承芳,等. 農業部門就業緩沖作用的再認識:
來自新冠肺炎疫情前后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證據[J]. 中國農村經
濟,2022(6):65-87.
[4] CISSé J D,BARRETT C B. Estimating development resilience:a
conditional moments?ba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135:272-284.
[5] PHADERA L,MICHELSON H,WINTER?NELSON A,et al. Do as?
set transfers build household resili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9,138:205-227.
[6] SPERANZA C I,WIESMANN U,RIST S.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ecological
dynamic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4,28:109-119.
[7] QUANDT A.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the household liveli?
hood resilience approach (HLRA)[J]. World development,2018,
107:253-263.
[8] 李志平,吳凡夫. 繼續增加財政轉移性支出可以提高脫貧質量
嗎:基于生計抗逆力和CFPS 數據的實證[J]. 農業經濟問題,
2020,41(11):65-76.
[9] 楊秀平,王里克,李亞兵,等. 韌性城市研究綜述與展望[J]. 地
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21,37(6):78-84.
[10] 李晗,陸遷. 無條件現金轉移支付與家庭發展韌性:來自中國
低保政策的經驗證據[J]. 中國農村經濟,2022(10):82-101.
[11] 張東玲,焦宇新. 農業保險、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與農戶家庭經
濟韌性[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1(2):
82-97.
[12] 鄭黎陽,黃薈婕,張鑫. 人力資本與脫貧地區農戶生計韌性:基
于門檻回歸模型的檢驗[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3,37(5):
69-75.
[13] 吳詩嫚,祝浩,盧新海,等. 土地綜合整治對農戶生計恢復力的
影響[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3,32(11):2431-2442.
[14] 劉格格,周玉璽,葛顏祥. 多樣化生態補償有助于緩解生態保
護紅線區農戶相對貧困嗎[J]. 中國農村觀察,2023(6):
161-180.
[15] 楊小軍,費梓萱,任林靜. 組態視角下流域多元化生態補償的
差異化驅動路徑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23(12):106-125.
[16] 劉格格,葛顏祥,張化楠. 生態補償助力脫貧攻堅:協同、拮抗
與對接[J]. 中國環境管理,2020,12(5):95-101.
[17] 任林靜,黎潔. 生態補償政策的減貧路徑研究綜述[J]. 農業經
濟問題,2020,41(7):94-107.
[18] 李一花,李佳. 生態補償有助于脫貧攻堅嗎:基于重點生態功
能區轉移支付的準自然實驗研究[J]. 財貿研究,2021,32(5):
23-36.
[19] 李坦,徐帆,祁云云. 從“共飲一江水” 到“共護一江水”:新安江
生態補償下農戶就業與收入的變化[J]. 管理世界,2022,38
(11):102-124.
[20] 鄭云辰,葛顏祥,接玉梅,等. 流域多元化生態補償分析框架:
補償主體視角[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7):
131-139.
[21] 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課題組. 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
政策研究[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206-208.
[22] 王金南,劉桂環,張惠遠,等. 流域生態補償與污染賠償機制研
究[M]. 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4:37-38.
[23] 靳樂山. 中國生態補償:全領域探索與進展[M]. 北京:經濟科
學出版社,2016:43-44.
[24] 沈滿洪,陸菁. 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J]. 浙江學刊,2004(4):
217-220.
[25] CARPENTER S,WALKER B,ANDERIES J M,et al. From meta?
phor to measurement:resilience of what to what?[J]. Ecosystems,
2001,4(8):765-781.
[26] CARL F. Resilience: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16(3):253-267.
[27] BARRETT C B,CONSTAS M A. Toward a theory of resilienc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
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4,
111(40):14625-14630.
[28] MICKELSON K D,WILLIAMS S L.Perceived stigma of poverty
and depression:exam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me?
diators[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8,27(9):
903-930.
[29] 詹和平,張林秀. 家庭保障、勞動力結構與農戶土地流轉:基于
江蘇省142 戶農戶的實證研究[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9,18(7):658-663.
[30] 廖柳文,龍花樓,馬恩樸. 鄉村勞動力要素變動與耕地利用轉
型[J]. 經濟地理,2021,41(2):148-155.
[31] 魏娟,趙佳佳,劉天軍. 土地細碎化和勞動力結構對生產技術
效率的影響[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17(5):55-64.
[32] 劉皇,周靈靈. 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與農業技術進步路徑[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43(1):94-104.
[33] 王向陽. 勞動力結構、家庭資源配置與農民家庭再生產:基于
農民家庭“積累—消費” 結構的分析框架[J]. 南京農業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19,19(5):64-73.
[34] 朱迪. 消費中的社會平等與公正:我國家庭消費不平等和消費
差距的實證分析[J]. 社會發展研究,2021,8(1):127-142.
[35] 汪險生,郭忠興,李寧,等. 土地征收對農戶就業及福利的影
響:基于CHIP 數據的實證分析[J]. 公共管理學報,2019,16
(1):153-168.
[36] 尹志超, 郭沛瑤. 精準扶貧政策效果評估: 家庭消費視角下的
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 2021, 37(04): 64-83.
[37]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
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38] 于婷,于法穩. 環境規制政策情境下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
用認知對養殖戶參與意愿的影響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19
(8):91-108.
[39] 管睿,王文略,余勁. 可持續生計框架下內生動力對農戶家庭
收入的影響[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19(6):130-139.
[40] 溫忠麟,葉寶娟. 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 心理科
學進展,2014,22(5):731-745.
[41] 江艇. 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 中國
工業經濟,2022(5):100-120.
[42] AGUINIS H,EDWARDS J R,BRADLEY K J.Improving our under?
standing of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
search[J].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2017,20(4):665-685.
[43] 牛志偉,許晨曦,武瑛. 營商環境優化、人力資本效應與企業勞
動生產率[J]. 管理世界,2023,39(2):83-100.
[44] WUEPPER D,YESIGAT AYENEW H,SAUER J. Social capital,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PanelData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
ics,2018,69(2):458-475.
[45] 李玉山,盧敏,朱冰潔. 多元精準扶貧政策實施與脫貧農戶生
計脆弱性:基于湘鄂渝黔毗鄰民族地區的經驗分析[J]. 中國農
村經濟,2021(5):60-82.
[46] 劉格格,周玉璽,葛顏祥. 生態補償何以促進生態保護紅線區
農戶共同富裕?[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4,34(4):
197-209.
[47] GüNTHER I,HARTTGEN K. Estimating households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and covariate shocks:a novel method applied in
Madagascar[J]. World development,2009,37(7):1222-1234.
[48] 莫勇波,劉國剛. 地方政府執行力評價體系的構建及測度[J].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69-76.
[49] ELLIS R P,MARTINS B,ZHU W J. Health care demand elastici?
ties by type of service[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7,55:
232-243.
(責任編輯:蔣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