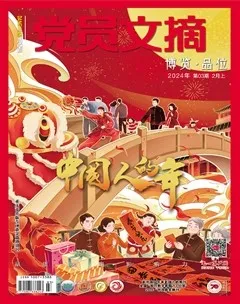永樂宮壁畫何以“封神”?
王皓
近300位人物畫像,從表情到服飾無一相同,他們相互獨立而又三五成群,若有所思、耳語相向、怒目圓睜,如一幅幅定格的彩色膠片,下一秒似乎就能聽到嘈雜熱鬧之聲。
這就是山西省運城市永樂宮元代壁畫《朝元圖》,所謂“朝元”,即朝謁元始天尊。畫師在400多平方米的墻面上,以傳統的對稱形式,畫出290位人物的隊伍。畫中人物主次分明,男女老幼,壯弱肥瘦,動靜相宜,文武相間,素有“東方畫廊”的美譽。
2023年11月,電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獲得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電影中,商王殷壽、姜王后、東西南北四大伯侯,他們的頭冠、服飾等造型靈感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這幅《朝元圖》。導演烏爾善坦言,永樂宮的壁畫構成了整個電影構思的基礎。
氣韻連貫,滿壁風動
35年前,當烏爾善還在中央美院讀書時,偶然的一次下鄉寫生,就被永樂宮壁畫深深震撼,至今難忘。
“壁畫非常大,超過4米的高度。”烏爾善回憶說。他從小學習美術,印象中在紙上畫一個40厘米的人像已經很難了,更別說在墻上畫得如此線條流暢、氣韻連貫。
永樂宮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運城市芮城縣,創建于公元1247年至1368年間。
山西省永樂宮壁畫保護研究院院長席九龍說,永樂宮現存壁畫面積1005.68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龍虎殿、三清殿、純陽殿、重陽殿4座元代建筑內。
擔任永樂宮講解工作的孔新芳說,永樂宮壁畫的精華就在三清殿內。站在壁畫前仔細觀察,每一根線條、每一筆勾勒都非常精細流暢,線條長有丈余、短不足寸、粗近厘米、細如發絲,最令人驚嘆的是一丈長的線條常常不見接筆停頓的地方,運筆流暢似一氣呵成。
“畫面中一排人物走在那邊,你不覺得他們很悶,也不會覺得很擠,整體是互相協調的。”電影《封神》三部曲美術指導兼造型指導葉錦添表達了他對壁畫的贊揚。
參觀永樂宮壁畫的游客無不對畫中人物形象嘖嘖稱奇。近300位人物畫像,個個面型豐滿,表情生動,衣冠服飾無一雷同。
“史無前例的搬遷工程”
永樂宮原址并不在現在的位置,而是在20多公里外的永樂鎮。
20世紀50年代,黃河三門峽水庫開始興建,永樂宮所在的永樂鎮處于工程淹沒區,為了保護這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國務院決定對永樂宮進行原物原貌整體搬遷。
“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文物搬遷工程,沒有任何先例可考,沒有外國專家支援,全靠我國的‘土專家自力更生。”席九龍說。
中國古代的木構建筑一般采用榫卯結構,建筑的搬遷相對容易實現,但壁畫的揭取當時在國內無先例可循,一時間難倒眾人。經過周密研究,最終確定了完整的永樂宮搬遷方案,即臨摹、揭取和修復三步方案。
從1957年2月開始,永樂宮壁畫的臨摹用了將近一年時間。從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開始對壁畫進行揭取、包裝和遷運,并對宮殿建筑進行編號、拆除,將它們運送到新址。從1962年下半年起,又耗時將近4年,才完成全部壁畫的加固和復原。
整個遷建工程到1966年結束,前后歷時近十年。“永樂宮的搬遷不亞于埃及古代神殿的移筑。”一位日本學者如是說。
壁畫臨摹工作和永樂宮的搬遷設計同時進行。當時,文化部及國家文物局組成由中央美術學院陸鴻年教授帶隊,包括中央美術學院和原華東分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的70多名師生在內的一支隊伍,來到永樂宮臨摹壁畫。
臨摹團隊首先在深入了解永樂宮歷史的基礎上,對原作的主題、內容、構圖、用筆、用墨、著色到壁畫的殘損情況,如裂縫、剝落、積塵、變色、霉點、后代修復、層次等環節進行研究分析,制定出臨摹總體方案。然后分組對龍虎殿、三清殿、純陽殿、重陽殿逐一進行實地測量,做好記錄,繪制平面圖,為搬遷、重建搜集檔案和資料。
1961年,遷建中的永樂宮被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在同一年,馮建宮出生在搬遷后的永樂宮西院,他的父親馮三戒曾經是搬遷團隊的一員,從教育局抽調來從事文字刻蠟版任務。隨后一家人就住在永樂宮的院子里,看管著這座文保單位。馮建宮回憶說:“建設永樂宮,父親給我起名就是這個寓意。”
“我的時間不夠用了”
在永樂宮遷建工程展廳內,擺放著一幅金母元君等比例臨摹圖,畫術精良、惟妙惟肖。
這幅臨摹作品的作者名叫范愛珠,她是永樂宮壁畫保護研究院陳展部的負責人。這些年,每當范愛珠走進壁畫臨摹室,總會情不自禁地全身心投入其中。“我總覺得我父親就坐在這里,好像是他拿著我的手在畫畫一樣。”范愛珠說。
范愛珠的父親叫范金鰲,曾是永樂宮文物保管所副所長。20世紀80年代,隨著永樂宮對外開放,前來探訪的學者、游客、媒體日益增多,帶來管理和保護問題。為了更好地保護傳承壁畫,范金鰲用近5年的時間組織臨摹了三清殿壁畫。金母元君這幅作品陳列在大殿旁的壁畫臨摹室里,至今仍是十幾所美院學生的教學范本,每年接待5000余名師生。
范金鰲在《80年代永樂宮壁畫臨摹始末》一文中寫道,“在臨摹過程中,大家經常一起討論、交流經驗,互相取長補短,青年畫家向老教授學習,在生活工作中主動幫助老教授做些力氣活,老教授熱情指導青年畫家……大家都能主動相互學習,這就保證了摹本的質量……在臨摹過程中,畫家們付出艱辛的汗水,在四五米高的高架上,一畫就是幾個小時,晚上常常加班到12點”。
完成臨摹任務后的十幾年,范金鰲依然“筆耕不輟”,不斷尋找和探索壁畫的靈魂。“我父親除了吃飯、上廁所,都在畫畫,他把壁畫看得比他的命更重要。”范愛珠說,自己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常常因為畫畫忘記接送她,她為此“懷恨在心”,十分叛逆地表達出對畫畫的厭惡。
數年后,父親病危之時,還想著讓女兒推輪椅帶自己去大殿看一看。“當時對我的觸動是最深的”,回憶起這段時光,范愛珠眼里泛著淚光,聲音哽咽。
2013年,范愛珠開始走上繪畫之路,她外出學習、不斷鉆研,進步也來得很明顯,大大小小畫了1000多張,成了業內小有名氣的畫家和壁畫修復傳承人。
“有次跟姑娘聊天我還說,現在理解你姥爺當時說時間不夠用了,我現在覺得我的時間也不夠用了。”范愛珠說。
在永樂宮景區的文創產品店鋪里,壁畫主題的畫冊、抱枕、絲巾、T恤、背包很受游客歡迎,在電影《封神》第一部熱映的時候,很多文創產品一度脫銷。不遠處,一行十余人的小學生研學團隊正在觀摩壁畫真跡、臨摹壁畫。帶隊的成都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陳榮說:“對于這些孩子來說,是第一次以這樣的形式畫畫,充分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摘自《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