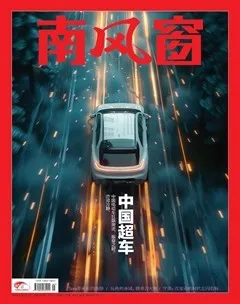屏攝、撤檔,電影還能在春節活下來嗎?
肖瑤
農歷新年剛過,2024年就“榮獲”“屏攝元年”之稱。
事緣歌手薛之謙一次屏攝行為及后續輿論的發酵。為支持好友韓寒的電影《飛馳人生2》,薛之謙在觀影后發了一篇長文,文中附上了幾張自己在觀影時拍攝的電影畫面。
暫且不討論薛的行為本身之正誤,因為無論從明文法規還是從道德法則兩個不同維度,對這件事的定性和評判,本不該存在爭議。
關鍵在于此事隨之產生的連鎖反應:不僅本人拒不道歉,甚至理直氣壯地宣稱屏攝不違法。其粉絲跟風大呼“屏攝無錯”,甚至為了支持偶像紛紛效仿。
隨后,人們發現,相當一部分觀眾、網友認為,在影院拍攝電影畫面,自行發布在社交平臺,只要不用于商業傳播,就完全屬于個人自由。
在一些規模頗大的線上社群平臺,甚至有人將從不知何處泄露的完整影片上傳分享,美其名曰“發福利”。我還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看見一位常駐一線城市、經驗豐富的律師,因為自己身在不便觀影的鄉鎮,便發朋友圈求問“誰有春節檔資源”。
我國對于電影行業版權保護的相關法規,相較于一些發達國家的確生效較晚。根據2017年3月生效的《電影產業促進法》第三十一條,“未經權利人許可,任何人不得對正在放映的電影進行錄音錄像。發現進行錄音錄像的,電影院工作人員有權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刪除;對拒不聽從的,有權要求其離場。”這是對動態錄像做出的規定,但對于靜態照片,目前仍無明確釋法。
不僅在電影行業,圖書、音樂、繪畫等各文藝創作領域,社會的版權法律意識和教育意識歷來欠缺。而若將消費者視為擁有某些階層共性的共同體,這當中只要有人站出來嚴詞反對“盜版”,恐怕還會被“多數”抨擊為精英主義的傲慢。
作為疫情結束后首個不“瞻前顧后”的春節檔,總計逾80億票房的2024年春節檔可謂勢如猛虎。可即便在如此強大的觀眾購買力面前,春節開端上映的八部電影,到春節結束前竟有四部頂不住競爭壓力,紛紛撤檔,只剩下一半“優勝者”仍然堅挺。
春節檔成了一塊戰場,血雨腥風,硝煙彌漫。最后活下來的,未必是質量最高的,但必定是最適合全家人一起觀看的,價值觀覆蓋老中青幼。譬如百分百圓滿的親情、勵志和熱血,其中又以喜劇為佼佼者。
在遠超平常的競爭強度下,影片本身質量并不差的《紅毯先生》《我們一起搖太陽》等影片迫于生存壓力撤退。留意網上的評論,會發現用心去看這兩部片的觀眾其實并不多,有觀眾將一部對藝術圈層生態的諷刺幽默理解為導演的“自戀”,也有人批評絕癥題材不該在合家歡時期上映,哪怕影片故事其實真誠而動人。
以強度最大的春節檔為代表,國產片假期檔越來越呈現出一種趨勢:藝術讓位給話題、營銷噱頭。文藝欣賞不再是百花齊放的盛宴,而是競相角逐的單向賽道。誰能滿足觀眾嗷嗷待哺的短視頻胃口,誰能在保守價值的框架內演一個好笑的小品,誰就是藝術之王。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我們需要戲劇,因為有限的人生可以被延展,因為人類有創作和接收故事的本能。在故事里,真相和情理才會穿越時空,被永恒流傳。
當戲劇變成熱鬧,和著電視機、煙花與飯菜服用,電影院也的確沒什么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