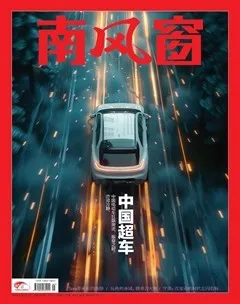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假冒偽劣”的年貨為何充斥農村市場?
“假冒偽劣”的年貨為何充斥農村市場?
楊華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本文節選自公眾號“新鄉土”
為什么假冒偽劣產品會充斥著農村市場?帶著這個問題,我做了個小小的調查,經多方訪談證實,那些原本屬于城市市民消費的產品,是在2007年、2008年左右成規模地擺上了農民的餐桌。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農民不再大規模自制年貨,理由是吃的人少了,人懶了。偶爾還有人家做,也是當作零食,而不是用于招待客人和拜年。

也就是說,從2008年左右開始,城市消費品全面取代農村自制消費品,成為農民餐桌上的主要消費品,也成為農民過年往來的禮品。這個“取代”是“突然之間”實現的,而不是一個緩慢、漫長的發展過程。可以說,在2008年左右,農村一夜之間對原本城市的消費品有了消費,并舍棄了自制的農村消費品。這種農民對城市消費品的需求,是突然之間制造出來的,不是充分認知基礎上的理性需求。
那么,“突然之間”農民對原來的城市消費品有了消費,在農村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需要由商家來填補。因為,這是“突然之間”出現的一個巨大市場,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數年前,農村人不喝牛奶,農村小孩也不喝牛奶,我作為伊利蒙牛的老總是不會預料到會有這么個市場出現的。那么,10年前我就不會先知先覺地預備好供應農村市場所需的牧場。我所有的牧場都是供應城市既有市場的。當農村市場突然出現的時候,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市場,手足無措,不哭還能怎么辦呢?
但是農村的這個市場太大了,利潤太豐厚了,在巨額利潤面前總會有不怕死的人。那么,很多小的生產廠家就開始向農村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正規知名廠家對這個市場雖然垂涎三尺,但原材料供應不上,只能作罷。但仍有些正規廠家還是耐不住寂寞冒了風險,“三鹿”就是這樣冒出來的。所以,農村假貨橫行的基本線條是:農村在某個時候突然之間制造了對原本是城市消費品的消費需求,正規廠家的原材料供給不上,假冒偽劣產品就一定會冒著風險去彌補這個市場空間。加上農民的各種意識都沒有跟上,假冒偽劣產品就一定會有市場。
“星鏈”在戰場:第一次商業太空戰爭
張涵抒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本文節選自《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
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中,馬斯克向烏克蘭投放的宇宙探索公司(SpaceX)產品“星鏈”(Starlink)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共同矚目。在俄烏戰爭爆發的第二天,馬斯克就為烏克蘭前線輸送了大批“星鏈”衛星互聯網移動終端,借助其運營的近地低軌道衛星(LEO)“星座”網絡,恢復了烏軍被俄軍切斷的通信網絡,以商業通信衛星資源填補了軍事通信被打擊后造成的空白。美太空軍負責人杰伊·雷蒙德上校也將其稱為“第一次商業太空戰爭”。星鏈在俄烏戰爭中真正的三大顛覆性特色是:冗余彈性網絡、低成本部署、商業航天的灰色身份。
首先是LEO星座構成的冗余彈性網絡。海量衛星布局使得網絡彈性極大、冗余度極高,讓傳統的反衛星武器陷入絕對被動的局面。雖然俄羅斯有能力擊落近地球軌道上的“星鏈”衛星或其他衛星,但成本極高而且難以奏效:摧毀一顆衛星需要一枚反衛導彈,而SpaceX的廉價火箭一次發射即可補充60顆衛星,效率與成本均相差數十倍。大多數人預計烏克蘭的通信或互聯網接入會在戰爭的頭幾天或頭幾個小時被切斷,“但這并沒有發生,現在也沒有發生”。美國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將軍也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馬斯克和星鏈確實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型星座或一個增殖架構所能提供的冗余和能力。”

其次是低成本部署。成本控制在軍事通信中也非常重要。事實上,發展由衛星搭建的天基互聯網作為軍事通信手段早在2002年就被美軍提上日程了,名為“轉型衛星通信計劃”(TSAT)。但這一系統的命運卻十分曲折,布什總統在2007財年為TSAT申請了98億美元的經費,但由于奧巴馬政府試圖削減國防開支,五角大樓于2009年取消了該計劃,并寧愿選擇帶寬只有TSAT能力5%的先進極高頻衛星。SpaceX公司由于掌握了太空從廉價火箭發射到衛星制造和運營全產業鏈的技術,已經能夠將單次發射的成本降低至50萬美元,很好地迎合了美軍對于性價比的期待。
最后,是商業航天在戰爭中微妙的灰色身份。星鏈并不直接對接國家力量,行動在法理上不代表國家行為,從而增加戰略回旋余地。由于商業衛星屬于民間資產,俄羅斯對其攻擊尚未有國際法的依據。為了避免沖突升級,再加上技術和成本上的考慮,俄羅斯一直無法實施直接的反擊。由于其不直接代表國家力量,擁有了進退自如的灰色空間。因此,星鏈在第一次商業太空戰爭中已經顯露了諸多具備顛覆性的特點與趨勢,將極大革新甚至重新塑造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博弈格局,深刻影響未來的軍事航天體系與作戰模式。
縣處級中年女性領導干部的成長障礙與破解之策
—以7名基層縣處級女干部為例
伊佳 趙云 黑龍江省婦女干部學院副研究員
本文節選自《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23年第2期
基于“女子本弱”的社會文化,組織常常給予女干部寬松照顧,但多發生在崗位分配和選拔任用時。在崗位分配上,女干部同樣需要經歷多崗位歷練,為未來晉升積累堅實的資本。但是,女干部的崗位調動往往局限在非主干線領域,職業性別的水平隔離仍然作用于公共部門干部的事業發展。
在干部選拔任用上,公共部門內的男性偏好問題,依然可以用“統計歧視”理論加以解釋。由于女干部更容易因生育或家庭因素而退出工作,將那些替換或培訓成本高的職位分配給男干部,就成為領導者的理性選擇。例如,上級領導常常考慮出差、外派、社交應酬的“性別適合性”問題,隨之而來的“性別照顧”則成為其在重要崗位上人事任用的慣性思維。可見,組織內部差異化照顧的背后,是傳統兩性價值觀在新時期組織環境中的演化。這不僅加深了女干部對自身價值屬性的錯誤認知,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事業上升的可能性。
在現行的干部選拔任用相關制度中,難以找到顯性的性別歧視規定。在制度執行過程中,黨委和組織部門也不會認同存在性別歧視情況,但干部選拔任用不平等現象卻是真實存在的,特別是在關鍵領域的干部任用上。組織的嚴苛往往發生在女干部走上領導崗位之后,表現在女干部遭遇的標志化境遇上。女干部面臨的標志化境遇,主要表現在日常工作的可視性和社交行為的可視性。例如,一些男干部對女性領導的工作動態過度關注、吹毛求疵,以期獲得“女人當不了家”的佐證;對女性領導的社交行為不當評價、求全責備,從而捕捉其能力短板。組織內部差異化的評價標準,既可能強化女干部的作風建設,又容易致使其束手束腳、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