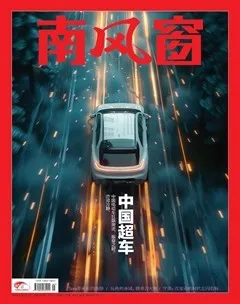超車!中國新能源
榮智慧

2023年底,一波中國新能源車“搶戲”。華為問界M9、極氪007、小米SU7先后面世。2024開年,小鵬MPV X9、吉利銀河E8、東風納米01、奇瑞風云A8紛紛登場。2月底,比亞迪“百萬級”純電超跑仰望U9開售。
目不暇給的新車,映襯的是中國汽車產業的輝煌:2023年,中國汽車出口522.1萬輛,同比增加57.4%,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汽車出口國。比亞迪累計銷售新能源汽車302.4萬輛,超越特斯拉,鎖定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冠軍。
這一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分別超過3000萬輛,全行業營收突破10萬億元,汽車產業已經成為中國工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自行車是進步的象征。到第14個五年計劃,包括電動載人汽車在內的“新三樣”出口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
從“自行車之國”到汽車產銷量世界第一,中國用了60年。從內燃機追隨者到新能源引領者,中國只用了30年。
而2023年的硝煙分外濃烈。優勝劣汰,物競天擇。3000萬輛的榮耀,背后是巨人、新王和過客的陰影。無論輸贏,中國新能源車“狂飆突進”的一年都值得銘記。
快慢車道的追逐
汽車出口量超過日本,比亞迪銷量超過特斯拉,成為2023年中國汽車駛進“快車道”的宏觀和微觀標志。
其中,新能源車“超車”引人注目:產銷兩旺,連續9年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突破900萬輛,同比增長均超30%,市場占有率達31.6%;銷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的六成以上。
“超車”勢必提速。2017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均不到80萬輛。2020年時,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只占全球四成。
“慢車道”上,“司機”各懷心思。
受德國、意大利施壓,歐盟暫時“放”內燃機“一馬”,允許2035年后銷售帶內燃機的汽車,條件是必須使用碳中和合成燃料。幾大老牌汽車強國松了一口氣。
2023年下半年,歐盟展開對中國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年底,法國發放電動車退稅補貼,不惜將最暢銷的三款汽車達契亞Spring、特斯拉Model 3和MG4排除在外,因為它們均在中國制造。
美國車企“三巨頭”通用、福特和斯泰蘭蒂斯,過去一年焦頭爛額。9月起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發起了長達46天、近5萬名工人參與的大罷工,帶來上百億美元損失。新達成的勞資合同約定,未來四年合同期限內為員工提供25%的加薪,將使三家車企的勞動力成本分別增加約62億、72億和64億美元。UAW勢頭正盛,工會主席費恩聲稱“我們能打敗任何人”。汽車業罷工潮呈蔓延之勢。
2023年底,《通脹削減法案》針對中國動力電池產業鏈的隱藏條款落地。根據指南,所有在中國注冊成立或中國政府持有其25%及以上股份的公司,都將被視為“外國敏感實體”,不得享受退稅補貼。
中國電池企業已經在想辦法繞開該規定。寧德時代通過技術授權的方式,為福特汽車代建美國電池工廠。國軒高科則直接在美投資建廠。上述出海項目是否涉嫌“違規”,有待進一步明確。
“超車”勢必提速。2017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均不到80萬輛。2020年時,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只占全球四成。“慢車道”上,“司機”各懷心思。
美國車企同樣受到波及。通用旗下幾乎所有電動汽車都將(暫時)失去補貼資格,不得不自行補貼消費者。
連續四年蟬聯全球第一大車企的日本豐田汽車,2023年經歷重大人事調整。社長豐田章男卸任,繼任者為豐田旗下豪華品牌雷克薩斯總裁佐藤恒治。豐田章男2009年出任社長,13年任期,經歷了電動汽車從萌芽到爆發的全過程。他個人不看好電動車,導致豐田汽車幾乎完全錯過“時代紅利”。
佐藤恒治上任后已提出“2026年前實現每年銷售150萬輛電動汽車”的全新電動化目標。然而,2024年1月,豐田章男公開表示“豐田要向沒有電的地方提供汽車”。前后矛盾的態度,透露出豐田發展戰略上的混亂。
2023年夏,中東財團大舉投資中國新能源整車企業,也投資了中國智能駕駛、出行服務和電池制造公司。儲能、駕駛、電子……中東資本幾乎覆蓋了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所有相關公司。
由越南首富潘日旺創辦的越南造車新勢力“VinFast”急轉直下。2023年8月納斯達克上市,市值最高時超過2000億美元,爬升到全球車企市值第三,僅次于特斯拉和豐田。
站上最高點的次日,VinFast股價狂泄千里,市值僅剩958.38億美元,近1000億美元灰飛煙滅。2023年VinFast在全球僅售出2.4萬輛新車,迄今為止尚未實現盈利。
在硅谷,Cruise的自動駕駛夢逐漸冷卻。
通用汽車旗下自動駕駛子公司Cruise,從大展拳腳到失去信任,只用了兩個月。2023年8月,Cruise的Robotaxi服務被允許在舊金山全天候運營。10月,發生拖拽行人致死事故,Cruise被暫停經營許可,9名高管遭解雇,3位創始人全部離職。
而攜帶FSD(full-self-drivingcomputer,全自動駕駛計算機)的特斯拉即將進入中國市場。背景是2023年11月發布的《關于開展智能網聯汽車準入和上路通行試點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更加完善的、關于智能汽車以及L3/ L4級自動駕駛的準入規則。
據馬斯克所言,特斯拉的FSD足以媲美OpenAI文本生成視頻應用Sora,其視覺方案原理幾乎一致。
中國新能源上高速
中國汽車2023年的主旋律是“降價”。
先是特斯拉降價,再是雪鐵龍降價。前者降價,尚沒有犧牲利潤。由于2023年碳酸鋰價格暴跌5/6,特斯拉毛利受到的影響不大。后者降價,則刺激不少燃油車走出“舒適區”,放棄坐守毛利的躺平心態。
至此,犧牲利潤、虧本銷售搶占市場份額、擠壓競爭對手的“價格戰”才真正開始。
純電動汽車領域,包含大眾、豐田、BBA(奔馳、寶馬、奧迪)等車企的純電動車型,極氪、智己等絕大多數品牌,都走向“七折”價位。
合資燃油汽車出現分化。一些企業放棄市場容量最大的8萬—15萬元區間,像福特直接放棄了福克斯,只想保住20萬元以上的市場份額;一些企業則努力守住“主流”地位,如大眾、豐田、日產和通用。
有能力的品牌則瞄準“插電式混動車型”。2023年底,新政策細化了該車型的技術要求,燃油車企不乏“翻身”希望。
價格戰背后,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從0到900萬輛的“大爆發”,產業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001年,“十五計劃”將電動汽車列入“863計劃”。“863計劃”起源于1986年3月四位科學家向中央報送的“關于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得到鄧小平批示。
2001年新能源汽車發展首次確定了“三縱三橫”的技術研發布局:三縱,指純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池汽車;三橫指電池及其管理系統、電機及其控制系統、多能源動力總成控制系統。這是當時世界上可以看到產業化前景的各種技術路線的總集成。
2009年,《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把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第一次提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同年,“十城千輛”試點啟動。
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苗圩,在最近出版的《換道賽車—新能源汽車的中國道路》一書中指出,該政策提出產業調整和振興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實施新能源汽車戰略。2010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決定》中,新能源汽車被列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
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發布,不僅進一步明確發展純電動汽車、插電式(含增程式)混合動力汽車和燃料電池汽車,也強調建設充電設施,為購買新能源汽車的消費者提供補貼,對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稅和減免車船稅。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從0到900萬輛的“大爆發”,產業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換道賽車》中,苗圩用“久久為功風雨路”描述了中國汽車工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頂層設計過程。
“限速”逐漸放開,機遇百年一遇,中國新能源汽車駛入高速路。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趕超戰略”,思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異曲同工。
出于能源安全的考慮,以及民族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發展戰略性產業的意志,中央政府通過增強資本要素稟賦、大力建設基礎設施、促進產業集群、補貼擴大市場規模、鼓勵產業競爭等外部手段,依靠頭部企業利用減少交易成本的“垂直整合”競爭策略,經20年努力,從大到強。
比較而言,同為東亞“卷王”的日本在汽車領域的傳統優勢,正遭遇多方位打擊。
2023年夏,豐田“亞洲龍”臻選上市,號稱有“五大撒手锏”—真皮方向盤、真皮擋把、真皮座椅、前排座椅電動可調、后排座椅6比4電動可倒,受到網友“群嘲”。
要知道,在中國15萬—30萬元的主流新能源車消費市場,技術更新速度極快。20萬元人民幣足可買到搭載高功率充電機、高倍率電池、高性能智能駕駛芯片以及輔助駕駛軟件,同時配備15英寸中控屏幕、連續語音識別、APP遠程控制系統、車內香氛裝置、后視鏡倒車自動下翻、32色氛圍燈、座椅加熱/通風/記憶以及無線充電等一大堆“報菜名”也報不過來功能的新款車型……亞洲龍“五大撒手锏”實在沒有任何吸引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高性價比的中國新能源汽車,即將走向“價格戰”新階段—像中國家電產業一樣,依托海外市場化解產能問題,邁入市場充分競爭階段。多年來形成的資源稟賦優勢產業,將打開更廣闊的市場。
產業政策疊加競爭優勢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高速發展,可以用產業政策和競爭優勢的疊加來解釋。
供應鏈能力、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集群、行業競爭和不斷迭代的產業政策,共同構成了新能源汽車發展要素。
中國制造業供應鏈相當成熟。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獲得長足發展,近年“賦能”制造業,二者為新能源汽車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在中美德日四個汽車大國中,美國有一流的信息產業,傳統制造業優勢已失;德日有一流的制造業,互聯網技術相對落后。中國的兩大產業均有足夠的資本和人力積累,由此具備獨特的競爭優勢。
信息產業風險高,顛覆性強,產品特征從功能性轉向智能化,資本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電動汽車的消費電子趨勢愈發突出,而燃油車是機械工業產品—前者需要更強大的風險投資。
2014年頒布的《指導意見》,引導一大批風險投資進入新能源汽車行業。其中既有獨立風險投資和私募資金,包括紅杉、高瓴、IDC等美國投資機構;也有企業風險投資,來自北汽、上汽、廣汽等整車大廠,以及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美團等互聯網巨頭。
中國地方政府引導基金經常與其他措施配套,為新能源汽車企業提供巨大優惠。2019年特斯拉入華,上海市臨港產業區憑借特殊機制和特殊政策,即實行“雙特”政策—包括雙定雙限房、土地彈性出讓等特殊政策以及政務服務的“臨港速度”,為項目引進和項目落地創造了條件。
2022年特斯拉公開的年度報表披露“連續3年獲得上海獎勵”,以及享受到15%的優惠稅收政策。
中國政府建設基礎設施時,充分利用了體制的協調作用。2015—2019年,政府先后發布涉及電動汽車充電樁接口及通信協議、充換電服務信息等一系列標準。國家電網還打造了智能充電平臺e平臺。目前,中國電動汽車充電樁數量在世界上處于絕對領先地位:中國公共充電樁保有量近230萬個,私人充電樁保有量近500萬個。據德國之聲統計,美國充電樁12.8萬個,荷蘭12.4萬個,法國8.4萬個,德國7.7萬個。
產業集群是中國企業應對全球化生產方式挑戰時,發展出來的特殊組織形態。相關產業在空間上集聚,不僅節省物流成本,降低人力資源成本,更提高信息搜集、交換的效率。
以江浙滬為中心的長三角,新能源汽車行業聚集了100多個年工業產值超過100億元的產業園區、數千家大企業。上海提供芯片、軟件,江蘇常州提供動力電池,浙江寧波提供一體化壓鑄機。長三角新能源整車廠可以在4小時車程內,解決所有配套零部件供應環節的問題。
廣東省以珠三角新能源整車基地為龍頭。省政府每年組織召開1到2次產業對接會,引導整車企業與零部件、材料企業合作,提升融合水平。工信部2022年認定的45個國家先進制造集群名單里,深圳占了4個,其中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智能裝備集群、先進電池材料集群均與電動汽車密切相關。
長三角新能源整車廠可以在4小時車程內,解決所有配套零部件供應環節的問題。
在企業自主競爭的同時,中國政府及時調整政策,打造有利于汽車企業發展競爭優勢的制度環境和結構條件,鼓勵企業深化競爭。
多樣化的政策工具行之有效。除了直接給車企和消費者“發錢”,政府在公交、出租車領域采購新能源汽車,較早幫助新能源汽車擴大消費市場。
雙積分政策自2018年執行,對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積分和新能源汽車積分進行管理。該政策同時促進能源節約和企業轉型。新能源汽車積分還可以買賣—很多車企賣分變現、提升利潤。
“綠牌”的發明獨具中國特色。“綠牌”新能源車不受城市規模限制,對一線城市消費者來說是巨大的誘惑。
隨著發展態勢變化,產業政策也在不斷迭代,促進產業高質量發展。
2023年12月11日,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關于調整減免車輛購置稅新能源汽車產品技術要求的公告》,明確了2024年后新能源汽車減免車輛購置稅政策適用的技術條件和執行要求,強調穩字當頭,技術創新,綠色節能,保障安全。
新政策中影響最大的,就是A00級和A0級代步純電車型的準入門檻全面提高。想要享受免除購置稅的優惠政策,入圍門檻從原先的純電續航100公里以上且電池包容量密度大于95瓦時每公斤,一步提升到純電續航200公里且電池包容量密度大于125瓦時每公斤。
像月銷量超過6萬臺的A00級汽車,如五菱miniev、長安lumin糯玉米、吉利熊貓、奇瑞QQ冰淇淋;以及A0級的零跑T03、五菱繽果,都需要改動。
也就是說,市面上最便宜的新能源車也得提升產品質量和性能:更好,更快,更強。
“迪王”及它的意義
比亞迪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佼佼者:占據中國四成以上市場份額,2026年將占一半以上。2023年,全球銷量前10名的電動汽車,比亞迪占據五席。它擁有或申請專利技術近3萬項,位居中國第一。
從比亞迪到“迪王”,中國新能源汽車“王者”的垂直整合發展戰略,從產業鏈的意義上看,令人聯想和反思支撐全球生產方式30多年的“豐田模式”。
風水輪流轉。美國福特汽車最早采用垂直整合模式,不僅生產所有零部件,還進入橡膠、煤礦和運輸行業。20世紀80年代,豐田依靠外部零部件供應商,打造全球價值鏈理論,從而將“外包”模式發揚光大。
如今,比亞迪“回歸”福特模式,自制大量成本占比高的零部件,包括電池、電機、汽車電子、模具、功率半導體、內外飾等。有人說“比亞迪加上福耀玻璃、中策橡膠輪胎和寶鋼鋼板,就等于完整產業鏈”。
比亞迪采取垂直整合戰略有其先天優勢:電池成本占電動汽車整車成本四成以上。2003年進入電動汽車領域前,它已經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手機電池生產商,曾占據23%的全球市場。
而外包往往導致“大而不賺”。典型的例子是計算機行業,龍頭企業體量大,規模約5000億元人民幣;寡頭壟斷,聯想、戴爾、惠普三家公司占全球市場份額六成;但沒法獲得最大價值,利潤很低。利潤高的,反而是上游供應商,比如英特爾、英偉達、微軟。手機行業也是如此,蘋果除外。
中國出口“新三樣”之一的太陽能電池,也遭遇“大而不賺”。光伏屬于重資產投資行業,上下游都對分工缺乏信任,導致整個產業幾乎不分“上下游”,彼此全是競爭對手。整個產業抵御經濟周期的能力也大大降低。
特斯拉“超級工廠”最先模仿福特百年前“胭脂河工廠”盛況。鋰礦、石墨、鎳、鈷……特斯拉全部自行采購,無需中間商。強勢如奔馳,在整個供應鏈上跟零部件的價值占比也只有三七開,但特斯拉做到了“對半分”。
同樣,比亞迪也打造了“采礦、選礦、基礎鋰電池原料生產、儲能、動力電池生產、零部件生產、模具生產”等縱向一條龍布局,超過特斯拉成為全球電動車“銷冠”。
此外,從遠期看,比亞迪的意義可以分解成兩層—一是電的應用,能源的管理;二是車的制造,汽車與電動汽車的未來。
在第一層意義上,中國出口“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太陽能電池、鋰電池,本質上都是“電能”的轉換和使用,這不僅意味著其制造業技術的創新、生產率的提升、出口外匯的增加、高端服務業的良好前景,更象征著信息時代進步的根基、成功的趕超。
未來,如何利用新能源汽車尤其是電動汽車,作為清潔能源電力體系的一部分,從而整體建設智能、節能的能源網絡,是一大重要趨勢。
在第二層意義上,首先,打破專業化分工、內化供應鏈的垂直整合戰略,一方面確實增大收益,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費。這一點蘋果值得學習:產品并非完全自行制造,而是打造強大的供應鏈整合水平,精準把控一切外部工廠的產能和能力。
即使世界已經被大大小小的“法案”和“調查”隔閡,“普惠”國內廣大鄉村和海外消費者,依然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目標。
其次,電動汽車的未來并非“一帆風順”,原因有四點。
第一,純電動汽車發展,受政策驅動和市場需求影響。“政策小年”可能遭遇一些困難。而且,中國燃油車“超英趕美”一直有難度,但市場依然龐大,壓制或放棄燃油車發展不符合中國汽車工業的核心利益。
第二,國際同行的“酸葡萄”言論漸增。2023年,本田、豐田高層均吐槽中國純電動汽車是“工業垃圾”,日系車企都把中國市場產品設計權限下放到合資公司,不外乎“你們自己去搞”之意。德國奧迪表示要“推遲純電汽車發展節奏”,重新大力發展燃油車。
一旦海外市場出現“逆流”,中國純電動汽車出海會面臨阻力—相比燃油和混動車型,純電出口量本來極小,而虧損率一直極高。
第三,全球資本對純電動汽車興趣減弱。除了中東財團“財務投資”,斯泰蘭蒂斯投資零跑,而零跑2023年以來大力推動插混路線;大眾投資小鵬,大眾是急需現金流的小鵬“技術變現”的支點。兩筆投資的輻射價值大于投資本身。
第四,純電汽車定價中,硬件依賴度會降低。隨著軟件和服務的競爭升級,各家車企將迎來新一輪洗牌。
1981年IBM電腦售價1600美元,折合成今天的售價約5000美元。40年后,一臺個人電腦大約1000美元。新能源汽車同樣遵循“學習曲線”:產量每翻一番,價格下降20%。1200美元/千瓦時的電池,10年內降至120美元/千瓦時,20年內降至12美元/千瓦時。
目前的成本和資本,不允許純電汽車在合理的價位上售賣。但三電系統特性如此,硬件價格遲早要下降,車用軟件的價值將進一步上升。
同為“消費電子產品”,新能源汽車行業應向手機產業看齊。如果不是中國物美價廉的手機,非洲有一半以上的用戶都沒法接觸“移動互聯網”。
即使世界已經被大大小小的“法案”和“調查”隔閡,“普惠”國內廣大鄉村和海外消費者,依然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