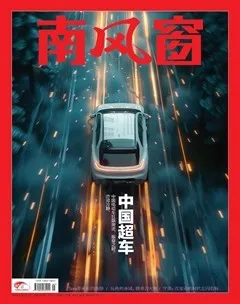宏觀政策,繼續向前
譚保羅

2月7日,按照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2193億美元。該數據較2023年12月末下降了187億美元,降幅為0.58%。
近年來,我國的外匯儲備一直穩定在超過3萬億的水平。從外匯儲備的產生機制來看,它很大程度不過是企業出口或外商投資,在結匯之后的產物,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個國家及其國民在某一時間點的財富存量水平。
但是,穩定和可觀的外匯儲備意義也十分重大。正如它的產生機制所體現的那樣,它背后是制造業企業出口創匯的能力,是外商投資的熱情,因此,也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質量和實體經濟活動活躍度的重要參考指標。
外匯儲備只是經濟的參考數據之一。2023年,我國GDP達到126.0582萬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5.2%。2024年,要繼續保持這樣的增速,未來還有一些困難和挑戰需要克服。
要繼續推動高質量經濟發展,除了調動市場主體的自發行為之外,宏觀政策的積極實施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資金效率
2024年春節前夕,證監會主要負責人的人事變動,無疑是市場最大的關注點。吳清接替易會滿,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近段時間,資本市場的一些變化值得關注。以2023年為例,資本市場已經查處了不少大案,其中,財務造假是最主要的違法行為。執法部門對財務造假的處罰力度,和過去一些時間段相比,明顯變高。
在過去某些時候,資本市場最被投資者質疑的問題之一的是,有企業通過財務造假,讓背后的大股東和實控人賺取巨額財富,但被查處之后的處罰力度卻并不高。一些投資者甚至打趣說,“賺了幾十億,被罰幾十萬”。無論這種說法是否夸張,它的確反映了資本市場一些結構性問題的根源。
如果做一個梳理,很容易發現,2023年的資本市場的很多違法案例中,處罰力度都以千萬起步,還有一些上億的處罰。對造假者的刑事處罰也時常見諸報端。顯而易見,對違法獲取巨額財富的大股東來說,刑事處罰的力量,勢必遠遠大于經濟價值上的暫時失去。失去自由,是對“不差錢”的違法者最具震懾力的處罰。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液。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市場主體的融資來實現,除了從資本市場的融資,從銀行的融資同樣重要。在中國,企業的融資總量中,從銀行融資的占比一直都高于從資本市場的融資。
發改部門的項目審批,金融監管部門的信貸政策傾斜上,趨勢都十分明顯,即要降低低效投資的擠出效應,提升好企業和好項目的融資可得性。
在銀行融資中,過去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一些效率低的項目對優質的企業形成了巨大的擠出效應。大量的銀行貸款進入“鐵公基”,而其中不少基建項目效率低下,資金回收都成問題,只能依靠銀行貸款不斷展期來應對。然而,由于其擁有地方政府的顯性或隱性信用背書,貸款并不難。形成對比的是,一些優質的制造業企業,卻很容易出現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
事情正在變化。從2023年開始,一些過去看起來必須上馬的“鐵公基”已經被叫停。地鐵大潮的退卻是最典型的代表,包括一線城市在內,一些收益前景不樂觀的地鐵項目并未獲得有關部門的許可。
地鐵項目是“鐵公基”中首屈一指的吞金獸。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地鐵建設平均每公里造價約為9.5億元,根據地理條件,造價高的超過10億,最低的也不低于5億。除了建設,地鐵的運營費用也是個大問題。即便不考慮前期的建設費用,一些地鐵項目即便要拿收入覆蓋運營費用都成問題。因此,一些地鐵項目是不折不扣的長期吞金獸。
高鐵的建設速度也慢了下來。高鐵建設的單位成本比地鐵低,平均在每公里1億人民幣左右,但高鐵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長。過去,一些“縣城通高鐵”“一座縣城三個站”的現象,本質上就是對資金的巨大浪費。
現在,市場上針對“無效基建”進行了討論。實際上,近來提升基建的效率,叫停“低效基建”“無效基建”,提升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加強對實體經濟的融資,已經成為了各方面的共識。在宏觀政策領域,比如發改部門的項目審批,金融監管部門的信貸政策傾斜上,趨勢都十分明顯,即要降低低效投資的擠出效應,提升好企業和好項目的融資可得性。
節省的資金,很多都進入了實體經濟領域,支持優秀企業的發展。按照金融監管部門的數據,截至2023年末,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貸款余額同比增長20.2%,其中,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占比均超過四成;制造業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7.1%,其中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29.1%。
民企的融資問題,需要長期持續的關注。金融體系要做的,是讓更多優秀實體民企,以合理的價格去獲得融資。無論是資本市場的股權,還是信貸市場的債務融資,它們都可以為企業發展和轉型提供急需的“血液”。因此,在宏觀政策中,資金的配置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核心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
財富視角
當然,另一個必須關注的維度是,金融體系除了融資功能之外,也承擔著財富管理的功能。維護普通儲戶和投資者的利益,同樣十分重要。在某種意義上講,維護普通人的利益,使普通人的財富能夠通過金融體系實現有效配置和保值增值,更是金融體系實現長期穩定的基礎。
在資本市場,這一規律表現得尤為明顯。當市場的投資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投資者可以獲得可觀收益的時候,市場的融資功能也能得到發揮,企業也可以從中獲得自己所需的資金。反過來,如果在某一時間段,片面和過度地強調融資功能,市場投資功能卻被忽視,那么市場就會產生相當大的波動。
資本市場的事情不用多說。中國老百姓的財富多數都配置在房子之中,按照不同的數據,這一占比都在六成以上。實際上,這個問題或許都不用看統計數據,城鎮居民持有的物業多數都有相對明確的市場定價,普通人自己進行實地調研,就基本上可以判斷,不動產在居民資產總盤子的占比的確有點高。
因此,樓市穩定對普通中國人的利益十分重要,必然是一些宏觀政策不可忽視的參考因素。當前,樓市可以分為三個“圈層”,分別對應著未購房者、已購尚未獲交房者,以及已拿到所購房者。
對未購房者來說,樓市的穩定或者說在價格上出現一定的結構性和階段性下調,對這部分人群最有利。2016年之前,主要城市的房價出現了大幅上漲,之后趨于穩定,但目前來看,大中城市房價相對于普通人的工資收入來說,依然不菲。因此,這一部分未購房的人在總體人群中占有相當的比重。
第二部分人群則是近期樓市各項政策的關注焦點。在這里,“保交樓”是一個基本底線。
2024年1月下旬,金融監管總局召開會議,部署推動落實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相關工作。會議強調,對開發建設暫時遇到困難但資金基本能平衡的項目,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通過存量貸款展期、調整還款安排、新增貸款等方式予以支持。
可以看出,這一表述十分具體,操作性高,充分說明了有關部門對措施必須落實的重視。此外,還有來自金融監管部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高達3500億元的“保交樓”專項借款,絕大部分都已投放到有關項目之中。可見,“保交樓”是樓市調控和金融政策的重中之重。
樓市巨大的存量按揭貸款,意味著對內需的削弱,對提振有效需求并不利。因此,適度降息,降低按揭人群的利息支出成本,是有必要的。
第三個人群是已有的住房擁有者。其中,一部分在房價走高階段購入,然后房產價格卻出現轉折,進入下跌通道。對這個部分人群,市場俗稱“高位站崗”。其實,這樣的稱呼有些冰冷。對普通人來說,購房款多半用掉了“六個錢包”中的大部分存量資金,是家庭資產的最大宗。即使是自住,如果房價過度下跌,也意味著資產的貶值,給家庭的財務前景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更重要的是,不少人背負著不菲的月供。從小處說,月供嚴重侵蝕著家庭的現金流,降低生活質量。從大處講,樓市巨大的存量按揭貸款,意味著對內需的削弱,對提振有效需求并不利。因此,適度降息,降低按揭人群的利息支出成本,是有必要的。
2月5日,央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向市場提供長期流動性1萬億元。有分析認為,2024年將可能存在一個長期的降息周期。無論是通過降準釋放流動性,還是指向寬松的公開市場操作,或者直接降息,無一例外,都可能讓社會的整體利率走低。對那些選擇了浮動利率的購房者來說,每月利息支出就會出現下降。雖然金額和支出相比,可能不太多,但對信心至關重要。
信心,在哪里都很珍貴。比如,在一些西方國家,凱恩斯經濟學最擔心的問題是“推繩子效應”。
在經濟過熱的時候,用緊縮的宏觀政策很容易把經濟的“溫度”降下來,這是“拉繩子”,從物理上來說,很容易辦到。但經濟偏冷的時候,用擴張的宏觀政策去刺激經濟卻很難,猶如“推繩子”。沒有人推得動柔軟的繩子,這是客觀的物理規律。一些西方國家在調控經濟的時候,之所以存在著“推繩子”難題,便在于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的信心問題,企業不愿意擴大再生產,而個人不愿意擴大消費,經濟就放緩了。
當下,從本質上講,宏觀經濟政策的最終重要指向同樣包括了信心問題。擠出低效投資、鼓勵優質企業融資,調動的是企業的信心。而關注股市、穩定樓市,指向的則是投資者和消費者個體的信心。
信心,一直都是宏觀政策的重要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