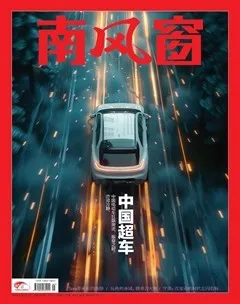美國效仿中國之后
人們普遍認(rèn)為,美中關(guān)系緊張是兩國之間巨大差異的不可避免結(jié)果—美國擁有一個(gè)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而中國政府則牢牢把握著經(jīng)濟(jì)的船舵。其實(shí),許多美中沖突都源自兩國日益增長的共同之處。尤其是,美國的相對衰落使其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促使其采取各類新經(jīng)濟(jì)和國家安全政策。隨著美國效仿那些對中國頗有助益的戰(zhàn)略,雙邊關(guān)系中的矛盾也成倍增加。
中國的驚人經(jīng)濟(jì)增長最終為世界經(jīng)濟(jì)帶來了巨大好處,因?yàn)樗鼮槠渌麌业钠髽I(yè)和投資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巨大的市場。此外,中國的綠色產(chǎn)業(yè)政策拉低了太陽能和風(fēng)能的價(jià)格,為全球低碳轉(zhuǎn)型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
其他國家自然也會對中國的干預(yù)主義和重商主義做法有所抱怨,但只要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的政策是由消費(fèi)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邏輯驅(qū)動,這些影響就不會給對華關(guān)系造成巨大壓力。
相反,許多知識界和政策精英認(rèn)為,西方和中國的經(jīng)濟(jì)操作是互補(bǔ)和相互支撐的。歷史學(xué)家尼爾·弗格森和莫里茨·舒拉利克創(chuàng)造了“中美國”一詞,來描述這種表面上的共生關(guān)系:中國補(bǔ)貼其工業(yè),而西方則樂于消費(fèi)中國提供的廉價(jià)商品。由于這種觀念在西方盛行,失利的工人和社區(qū)得不到什么幫助或同情;他們被告知,要重新接受培訓(xùn)并搬到就業(yè)機(jī)會更多的地方去。
但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xù)的,好工作的消失、地區(qū)差距的擴(kuò)大以及重要戰(zhàn)略產(chǎn)業(yè)對外依賴性的增加所帶來的問題,已變得不容忽視。美國政策制定者開始更加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的生產(chǎn)方面,而新戰(zhàn)略所圍繞的產(chǎn)業(yè)政策,與中國長期以來實(shí)行的那些并無太大區(qū)別:新技術(shù)和先進(jìn)制造活動得到補(bǔ)貼,可再生技術(shù)和清潔工業(yè)也不例外;本地供應(yīng)商和國產(chǎn)零部件受到鼓勵(lì),而外國生產(chǎn)商則無法獲得同樣的優(yōu)惠。
根據(jù)“小院高墻”理論,美國試圖限制外國獲得那些被認(rèn)為對國家安全至關(guān)重要的技術(shù)。倘若這些政策能使美國社會更加繁榮、團(tuán)結(jié)和安全,那么世界其他國家也將從中受益—正如中國的產(chǎn)業(yè)政策通過擴(kuò)大本國市場和降低可再生能源價(jià)格使其貿(mào)易伙伴受益一樣。因此,這些新政策和新優(yōu)先事項(xiàng)并不意味著美中沖突必須加深,但它們確實(shí)需要一套新的規(guī)則來管理兩國關(guān)系。
良好的第一步是雙方都卸下面具,承認(rèn)各自做法的相似性:中國在敞開的窗戶上裝上了紗窗,而美國則在小院四周圍上了高高的籬笆。
第二個(gè)重要步驟是,提高政策目標(biāo)的透明度并加強(qiáng)溝通。在一個(gè)相互依存的全球經(jīng)濟(jì)中,許多針對國家經(jīng)濟(jì)福祉以及國內(nèi)社會和環(huán)境優(yōu)先事項(xiàng)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會對其他國家產(chǎn)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貿(mào)易伙伴們需要在各國采取產(chǎn)業(yè)政策來解決重要市場失靈問題時(shí),給予寬容和理解,并將此類措施與那些明顯以鄰為壑的措施(也就是這些措施在本國產(chǎn)生利益的原因恰恰是因?yàn)閾p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區(qū)分開來。
第三,必須確保那些限制性國家安全政策是目標(biāo)明確的。美國將其出口管制定義為針對 “一小部分”引發(fā)“直接”國家安全關(guān)切的先進(jìn)技術(shù)的“精心定制”措施。這些自我標(biāo)榜的限制措施無可厚非,但對半導(dǎo)體的實(shí)際政策是否符合這一描述,以及其他措施可能是什么樣子,還存在疑問。此外,美國經(jīng)常會用過于寬泛的術(shù)語來定義其國家安全。
美國將繼續(xù)把經(jīng)濟(jì)、社會、環(huán)境和國家安全放在首位,而中國也不會放棄其國家主導(dǎo)型經(jīng)濟(jì)模式。合作難以成為當(dāng)今中美關(guān)系的主流,但如果兩國都認(rèn)識到自身政策既不會有太大差異,也不一定會給對方造成傷害,那么合作可能會變得容易一些。
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學(xué)肯尼迪政府學(xué)院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授、國際經(jīng)濟(jì)學(xué)會主席,著有《貿(mào)易直言:對健全世界經(jīng)濟(jì)的思考》。本文已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