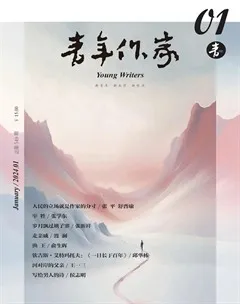走親戚
我們忽視了昂貴的高麗參,漠視了整齊排列的柏樹,在洼地中,我們發現了盛開著的一朵朵藍色的風信子,它們代表著新婚,根系橫貫彭塔內拉山和艾崗山,是由當地的一位獵戶移植過來的。獵人扎拉豐住在塔樓里,是個很有情調的男人,長相英俊但牙齒毛糙,他羞于絕望,但從不沉溺,他對挫折抱有一份靦腆的忍耐,他不過分審視命運,對他人的命途亦漠不關心。他認為,挫折降臨,便是困難對他犯淫了,貧窮寵壞了他,它欲與他成為一體。他獨愛孤獨,只對厄運敞開心扉。這些年,他在女人的愛與肥胖中越陷越深,在一輛車里他差點被自己的妻子燒死,這挫敗了他良善的品德,打那之后,他就開始和人吵架,他就喝酒,他就痛到吃一顆糖丸,想一想,就痛到吃一顆糖丸。唯一的安慰是他那埋在心間的,懶惰、拒絕、憂郁和酸澀的初戀。他向我們談起一個女人。曾幾何時,他總把身體洗得干干凈凈,像駿馬一樣追隨著她。
那年,扎拉豐還是個率真俊俏的男童,他成績最好,不懂庸俗,他謹慎、平和,夢想著做一個開朗的富人。當母親生下他,看到他,就只說了一句話:“你這個壞蛋出生了。”在別人面前做榜樣是件好事,但卻讓他睡不好覺。前些天吃的韭菜,也讓他的舌頭漲得通紅。他跟著爸爸去探親。他們去見陳嬤嬤。她是個八十二歲的大商人,傳聞她是個陳舊的人,這樣的陳舊也是一種福氣嗎?扎拉豐和爸爸扛著行李從鄉間大巴上下來,氣喘吁吁,灰頭土臉,他們都覺得熱得厲害。廢墟已成,天氣漸暖,痢疾已遠去,牛群在鍍金的道路上爬行。這幾天過節,每個人的手都油膩膩的。他們走了一段路到了市場。爸爸從外套里拿出護照,里面夾著現金,他給自己買了抗生素和燒餅,還給兒子買了一塊新烤的培根。爸爸因膿腫切除了一半肝臟,他曾為此感到傷心,不過他現在也試著愛它留下來的空間。扎拉豐周圍盡是些躲躲閃閃的面孔,草坪上來了一群寫生的學生,她們在清晨作畫,他好奇地看著她們紫紅色的皮膚。一群孩子爬上塔頂,大喊新年快樂。他們的耕作被種植和采摘,他們的游牧被飼育和屠宰,但陳嬤嬤和植物一樣富有,在她的宮殿里一切都平淡而威嚴,中堂內外擺滿了食物,每條街上都有草坪,已被豐沛的雨水灌滿。她度過了輝煌的一年,她切割出一條發臭的河流,一頭牛當作三頭賣,所有的收成都落在了她的頭上。在這條路上,扎拉豐沒有休息,他有了自己的想法。
歡迎光臨。有人來接他們,她走出來,是陳嬤嬤的女傭,她充滿愛意,她有點瘦。他們一眼就看到了她。他們順著宅子東邊走,女傭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她和扎拉豐一般大,她不假思索地提出要求,滔滔不絕,他卻無言以對。她覺得他有點霸道,要讓他吃點苦頭。“城里的小蒼蠅。”她說。扎拉豐感覺舌頭發麻,捂住了自己的手。“著急什么?為什么這么著急?”她抱怨,但還是匆忙穿過那些密集的走廊,她把路看得清清楚楚,只抬著下巴走,不在乎地上有什么。這挺讓人開心的,而且他根本沒辦法制止這種快樂。
這里,一切都像電影一樣變幻著,數字跳動,陽光明媚,墻壁吱吱作響,仿佛剝落著,追隨著記憶。他們抵達陳嬤嬤的居所,里面彌漫著令人陶醉的香氣,處處點綴著華美的裝飾品。陳嬤嬤靠在一張躺椅上,身前點著香爐,扎拉豐第一次目睹她的面龐,感覺她老去的容顏可憎而丑陋。爸爸示意他過去,他便邁出步伐,臉貼著地面。陳嬤嬤伸手拉他起來,親了他臉頰兩側,“你幾歲?”她問。
“誰知道。”扎拉豐說。他盯著她蒼老的手上的亮閃閃的首飾。上面刻著一段字:美麗的心永不凋謝。她好黑,他想,她的嘴唇也是黑色的,她的頭發也又厚又黑。她冒著香噴噴的熱氣,她比一般的老人要胖。
她便回頭問他爸:“你怎么帶著他?”
“他最好。”爸爸回答。
“趁你翅膀還在,我好好招待你,好嗎?”她說。
“啊,奶奶,什么翅膀?”扎拉豐問。沒人回答他。那個領著他們進來的女傭正在切果盤里的香葡,并用銀鑷子挑出里面的葡萄籽。
“你想媽媽了嗎?兒子,沒有什么能溫暖你。”陳嬤嬤看向父親說。
“我不是你兒子,我是來干活的,老板。”爸爸說。
“那你為什么帶著兒子來?你帶著他來,你就是我兒子。”
“我只是帶著他來。”
“儲藏母乳的好地方是哪里?你覺得是嬰兒還是奶子?”
“我只干活兒,不問別的。”父親固執地說。
“你奶奶死了,你就沒地方去了,我媽媽就把你抱走!讓你睡在炕下面,還不給你飯吃,”她惡狠狠地說,“哎唷,你跟在城里女人的屁股后頭。據說這也是所有師徒革命的開始。兒子,你怎么去城里了,你像牛一樣壯,但是人家給你圈起來了。你得留在這兒為我種地。其實你想當我兒子,所以才把他帶來。”
她一邊罵著,一邊低頭吻扎拉豐,吻這個英俊的小男孩。他把頭枕在她的胸脯上,枕在絲綢和珠寶上。臥在這肥大的女人身上,扎拉豐饑渴難耐。
“我來干活兒的,老板。我可聽不懂你在說什么。”爸爸坐得遠遠的。
“為什么這么說,我活該一輩子沒人陪著是嗎?”她仿佛不屑一顧,甚至不愿為他沏一杯茶。她總是讓他獨自守在窗前,也不怎么和他說話。其實她看他可愛,恨不得把他放到嘴里含著,這個兒子是最忠誠的。她讓他打起精神來,屋子里所有人都在問他問題,所有人都在關注他。因為他是一臺抹了油的機器。
“我陪著你,奶奶。”扎拉豐悄聲說。
“你真是膽大包天,”她低頭看著扎拉豐,感慨萬千地說,“但愿你不會走上你母親那條不歸路。”
屋里頭的人隨意插嘴道:“是呀,我可不怕她。她這樣的人——總覺得全世界都在圖謀害她。她總是懷疑別人,懷疑別人想害她,疑神疑鬼的。您別以為我在瞎說,租賃的那位老教授也是這樣的人,別人稍微咳嗽一聲,他就覺得這是對他的陷害呢!我對這種人了如指掌。”
“他們自我陶醉著——卻缺乏同情心。”
“有一次,他在哭泣,而她也跟著一起哭,”女傭說,“其實那是裝模作樣,那幫人,只會為自己流淚,不懂為他人流淚。如果別人哭了,他們反而感到快樂。誰曉得她折磨過多少人?”
“聽起來是一群小人,必須讓別人對他們刮目相看。”
“他也是那樣的嗎?”
“這是咱們這兒的小福星——他可是扎拉豐小將軍,他和他媽媽不一樣,他要留下來陪我。我要給他一塊地。”陳嬤嬤大笑著說。
“我們不閑聊了。”這時候爸爸開口道。他讓扎拉豐過來,但是他沒走。陳嬤嬤就又把他抱在了懷里。
“別急,為什么不聊聊天?”
“因為我來這兒不是為了聊天的。”爸爸說。
“你在城里待久了,你把城里的形式主義帶來了,兒子。我們這兒不流行那東西。形式只是靈魂的追隨者。你以為你公事公辦,其實你想讓自己變得天真,因為那天真的模樣,是多少人心所向的。”
“我沒工夫考慮這些。”
“這沒什么問題,人們都渴望擁有天真,是擁有,而不是成為天真。誰都可以擁有它,卻無法成為它,就像你老婆,就像他媽媽。”
“你別罵我。”
“誰罵你?你以為你一點毛病沒有嗎?哎,我們一家都是神秘的神話,別期望擁有天真。你想一想,兒子,究竟誰為寂靜的世界增添了灰燼?——死人。活死人。火死人。我們都被一把火燒死了。”
“我還沒死呢。”父親把牙咬得死死的。
“你當然沒死,因為你想找個人投靠。去吧去吧,別再來我這兒。但在你走之前,把事情辦好,我叫你來是因為這件事只有像你這樣的閑人才能做到。我們得時刻盯著自己的口袋和后背,根本來不及看顧全局。”陳嬤嬤不耐煩地揮了揮手。她抓起扎拉豐的小手指,刷了刷自己的金牙。
又看著他說:“揉揉我,我累了。”
扎拉豐跪下來,又盤起雙腿,揉著她的腳。她為什么讓他揉腳?她的腳黑得像是炭,滑得像是泥鰍。扎拉豐心服口服嗎?他認為這似乎是一個“天真”的調情嗎?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或者不是調情,而只是搓磨。他想不明白,或許他來這里只是為了經歷一場慘敗。調情或是搓磨,這是多么古典的抉擇。他言聽計從,像他爸爸一樣,他們都被激情和欲望綁在自己的心上。她說她累了,也許她不累,他透過一雙腳直達心靈的窗戶,他可以感知她,洞察到她的眼神、動人的笑容;如果感情濃烈,甚至能隱約聽到她心跳的聲音。扎拉豐多么在乎她那閉耳不聞的寬恕之心。她的心不對稱,她每次只說兩句不一樣的話。她是個聰明的買賣人。她還說,為什么人都在賣力地演出?明明靈感可以讓你輕易做出抉擇。如果你想活命,就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你想怎么處置我的孩子。這里面一定有一個真相。
“把他留下來。你帶來了就不能帶走。他還在吃奶嗎?”陳嬤嬤動著腳趾說。
“他媽媽想他。”爸爸說。
“那就賣給我,把錢給你老婆。”
“你在說什么糊涂話?”爸爸問。
陳嬤嬤就把扎拉豐拉起來,讓他坐在她身旁。“我命中注定要和你一起見到你。”她說。
“你能為我倒杯水嗎?”父親問女傭。
“別使喚她。”女傭想站起來,但是陳嬤嬤不讓。
“我就是想喝一杯水,在你這兒干活兒連一杯水也沒有嗎?”
“沒人愛你。沒人會愛上別人,我們的祖先怎會相愛?你為什么使喚我這個老人家?你踩著我的身體走到這里,別忘了我向上的恩情。你別喝水了,你干完活就走。”
“你要我干什么?”爸爸站了起來,上前把扎拉豐拉了過來。
“我們做著非常小的生意。但總有意外。她的小兒子被一頭麋鹿頂死了。你去打死那頭鹿。”她說。
“我怎么知道是哪頭?”爸爸問。
“角上有血的。”陳嬤嬤說。
“好。”父親帶著他離開,沒人來送他們,女傭去睡覺了。
“爸爸,鹿真的能頂死人嗎?”扎拉豐問。
“別問。”
“那我們打死了那頭鹿,要拿來吃嗎?”他問。
他們走過一條又一條街道,來到一家旅店下面,父親摸索著自己的槍,進了電話亭給人打電話,不知在聊些什么。“難道要我白白受苦?九月份開始,我只為自己干活,從這之后,別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他說。父親掛了電話。他們在旅店睡了一晚。從旅店里醒來,肚子空空,來到浴室,鏡子里冷冰冰的,叫人毛骨悚然。賬單夾在餐單里,服務員的名字在肉菜的行間,看起來像一張臉,他扎根菲律賓。飯后,扎拉豐又見父親去打電話,這次應該是打給媽媽的,“我怕我熬不過去。”他紅著眼睛說,很快掛斷了電話。還有一段插曲,昨天半夜,陳嬤嬤來電至旅店,問扎拉豐要不要一直住在她這里。爸爸拒絕了,還對他說:“我們要清清白白做人,孩子。”但是陳嬤嬤不在乎,她叫扎拉豐自己做決定。
今天中午,他們準備獵殺那頭角上帶血的鹿。扎拉豐以為獵物在林中,然而父親卻帶著他返回到了陳嬤嬤的寓所。依舊是那位瘦瘦的女傭引領他們進入,依舊是昨日的那棟房子。但與昨天不同,房間里擠滿了人。這些人心寬體胖,品德高尚,開始輪流上前咬陳嬤嬤的腳背,然后坐下來陳述觀點。扎拉豐和他的父親坐在門口,他看到一個氣派非凡的男人站了起來。他穿著乳白色的菠蘿纖維短袖襯衫,上面繡著精致的圖案,下身是酒紅、翠綠和橙色的印花褲,腳上一雙皮革拖鞋,他脫下的運動服搭在椅背上。禿頭,大耳朵,沒有鼻子。胳膊上的金銀首飾深深鑲嵌在肌肉里,他開口唱道:
“尊敬的母親,需向您提起,最大的問題是單一作物,它們一模一樣,而霉菌很快就來。它們與世界融為一體,與那些孱弱的單一作物融為一體,為所欲為——我見過。原本還可以分五個小麥區,現在只有三個了,最終的結果是每個人都沒有東西吃。我敢于打擾您,因為那些太過冷漠的人太過抽象——我明白您不是那樣的人。這有多微妙,對吧?只要玉米和土豆養得起自己,只要玉米和土豆自食其力,只要玉米和土豆可以償命,我們的大部分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誠然,玉米和土豆的確養得起自己,也能自食其力,但它們無法償命。因為人們認為它們不如人值錢。但這不是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只要大家都蠢蠢欲動,玉米和土豆的價值就上來了——那么玉米和土豆就可以償命。只要人躁動起來,玉米和土豆的葉子就永遠是鮮嫩的,那么,腐爛也無從談起了。我們上哪兒去找那么多人?這同樣無需您操心,因為舞臺上沒有人缺席,人們從不會期待人的缺席,因為到處都是人啊,哪里都是人,上面是人,下面也是人。要讓人動起來,這需要有才華的人才能做到,因為他們可以想象:自己好像聞到了霉味,多年以后搶了一些發霉的麥粒,突然覺得霉味透露出一些道理——這就是聯想能力。就工匠和藝術家而言,他們必須看到真實的人是多么愛他們——他們必須為此感到煩惱,就像他們突然意識到某處有水,卻為自己沒有游泳經驗而感到煩惱一樣。我們需要依靠他們。當然,統一派不愛他們是對的,兩個道理不要混淆。人應該有自尊嗎?他們越是有自尊,就越不滿足于虛假的崇高和特權之美。我們不能挖苦他們,這個世界上有更微妙、更嚴格的人,他們不是最可靠的人,但意義和美是隨他們的興趣而定的。因此,您將他們全都埋進土里得不償失。說什么該法取決于氣候……豐富是沒有止境的——都是胡說八道。您不怕遭受報應,我也不怕被別人騙。謝謝你給我三天假。
“昨天,我躺在床上時,我發現我們只是在睡覺。我們被它的根所驅使著往下走,走進墓地的深處。它是在思想的深處扎下根來的。以您的自由為例,您認為您會因為您在睡覺而感到不安嗎?白天失眠率低,是因為大家都在晚上睡覺。如果您要我想象一下同情心,我當然做不到,可您要是叫我吐出幾個罵人的詞,我一定照辦。我罵了他,所以他睡了。我給那個可憐漢——你的小兒子,講了一點黃色笑話,還給他倒了一點鹽,希望神救他,反正您是救不了他了。他已經好幾天沒有離開家了,或許離開了,不管他在哪里……他們只燒毀了麥田的一側,但剩下的能喂飽他們所謂的英雄,他們說鮮血會使草長得更高更密,我感謝他們的芬芳,要知道他們是怎么來的,我們得先確認地球上的鹽是怎么來的。這群人中沒有人愿意多挖一個洞,所以他們流血更多,看起來更臟。我們的人現在到處都是,如果一堵墻太薄,就會塌,希望您注意到這一點。現在那些地是我的了,還有那些羊,或者土豆或者玉米。祝您健康。雖然他死了,但也祝您快樂。”
陳嬤嬤一直盯著他,她取出了自己的假牙交給女傭,又戴上了一副新的。自打扎拉豐和父親進來,她就昏昏欲睡了。房間里擠滿了人,蒼蠅也不斷飛進來,女傭用扇子驅趕著它們,還打開了風扇。
“兒子,”她對那個氣派的男人說,“我記得你一直想當個護士,小時候和兄弟在劇院里唱歌,鬧傳染病那年你還沒出生哩,病房里都滿了,我們整天整夜不睡覺。”
“您給人打針?”
“我給死人洗澡。”她說。
男人雙手插在腰上,皮笑肉不笑,陳嬤嬤又看向扎拉豐,叫女傭把他抱過來。他來到她身邊,她迅速脫下他汗濕的衣物,那只漆黑肥大的手環繞著他的腰,將他轉向眾人。她用手像拍西瓜一樣拍擊著他的肚皮。屋內的眾人注視著他,仿佛在看一只珍貴的貓。
“扎齊,好兒子,”她握著扎拉豐的手腕,對著那位男人說,“那塊土地是為他準備的。”
她話音剛落,扎拉豐就看到扎齊的臉漲得通紅。他呼來一名穿著迷彩服的男人,直接從陳嬤嬤手中將扎拉豐搶走。扎拉豐拼命掙扎,發出慘叫聲,但那野蠻的男人徑直朝外走去,無人阻攔,就連扎拉豐的父親也在一旁退讓。這男人臉色通紅,他神情有些狂熱,腰間藏著一把刀子,一直在和扎拉豐說話,他們穿過集市,一直走到鎮子的深處,似乎想將他帶進林子里。
“別殺我,別殺我!求求你,求求你!”他開始大喊,用力蹬腿。他掉下來了,那個男人就又把他抱回來,把胳膊橫在扎拉豐的肚皮上。當他試圖把手伸向他的刀子時,槍聲響起了,伴隨著爆裂和釋放的響動,那個男人倒在了地上,沒穿襪子的左腳也從鞋子里掉了出來。有兩個人跑了過來,但都不是屋子里的。扎拉豐摔在了地上,他倒在一塊石頭上,渾身是血,恐懼壓迫著他,他盯著那被槍打死的人的手掌,他的手掌似乎正在向四周展開,無邊無際,看不到頭。扎拉豐再次升起對他的恐懼。他的手掌簡直變成了大海,而一只漆黑的烏龜正迷茫地漂浮在上面。他不敢看著他的手,他抬起頭注視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如羔羊般、如牛犢般順服。他認為那是智者的雙眼,唯有看著他順服的目光,他才不會瑟瑟發抖。可他又默默察覺到,他應是這死人的一部分,他充滿柔順,他于塵世服服帖帖。他或許是他的一根頭發,又或許只是他萬千細胞中的其中一個。他才是微不足道的,他陷入了窘迫。他沒死,卻墜入深淵,痛苦迅速蔓延,他不知歸處何在,風呼嘯而至,無人給他答案。他只能繼續在虛空中漂浮。他身上被人罩上衣服,另一些人將他抱離現場,總而言之,他死了,但奇異的是,死后反而像是活了一般。
人們拉著他又回到了陳嬤嬤的住處,簾子一撩開,穿著印花褲的扎齊已經倒在地上,血流成一攤。
陳嬤嬤說:“拉尸體的時間到了。”
冷汗澆背的扎拉豐突然動了起來,他沖上去壓在了扎齊身上,他扇打尸體的臉,他聽見爸爸在呼喊他的名字,扎拉豐,快別這樣!人們哄堂大笑,而陳嬤嬤只是遠遠看著。于是他又撲了過去,搶過了那個挑葡萄籽的女傭手里的銀鑷子,插進了那個男人的臉里,他共插了兩次,后來因為害怕而停手。他爬到陳嬤嬤的腳下,陳嬤嬤打量著他說:“他和你一樣只是個窩囊廢。”父親聽罷,便冷笑著,或只是為空虛而哭泣,他們當晚就買票回家了。她給了爸爸一大袋鈔票,給他的則是一束瓦藍的風信子。
【作者簡介】渡瀾,蒙古族,生于1999年,內蒙古庫倫旗人,武漢文學院簽約作家。作品發表于《收獲》《人民文學》《十月》《青年作家》等刊。曾獲華語青年作家獎、丁玲文學獎、十月文學獎、 “京師-牛津‘完美世界青年文學之星”獎、《小說選刊》新人獎、索龍嘎文學獎等,入選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計劃·年度特選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傻子烏尼戈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