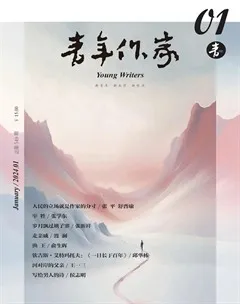漁 王

2016年,于我而言,有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關于龍潭二中舊址的爆破,那天臺里的領導特意讓我去報道這件事。
我記得那是八月,北戴河西岸的土坡上人頭攢動。
那天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其實都是龍潭二中以往的學生。其中不乏有像李東如這樣開著車爬上制高點,戴著墨鏡從天窗中探出腦袋,占據有利觀賞位置的。我同樣看見了不少熟識的面孔。其中有當時的高中班主任,后來以政教主任身份退休的曹云波,如今他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著,面朝即將倒塌的學校舊址。我特意將鏡頭對向人群,又穿梭其中,采訪個別人對于爆破的看法,其實我還有一個目的是想尋找一個人——馮明。直到那天下午兩點,喇叭響起長鳴,全場肅靜,我也沒有看見馮明的身影。緊接著便是倒計時的結束,高速運轉的攝像機記錄下幾棟教學樓在轟然之間倒塌,掀起巨大灰色塵埃的同時席卷著沖擊波向四周擴散。人群像是秋風里的麥田齊刷刷地往后揚去,被汗水打濕的襯衣在那一瞬間也脫離了皮膚的束縛,幾秒過后,人群再次喧鬧,響起掌聲。這一幕,是那么似曾相識,使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和馮明在北戴河東岸留下合影的那個夏日。
第二件事便是關于馮明的。2016年末的冬天,他的尸體被人發現擱淺在北戴河的岸邊,混雜著兩岸菜場的聒噪散發惡臭。他那個終生以賣菜為生的母親,被人喊到岸邊看熱鬧。她一眼便認出這具全身腫脹,皮膚慘白,甚至開始腐爛的軀體便是她的兒子。
我不清楚這兩件事情之間是否有聯系,只知道2016年對于龍潭而言,也應該有兩件大事。第一件事與我的一樣,也是關于龍潭二中舊址的爆破。
另一件則是關于一家全國知名的電子加工廠將在龍潭北部設廠,它將從龍潭二中舊址的位置開始建設,一路延伸到北部的月湖。那段時間里,龍潭的大街小巷都會看見宣傳標語:“緊跟時代,迎接煥新。”似乎一切都充滿希望。
龍潭二中舊址爆破完的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地想起與馮明經歷的那個夏天。
從我對那棟八十年代造的筒子樓有印象起,馮明一家便一直住在我家樓下。八歲之前,小孩、和我差不多大、瘦小,這些名詞與形容詞是我對馮明所有印象的標簽。在那之后,他們家出了一件龍潭人盡皆知的事情。有一天,我的父親告訴我,樓下的那個小孩的爹死了。我問,為什么?他和我描述,那天龍潭機械廠中的一個工人從二樓墜落,恰巧落在運作的機床上,巨大的齒輪撕裂了那個工人的身體,連同工作服的纖維一并嵌入了工人的肉體,當場斃命,那個工人就是樓下小孩的爹。一旁的母親開口問,那衣服怎么燒?總不能連著人一塊。我當時對于這個問題并不懂,只是從那以后,在樓旁的河邊玩耍時,時常會看見幼年的馮明。他有時會躺在野草堆里,一躺就是一下午,有時會拿起一棵狗尾巴草放進嘴里,就在這時,我看不下去了,跑過去對他說,這不能吃。他問我,為什么?我說,我爸說了,草不能吃。他說,我爸說不了了。說完,他坐下,夸張地咀嚼那株草。我忍不住好奇心問他,什么味道?他說,苦的,后面就甜了,剁碎了母雞應該喜歡吃。我問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說,我猜的。這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和馮明對話。
讀初中時,馮明一度迷戀上了弗洛伊德,這位大師讓馮明對分析自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馮明對我說,銳子,其實我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在人群里,一個是在人少或獨處的情況下。我說,誰不是呢。
那段時間里,馮明常拉著我跑到北戴河的岸邊。他會按照某些奇奇怪怪的書里描述的樣子,脫光衣服,走到水里,當水即將沒上脖子的時候,大口呼吸,仿佛在試圖往肺里儲存氧氣,直到讓河水包裹住頭頂最高處的一絲頭發。身體完全舒展后,神奇的是,他會短暫地被水遺忘,仰面浮在河面上。有時候夕陽在水上的波紋會漫延到他的肚皮上,給若隱若現的絨毛勾上一圈金邊。但這樣的時候不會很久,等到流水意識到他的存在后,身體會慢慢下沉,沉到水下的馮明在經過兩三秒的寂靜后,一個鯉魚打挺,鉆出水面。我也嘗試過,因為不會游泳而充滿恐懼,恐懼讓我差點窒息。
后來,他不滿足于北戴河的河水,便和我跑到龍潭北部的月湖,平靜的湖水延長了他的身體被水遺忘的時間。馮明爬上岸后,眼里泛著淚光,他問我,銳子,我是誰?
他的這一行為最終結束于一次垃圾傾倒事故。那輛偷倒垃圾的車輛并沒有注意到馮明漂浮的身軀。至于馮明為什么沒有聽到車輛到來的聲音,我對此并不知情,那天我并不在現場。我只知道,當他來到我面前的時候全身散發著異味,他在那天之后再也沒看過那奇怪的書一眼。
在臨近高三的暑假里,無所事事成了我與馮明的常態。我們經常在龍潭大街上閑逛,蹲在路旁,撿起被風吹落的傳單,然后一下午都在研究上面羅列的一堆傳染病的名稱,它所宣傳的醫院一般會取一個“阿波羅”或者“宙斯”之類我們看不懂的名字,隨后留下一個大城市的地址,引起我們的遐想。那時候,彩票店對于龍潭而言是一個新鮮事物,我們在那個夏天第一次走進彩票店,我掏出僅有的四塊錢,隨機買了兩注快三。等待了十分鐘后,遞給店主,得知我們中了四十塊。我帶著馮明買了兩瓶冰紅茶,坐在被曬得滾燙的石階上。馮明喝了一大口后和我說,銳子,我以后肯定也會賺大錢。我沒開口。他繼續說,我一定不會虧待你的。我當即從牛仔褲兜里掏出剩下的34塊,抽十元遞給他,告訴他,別以后了,我現在就不會。我至今無法忘記他當時的表情,陽光下的馮明滿臉油光,笑容在他瘦削的面部一直延伸到顴骨。
從那之后,我和馮明發現龍潭的街上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外來人似乎比往年更多,很多人在北戴河中游的兩岸支起魚竿,整日在那釣魚。一開始,我和馮明會好奇地坐在岸邊的草地上,看著那些外來人頭戴漁夫帽,重復著下餌、起網、又放生的行為。我們通過詢問才得知,原來是龍潭為了響應“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政策,決定在八月舉行“龍潭漁王大賽”。馮明似乎對此頗感興趣,他在草地上想象并模擬自己手持釣竿,用力甩出一條大魚,他又如何與之周旋博弈的過程。終于有一天,他從月湖東邊的竹林里砍了一根竹子,用不知從哪弄來的線輪組裝了釣竿,跟我說,走,釣魚去。
開始的幾天里,我們用逮來的螞蚱、挖來的蚯蚓當作魚餌,釣上來的頂多是巴掌大小的鯽魚,大多時候都是些垃圾。有一次釣到一條女式內褲,馮明拿著它湊到鼻前聞了聞說,應該剛扔不久。我問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說,上面還有味道。我不得不承認,馮明的嗅覺的確比一般人靈敏,時常我早上吃了什么,他在晚上聞一聞都能說出來,可是這對于我們釣魚并沒有什么幫助。馮明拍了拍腦袋和我說,銳子,我突然想起曹老師說的一句話。我問,什么?他說,書本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他恍然大悟似的進了一家書店,從書架上挑選了一本《釣魚指南大全》。
第二天,他仿佛學有所成,跟我說,銳子,你知道嗎,釣魚前得學會打窩。我問他,什么叫打窩?他說,就是用料把魚吸引過來。他捏起一根雜草說,這魚還分冷性魚和暖性魚,有些喜光有些不喜,有些喜歡葷餌有些只喜歡素餌,里面門道多了去了。我若有所思地問他,那你都弄懂了?他把手里的草放進嘴里,瞇著眼像是在細品,他說,懂了個大概,不過沒事,你放心,曹老師不是說過嗎?學無止境。他似乎品出了個大概說,這草要是混著螞蚱肉一起搗碎用來打窩,一定能釣上來草魚。
馮明信心滿滿地找來個塑料盆,捉了十來只螞蚱,混著青草,用根樹枝攪拌。他看差不多了,就沿著北戴河找打窩的地。他說,草魚喜歡在水草多而水淺的地方聚集,我們就找這種地方打窩。終于找到一處,他把先前攪拌的餌料往水里一灑,持著魚竿在一旁靜候。太陽西沉,馮明深吸一口氣,又用手指在水里感受了一下跟我說,差不多了,這香氣都散開了,水溫也合適了。說完,他在鉤上掛上餌,準備下竿。我特意觀察發現,他在魚線上多裝了幾個鉤子。他告訴我,這是為了增加咬鉤的幾率。
天色漸沉,也不見有魚上鉤,我們望著河面上夕陽的倒影。馮明看見魚標一沉,揉著眼大喊,上鉤了。他站起來,向后走,開始收線。我問他,大不大?他說,大。我們已經可以看見那條草魚翕張著魚唇在水面努力掙扎,可惜我們沒有撈網無法將它在此時撈起。馮明順著它的掙脫方向慢慢移動,那根用竹子做的魚竿,一會兒彎曲似乎就要被折斷,一會兒筆直似乎從未有魚上鉤。漁人與魚互相消耗著對方,等待彼此之間最后一點氣力耗盡。此時河面上只剩下一片薄云像是被野火快要燒盡,馮明累得出了一身汗,白色短袖像是一層膜敷在他的后背。他說,差不多了。說完,他奮力收線,雙手向后用力,整個身體往后傾倒,試圖將魚一把拉出水面。
“啪”,魚線斷了。
馮明的身體順著慣性,一屁股跌坐在草地上。我順勢坐到他的身旁,就這樣,兩雙眼睛望著平靜的河水里只剩幾盞路燈的光亮。
這次的失敗并沒有讓馮明退縮,他告訴我,這至少證明了他的餌料真能釣到大魚。為了買新的釣竿與撈網,他回到家偷了他媽的錢。整個前半夜的居民樓里,都是他媽歇斯底里的咆哮,伴隨著桌椅斷裂的聲響。在我們那種老式的小區里,任何一點細微的動靜,都會被狹窄的樓間距無限放大。
第二日中午,馮明與我在河邊見面。他手持新買的裝備,試圖用笑意掩飾小腿的淤青。他把手中拎的塑料桶遞到我的面前說,快看看。我看向桶中,是半桶像排泄物一般的東西,我問他,這是什么?他說,這是早上自己特制用來打窩的。說完,他帶我去向上次讓魚跑掉的地點,把桶里的窩料再次灑在水面上。他跟我說,這料的香氣比上次的更足,引魚就更快。他問我,你猜我這回添了什么?我反問,什么?他說,這次我加了芥蘭末,從我媽那偷的。我問他,你不怕被你媽揍?他說,怕啥。說話間,他從包里取出特調的餌料,完成一系列調試、拋竿、下釣的過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馮明已經是有多年釣齡的老漁夫了。
那天也正如他所設想的,沒過多久就有魚上鉤。他站起身準備起竿,與那條魚博弈的瞬間,他開口和我說,這應該就是上次那條。我問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說,感受到的。接著他大喊,銳子,快把撈網拿過來!我從他身后抄起那張網,伸到水底,探到魚身下面,看準時機,一把撈起。那條草魚的魚鱗在陽光下反射光芒,扭動著想要掙脫,可惜已經無濟于事。我把它一把抬到身后的草地上。馮明很興奮,先是從魚嘴里取下鉤子,雙手握住魚身,他說,這魚至少得有十斤重。我應和著說,差不多,拿去賣至少得四十塊。馮明用裝窩料的桶舀起半桶水,把那條魚放進桶里,他說,不急,再釣會兒。
我們釣了一下午,他收線,我起網,收獲頗豐,桶里滿滿的都是戰果,有黑魚、鯽魚、鰱魚,以及那條大草魚。眼看天色漸暮,馮明起身和我說,銳子,今天差不多了。我感到尿急,轉身朝向一塊空地,忽然聽見“撲通”一聲,還以為馮明興奮地跳了河,我轉過頭看見他手持窩料桶,把魚全都扔回了水里。我跑回去問他,干什么?他解釋說,銳子,我也要參加那個漁王大賽,獎金有五千塊呢。我問他,那和放這些魚有什么關系?他說,現在釣一條就少一條,你想是不是?我點了點頭。他接著說,要是那天我再用這餌不就又把它們釣起來了?我心里一想,笑了,拍著他的肩說,明子,你還真是個天才。于是一直到八月十五大賽到來的那天之前,我和馮明一天到晚都在北戴河的兩岸不斷嘗試新的釣點。我們發現中游的草魚多,就得用偏素的餌料,下游通向月湖那塊水深,鯽魚多,喜歡吃葷,就得多抓蚯蚓。我們也算是摸清了些路數。
有一回釣上來一條從來沒見過的魚,全身沒有魚鱗,又長又黑。我和馮明去查資料才知道這魚原來是英國來的,名字叫亞東魚,書上說它是外來物種。我說,英國魚,一定很好吃吧。我看見馮明的手指向文末的最后一句寫著“我國二級保護動物”。我看見的倒是五個字,白歡喜一場。
馮明對于釣魚大賽所展現出來的積極性與他從前種種的行為,一直是我心頭的疑惑。這使得我盡管與他的肉身近在咫尺,心靈卻存有距離。
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這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被解開于馮明的葬禮上。在那堆即將被焚燒的遺物里有一本帶有鎖頭的日記本,我生拉硬拽打開本子的封皮,借著火光,窺視到了有關他的一切秘密與答案。
在日記本里,他寫過一首詩,題目是:我如何愛你?內容是:我的生命猶如浮萍/語言匱乏,淚水無力/謊言編制盔甲,行為掩埋真實/我是誰?/生于你,也將死于你/這是必然/必然,我伸出螳臂/聞嗅每一個生靈,身軀與你保持平行。
這首詩寫于多年前的那個九月。它解答了我所有的疑惑,被我丟入火堆。我凝視著火堆想到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我記憶里被他的謊言填充的瞬間,這注定了我們的關系里將存在那些不純之物;第二件是一些無意識閃過的畫面,它又讓我想起了那個與馮明留下合影的夏日。
即使過去了這么多年,我依然記得釣魚大賽的那個夏日。那天風和日麗,北戴河兩岸前所未有地熱鬧,西岸的土坡和東岸的菜場集市,都擁擠著站滿了圍觀的人群。賽制很簡單,從上午十點開始,一直釣到下午四點,誰釣的魚加起來最重,誰就獲勝。大賽是單人制,馮明只能單槍匹馬地去了,而我選擇坐在專門為選手家屬準備的觀賽席上。我看見主持人站在那座擁有百年歷史的石橋上,可以看見橋墩下還懸有一把劍,聽說是古時為了防止水中蛟龍作怪,專門放置的法器。主持人一聲令下,大賽開始,幾門禮炮齊鳴,全場爆發掌聲,這一幕與十年之后龍潭二中爆破的場面是多么相似,甚至更加宏大。
馮明被分在中游一處水流匯集點,我為他感到慶幸,這兒離我們第一次釣到大草魚的地點很近,也是我們最熟悉的水域。那天,我冷靜分析了賽場的競爭對手,最有實力的恐怕就是來自省城富有盛名的老漁王。他是組委會專門請來的嘉賓,我看見他圍著一條自行車賽手才會圍的遮陽圍巾,戴著自行車賽手才會戴的墨鏡,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剛從自行車賽場下來。他每釣起一條魚,眾多的粉絲都會在東岸的觀賽席上手舞足蹈。除了像他這樣實力強勁的對手,也有很多只是來湊熱鬧的人,其中便有我們的同學李東如,他爸是國土局的副局長,給他買了一整套專業的設備,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半天也釣不上來一條魚的結果。反觀馮明,動作有條不紊,每隔十多分鐘就能釣上來一條魚,好幾次一竿能咬鉤兩條。我看了看老漁王的桶,發現馮明和他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中午的時候,選手有三十分鐘停賽休息的時間,馮明吃著盒飯在岸邊向我招呼,他湊到圍欄邊和我說,銳子,今天的魚,我感覺不一樣。我問他,怎么不一樣?他說,說不清。他低頭扒拉兩口飯,鼓著腮說,我想用一個東西來重新打窩。我問他,是什么?他湊到我耳邊,低聲地告訴我幾樣東西,讓我去準備。我很驚訝地問他,這能行?他吃著飯,又點頭說,有感覺。我看他很有自信,沒多說,趕忙跑到菜場給他準備好,用個裝魚的塑料袋裝起來遞給他。
下午比賽開始,參賽選手走了小半,多是些原先只想湊熱鬧的人,被太陽曬得受不住了。陽光正烈,魚都不上來,全沉進水底。選手們的上魚速度顯然也受了影響。兩岸的觀眾支著傘,靠著圍欄圍觀。馮明他媽那天也不賣菜了,她把平時賣菜遮雨的大棚支過去,賣起了糖水,坐在棚里看著自己兒子比賽,逢人都要說一句,那個沒戴帽子的,就中間那個,是我家娃。
我倒沒像他媽那樣大張旗鼓,我一言不發地注視著馮明,發現他的白色短袖現在已經濕透,貼在了背上,皮膚的顏色清晰可見。就當全場氛圍有些低落時,人們看見老漁王有了新動作,他從身后包里掏出新魚竿,又拿出新的料開始調制。主持人也被這一幕吸引,兩個音響里爆發出驚訝聲:“快看!老漁王居然要重新打窩。”
只見老漁王把新調的窩料灑進河里,沒過多久,他開始用新的釣竿。人們這時才發現,他的釣法很奇怪,魚線不完全下去,只是甩出去,蜻蜓點水似的,又慢慢拉回,不斷重復這一動作。觀眾席上有懂行的人驚呼,這是飛釣,也叫飛蠅釣。果不其然,老漁王的改變有了效果,立馬讓比賽的懸念產生了傾斜。他釣起來的魚都不大,不過數量很多,沒過幾分鐘就上來一條,帶來的魚桶都快裝不下了。他選擇拿漁網浸到水中,留著口在岸上,把釣來的魚都放進去,免得魚死掉。
在同一時刻,馮明也面臨著與其他選手同樣的困境,日光直射,上魚更加困難。比賽至此時,不僅僅是運氣與實力的比拼了,更是耐力與體力的對弈。大概下午兩點多時,我看見馮明終于有了新動作。他起身走向我給他的那個塑料袋,從中拿出幾樣東西。他用袋中的細網包住最重要的關鍵之物,用一根細繩拴住,一把扔進河里,重新打窩。觀眾席上有人問,那是什么?我說,是豬肺。有人疑惑起來,豬肺?那段河里都是些草魚之類的,用豬肺打窩,不是把魚都熏跑了?其實這也是我心中的疑問。馮明這一舉動沒讓眾人感到意外之喜,反倒使人覺得他是病急亂投醫。
馮明不慌不忙地開始重新組裝魚竿,他從岸邊撿了幾塊石頭掛到魚線上,我看出來,他是想讓魚餌沉到深水中去。只見他用力一甩,魚線順勢飛出去,石頭在水面濺起水花后又恢復平靜,慢慢沉入水底。
馮明等待了將近一個小時也沒有魚上鉤,倒是不遠處的老漁王借著水溫開始下降的間隙釣了不少魚上來。馮明看來是沒有機會了。
等馮明的魚標有反應的時候,整個賽場中只剩下為數不多的選手,兩岸的觀眾反而興致勃勃地伸長腦袋等待龍潭漁王的誕生。全場寂靜的同時,我捏緊拳頭,期待奇跡的發生。我看見馮明的魚竿極度彎曲,呈現出驚人的弧度。馮明已全身繃緊,透過濕透的短袖可以看見他瘦小的臂膀上肌肉的曲線。他兩腿彎曲,將整個人向腹部蜷縮,顯出用力的模樣。他一邊緩慢移動,一邊收線,但也不敢用力收,收一段,緩一會兒。順著魚游動的方向,一會兒用力與之對抗,一會兒收力使其放松警惕。它們就這么僵持了十幾分鐘,也不見那條魚的身影浮出水面,主持人注意到了這一場景,大聲喊道,大魚,一條很大的魚。
我自己也按捺不住了,從座位上站起來喊,明子,加油啊!遠處,馮明他媽也與我遙相呼應,甩著手中的毛巾喊,娃娃,加油哇。觀眾都注意到了馮明拼盡全力的動作。他拉著魚竿,向后退,一邊收線,一邊又往岸邊回去。終于,人們可以看見那條大魚的身軀了。它張開大嘴,嘴上長著至少三十厘米長的魚須,它的身體掙扎著想鉆回水中。人們都認出了那是一條巨大的鲇魚。在龍潭許多關于兒童在河邊失蹤的傳說中,鲇魚一直是最大的懷疑對象,只不過人們見過最大的鲇魚也不過二十幾斤,都不足以一口吞下人類的孩子,但現在一切都不一定了,現在與馮明對峙的這條大鲇魚,目測足有一米多長,它的大嘴絕對可以一口咽下一個小孩。
馮明身旁的選手把自己帶的魚叉準備遞給馮明,希望馮明可以用它把那條鲇魚扎死然后拖上岸。馮明卻給了他一個眼神,似乎在說,不需要。在臨近比賽結束的最后關頭,那條鲇魚與馮明都已處于精疲力盡的狀態,只見馮明屏住一口氣,準備與這條魚做最后的決斗,那條魚被一點點拖向岸邊。
我望向天空,看來運氣在馮明這一邊。凸月在東邊的天空已經清晰可見,北戴河的河水在黃昏時自然地發生了水位下降。大魚被擱淺在河床邊的淤泥上,再也無法回到水中。馮明蹲下身子,伸出手抓住魚嘴,用力地向岸邊拖拽。終于,那條鲇魚被拖上了岸。
比賽正式結束。
在兩岸的歡呼聲中,我翻過護欄,下到河邊,跑到馮明身旁。我看著他虛脫的模樣說,這魚可真他娘的大。說完,我幫他一起把魚扛到大賽舞臺上。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稱魚的結果,最終,馮明以五斤的優勢險勝老漁王。老漁王摘下自行車墨鏡露出雙眼,走到馮明跟前,伸出手說,恭喜,小伙子。主持人拿著話筒宣布了這一結果,馮明他媽在一旁抹著眼淚說,娃娃,出息了。主持人繼續宣布:“讓我們恭喜龍潭漁王!”全場轟動,我可以確定地說,那一瞬間的氣氛一定完全蓋過了十年后龍潭二中舊址爆破的場面。
我抬起那條鲇魚的魚頭,馮明一手持著魚竿,一手抬著魚尾,龍潭的副縣長站在中間抱著魚身,在留下合影的同一時間,兩岸的觀眾高呼著:“漁王!漁王!”副縣長接過主持人的話筒說,縣里決定將這條大魚制作成標本,放在縣政府的大廳里。全場再次響起掌聲。
但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馮明的手微顫著搶過話筒,他說了一句,我不同意。他把話筒扔到地上,用力抬動那條鲇魚,發現自己抬不動,他轉頭向我說,銳子,幫我一把。我有些沒反應過來,聽著馮明的指揮,抬著那條魚跟著他一起移動。
大賽舞臺就設在那座百年石橋的旁邊,馮明帶著我和那條魚走上橋。他說,放上去。我照做。他說,把它推下去。我問,放了?他說,放了。他用力一推,那條鲇魚扭著身體,墜入水面,很快就不見了蹤影。
這一幕讓臺上的副縣長啞口無言,尷尬地愣在原地,兩岸的觀眾也不清楚為什么會發生這么一幕。
倒是李東如他爸,那位國土局副局長,作為大賽的評委從評委席上走了出來,撿起臺上的話筒發出聲音說,喂喂,那位小選手,我有一個問題。
李東如他爸問了起來,小選手,你后來打窩用的是什么?
馮明努力在眾人的面前發聲說,豬肺。
李東如他爸問,小選手,你的參賽報備餌料里應該沒有這個東西吧?
馮明點了頭說,是我讓人去買的。
李東如他爸說,鄉親們,這就對了。這位選手自己承認了,他違反了大賽的規則,擅自用場外的協助,作為大賽的評委,我覺得有必要取消這位選手的參賽資格。他的目光看向一旁坐著的老漁王說,所以鄉親們,我認為,這屆“龍潭漁王大賽”的冠軍依然是老漁王。
觀眾似乎沒反應過來,幾秒后,才響起掌聲。
在那天后來的掌聲中,恐怕只有我和馮明他媽是最不知所措的。首先,我愣在那座石橋上看著臺上發生的一切。然后是馮明他媽,那個右眼永遠腫脹著一顆紫色肉瘤的女人,茫然地站在臺上,隨后放聲大哭,那應該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成為眾人的熱鬧。而馮明呢?他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一個人走向北戴河的西岸,往龍潭二中的方向走去。我后來才得知,那晚他去了月湖,獨自坐了一整夜。
從那天之后,馮明變了。在剩余的夏日中,我找遍了小區、河邊、大街都沒有看到他的身影。在高三到來的秋天,馮明總是坐在他那張靠窗的椅子上望著天空發呆。他有時神神叨叨,說著稀奇古怪的話語;有時又像是個詩人,對一切都充滿惆悵。我懷疑他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或是精神出了什么問題。一天午休時,我湊到他耳旁問他,明子,你怎么了?他說,銳子,你知道嗎,北戴河在哭泣。我問,你怎么知道的?他說,我聽見的。我問,它為什么要哭泣?他說,北戴河失去了太多的孩子。還未等我開口,他又補充道,那天所有的魚都被送進了一輛卡車。我問,那又能怎么辦?他的目光與我對視,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觀察那雙單眼皮的小眼睛,以及淚腺分泌淚水從眼角流出的全部過程。
從一段時間起,馮明總會在下午的課堂不知所蹤,一開始是放學的最后一節自習課,后來是整個下午,再后來臨近一模考試,他甚至開始不來上學,直到最后有一次星期五的班會課,馮明他媽出現在了教室的門口說,曹老師,我來了。這個永遠板著一張臉的班主任先是對我們說,大家先看看這道題有沒有別的解法。隨后快步走向門外。
幾個好奇的學生把腦袋從后門口探出,看見馮明他媽從不斷訴說到開始動手動腳拉扯,最后試圖下跪的場景。整個過程中,曹云波無動于衷,雙手背在身后,巍然不動。
馮明他媽最后引起了全校的關注,她四腳朝天躺在教學樓中心的天井中,發出凄慘的哭聲,這一行為驚動了校長以及一群校領導前來勸說。她扭動著像是一條只剩一小截、將死的蚯蚓。一群經驗豐富的教育者,此時卻對一個哭鬧的婦女束手無策。曹云波只好轉頭看向樓上的學生喊了一句,都別看,回教室去。
這件事的結果是,馮明他媽哭腫了另一只沒長肉瘤的眼,高血壓致使她當場昏迷過去。關于馮明的消息則出現在了第二周的布告欄中,上面寫著“我校高三(12)班學生馮明,因多次無故曠課,給予勸退處理”。
在高考之前的日子里,我只見過馮明三次,有兩次是在北戴河邊看見他持著釣竿在釣魚,我過去和他打招呼,他隨聲應和完,便直勾勾地盯著水面,不說一句話。還有一次是在龍潭大街與開運路的交匯口,他低著頭,行色匆匆地從一個巷口竄出,沒看見我。
從前我和馮明在大街上閑逛時,總會發現一些濃妝艷抹的女人站在開運路上的某個位置,又與一個外來的男人勾肩搭背消失在某個巷口。我們那時總對開運路充滿好奇,謀劃著有一天去一探究竟,看來馮明已經先我一步。
在高考之后的暑假里,我再也沒見過馮明。馮明他媽還是每天一早四點半出門,推著一輛板車到菜場上支起棚子,叫賣著:“青菜哇,芥蘭哇,土豆哇……”我很多次經過那個菜攤,卻因為不敢直視那只長有紫色肉瘤的右眼,只匆匆而過。
從那時算起,我一生中也僅再見過馮明三次。第一次是我大四那年的春節,我已經快要從當時所在的大城市回到龍潭了。
我在大年初五的傍晚出門,下樓梯時遇見馮明。我開口喊住他。他的目光看向我,想了幾秒才反應過來說,趙銳啊。我問他,吃飯了嗎?他說,沒吃。我說,一起吃口。他規避我的眼神看向口袋中的手,隨后又點了點頭。
我問馮明,現在在做什么?他說,在月湖那兒。我問他,具體干些什么?他說,說好聽點叫水質監測員,就是個看湖的,每天早上和晚上裝一杯水,等周日有人來取。我說,那挺好,還挺閑。我又問他,怎么去那兒的?他說,我媽找我爸原來那廠子的廠長,現在林業局的,把我弄過去的。我說,那還挺講情義。他說,吞了我爸那么多賠償款,能不講情義?被他這么一說,我沒話說了。悶著頭吃完面,他也沒再說話。
我第二天再想去找他,發現他早回月湖去了。
畢業后的幾年,我進了云節市的電視臺,每天除了采訪就是寫稿。雖然就在龍潭不遠,但除了春節也很少回家,后來就干脆在云節買了房把爸媽接了過去。原先那房沒人住,一直空在那里,這次為了報道龍潭二中舊址的爆破,還特意找出這房的鑰匙,回來住幾天。我第二次見到馮明便是在龍潭二中爆破完的第二天,整夜我都想著這個名字,促使我產生了去月湖找他的念頭。
月湖說是湖,實則也不大,頂多算是個大點的塘,形狀神似天上的月牙,因此得名。北戴河的河水最終都會匯入月湖。它滋養了東面的竹林,南面的草地,離它不遠的北部是一條重要的高速公路,隔在中間的水杉林形成了天然的隔音墻。一般開車只能到龍潭二中舊址的位置,往北是片林子,必須得步行。步行兩公里多,會看見一大片天然草坪,再往前就是月湖。
我看見湖邊有個身影,走近了發現馮明戴著一頂農作時才會戴的草帽,穿著灰色呢絨外套,坐在一張板凳上,持著釣竿。我喊了聲,馮明。他轉過頭,看向我。他問,你怎么來了?我說,來看看你。
我坐到他身旁的草地上,開口問他,怎么樣?
他問,什么?
我說,魚情。
他說,不怎么樣。
我問,那最近呢?
他說,也不怎么樣。
我問,怎么說?
他說,廠子要造過來,就要走了。
我問,去哪?
他說,不清楚,可惜了這湖,多好。
我說,是啊,你看平時還能釣魚,以后釣不到了。
他最后說了一句,何止。說完便把頭躲進了草帽的陰影中。
我陪他在湖邊坐了近半小時,也沒見他上魚,我想是他現在技藝衰退了,又不好點明。
“隆隆”的響聲從身后傳來,馮明開口說,來了。我問,什么?他說,兇手。
我看向來時的道路上,出現了一群人,領頭那人看著眼熟,戴著墨鏡,穿件范思哲短袖,套件皮制外套。他靠近了,我這才看清原來是李東如。他們一行七八個人,有幾人在后面推著個機器,引擎發動著,震耳欲聾。李東如帶人來到馮明身后,拍拍馮明的肩膀說,該走了,別拗了。他注意到一旁的我,和我打招呼,趙銳也在啊。他說完又催促起馮明,他說,明子,放心吧,我爹都安排好了,你回林業局天天喝茶就是了。
馮明聽后不慌不忙,悠悠起身,回線、收竿。李東如在一旁說,這不就對了嘛。他用手一招呼,原先在后面推機器的幾人,齊心協力,準備將機器推到岸邊。
馮明的舉動與十年前他扔魚那次一樣出人意料,他將身體擋在那機器的必經之路,并把草帽摘下置于胸前,像是騎士將與一切訣別。他張開胳臂,像眼鏡蛇面對危險時展現自己的意圖。李東如這時開口說,馮明,這又是什么意思?馮明發出聲音,很低沉,他說,要么從我身上碾過去。
李東如自然不慣著他,上去就是一巴掌。我看見馮明的面部扭曲變形,頭部偏向一旁。他像是電影《天注定》里趙濤飾演的角色,強忍著正過臉,怒視李東如。我當即一個箭步來到李東如面前,阻止他的下一步動作。李東如將我的手甩開,看向身后的人說,把他拽走。幾人反應過來,馮明也不躲閃,其中一人一個絆腿,馮明枯柴般的身體向后倒去,一個人控制他的雙腿,馮明掙扎中踹了那人的臉一腳,還有兩人一人一側,控制住他的上半身。馮明扭動的身軀讓我想起十年前他媽在龍潭二中上演的那一幕,心里不由得唏噓。
李東如指揮著另外的人把機器推到岸邊,接上管道,沉入湖中,馬達轉動,湖水被抽到草地上。
馮明在一旁大喊大叫,抽不得,不能抽啊!李東如沒有理會馮明,他拿起手機撥通了電話說,爹,治理開始了,一臺不夠,你再調幾臺來,最好喊些施工隊的來把湖口堵上。他掛了電話。我看見馮明的神色驚恐,眼珠亂轉,仿佛世界將要崩塌,他最后說了一句,龍潭沒了潭,我們都要完蛋。說完那句話,他沒再出聲,其中一人拍拍馮明的臉說,老板,他昏了。他們將馮明的身體放在草地上,我就坐在他的身旁。我對李東如說,不是辦法,你得找人送他去醫院。
說完,我的視線躍過月湖,落在北岸,在流水嘩嘩的巨響中,我清晰地聽見湖面傳來異響,現出一條大魚,通體漆黑,足有近兩米長。我想起十年前與馮明留下合影的那條鲇魚,是否就是它?有一瞬間,我產生了錯覺,感覺那道身影就像是馮明,只見它高高躍起,砸落在水面,濺起水花的同時,所有人都聽見了一聲動物發出的低吟,像是象聲,卻又不像,低沉卻很響。李東如問,什么東西?沒人能夠回答,因為在所有人的視野里除了藍天白云,綠樹清水,別無一物。
那到底會是什么?
我守在病房里,他睜眼看見我,又望向天花板,長久地盯著一個虛無的點。
我當時很想和他說些什么,后來接到了臺里的電話讓我趕快回去,和馮明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再見。從那天的再見之后,我們沒再聯系過,直到2016年12月末得知他的消息,他的尸體在北戴河岸邊被發現。這便是2016年對我而言的第二件大事。
警方很快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查出馮明專門跑到云節新造的跨江大橋上縱身躍入長江。神奇的是,他的尸體又漂回了北戴河這條幾乎干涸的三級支流。
我得知去參加他的葬禮的那天是2017年的元旦,正加班加點地趕著關于“2017年龍潭縣將正式撤縣設市”的新聞。其中幾張照片關于那家電子加工廠的開工典禮,聲稱龍潭緊隨科技發展道路的政策。還有幾張照片是在那天的宴會上,餐桌正中的主菜我一眼便認出來了。那條鲇魚被開膛破肚,呈現出盛開的模樣,承載著各色的海鮮與水果。
我回到龍潭去見馮明最后一眼,那便是我第三次再見他。
他被白布蒙著臉,像兒時在草地上靜躺著,目送一朵朵流云的聚合、變形、消失。
馮明他媽哭得撕心裂肺,比十年前在龍潭二中哭得還要傷心。我想起很多年前馮明他爸的死,慶幸的是,至少馮明的火化不會像他爸當時那么麻煩。李東如也出現在了葬禮上,在眾人的目光下把一個紅包塞進了馮明他媽的手里。這個半輩子為了一毛、兩毛都要斤斤計較的女人,當眾把那一沓錢扔進了屋外焚燒衣物的火堆里。
那天夜里,我毫無方向地行走在龍潭,從小區走向大街,走到原先是草地如今變成廣場的位置,最后走上了那座百年石橋。我望著如今的北戴河,想起十年前的那個夏天,碧波泛蕩、水草豐茂的過去,如今的北戴河儼然像是遲暮的老嫗,奄奄一息,即將走向生命的死亡。原先寬闊的河床上,如今散布著兩岸遺留的垃圾,只剩及膝的河水散發腐爛的氣味,緩緩流淌著。
【作者簡介】俞生輝,生于2001年,吉林長春人,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現為導演、制作人,上目書館簽約作者。主演并執導話劇《又見麥克白》、電影短片《無孔不入》,文學作品見于《世界文學》(香港)、《中國校園文學》《微型小說選刊》等刊,曾獲《收獲》無界漫游文學獎入圍獎;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