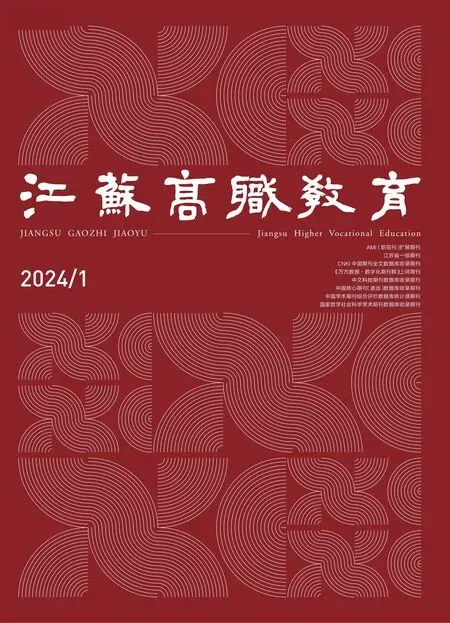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走好通往專業高職之路
——基于ISCED2011及《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評核報告的新視角
袁益民,李芳苑
(1.江蘇省教育廳,江蘇 南京 210024;2.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電子信息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國際教育標準化分組2011(以下簡稱ISCED2011)通過職業專業與普通學術兩種取向的劃分,為國際層面更好地收集、比較和分析各國教育系統數據打開了一扇方便之門,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該分組1997版本在概念準確性和實踐適切性方面的缺失,使各國報告第三級教育所有層級專業或學術教育計劃數據成為可能。該標準化分組工具在國際范圍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其對于專業取向高等教育分組的提議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但囿于其對專業取向具體定義的懸而未決,仍讓國際間數據收集、比較和分析工作無所適從,留下了進一步研究解讀和實踐探索的空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OECD)2022年發布的職業教育與培訓評核報告《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理解高等職業與專業第三級教育系統》(Pathways to Professions:Understanding Higher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Systems,以下簡稱評核報告)較好地回應了這一問題,找到了務實可行的進一步定義方案,是ISCED 2011提出專業取向分組設想后的又一項重大進展,如能就取向區分達成共識,將帶來巨大回報,釋放專業第三級教育數據持續收集的潛能[1]。當然,“由于當前缺少國際公認定義來強化數據收集而削弱了比較分析,更好的數據仍在門口的臺階上等候”。評核報告以相關國家系統數據及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了各國高等教育計劃,特別是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的實際現狀,包括導入專業教育計劃的通道及其向繼續學習或勞動市場的過渡,專業教育計劃所服務學習者的年齡、性別、經濟社會背景,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通過雇主參與、基于工作的學習、適切勞動市場需求的目標學習領域與社會合作伙伴及工作世界的鏈接,及其以學習成果與就業情況為表征的質量等。報告闡釋了技術變革時代經濟社會對理想技能的新要求,在繼承和發展ISCED2011的專業取向構念基礎上,提出了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分組的架構與思考。該報告提出的關于聚焦專業取向教育計劃的政策辯論意見、“三向度”高教分組中的“二向度”專業教育計劃分組方案以及專業取向教育的獨特性、增值性和高等性等理念,對于我國把握終生學習背景下的職教類型定位、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分組下的貫通銜接以及技能型社會的技能需求和專業技能系統的治理等有諸多新的啟示。正確理解ISCED2011以及評核報告關于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分組的設想與建議,積極吸收和借鑒其對于我國現代高等職教體系構建的有益經驗,有利于我們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走好通往中國式現代化的專業高職之路。
一、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分組的新探索
自ISCED2011提出職業專業與普通學術兩種取向劃分的極具創見性的提議以來,比較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國際層面更是未能就此達成共識,長期缺乏統一的理解和定義[2]。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助力改進專業第三級教育的跨國比較數據搜集以供該領域的相關決策咨詢,OECD于ISCED2011修訂版發布十周年之際發起了“高等職業教育與培訓—專業第三級教育”項目,以期揭示擴大專業教育計劃現存及未來數據收集覆蓋面的可能性,并就促進達成國際公認定義及第三級教育計劃取向分組進行對話。除了其它方面來源,如歐盟勞動力調查(European Union Labour Force Survey,以下簡稱EU-LFS)和成人技能調查(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以下簡稱PIAAC)的數據收集時間不盡相同以外,該項目的OECD專業第三級教育數據收集工作在2021年開展。
在該項目實施過程中,OECD秘書處得到了專業第三級教育特別工作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Professional Tertiary Education)的實質性指導及投入,也獲得了職業教育與培訓國別專家小組(Group of National Expert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總體指導。OECD技能中心的Viktoria Kis和Simon Normandeau在起草該項目報告即《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評核報告過程中,得益于機構內外多方支持,包括專業第三級教育特別工作組成員的參會、就工作文本提供意見和完成OECD的專業第三級教育數據收集,以及歐盟委員會、教育系統指標工作團體(Indicators of Education Systems Working Party,以下簡稱INES)、勞動市場與經濟社會成果網絡(Network on Labour Market,Economic and Social Outcomes)和高等教育國別專家小組(Group of National Experts on Higher Education)等方面同行及內外部專家的支持。評核報告文本制作由歐盟提供資助,并于2022年正式出版。
該項目涉及大量的案頭分析、對話和數據收集工作。首先,復核各國相關系統、政策與實踐方面的現有證據,評價相關比較數據(如OECD成人技能調查數據、INES收集數據和歐盟勞動力調查數據)質量,并分析比較數據。同時,通過專業第三級教育特別工作組邀請相關國家及國際組織參與討論關鍵政策問題,以OECD國家專業教育計劃信息充實該項目,并商討有關第三級教育計劃取向可能的國際公認定義問題,共有27個國家和6個國際組織參與。再者,OECD成員國、主要伙伴以及非OECD成員國的歐盟成員國和候選成員國被邀請完成一份問卷調查,其中包括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尋求補足ISCED編碼下和前期調查中的相關現存信息,后一部分尋求收集專業第三級教育領域的政策與實踐案例,37個國家完成了問卷。該項目的調查研究范圍涵蓋了ISCED5—ISCED7的教育計劃,大部分分析聚焦在ISCED5和ISCED6兩個層級。評核報告使用了幾個來源的比較數據,它們大多基于ISCED2011。一些數據來源允許在幾個層級上進行教育計劃取向的分解,此外,即便是不允許如此分解的數據來源也能提供兩個方面的洞見:一是有些數據來源區分了ISCED5層級的教育計劃,而實際上專業取向的計劃在其中占了壓倒性的優勢;二是有些數據來源為高中階段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畢業生所尋求的通道情況,特別是他們進入第三級教育以及在其中的進階情況,提供了有價值的洞見。
在比較數據中區分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的基本依據是ISCED2011。它允許在第三級教育的所有層級區分專業教育計劃,但其潛能尚未充分發揮。在更早的框架即ISCED1997修訂版中,第三級教育在層級5和層級6進行區分,層級6留給了Ph.D教育計劃這樣的高級研究,包括碩士層次在內的絕大部分第三級教育計劃放在了層級5,細分為5A與5B。其中,5B定義為實務取向、面向特定職崗(指occupational,而非vocational,以下稱“職崗”,以示區別)的教育計劃;但5A既包含了純科學與人文方面更為理論化的研究,又有諸如醫學和建筑等具有高級技能要求的專業行當所要求的更長的教育培訓計劃,這使得5B尷尬地落到了除去高級職位以后的專業教育計劃范圍[3]。ISCED2011尋求通過第三級教育不同層次的更多區分解決這一問題,方法是在更多的層級上(ISCED5—ISCED8)允許每一個層級的教育計劃區分為“專業”或“學術”兩個不同的取向范疇。這樣一來,由于第三級教育所有層級中都有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具有專業的特征不再附帶教育計劃地位或長度的意涵。
然而,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因“專業”或“學術”缺少國際公認定義,ISCED5仍使用ISCED低端層級的“職業”教育計劃采用的定義,對于ISCED6及以上層級,各國或是根據自己對“專業”和“學術”的定義進行取向的分解,或是在報告教育計劃時將其列為“取向未定”,實際削弱了比較數據的可比性。調查數據顯示,同一個職崗的教育計劃在報送數據時被不同國家分別列入“專業”“學術”“兩者都是”或“未定取向”,有的沒有答復。盡管這在有些案例中可能反映了各國培養方式實際存在的差異,但并不排除大比例的答復與定義方式上未計入的差異有關。ISCED框架下所收集數據的另一個局限是其并不包括正式教育及培訓系統以外提供的資質。而有些國家的此類教育計劃(如產業主導的證書)在為高等技術職崗作準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美國的高級水暖工(master plumbers)考試就發放執業證書,但它不屬于一種正式教育資質;法國也有一個歸入全國注冊系統而非作為正式教育的龐大專業資質證書體系。此類產業主導證書的比較數據只有在某項教育計劃同時頒發正式教育資質和產業認可證書時才能被捕獲。
可見,在“專業取向”相關概念及術語的使用上仍有一些問題亟待厘清。評核報告除了推動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分組的實踐探索,在術語使用和概念定義方面也提出了很有價值和創意的理論設想與實際建議。該報告使用“專業”一詞指代ISCED5層級的所有教育計劃,無論其當前在國際數據收集中被分為何類,因為絕大多數該層級學生尋求的教育計劃均被歸入了專業取向,其余許多教育計劃即便被歸入了專業以外的取向,但看上去仍然是專業性質的。而在ISCED6和7層級,基于ISCED編碼及相關國際數據收集方式分別使用“專業”“學術”或“未定取向”。但該報告在描述國際公認的定義提議時則使用“行業取向”和“專業取向”,具體內涵與歐洲近期相關研究提議的“高等職業教育與培訓”(higher VET)的寬泛定義一致。報告使用的“高等職業教育與培訓”概念實際指代具有專業取向的中等后及第三級教育計劃,而報告使用的“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與當前ISCED框架的意涵相同。至于“專業取向”和“應用”兩詞,在報告中則針對相關國家的適切背景情況使用(如“應用科學大學”“專業取向學位”)。
與國內的“學術(科學)”“專業”“應用”“職業”等劃分方法明顯不同,無論是在ISCED2011還是在評核報告等相關國際文獻中,“專業”在第三級教育中是涵蓋了“應用”與“職業”的。首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里的“專業”一詞與學科專業中的“專業”(program)完全是兩回事,但與國內“專業學位”中所指的專業意涵相仿,其形容詞形式professional用來形容具有更高資質要求的教育計劃及職崗門檻的性質,其名詞形式profession即指這樣的專業行當,而形容詞形式作名詞使用則指專業人士[4]。最早的專業行當是從草藥制作者、巫師和年長調解人演進而來的醫師、牧師和律師等所謂“三大最古老的專業行當”(the three oldest professions)。到了現代,工程、教學、護理、室內裝潢設計、烹飪藝術、商學、食品工程等許許多多行當均已被歸入了專業行當,其中許多行當不僅有一定的職崗資質門檻,而且與第三級教育資質掛鉤。該評核報告使用的形容詞及名詞形式的“專業”概念可如是理解。
該評核報告在相關概念定義的深入剖析及務實使用方面進行了有益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為了更好地解決各國數據收集中遇到的問題,報告極大地收窄了“專業”與“學術”之間的灰色區域,實際上提出了一種“三向度”的高教分組方案。一是對“專業取向”范疇進行了細分,將原來的專業取向分成“專業取向”(profession-oriented)和“行業取向”(sector-oriented)。其中,前者指提供設計用來使學生具備實際從事特定專業行當所需知識與技能的應用性教育與培訓的(教育)計劃;后者指提供設計用來使學生具備在某種職崗族系或產業版塊工作所需知識與技能的應用性教育與培訓的(教育)計劃。二是嘗試定義原先的“學術取向”,并將其改稱為與ISCED5以下層級相同的“普通(general)取向”。“普通取向”指提供純科學、人文與藝術方面學科取向教育的(教育)計劃。盡管這類教育計劃也應提供具有勞動市場適切性的知識與技能,但適用于非常多樣化的背景,而非旨在為學生進入特定專業行當、職崗族系或產業版塊作準備。報告還為這一包含“專業、行業、普通”的“三向度”高教分組方案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分組的補充指標,包括實務培訓的份額、基于工作的學習份額、雇主的參與等。
該評核報告在相關概念定義和務實使用方面的做法及提議極具智慧與遠見,詳情見圖1。首先,ISCED2011明確ISCED5—ISCED8層級使用“專業”與“學術”取向區分,而ISCED5層級分組仍使用“職業”取向概念,直至國際公認的“專業”“學術”定義出現[5]。在這樣的情況下,評核報告允許ISCED5層級數據按ISCED框架收集,但在數據分析上做了有意義的比較,使得因定義缺失造成的各國比較數據質量減損影響降到了最低水平,較好地平衡了規范性、簡捷性和有效性原則之間的關系,既顧及了局部,又看到了整體。同時,對于“學術”取向改稱“普通”取向的提議也是大膽而又審慎的。其實,“專業”與“學術”的二分法確實存在問題。“學術”的詞源學淵源可追溯至柏拉圖時期,其英文的形容詞形式源自拉丁文和中世紀法語。大部分詞典(如《劍橋詞典》《牛津英語詞典》)均認可“學術”的兩層含義,一是與高層級教學、思考與學習有關的,二是沒有實際應用的。就如報告分析的那樣,這兩層含義具有潛在的矛盾性,以“學術”分組“不會被廣泛接受”,因為高層次教學、思考與學習常常確有實際應用,而法律、醫科院校及應用科學大學深深地依著于高層次教學、思考與學習,不應只因其涉及應用性專業訓練就將其歸入非學術取向。前期研究已經表明,院校使命方面的所謂“職業漂移”(vocational drift)與“學術漂移”(academic drift)并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可以并存的,“學術—專業”區分被認定為是“虛假的”。因而,使用“普通”概念既能保留與“職業”“專業”概念的分野,也避免了上述定義的含義與現實的矛盾。報告的特別亮眼之處還是在第三級教育中堅持使用“專業”取向概念的相關方案。一方面,相較于“學術”概念的含混與矛盾,“專業”概念的定義更為直白,如《牛津英語詞典》將之定義為“連結一項需要特別訓練或技能的工作,尤其是需要高層次教育的工作”。在這里,它與“職業”(vocational)概念清晰地區隔開,為其指代第三級教育計劃提供了適切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專業”不僅沒有“學術”那樣的概念專用性上的沖突,反而同時涵蓋了“特定專業行當以及職崗族系或產業版塊工作所需知識與技能”和“高層級教學、思考與學習”兩層意涵。更為巧妙的是,以“專業”指代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及專業考試、專業學位等資質的標準化分組,并不會與現有的ISCED2011框架和歐洲資質框架(EQF)等國際及區域標準相沖突,與通過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及專業考試、專業學位等資質以外的方式同樣可以進入專業行當也不構成邏輯上的矛盾,而是以簡捷性與務實性排除掉了純科學性與應用性以及某一專業行當與所有專業行當之間的模糊空間。當然,其中最具價值的部分仍然是對于才智繁雜性(intellectual complexity)的處理。ISCED2011標準化層級分組已經對基于共識的就讀期限及學科內容繁雜性程度作出規定,歐洲資質框架等標準化工具也已將同層級的才智繁雜性設定為是相同的,在這種情況下,避開就學術性與專業性、專業性與職業性、專業性與普通性之間困難到無解的才智繁雜性程度測量進行糾纏,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較為理想的一個做法。筆者認為,其中應還有對教育公平和技能習得規律的考量。

圖1 ISCED2011框架下《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評核報告的取向分組
二、專業取向第三級教育計劃的新圖譜
教育計劃的同一通道前后之間以及不同取向的教育計劃之間都應該是一個連續統一體,但沒有一個標準化分組圖譜可以將各國不同結構的教育與培訓系統涇渭分明地標注得一清二楚,因而采取一種務實的方法來對同一通道的層級進階和不同取向的對接轉換進行區分,是十分有益的。評核報告依此對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的進入與進階通道及其向繼續學習或勞動市場的過渡等進行了介紹,將專業第三級教育作為國家技能系統的關鍵要件進行了刻畫[6]。
大學同專業教育與培訓的聯系由來已久,中世紀大學就出現了某種專業訓練。13世紀的歐洲大學不僅教授“七藝”,而且教授法學、醫學和神學。然而,至19世紀中葉,大學變得專注于人文教育與純粹研究,“將專業準備留在了它們墻外”。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現代高等教育的出現帶來了從小型同質性大學向多樣化和越來越專業化的高層次學習系統的轉變。在19世紀,許多國家建立了具有專業聚焦的院校(如加拿大的多科技術大學、美國的基于大學的專業學院)。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來,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高等院校的使命和學習形式等方面實現了多樣化,一個重要方面的表現是高等職業及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的發展,包括設計及功能非常不同的教育計劃,如副學位、高等技術教育、專業學士資質和專業考試等,涵蓋范圍從兩年制第三級教育計劃到為提升現有從業者技能而設計的獨立考試。在院校使命的多樣化方面,應用科學大學與傳統大學并駕齊驅,一些歐洲國家專業第三級教育版塊的招生規模與常規大學旗鼓相當、不分伯仲。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常被看作是吸引非傳統學習者和促進社會流動的有效手段。當然,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建立了單獨的專業第三級教育版塊,美國等一些國家的應用、實務取向類教育計劃(如商學或烹飪藝術)是放在多目的院校(multi-purpose institutions)里,與物理、歷史這種聚焦單一的學術取向學科一起教授的。但是,即便是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或美國等維持和轉向一體化高教系統的國家,高教擴張及學生主體多樣化也伴隨著對勞動市場需求日益增強的敏感性。
在學士層級,許多國家開發了聚焦應用性、職崗取向(occupational-oriented)學習的教育計劃,在獨立層次院校或多目的院校(如應用科學大學、大學學院)中開設,代表了本科教育向職崗—專業學位聚焦的轉變。在提供數據的大部分國家中,持有專業ISCED6資質已經變得更為普遍。而在ISCED7層級的比較數據僅有12個國家提供,且基于各自對于教育計劃取向的定義。大部分國家將所有學生報告在“未定取向”教育計劃項下,而有些國家將所有教育計劃放在“學術”項下。法國在碩士層次專業取向學生的高份額是由于將工程、商學、法律、教育、醫學、藥學、牙科、產科等列入了專業取向,而大部分其他國家將相關教育計劃列為“學術”或“未定取向”。除了對法國、荷蘭、智利、立陶宛、盧森堡、西班牙和以色列相關項目的簡單提及,因數據及專業取向定義的局限,評核報告未有這方面的進一步分析。ISCED6—ISCED8層級的專業取向教育計劃標準化分組情況似與我國有很大不同。多樣化發展的另一個標志是,隨著許多要求比傳統3—4年大學資質更低崗位的出現,導向副學位或副學士資格的更短期教育計劃在英美等國得到了擴展。這些短周期第三級教育計劃通常不僅是通往入門層次工作的路徑,而且成為學士層級繼續學習的奠基石。第三級教育計劃專業版圖的另一個版塊是從職業高中教育與培訓演變而來的,并不來自傳統大學教育,有時與具有悠久歷史的“工長”(德語Meister,也作大師、巨匠解)資質技藝和營生有關,其相關形式包括1—2年的教育計劃或基于考試的資質(如工藝大師考試、專業考試)。即便是在過去的二十年,應用性和專業性教育計劃仍在不少歐洲國家得到成長:2000—2013年間,這類計劃的參與率在12個國家有所增長,西班牙報告的高等職業教育計劃招生數增長高達39%;應用科學大學的教育計劃數也在許多國家得到了實質性增長,奧地利的招生數增加112%,愛沙尼亞報告的專業高等教育增加30%,德國雙元制學習計劃增加57%。歐洲教育區的一項目標是,到2030年將第三級教育中的30—34歲人群份額擴大至50%,專業教育計劃有助于通過吸引那些對應用性學習形式感興趣者達到這一目標。
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在職業教育與培訓畢業生技能提升培訓、社會焦點技能培訓和現有勞動力技能更新培訓方面擔任關鍵角色。它有時是中等職業教育與培訓畢業生唯一能夠直接進入的教育版塊;在有些情況下,則是一些數據報告國家提供的進入“學術”高等教育的橋梁;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它也是取得進一步學習機會和進入工作世界資質及不斷自我更新知識與技能的必要途徑。在提供為進入勞動市場作初始性準備的教育計劃中,包括許多歐洲國家的短周期第三級教育計劃和專業學士計劃,年輕人壓倒性地占了絕大多數;在其它計劃中則以成人為主,如為提升現有專業人士技能和更新成人技能專門設計的專業考試。不同人群的教育與培訓需求存在差異,培訓的目的與形式也應各不相同,詳見表1。正如聯合國秘書長關于轉變教育的愿景聲明中所說,必須允許所有年齡段的人們通過焦點技能培訓、技能更新和技能提升學會做事[7]。基于工作的學習通常是專業第三級教育的一個要素,特別是在ISCED5層級,但不總是法定的。專業學士計劃常常包含強制性的實習,雙元制第三級教育計劃的數量也在增長。適切的以往或當前工作經歷常被認為是某種基于工作的學習。以往或當前具有工作經歷在第三級的學生中是普遍現象,特別是其中具有職業高中背景者也比普通教育背景者更可能已從事過高技能工作。根據該報告的數據,被調查的第三級教育年輕畢業生中有40%在該階段學習期間從基于工作的學習中獲益,顯示出學習計劃與工作世界的緊密聯系。在第三級學習中獲益于基于工作的學習的成人,比沒有此經歷者更可能有更高就業率,而長期(6個月及以上)有償工作安排能帶來最好的就業結果。

表1 焦點技能培訓、提高技能培訓與重塑技能培訓的相關區分
提供高層次技術、專業技能教育計劃及院校的發展出現在快速技術變革和勞動力市場被工作兩極化形塑的背景之下。常規任務日益被自動化替代,要求中等技能的工作在勞動市場重要性的降低伴隨著高技能要求(如工程師、醫師)和低技能要求職崗(如難以自動化的長者基本照護)的增加。根據相關預測,下個十年工作兩極化將會繼續,專業人士、技師和輔助性專業人士的就業增長將是最強勢的,經理人、服務及營銷工作者和初級職崗將有增長但會慢一些,而被看作中等技能的職崗(如技藝與相關營生交易工作者、普通職員和農技工作者)就業將下跌。在OECD國家,自動化將在接下來的年份取代14%的工作崗位并顯著重塑另外32%的崗位,重新創造的工作崗位也將與那些消失的崗位有不同的技能要求。這些對技能系統而言有多重的意涵:一是初始教育不再能為人們整個事業生涯尋求的一個職崗一勞永逸地作準備,而必須讓其具備尋求繼續學習的基本技能;二是技能系統須給追求高級職崗技能者(包括需要提升或重塑技能的成人)以成人友好型的方式提供適當學習機會,允許其基于先前的經歷填補技能組合的任何特定空缺,并以兼容其更多其它需求的方式開展學習。
評核報告在闡釋技術變革時代經濟社會對理想技能組合的新要求基礎上討論了對策方面的相關研究與思考。學習者不僅需要具備尋找第一份工作時所要求的技能和資質,還需要有適應終生事業生涯的變化環境和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進入勞動市場尋找第一份工作所需的技能及資質是重要的,以便一開始就快速順利過渡,對事業生涯前景有長期影響。有些勞動市場的趨勢降低了雇主提供在崗培訓的主動性,因而初始教育與培訓在提供普通教育同時讓年輕人具備特定專業取向技能的需求不斷提高。一個務實的方法(常常包括基于工作的學習)有助于在培養特定技能的同時發展寬廣的就業技能,如團隊合作與溝通。歐洲的雇主在錄用近期的高教畢業生時,將專業(或行業)以及人際技能的組合視為關鍵。工作場所提供了習得技術技能和通用就業技能的超強環境,學生可以從實際生活中學習、從熟悉最新技術和工作方法的專業人士處學習。同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普通教育可以幫助年輕人更好地具備工作與生活所需的個體適應變化環境的良好通用技能,以便既能尋求成功的事業生涯又能更好地參與社會生活,該觀點的論據是更為具體的知識與技能可以轉而于取得資質后在工作崗位上習得。
三、專業取向第三級教育體現的新理念
在ISCED2011提出的專業取向分組設想基礎上,《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評核報告通過與教育標準化分組相關核心概念的辨析和OECD相關國家專業第三級教育情況的介紹,闡釋了專業取向教育計劃的獨特性、增值性和高等性特征,彰顯了這一教育版塊的不可替代性、重要價值和應有地位以及相關新理念。
(一)確立了專業取向教育與培訓的獨特性
ISCED2011雖以取得國際共識的文件形式規定了“專業”與“學術”教育計劃的區分層級及大致范圍,卻并未提供任何定義。評核報告通過相關概念的辨析與詮釋提出了具體的、明確的定義方案,不僅避開了與“學術”的概念專用性的沖突,而且確立了自身的專有屬性,即其與一個特定專業行當和一個職崗族系或產業版塊專業行當的直接關聯。“三向度”高教分組中的“二向度”專業教育計劃分組定義較好地排除了與其它相關概念之間的模糊空間,而對于OECD相關國家專業取向教育與培訓情況的全面刻畫,進一步明晰了整個報告聚焦的這一主題概念的獨特內涵。“專業”概念的定義和相關介紹代表了ISCED2011提出“專業”取向分組后的最重要進展,也應是相關重要國際研究成果文獻中第一次對此作出規定性的解釋。
(二)揭示了專業取向第三級教育比較的增值性
哪種教育與培訓才有利于實現經濟社會所需混合技能的培養?幫助人們不僅為第一份工作而且為終生事業生涯及成功參與社會生活做好準備的最佳方式又是什么?是專業取向的教育計劃最適合于保障年輕人初次順利進入勞動市場,還是更具普通取向的教育計劃能使年輕人具備良好的通用技能以適應貫穿其事業生涯的新要求?而在第三級教育計劃中,又應該有多大比例將特定的職崗而非學術領域作為出發點?評核報告通過跨國數據的比較分析較好地解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問題并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改進跨國數據比較的質量有利于支撐和完善相關研究。其實,實踐中的教育計劃并不是涇渭分明的,所有專業教育計劃均有相當多的普通教育內容,特別是語數方面的基本技能,而普通及學術教育計劃也發展勞動市場的適切技能。但是,盡管與工作世界的緊密聯系對所有第三級教育均是重要的,卻對專業取向教育計劃尤其重要。
由此可見,“三向度”高教分組中的“二向度”專業教育計劃分組的比較數據,不僅彰顯了這一教育版塊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還追加了更多地認識該版塊自身重要價值和更好地認識與普通教育重要關系的雙重價值。
(三)明晰了專業取向第三級教育計劃的高等性
評核報告不僅明確指出了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高層級教學、思考與學習”的屬性,而且以“連結一項‘尤其是需要高層次教育的工作’”的界定將之與職業概念清晰地區分開。同時,還明確地將包括“三大最古老專業行當”在內的高層次專業學習領域歸屬于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之內,并拓展到了工程師、教師等專業行當以及其它高等應用性教育服務的專業行當。這樣一來,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的高等性本質屬性就躍然紙上了,而報告對于專業第三級教育計劃針對高層次技能(high-level skills)而非低端至中級(low-to-medium)層次的刻畫,則完全擺脫了ISCED1997有關5B范疇的尷尬定位。
四、專業取向理念對專業高職的新啟示
我國現有的高職教育限定于特定的層級和軌道,既不包括ISCED6層級的高等職業教育,也不涵蓋專業碩士與專業博士學位教育,與這些層級教育縱向交叉銜接和與普通教育橫向跨界貫通的制度化水平還不夠高。進入一個層級教育的院校、專業和學生要過渡到另一個層級尚有一定制度、技術層面的障礙,而進入一個軌道的院校、專業和學生也還不能輕松地轉換到另一個軌道。但是,技能習得的規律以及人才成長的路徑并不能被如此簡單設定,無論是先天的稟賦還是才能的潛質都需要通過完全不同的個體以不同的時機、不同的節奏與不同的方式去成就。不同層級的教育當然有學科內容的專門化程度及教育內容的復雜性程度區分,也有學習長度與學習形式的區分,但并無智商、社會身份等的限定,也不應在學習時機、節奏與方式上作出過于嚴苛的規定。教育要強調平等性公平、補償性公平,也要重視差異性公平,為非傳統學生和具有超常規需求的學習者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我們不僅要算學術型、應用型、技術技能型專業人才分類培養效率的小賬,還要算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效益的大賬,而這些各條戰線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并不能被早早地限定在單一軌道上,以事先規定好的時機、節奏與方式培養出來。不同個體對于理論知識、實踐技能、關鍵品質的習得與把握,并不能在特定層級的特定類別教育中一站式地完成,而是會有不止一次的反復、搖擺和頓悟,甚至還會有調整、轉向和逆襲。
我國不僅有勤能補拙、笨鳥先飛等群眾智慧,也有亡羊補牢、大器晚成等古老格言。掌握性學習的提出者布魯姆也告訴我們,如果提供適當條件,所有的孩子都能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學習,只不過他們需要不同的時機、節奏與方式[8]。他隨后又說,能夠達到極高才智的那幫人實際上是相當廣泛的,在運動、藝術和學術上到達最高層級的是那些努力刻苦且遇到有挑戰性卻充滿感情的父母和頂級老師的人。在技術變革及經濟社會發展使一勞永逸的教育不再可能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在一個更理想的層次上重新架構服務技能型社會的終生學習體系,讓具有不同先天稟賦與才能潛質的人群都能在一個開放融通、進階通道暢通、跑道轉換不再那么艱難、任何時候學習都不會過晚、中途因故離開也無需過于擔心再無反悔機會、盡可能地排除了人為教育與職業偏見的定制環境中更加自由、方便地自主選擇,更加自如、自在地發展,讓學習方式與節奏選擇的高利害性明顯降低,讓升學競爭不再成為太多人的畏途,讓前往理想專業行當的通道不再遙遠[9]。這一理想定制環境并非遙不可及,考試評價制度改革的加快推進和相關政策的持續引導將有可能為其提供堅實支撐,當然也需要社會各方的理解與支持。以教育類型化問題為例,研究者需要有對于教育類型化特征的分析與理解,管理者需要有對于不同教育類型規律性的認識與把握,而學習者更需要從內容復雜、結構繁雜、體系龐雜的設計中一目了然地看清自己的理想路徑與可選空間。盡管社會大眾總會對教育制度設計與政策框架有各自理解,但專業的理想設計不可或缺。
那么,這一理想設計的設計原則應該是什么?是將普通與職業、科學與技術、知識與技能分得一清二楚,還是著眼于它們之間的聯系與整合?從目前的政策取向與實踐倡導來看,無疑是傾向于融合融通、明確地主張貫通銜接,但在如何融合融通、貫通銜接方面還有不少功課要做。這些功課包括要弄清誰與誰融合貫通、在什么上面融合貫通、如何去達成這樣的融合貫通。最終,要能積極吸收ISCED2011這一代表標準化教育分組國際共識最新權威文件和OECD《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評核報告等國際最新研究成果的有益經驗,以專業取向相關先進理念為指導,并結合自身實際,建立完善我國的專業高等職業教育體系。
(一)誰與誰融合貫通: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統籌設計專業取向高等教育
在高教多元化、高教服務提供者和高教服務對象多樣化背景下,教育計劃應該如何優化?除了依循管理便捷邏輯、社會實踐邏輯,首先要遵從的是科學專業邏輯。關于這一點目前已有職業與普通教育的分類,研究生教育階段有學術與專業的分野,也有學者提出科學、應用、職業等的區分。但從ISCED2011以及OECD《前往專業行當的通道》評核報告的最新研究成果來看,我們的不少研究仍停留在對于ISCED1997的理解,亟待更新相關理念,對教育計劃的取向甚至院校分類依據等進行進一步深入思考,為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的優化提供參考。這樣的思考不應只局限于現有相關層級與類型專業的必要調整,也應在院校定位及使命上作出相應的完善,更要在專業取向高等教育的一體化統籌設計上積極探索、大膽嘗試,甚至應當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可能性的討論。
目前可以嘗試推動的職業教育類型定位優化方案具體建議包括:在各層級普通教育與職業、專業取向教育一體化謀劃的思路下,將高職教育加入專業第三級教育之中,增加本科專業學位范疇,將整個專業學位體系納入專業第三級教育進行一體化統籌設計,為職業取向教育和中等后專業取向教育上下對接、各層級普通教育與職業專業教育左右貫通作出更多制度化安排。從根本上來看,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目的就是要通過調整各級各類教育之間以及教育系統內外的關系,將職業教育放在更加合理的位置上。目前職業教育在教育系統內外均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尚未真正得到系統內外各方的足夠重視,這與其在經濟社會發展及人才成長中的作用是不相稱的。這一問題應當通過制度重塑和相關方面的調整較好地予以解決。
(二)在什么上面融合貫通:確立專業技能層次結構,做好專業高職教育貫通銜接
我們的融合貫通不能只停留在政策主張上,還需要落地,那最終要落在哪里呢?筆者認為,應落在技能身上,當然這是包含了知識、能力甚至態度、價值觀的廣義的技能。目前,我們對于技能的層次、類型等的認識還十分局限,技能型社會的技能治理系統架構仍亟待完善,支撐與生命一樣長、與生活一樣寬、與人生一樣高的普惠、普適、普優的終生學習理念更是遠未完全落實到我們的培養目標及方案之中。當務之急是要正確理解與職業專業行當密切相關的有針對性專門技藝(specific skills)、奠基性的基本技能(literacy)和包含各種通用技能(generic skills)的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ies)之間的關系,并在學科內容及教育內容中分層次地具體落實好這些技能的要求,詳情見圖2。這是確立專業層次結構的主要依據和做好專業高等職業教育貫通銜接的基本前提。不同層級及不同取向教育機構及教育計劃之間要有一體化設計和相應的分工與側重,以專業崗位技能要求的層次關系為依據,以學科內容專門化程度及教育內容復雜性程度為主線,動態對接專業行當崗位技能要求,及時調整專業人才培養規格,綜合考慮知識、專門技能及通用技能方面的合理組合,不斷完善培養方案,加強課程一體化設計,將教學內容按不同層級要求做好接續、重構和拓展工作,落實交叉性、整合性、融通性,解決好可能出現的相互脫節、簡單堆積和重復教學等問題,以真正實現越級銜接和跨界貫通。

圖2 支撐技能型社會和終生學習體系構建的技能培養結構關系
做好專業高等職業教育貫通銜接,可以根據ISCED2011的規定對不同層級的技能聚焦,結合細分專業學習領域的技能要求,進行相應的定位和設計[10]。教育計劃的取向在ISCED2—ISCED5層級上已有ISCED2011作出區分,目前在ISCED6—ISCED8層級上也有了OECD的定義方案。按照ISCED2011的規定,教育計劃在初級中等層級就存在職業取向,一般為希望直接進入低技能或半熟練技能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提供選擇,屬于第一梯級的職業教育。ISCED3教育計劃同時為準備進入高等教育和/或提供切合就業技能服務,為學生提供比層級2更加多元、專門和深入的教學。ISCED4中等后非高等教育計劃也為進入勞動市場和高等教育作準備,為完成層級3但未授予升入高等教育或進入就業的資質的個體提供所需的非高等教育資質。ISCED5或者短周期高等教育計劃提供專業的知識、技能和勝任力,典型地屬于基于實踐的、具有職崗針對性的并為進入勞動市場作準備的,同時也提供進入其他高等教育計劃的通道。ISCED6學士或同等層級的教育計劃提供中級學術和/或專業知識、技能與勝任力,屬于典型的基于理論的,但可以包括實用的構件,受前沿研究和/或最佳專業實踐的實質影響。ISCED7碩士或同等層級的教育計劃提供高級學術和/或專業知識、技能與勝任力,具有實質性的研究要件,屬于典型的基于理論的,但包括實用的構件,受前沿研究和/或最佳專業實踐的實質影響。ISCED8博士或同等層級的教育計劃主要被設計帶來高級研究資質,專注于高級研習和獨創研究,典型地由研究取向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博士教育計劃同時存在于學術和專業領域。
國際上有關技能的跟蹤研究較多,除了歐洲參考框架2006與2018提出的八項關鍵能力,還有美國的21世紀技能、加拿大的綜合學習指數和澳大利亞的就業技能等能力框架研究。此外,歐洲工會聯合會(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等組織早在2002年就制定了“能力與資質終生發展的行動框架”,并進行了追蹤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20年發布了《第三級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新資質與能力趨勢》(Trends in New Qualifications and Competencies for TVET)報告,從歐洲視角闡釋了對于連結創新與學習的看法;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10月召開的以“追求卓越:形塑技能發展和加強第三級職業教育與培訓全球協作”為主題的論壇上,又呼吁第三級職業教育與培訓院校為“3I”作出貢獻,即識別(identifying)新資質與能力、整合(integrating)這些資質與能力進入課程及培訓法規、以創新培訓方式落實(implementing)這些資質與能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也持續關注工作世界的技能需求,在其發布的《未來工作調查2023》(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報告中,介紹了2023核心技能的跟蹤情況,反映了批判性思維、分析性思維及技術基本技能等方面技能需求的趨勢,預測了2023—2027年頭部產業的技能要求增長情況和技能重塑、技能提升需求以及技能版圖演進的相關情況,此外還有AI戰略和“軟”技能的行業偏向等方面調查情況[11]。OECD最新發布的《OECD技能展望2023》(OECD Skills Outlook 2023),也對一個服務更有韌性、更加綠色和數字化轉型的技能系統進行了分析[12]。
(三)如何達成融合貫通:強化專業技能系統治理,滿足技能型社會的技能需求
首先,要整合教育、財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市場監管等各方力量,大力吸收行業企業和社會專業力量參與,建立完善專業技能系統一體化治理的管理架構。這一架構是達成融合貫通的重要前提。同時,相關的專業系統是融合貫通的技術支撐,要加快構建成人基本技能調查系統和勞動力調查系統等基礎設施,開展類似于PIAAC和EU-LFS的相關調查。如,歐盟按照高技能白領、高技能藍領、低端—中等技能白領、低端—中等技能藍領等四大范疇進行的勞動力調查,就對技能系統治理有很好的助益。最后,要切實推動產教融合落實落細。行業企業的參與、基于工作的學習和實務方面的培訓是體現專業第三級教育與培訓真正價值的重要方面,也是學生習得專門技能和通用就業技能的重要方式,還是滿足技能型社會未來技能需求的重要途徑,產教融合是融合貫通的必由之路。總之,強化專業技能系統治理,完善技能系統相關基礎設施建設,落實教育系統技能培養的有效策略,應成為我們應對技能型社會挑戰的主要戰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