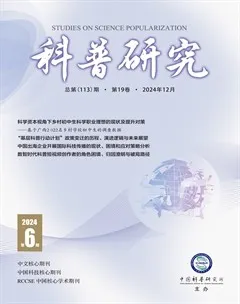科學資本視角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現狀及提升對策








[摘" "要] 初中階段是青少年科學職業理想發展的關鍵時期,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研究是科學教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話題。其中,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研究更是學界和社會的重點關切。已有研究發現,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表現不佳。本研究引入科學資本概念工具,對廣西2 022名鄉村學校初中生開展問卷調查,利用有序邏輯回歸和邊際效應分析,探查科學資本不同要素對我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現狀的影響效果。研究發現,科學資本水平對我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起到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擁有越高科學資本的初中生在科學職業理想上的得分越高。具體而言,科學文化資本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作用呈現兩重性,科學社會資本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科學相關行為與實踐維度發揮的影響則不甚顯著,甚至個別要素出現負面影響。根據調查結果,本研究從科學資本的3個維度分別提出提升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針對性對策。
[關鍵詞]科學職業理想" "鄉村科學教育" "科學資本
[中圖分類號]" G633.98;N4 [文獻標識碼]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6.001
科技人才是推動國家科技創新與社會進步的第一資源,中學階段是科技人才早期培養與成長的關鍵時期[1]。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科學教育要“培育具備科學家潛質、愿意獻身科學研究事業的青少年群體”[2]。因此,培養學生學習科學、從事科學的興趣與動機是科學教育的重要目標。研究證明,13歲左右是培養學生科學興趣與科學職業理想的關鍵時期[3],在我國,13歲學生正經歷著從小學綜合科學向初中更為困難的分科科學學習的轉變,正處于科學興趣與期望的初步形成期。因此,初中階段青少年的科學職業理想培養值得被教育者與研究者重點關注。
然而,目前我國中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狀況并不樂觀,我國參與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測評的學生中,持有積極科學職業理想的學生占比在2015年和2018年兩輪測評中均低于OECD平均水平[4]。尤其是相比城市學生而言,我國鄉村學生在測評中顯現出對科學的認識論信念較低、30歲時愿意從事科學事業的學生人數少、對科學的自我效能感較為消極等問題[5-6],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城鄉學生在科學職業理想上的分化。在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關注我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現狀并提出針對性提升對策,對于構建高質量、公平、可持續的中國特色科學教育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鄉村學生科學職業理想低下的問題并非中國獨有,國際學界對于鄉村學生科學職業理想現狀及其原因的相關探討也有很多。其中,英國學者阿奇爾(L. Archer)在弱勢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有廣泛影響力,他構建的“科學資本”概念框架是“一種用來整理與科學相關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的概念性工具”[7],將科學職業理想相關的影響因素整理為科學相關的文化資本、科學相關的社會資本和科學相關的行為與實踐3個方面[8],為揭示弱勢學生群體在科學職業理想形成中的劣勢情況提供了一個整合性的分析視角。
科學資本概念起源于英國,近10年在國內外科學職業理想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有學者指出,科學資本在不同國家教育環境中對學生科學職業理想的解釋力可能存在差異,需警惕“歐洲中心”的概念與推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9]。因此,科學資本是否適用于解釋我國鄉村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仍有待更多的本土證據支撐。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我國鄉村初中生為研究對象,基于問卷調查法呈現我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現狀,分析科學資本的不同維度對于現狀的具體影響,并探索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提升對策。
1文獻回顧
1.1科學職業理想
科學職業理想(Science Career Aspirations)也有譯為科學職業抱負,是指在未來想繼續學習科學知識、科學相關專業或者從事科學相關職業的理想[10]。大量研究證明,中學階段的青少年正處在接觸科學、塑造科學職業理想的關鍵時期[11-12],青少年中學時期的職業偏好及期望對于其成年后的職業選擇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低科學職業理想往往預示著低科學職業選擇,而具有高科學職業理想的學生獲得科學學位和選擇科學職業的可能性往往比其他學生高出3~4倍[13-14]。因此,擁有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是青少年日后從事科學職業的基礎。
科學職業理想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以往對于弱勢學生群體職業理想的研究多側重于關注其個人背景因素的影響。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數據顯示,學生的職業理想與其學校的資源水平有關[15]。國內相關研究發現,鄉鎮中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顯著受到學生家庭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父母職業、科學成績的影響,這種影響遠高于來自城市中學的學生[16]。從社會學研究的視角看,相較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中低水平的學生來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學生未來選擇從事科學研究或科學相關工作的意向更強烈。家庭經濟地位的差異,以及家庭對教育資源截然不同的占有和利用策略,使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最終導致階層分割[17],進一步擴大不同階層學生在資本積累上的差異。優勢階層的家庭通過再生產策略,即借助家庭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家庭慣習再生產出較高的科學資本與科學職業理想,這種策略充分發揮了家庭教育的優勢,但經濟制度、學校教育等因素,使得這種優勢再生產在不平等的軌道上運作,這種不平等既是再生產的一個環節,也是再生產的結果。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優勢家庭實現了對學生科學資本的擴大再生產,階層地位進一步固化。因此,優勢家庭的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未來選擇科學職業的意愿會更強烈。
1.2 科學職業理想與科學資本
科學資本(Science Capital)源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是布迪厄“資本”概念系統之下的一個概念。阿奇爾最早在2012年的ASPIRES項目中運用科學資本理論進行實證研究,他將科學資本的概念定義為,科學資本不是一種單獨類型的資本,而是一種用來整理與科學相關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的概念性工具,特別是那些有可能為個人或群體提供使用或交換價值的資本,以支持和加強個人或群體在科學方面的獲得感、參與感和分享的意愿[18]。科學資本的目的是幫助人們了解科學相關的資源如何在社會中不均衡傳播,以及這種不均衡傳播對青少年接觸、參與和從事科學的影響。在阿奇爾提出科學資本概念以后,有學者對2015至2021年間運用了該理論框架發表的文章進行梳理與綜述,發現51篇文章中有33篇來自英國、6篇來自美國,僅有1篇來自中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我國對于該理論的關注與應用還遠遠不足[19]。在已發表的科學資本相關研究中,大多數體現出了對科學學習中的“弱勢群體”的關注,如女性、少數族裔以及偏遠鄉村地區學生的科學學習資源配置等問題。我國現階段的城鄉科學教育教學資源和水平仍存在明顯的不均衡,本研究以科學資本為視角聚焦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具有獨特意義。
國外諸多研究已經證明了科學資本與中學生科學職業理想的相關性,德威特(J.Dewitt)等人于2016年分析了英國弱勢地區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發現相較于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科學資本在解釋學生是否選擇科學職業上更具決定性影響[20]。國內也有學者基于科學資本探討了我國西部地區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發現相比持有中、低科學資本的學生,持有高科學資本的學生更傾向于從事科學相關職業,且科學資本對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具有群體差異[21]。然而,也有學者通過中、英學生在PISA國際測評數據的對比分析指出,相比于中國學生,科學資本對于英國學生的科學職業理想更具解釋力[9]。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科學資本視角下,我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現狀如何?影響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關鍵科學資本要素有哪些?這些要素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效果如何?以及從科學資本的視角來看如何幫助鄉村初中生形成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
2研究設計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聚焦我國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情況,于2023年9月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選取了3個縣鎮,包括兩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及1個國家城鎮化試點縣,并于每個縣下屬鎮分別隨機抽樣3所鄉村中學,共抽取9所中學,在每所學校初一年級隨機選取5個樣本班級,并通過問卷調查法收集樣本班級學生的基本信息、科學資本情況和科學職業理想情況。
2.2研究工具
科學資本測量方面,阿奇爾等人于2015年構建的科學資本測量工具是后續許多研究的基礎,該工具將科學資本劃分為科學相關文化資本(Science-Related Cultural Capital)、科學相關社會資本(Science-Related Social Capital)、科學相關行為實踐(Science-Related Behaviors and Practices)。其中,科學相關文化資本包括科學素質 、科學態度與偏好、關于科學在勞動力市場中可轉移性的象征性知識;科學相關社會資本包括認識從事科學職業的人、父母科學資歷和與他人談論科學;科學相關行為實踐包括科學相關的媒體消費和校外科學活動參與。基于該工具框架,本研究共形成了包括31個題項的科學資本量表(見表1)。經信效度檢驗,量表整體與一級維度的3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均高于0.7,量表所有題項的因子載荷在0.51~0.85之間,符合教育測量學要求,可以用于數據分析。因此,鄉村初中生在這13個維度、31個題項上的具體得分之和代表了其擁有的科學資本,參考德威特等研究者對科學資本水平的分組方式[20],本研究根據得分高低將科學資本得分(分值范圍為13~65分)平均劃分為3組:低科學資本組(13.00~30.16)、中科學資本組(30.17~47.83)、高科學資本組(47.84~65.00)。
同時,本研究通過4道李克特量表題衡量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分別是“我對科學相關的職業感興趣”“我想在未來學習科學相關的學科或專業”“我未來想要從事科學相關的職業”“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適合從事科學的人”。經信度檢驗,該量表整體的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53,量表較為可靠。在對缺失數據進行均值替補后,同樣根據量表的得分情況將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得分由低到高劃分為3組:低科學職業理想、中科學職業理想、高科學職業理想,從而將因變量轉化為一個分類變量。
本文為了對科學資本的影響進行更全面的衡量,引入了性別、民族、綜合學業成績、是否留守兒童等指標作為控制變量,以最大程度地控制誤差,確保最終模型結論的有效性。
3數據分析
3.1樣本基本情況
本次問卷調查最終回收問卷2 159份,剔除其中空答率50%以上的問卷樣本,最終剩余2 022個樣本,有效率為93.7%。其中,少數民族學生、留守兒童學生占比高,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2所示,參測學生在性別分布上基本均衡,通過入學后綜合成績的班級排名反映學生平時的學業表現情況,呈現出的排名情況基本符合正態分布。
通過進一步對表2進行整理分析,發現樣本具有以下突出特點:(1)少數民族學生占比高。由于選取的鄉村學校地點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最終回收的學生樣本中少數民族學生的占比近55%,漢族學生占比反而偏低。(2)留守學生數量多。父母雙方進城務工導致的大規模留守兒童是我國鄉村學校中,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樣本參測學生中分別有30.1%和27.9%的單親留守兒童和雙親留守兒童,留守學生數量龐大。(3)學生父母大多未接受過高等教育且從事非精英職業。根據參與測試的鄉村初中生的父母受教育情況和從事職業調查,發現超67%的學生父母未受過高等教育,同時,參考邊燕杰對“精英職業”的分類,本研究對學生父母所從事的職業進行了整理[22],精英職業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與工作人員”(政治精英)、“企業/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經濟精英)、“教師、工程師、醫生、律師”(技術精英);而非精英職業包括“技術工人(包括司機)”“生產與制造業一般職工”“商業與服務業一般職工”“個體戶”“農民”等。依照該分類標準,本研究樣本中超過六成學生的父親或母親從事的是非精英職業或處于無業狀態,總的來說,鄉村青少年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處于弱勢地位。(4)學生的未來教育期望整體仍處于積極水平。盡管在人口學變量描述上,鄉村初中生的學校、家庭背景處于相對弱勢的情況,但學生對自身未來的教育期望仍然較高,48.5%的學生期望自己能夠在完成中學教育后繼續修讀大專或本科,甚至有高達42.9%的學生希望自己未來能夠進入碩士、博士研究生學段的學習,這為培養其科學興趣與科學職業理想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3.2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資本及科學職業理想現狀
本研究將鄉村初中生在科學職業理想與科學資本水平的分布情況整理為表3,由表可見,樣本中大部分鄉村初中生未能對科學職業產生高水平的興趣及期望,持有高科學職業理想的學生占比不足15%。
同時,表3還呈現出科學資本在我國鄉村初中生中的分布極其不均衡的現象,僅有4.8%的鄉村初中生擁有高水平科學資本,絕大多數初中生擁有的科學資本分布在低到中的水平。
由于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和科學資本水平均屬于有序分類變量,所以可以基于Kendall’s tau-b相關系數判斷科學資本水平和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相關性,經檢驗,科學資本水平與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肯德爾相關系數為0.540,在0.01級別表現出顯著相關。為了進一步呈現科學資本高低與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分布的規律,本研究將數據進行分類整理(見表4),發現在擁有低科學資本的650名初中生中,其中71.7%的學生也對應擁有中或低水平的科學職業理想,而隨著擁有的科學資本的增多,更大比例的學生分布在了中科學職業理想和高科學職業理想群組中,科學資本的增多和科學職業理想的增長存在著對應的規律關系。
4科學資本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作用
4.1 科學資本各要素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有序邏輯回歸
為進一步分析不同要素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具體影響作用及影響程度,在對模型進行平行性檢驗后,本研究對鄉村初中生在科學資本各要素上的標準化得分與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做有序邏輯回歸,所得結果如圖1所示。
根據圖1的分析,在科學相關文化資本維度,對待學校科學的興趣(A1)、參與非正式科學的偏好(A2)、科學工具性價值認知(A3)、科學自我效能感(A4)4個要素與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意味著鄉村初中生在這些要素上擁有越多的文化資本,則越有可能形成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在科學相關社會資本維度,他人對我的科學身份認同(B1)、他人對我科學學習的支持(B2)、感知到的科學教師關心(B3)3個要素均對因變量起著顯著的正向影響,意味著他人對其科學身份認同越高、科學學習的支持態度越強、科學教師對其學習越關心,均能夠幫助其形成更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而在科學相關行為實踐維度,僅有接觸大自然(C1)要素與科學職業理想水平正向相關。對比各要素的標準化估計系數絕對值大小,本研究發現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起到主要正向影響作用的要素分別是參與非正式科學的偏好(A2)、他人對我的科學身份認同(B1)、他人對我科學學習的支持(B2)。
另外,我們也觀察到一些要素與因變量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呈現出顯著負相關的現象,分別是看待科學的態度(A5)、參觀科技場館頻率(C2)、閱讀科學課外書籍頻率(C4)3個要素,當鄉村初中生在這些維度上得分升高,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反而呈現降低的趨勢。
由此可見,雖然從整體分布趨勢上看,擁有高科學資本的鄉村初中生更傾向建構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但是科學資本各組成要素對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影響卻不是單一的。為解釋這種復雜的影響作用,本研究在有序邏輯回歸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科學資本各要素對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影響作用的邊際效應,并在下文中按照科學相關文化資本、科學相關社會資本和科學相關行為實踐3個維度分別對數據結果展開細致的討論與分析。
4.2 科學文化資本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作用呈現兩重性
文化資本是代際間傳承的文化傳統、習俗、知識、性情等。科學相關的文化資本則能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賦予人們持久的科學氣質,通過學習科學知識與訓練科學技能從而提升科學素養 ,將科學內化為人們根深蒂固的個人習性[23]。在西方國家的過往研究中,科學文化資本被認為是影響科學職業理想的核心要素,但是本研究通過邊際效應分析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科學文化資本對我國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影響作用呈現出兩重性,即一部分要素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另一部分要素表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作用(見表5)。
科學文化資本的正向影響作用表現為,初中生對待學校科學的興趣(A1)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概率顯著降低4.3%,被預測為中科學職業理想、高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分別顯著提升1.6%、2.7%;參與非正式科學的偏好(A2)、科學工具性價值認知(A3)、科學自我效能(A4)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概率分別顯著降低11.4%、4.1%和2.7%。
而鄉村初中生看待科學技術的態度(A5)對其科學職業理想呈現負向影響作用,該要素得分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概率反而上升2.5%,被預測為中科學職業理想、高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分別降低0.9%、1.6%。
本研究中A5的得分由若干個量表題得分組成,例如“科學和技術對(人類)社會很重要”“科學和技術領域正在發生著許多可喜的事情”等,該要素的得分呈現了學生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態度傾向。根據上述分析,鄉村初中生在該要素獲得越高分、越認可科學的重要性,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反而越低。這一研究發現并非首次出現,有學者認為在科學學習環境中,弱勢學生會明確區分“喜歡科學”和“喜歡從事科學”兩個概念,對科學的興趣與認可并不能直接使弱勢學生產生科學職業理想[24]。因為弱勢學生相對更難在科學學習中構建積極的科學身份與自我效能感,從而幫助其將科學興趣轉化為自己的職業理想并付諸行動。
以本研究中的鄉村初中生為例,他們對于科學及科學相關職業的了解大多數源于間接經驗,而缺乏如參觀科學實驗室、與科學相關職業的人交談等直接經驗,因此許多鄉村初中生對于科學的認識是抽象且遙遠的,即使能通過教科書、新聞媒體等途徑認識到“科學很偉大”“科學很重要”等模糊的觀念,但最終這些觀念反而更容易導致其產生“科學過于重要而不適合我這樣的人”的消極身份認知。
4.3 鄉村初中生在科學學習中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對其科學職業理想具有積極影響
科學社會資本方面,各要素均呈現出對科學職業理想的顯著正向影響(見表6)。他人對我的科學身份認同(B1)得分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顯著降低10.9%,被預測為中科學職業理想、高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分別顯著提升4.1%、6.9%;他人對我的科學學習支持(B2)得分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顯著降低5.7%,被預測為中科學職業理想、高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分別顯著提升2.1%、3.6%;感知到科學教師關心(B3)的得分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顯著降低3.0%,被預測為中科學職業理想、高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分別顯著提升1.1%、1.9%。
這意味著鄉村初中生在科學學習中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均能夠在其科學職業理想建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這種社會支持包括周圍人認可我的科學身份、周圍人支持我的科學學習、科學教師對我的關心。期望價值理論認為個體的期望價值受到對勝任力的感知、個體目標和自我圖式、對他人態度及期望的感知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在以往針對弱勢學生群體的科學職業理想研究中,研究者們對于城鄉差異、重點與非重點校、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關注較多,但根據期望價值理論,以上這些因素并不能對個體的主觀職業理想產生直接作用,個體所感知到的環境中“重要他人”的態度、期望、信念和行為才是關鍵,這些因素通過作用于個體職業選擇的期望價值影響其職業理想的形成。本研究結果也同樣證明了社會支持能夠彌補弱勢學生在其他科學資本維度所存在的劣勢,促使學生形成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
4.4鄉村初中生參與非正式科學實踐對其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不甚顯著甚至出現抑制作用
根據邊際效應分析結果,科學相關的行為與實踐方面各要素對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職業理想呈現不顯著或低顯著的相關性(見表7)。鄉村初中生接觸大自然(C1)、參加科學社團活動(C3)和瀏覽科學媒體(C5)的活動頻率并未呈現出與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顯著相關,意味著即使鄉村初中生更多地參與上述活動,也并不能使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提升或降低。甚至在參觀科技場館頻率(C2)和閱讀科學課外書籍頻率(C4)兩個要素中,鄉村初中生得分每提升一個單位,學生被預測為低科學職業理想的概率反而分別提升1.5%、1.8%,呈現出負向的影響作用。
盡管以往理論和研究都表明,參與非正式科學實踐能夠支持中學生發展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但本研究似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果,發現鄉村初中生參與非正式科學實踐活動的頻率對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影響效果甚微,部分科學實踐甚至反而抑制了他們形成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
這一研究發現并不是在否定非正式科學實踐活動的意義與價值,恰恰相反,我們呼吁加強對弱勢學生參與非正式科學實踐活動的關注與反思。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非正式科學學習比一般課堂的正式學習更依賴軟硬件環境的作用,非正式學習的效果受到更為復雜的因素影響。以科技場館的參觀學習為例,有研究發現青少年在科技場館中的學習受到性別、文化信仰、先驗知識與能力、身份認同、話語形式、輔助支架以及活動形式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25]。對于鄉村青少年而言,在上述條件未能達成時,參觀經驗反而可能抑制青少年發展科學興趣,呈現出參觀科技場館頻率(C2)越高,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反而下降的分布趨勢。
因此,僅僅為鄉村初中生提供非正式科學實踐的機會、提升其參與非正式科學實踐活動的頻率,并不能直接促進其構建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鄉村科學教育應著力于打造更具公平性的非正式科學學習空間,切實提升科學實踐活動的有效性。
5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5.1.1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水平現狀與分布規律
從科學職業理想的整體水平上看,本研究中的大部分鄉村初中生未能建構高水平的科學職業理想,中低水平科學職業理想分布的學生占比分別為57.1%和28.2%,處于中等水平科學職業理想的初中生居多。同樣,鄉村初中生的科學資本水平趨于低水平分布,僅有4.8%的參測初中生擁有高水平的科學資本。
本研究在對科學職業理想與科學資本做交叉分析后發現,鄉村初中生科學資本的增多與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升高存在著對應的規律關系,擁有中、高科學資本水平的青少年大部分在科學職業理想水平的得分上也分布在中、高水平,這為進一步探討科學資本對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提供了基礎。
5.1.2科學資本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作用
(1)根據有序邏輯回歸結果,從總體上看,鄉村初中生擁有的科學資本越多,越可能建構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這與我國已有相關研究的發現一致[21]。其中,發揮關鍵影響作用的科學資本要素依次為參與非正式科學的偏好(A2)、他人對我的科學身份認同(B1)、他人對我科學學習的支持(B2)。
(2)科學文化資本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作用呈現兩重性。一方面,初中生對待學校科學的興趣(A1)、參與非正式科學的偏好(A2)、科學工具性價值認知(A3)、科學自我效能感(A4)對其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另一方面,研究發現鄉村初中生看待科學技術的態度(A5)對其科學職業理想呈現負向影響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弱勢學生容易形成消極的科學身份認知與自我效能感,從而使其難以將對科學的認可轉化為自身科學職業的期望。
(3)科學社會資本對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水平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研究證明,鄉村初中生在科學學習中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均能夠在其科學職業理想建構中發揮積極作用,這種社會支持包括周圍人認可我的科學身份、周圍人支持我的科學學習、科學教師對我的關心。科學相關的社會資本能夠彌補弱勢學生在其他科學資本維度所存在的劣勢,促使學生形成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
(4)科學相關行為與實踐維度的各要素對鄉村初中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不甚顯著,參觀科技場館頻率(C2)和閱讀科學課外書籍頻率(C4)兩個要素甚至呈現出負向的影響作用。這呼吁研究者加強對于弱勢學生群體參與非正式科學實踐活動有效性的關注,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科學實踐空間。
5.2對策建議
5.2.1科學文化資本:營造科學氛圍,促進鄉村青少年對科學的價值認同
本研究發現,科學文化資本中的大多數要素都對鄉村青少年的科學職業理想起到正向影響作用,因此,通過營造平等的、崇尚科學的文化環境,豐富鄉村青少年的科學文化資本,能夠促進鄉村青少年形成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
學校科學在鄉村青少年理解科學本質、發展科學身份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學校應當成為豐富鄉村青少年科學文化資本的主陣地。根據斯蒂芬尼·克勞森(Stephanie Claussen)和約納坦·奧斯本(Jonathan Osborne)的劃分,學校科學主要以3種形式向青少年提供文化資本:傳授的科學知識本質,培養的科學技能與思維,以及提供的科學制度化資本(Institutionalized Capital)的價值信息[26]。
一方面,鄉村學校科學所傳達的科學知識、技能與思維方式應該符合弱勢學生的文化價值,展現出對弱勢學生的包容性。有國外經驗發現,向鄉村學生證明他們的文化如何反映在科學中,或是幫助鄉村學生感受科學技術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所帶來的效益,都可以促進鄉村學生參與科學[27]。具體來說,鄉村學校可以通過科普讀物、媒體突出宣傳出身鄉村文化背景的科學家故事,讓鄉村學生產生積極的科學身份認同和自我效能,也可以聯動本土科技企業開展校園宣講或企業參觀,幫助鄉村學生理解科學技術對本地生產、生活的效益價值。
另一方面,幫助鄉村青少年理解科學作為制度化文化資本的價值對于培養其科學職業理想是至關重要的。制度化文化資本指的是學校等單位授予的學位、稱號,是對個體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制度認可與保障[28]。科學知識與學歷在勞動市場具有較強的制度價值,而在弱勢學生的家庭慣習中缺乏文化資本幫助他們理解這種價值,因此學校科學提供科學制度價值的相關信息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改善弱勢學生在科學教育中經歷的“象征性暴力”。科學教師應該在課堂中強調科學知識在勞動市場中的制度價值,包括如何通過獲得科學學位和資格證書來提高個人的職業前景和社會流動性。同時,學校還可以通過舉辦講座、研討會和職業規劃活動,邀請科學家和行業專家分享他們的經驗和見解,營造崇尚科學、熱愛科學的校園文化氛圍,促使鄉村青少年認識到科學學習的外部價值、形成科學職業興趣。
5.2.2科學社會資本:家校社聯合,支持鄉村青少年構建科學身份
根據本研究結論,鄉村初中生在科學學習中感知到來自家庭、同伴、教師等“重要他人”的支持非常關鍵,能夠組成他們的科學社會資本并支持其發展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通過有效整合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資源和力量,為鄉村學生提供一個“強支持”的積極科學學習環境,幫助他們構建科學身份、培養科學興趣和科學職業理想,進而促進其個人成長和職業發展。
家庭方面,以當地政府、社區、科普機構和鄉村學校為支點,積極組織科學家庭教育課程、工作坊和家長會活動,幫助家長理解科學的基本概念及其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提升家長的科學素養和意識,促使他們更能支持孩子的科學學習。同時,基于學校科學的課后服務項目深入推廣家庭科學實驗和活動,例如通過家庭科學夜等活動增強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讓孩子們能在家庭環境中體驗科學的樂趣和意義,形成支持性的家庭科學學習氛圍。
學校方面,促進、組織學生組建科學類學生團體,包括科技類社團、科學興趣小組、科學研學團等多種形式,為鄉村青少年構建支持其科學學習的同伴環境與支架。學校應強化對學校科學興趣團體的支持、管理和規劃,通過對學校已有科學實驗室、活動室等場地的規劃、分配,為學生活動提供場地支持,并設立科技輔導員為學生團體提供專任的指導老師,鼓勵鄉村學生以團體的形式參與科學實踐、交流科學職業、發展科學職業興趣。
社會方面,通過廣播、海報、短視頻等大眾媒體方式,在鄉村加強科學普及宣傳,提升全民科學素質,讓更多鄉村居民認識到科學的價值,從而能夠形成支持青少年科學學習社區環境。同時,籌建、成立鄉村科普支持專項資金,以社區科學中心、科技場館為支點,在鄉村舉辦科普講座、科學展覽、全民科學日等科學活動,并搭建與學校、地方企業及研究機構的合作關系,整合科普資源,發揮最大合力,增大科普活動覆蓋群體,落實科普活動實效,幫助鄉村青少年在更豐富、有趣的科普活動參與中建構對科學職業的理解、認同和興趣。
5.2.3科學行為實踐:拓展學習空間,幫助鄉村青少年創造積極的科學體驗
本研究結果揭示了鄉村非正式科學實踐不僅要“數量”,更要“質量”,僅僅提高鄉村青少年參與非正式科學活動的頻率并不能支持其發展積極的科學職業理想,質量不佳的科學活動甚至會抑制青少年的興趣和熱情。因此,需要為鄉村青少年提供積極、豐富、包容的科學實踐體驗,這需要活動組織者加強對非正式科學實踐活動的體系設計、質量管理和學習效果追蹤,避免零散化、形式化、重復化的科學活動“以次充好”,擠占鄉村青少年的非正式科學學習時間和精力。
一方面,受客觀因素制約,我國鄉村非正式科學學習資源如場館、設施、人員等方面的建設仍需補充支持力量,在政策制度保障、社會資金支持等方面應當適度傾斜鄉村弱勢地區,為鄉村引進更多的科學場地、科學實驗用具、科學展品以及專職科普人員,提升鄉村非正式科學活動的質量。
另一方面,鄉村科學教育工作者需要進一步審視、思考和改善現有的非正式科學學習活動模式。有研究證明,弱勢學生受到文化習俗、知識和價值觀差異的影響,在科技場館參觀時可能無法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反而會產生“這些展品并非為我而設計”的想法[29]。因此,鄉村科學教育工作者在活動設計和場館搭建時不能照搬城市科普模式,要打造更符合弱勢學生知識水平和認知習慣的非正式科學學習方式,嘗試從當地的鄉村生活中開發、挖掘可用于非正式科學學習的資源,并將其融入鄉村科學學習,例如設置本土科技產業技術展品、宣傳當地常見農作物種植中的生物及工程知識、科普鄉村自然地貌類型及形成歷史等,讓鄉村學生覺察到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科學,親身觀察、體驗、參與更多的科學實踐,并思考用科學知識解決實際生活問題,進而產生對科學職業的理解和興趣。
6結語
本研究基于我國鄉村中學2 022名初中生的問卷調查數據,探討了科學資本視角下我國鄉村學生科學職業理想的現狀、影響因素及提升對策。根據研究發現,科學資本對我國弱勢學生群體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作用呈現復雜性,其中深層影響機制與作用過程有待挖掘,通過對質性研究相關數據的挖掘和分析,能夠為量化數據結果提供更為豐富的支撐和解釋。同時,科學資本理論源于英國,目前我國相關研究起步不久,未來研究可以著眼于科學資本理論模型與測量工具的本土化改良與應用,結合科學資本理論為我國鄉村學生的科學學習劣勢問題提供新的分析視角,探索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參考文獻
鄭永和,周丹華,王晶瑩.科學教育服務強國建設論綱[J].教育研究,2023,44(6):17-26.
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并發表重要講話[EB/OL].(2023-02-22)[2024-05-22].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2/content_5742718.htm.
Lindahl B.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udents’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and Choice of Care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R]. New Orleans,LA:NARST Annual Conforence,2007.
OECD. PISA 2015 Results(Volume I):Excellence and Equity in Education[M].Paris:OECD Publishing,2016.
王曉華.中國四省市學校科學表現、影響因素及啟示——基于PISA 2015中國四省市數據[J].教育科學,2019,35(1):23-31.
趙德成,郭亞歌,焦麗亞.中國四省(市)15歲在校生科學素養表現及其影響因素——基于PISA 2015數據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7,38(6):80-86.
徐海鵬,趙洋,陳云奔,等.影響10~19歲學生塑造科學職業理想的新探索——英國ASPIRES 2項目述評[J].科普研究,2022,17(4):40-47.
Archer L,Dawson E,Dewitt J,et al.“Science Capital”:A Conceptual,Methodological,and Empirical Argument for Extending Bourdieusian Notions of Capital Beyond the Art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5,52(7):922-948.
Du Xin,Billy W. Science Career Aspiration and Science Capital in China and UK:A Comparative Study Using PISA Dat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9,41(15):2136-2155.
Macbrayne P S.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of Rural Youth: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Research in Rural Education,1987,4(3):135-141.
Dewitt J,Archer L. Who Aspires to a Science Career? A Comparison of Survey Responses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5,37(13):2170-2192.
Shapka J D,Domene J F,Keating D P. Trajectories of Career Aspirations Through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Early Math Achievement as a Critical Filter[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2006,12(4):347-358.
Bandura A,Barbaranelli C,Caprara G V,et al. Self-Efficacy Beliefs as Shapers of Children’s Aspirations and Career Trajectories [J]. Child Development,2001,72(1):187-206.
Riegle-Crumb C,Moore C,Ramos-Wada A. Who Wants to Have a Career in Science or Math? Exploring Adolescents’Future Aspirations by Gender and Race/Ethnicity[J]. Science Education,2011,95(3):458-476.
Rowan-Kenyon H T,Perna L W,Swan A K.Structuring Opportunity:The Role of School Context in Shaping High School Students’Occupational Aspirations[J].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2011,59(4):330-344.
王晶瑩,辛偉豪,鄭永和.城鄉教師素養如何影響中學生的STEM職業期望?——基于PISA 2015中國四省市數據的循證研究[J].教師教育研究,2020,32(6):76-83.
吳愈曉,黃超.基礎教育中的學校階層分割與學生教育期望[J].中國社會科學,2016(4):111-134.
Archer L,Dewitt J,Willis B. Adolescent Boys’Science Aspirations:Masculinity,Capital,and Power[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4,51(1):1-30.
Ferraro J L,Heck G S. Science Capit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between 2015-2021[J].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Estudos Em Educa??o,2022,1389-1416.
Dewitt J,Archer L,Mau A. Dimensions of Science Capital:Exploring its Pot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Students’Science Particip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16,38(16):2431-2449.
李玲,朱海雪,潘士美.科學資本對西部學生科學職業理想的影響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38(7):117-126.
邊燕杰.中國城市中的關系資本與飲食社交:理論模型與經驗分析[J].開放時代,2004(4):94-107.
Archer L,Dewitt J,Willis B. Spheres of Influence:What Shapes Young People’s Aspirations at Age 12/13 and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Policy?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2014,29(1):58-85.
Wade-Jaimes K,King N S,Schwartz R.“You Could Like Science and not Be a Science Person”:Black Girls’ Negotiation of Space and Identity in Science[J]. Science Education,2021,105(5):855-879.
翟俊卿,毛天慧,季嬌.兒童如何在參觀科技場館過程中學習科學——基于國外實證研究的系統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18,40(7):68-77.
Claussen S,Osborne J. Bourdieu’s No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cience Curriculum[J]. Science Education,2013,97 (1):58-79.
Hite R,Mcdonald T L. Exploring Science Relevancy by Gender and SES in the Bahamas:Secondary Bahamian Students’Interests in Science and Attractive Attributes of Future Care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2021,43(11):1860-1879.
Dubos R. 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M]. New York:Routledge,2017:42-43.
Dawson E.“Not Designed for Us”:How Science Museums and Science Centers Socially Exclude Low-Income,Minority Ethnic Groups[J]. Science Education,2014,98(6):981-1008.
(編輯" 顏" "燕" " 和樹美)
收稿日期:2024-09-01
基金項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委托課題“中國鄉村青少年STEM活動的成效及其影響因素研究”(1232100004)。
作者簡介:高瀟怡,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課程與教學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科學教育,E-mail:gaoxiaoyi@b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