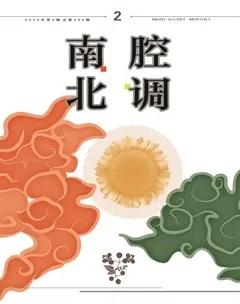以文學感覺重建人的精神世界
陳沙沙
人類擁有一個復雜靈妙的內宇宙[1],其同外在的寰宇一樣,引人勘探。自20世紀初“人的文學”被提出以降,文學如何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問題再次成為中國文學著力表現的內容。20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的討論就是對人的心靈宇宙的一次關懷。位于人面部正中的鼻子其實是一個精雕細琢的感受器,它能分辨的氣味至少有一萬種。嗅感如此發達的鼻腔仿佛就是一處微型內宇宙!從鼻腔掘出一條通往內宇宙的道路,社會科學、心理科學開辟了不同的進路,然而,氣味的難以留存與須臾易逝,使得氣味難以用理性、邏輯、概念演繹,它更偏好深掘人無意識潛流的文學創作。作家、詩人被認為是最擅于探測幽微世界特別是人的精神性世界的人,科學界對嗅覺引發人深層次回憶現象的研究就啟靈自“普魯斯特效應”①,充分展露氣味深具敘事力量的一面。作家老藤近年來的創作也顯現出關注嗅覺—空間—心靈同構性的敘事傾向,圍繞文學地理中的地景重構和伴隨而來的人的精神景觀的呈現與處理問題,其將嗅覺地景視作內在的敘事策略,考察氣味在勾連人的(空間)住所、文化記憶、欲望想象、自我身份方面的建構功能與精神指向,為東北文學引入新的表現領域:一方面,重構新時期以來當代東北小說在解剖人的精神風景方面的景觀化、奇觀化旨趣;另一方面,煥新東北文學在演繹記憶、權力、身份等主題上日益固舊的想象方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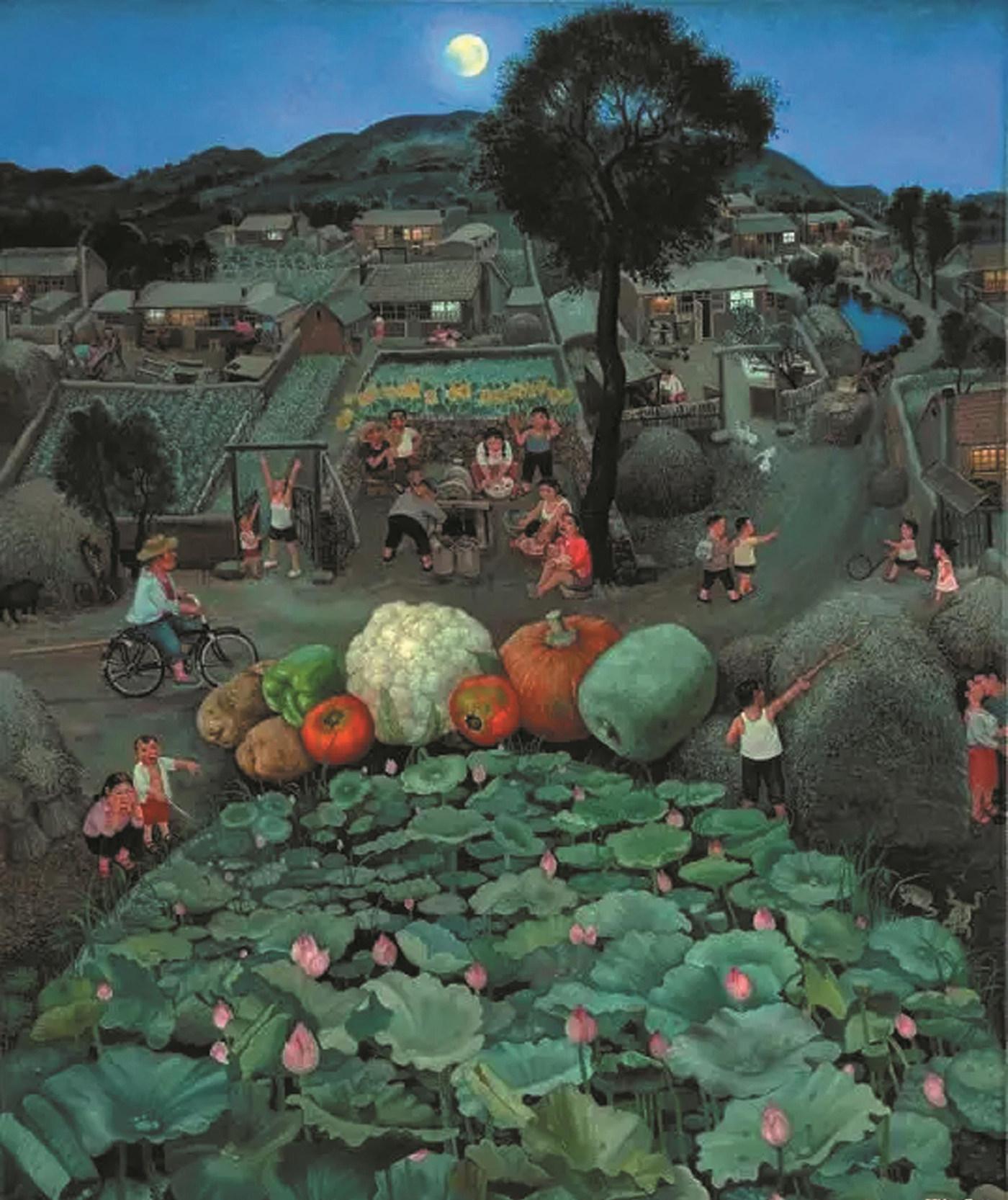
一
嗅覺,相對于其他四感尤其是視覺來說,因缺少限制,因與呼吸同在,更能直達個體生命[2],深具建構力量。但是,道格拉斯·波爾圖認為氣味也因深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形塑,造成這種“非視覺”感官記錄的困難,阻塞了個體智性在私我與共享空間中的流通閥門。他隨之提出“嗅覺地景”②(smellscape)的概念,并指出基于文學超越時空的雙重屬性,在文學中探索氣味在時間和空間上完整循環的可能性,顯示出嗅覺通聯文學時空超越現實時空形成的嗅景在重溫逝去的記憶,重構獨特的地域空間乃至心理地理上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并且,嗅景還包蘊著作家對于社會、個體世界的一種未來性想象,就比如說,“東北的白山黑水一再成為現代中國想象共同體的場景。”[3]
對東北白山黑水的發現、檢視、定位是一種地理體驗,亦是一種敘事過程。
“‘東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感覺結構——因器物、事件、風景、情懷、行動所體現的‘人同此心的想象、信念甚至意識形態的結晶。”[4]對東北(風景)的考古、發掘伴隨著感知過程、認識裝置的內化。《林海雪原》《額爾古納河右岸》以漫山遍野的皚皚白雪為原初、野性的山林世界賦色;《鋼的琴》《鐵西區》用西洋樂與中國樂的拼貼、復沓反襯工業基地的廢墟圖景;《呼蘭河傳》《平原上的摩西》中泥濘的石坑、破舊的煙盒與課本任摩挲的手掌撫摸、懷想。《刀兵過》《麻櫟樹》通過“干稻草散發出來的味道”嗅識關內、關外,人、事、物、景閃動的情愫……這條視、聽、觸、嗅的敘事脈絡,“無不以地緣景觀召喚東北最生動的感覺”[5],也無不以一個有色彩、有聲音、有形狀、有氣味的“生命活體”[6]重啟內在、性靈的感覺書寫。在這具生命有機體中,唯有嗅覺帶來的感受是永不會腐朽的。且看《刀兵過》開頭鋪設的一處嗅覺地標:
窩棚外空氣里彌漫著一股海腥味,這腥味仿佛來自許久沒有洗澡的腋窩,顯得有些曖昧……他登上土坎,極目南望,頓時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呈現在眼前的是無邊無際的紅!這是一種從沒見過的紅,紅得熟紫,紅得自信,像連片的珊瑚,似晚霞覆地,如果不是有一群白色的鳥兒列隊飛過,這情景真讓人想到是連片的火海了——這不是乩文中的水泊之上燎原火嗎?
綠葦紅灘,地平河闊,一幅多么讓人心動的圖畫!
撥開蒲葦,他疾步跑過去,在就要接近這紅色的時候,兩只腳被軟泥深深地陷住了。他退回來,知道這里是海灘,要找對路徑才可以進。無邊的紅色里,可見一條蜿蜒的小溪,正流向遠處。……他忽然嗅到了那種熟悉的野燕麥干草的味道,甜而軟,沖淡了先前的海腥味,他知道,這干草的味道應該來自身后的窩棚。[7]
不難想見,“氣味可以活化插曲式記憶。就算無法說出氣味的名稱,或對此氣味作更精確的描述,嗅覺仍可以充當起動機,讓人記起遺忘的經驗和過去的事情。”[8]老藤在創作談中談及為何以《刀兵過》替換《九里》時就從嗅覺的角度介入,他說:“其實,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過刀兵的歷史,翻開二十四史,間或總能嗅出血腥氣。”[9]的確,九里村數十次過刀兵的歷史,總有一股腥味盤桓于此。如:1895年寇賊侵擾,“風從紅海灘刮來,帶著一股濃重的咸腥”[10];1924年霍亂侵襲,“一片片生生不息的蘆葦被連根掘起,王克笙嗅到了一股從來沒有聞過的泥腥味,這是一種被沉淀了千百年的味道,從葦地的傷口處散發出來,令人惶惑窒息。”[11]不同于宏闊的大場面描寫,細處攢動的嗅覺表現成為特定歷史風貌的鏡像性顯現。腥紅味(私我空間)楔入綠葦紅灘(共享空間),正是以集結可視、可觸、可聽、可嗅等多種感覺的地景突入主體性真實在場的意義域,重構一種起源性的敘述方式。血腥味是東北戰爭史的一個側影,咸腥味、泥腥味是東北農耕史的獨特標志,腥紅味、干草味是東北文學史業已失落的感知主體……嗅景“所揭示的不僅是一定的社會歷史內容,更重要的是人的廣闊的內心宇宙和人的生命意識的深層結構”[12]。正如王堯所說,在色彩表達上,相較于蕭紅、遲子建黑白色調的東北,老藤凸顯的是“紅”色調;在氣味空間上,“腥味、堿灘、珊瑚”不僅組構了海洋性質的東北,它們還讓人覺知到“被抽象為同質化存在的‘東北有著怎樣具體而微的空間差異”[13]。也就是說,徘徊不散的腥紅味不僅是白山黑水的物質遺產,它同時也是從嗅覺視角反視作為現代公共風景的“東北”的心理地理。伴隨氣味景觀的積聚與人文地理的延伸,嗅覺部分恢復了我們對于現代東北“風景”的記憶,激活了我們看待現代中國“風景”的眼光,也影響了以九里人為代表的東北社群選擇居住地的傾向。例如,九里建村的歷史就堪稱一部氣味的文化史。灌注在九里世界中祁門安茶的糲香、蒲葦清香、蘆花(蓬蕽)藥香、道觀檀香……不僅是老藤的文本世界中源源不斷異彩紛呈的地域風物與地緣密碼,它還發掘了作為“身體感意象”③的嗅覺書寫的開源功能,樹立起九里人“幸福、圓整、寧靜、信賴的原初感受”[14]。
《刀兵過》這類嗅覺敘事文本,其意義在于“以熟悉且親切的氣味為坐標,由氣味串聯起看似不同范圍內的人、事、物,復制、碎裂與重構已被遺忘的記憶”[15],從而搭建起氣味與獨特地理景觀、理想生存環境的溝通橋梁。這就是段義孚指陳的,“如果沒有一種歷久不變的感官體驗的幫助,比如說海藻的咸腥味,我們就不能完全重溫長大之前對世界的感受了。”[16]盡管這樣的氣味表現還尚顯粗糙,但以嗅感“喚醒”人的朦朧、感性的內在風景與主體意識,未嘗不是一種“新的感覺美學在崛起”。
二
面對生活實感的緊縛與自我需求的膨脹,柄谷行人將“風景的發現”升格為日本文學現代性起源的心理特權裝置。正如風景的發現,“氣味的發現同樣需要改變的是我們的感知形態”[17]。當卷入“社會主義風景”變革進程的個體氣味、嗅覺情感展演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記憶、權力認同時,“風景”也不再是單純的自然想象物,“風景與其說是自然所提供的一種形式外表,不如說它更主要的是文明繼承和社會價值的體現。”[18]“氣味即心境”,在歷史社會記憶的遞變、文化權力的認同中,氣味展覽了多元的敘事風景。
(一)深描個體心靈的記憶嗅景
在老藤的小說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連接關系常被人與動物在山林、鄉野等自然生態中的互動、救贖替換。這固然深受作家生態保護意識影響,但實際上,也關乎人的解放與心靈的救贖這類宏大的文學命題。《北地》這部歷史小說,章節與章節的銜接處排列著無數“歷史景觀”,透露出歷史變革巨大毀壞與再造力的當屬“一處農場和兩座墓碑”的變遷,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其實是由氣味生產的記憶之所。這種敘事指向,創造了一種結構性的回想文本,把北地業已隱匿的過去與現在的地點重新聯系在一起。而且從探源動植物身上特有的流彩馥郁的氣息,逐漸演變為一場再造北地“場所力量”的敘事活動。人們意識到,在氣味變遷背后,是一段個體創傷記憶的嬗變與復呈。格拉秋山農場是常克勛任職北地的第一站,在褚三祿的回憶中,倆人的交往甫一開場就充斥著五只狍子和狼群之間慘烈撕咬的血腥味,同時又混雜著類似于羊和鹿的膻味、貂的腥味、大雪冰封的冷氣、掃帚梅的香氣以及在寒衣節為“十八烈士”燒線衣的衣料、香火味……這一股股纏繞在老人數十年記憶中的氣味終于在子輩常寒松、任多秋時隔40年后的田野采訪下得以全面釋放,而那股無法揮發的狍子味則出人意料地使得氣味接受者褚三祿在回憶狍塚時“思維如此清晰,講述極有條理”[19]。但是,腦海中記憶的畫質越高清,越引出這樣一個問題:人在口述歷史事實時,一旦動用氣味修辭還原歷史現場,人的主觀意志是否會無限飛揚?實際上,嗅覺因其特殊的生理構造被認為是唯一能進入大腦中心的感覺,故被稱為“嗅腦”。相比于語言和文字,氣味其實會立刻準確地把你需要了解的訊息告訴你,對這種感覺的充分調動,在某種程度上是為逝去的無法復現的記憶的一次“命名”,是對社會精神史與個人精神史的一次“繪制”,“在這個味覺的長河中間敞開了一個空洞,一個隱藏的褶皺,里面就隱藏著那種香氣。”[20]
此外,“社會主義農場”這個帶有自省與自審的場所還是“十七年”歷史褶皺中的一個交界地帶,常克勛履職生涯的謫遷地——“五七干校”原身就是一處農場,其在后輩重訪時已經被改為養貂場,被貼上“味大、難以靠近”的標簽。印刻著個人存在氣息的農場氣味,彌散在遙遠的改建回憶中,個體的存在正遭遇被抹除的危機。莫言在《生死疲勞》中也調動了動物的嗅覺來回望高密東北鄉的變遷史與變革史,“變”于時代來說如曇花一現,但于個體來說卻如猛虎細嗅,充滿未知的驚顫。經歷輪回轉世的“西門狗”進入人世時恰逢改革開放頭十年,當它帶著西門鬧的肉身記憶走街觀屯時,“當年,屯子里最濃郁的牛的氣味、騾馬的氣味消失殆盡,而許多人家院里都散發出濃重的生銹鋼鐵的氣味……。”[21]勞作汗味、動物鼻息、花香草氣留下的氣味印痕連同原始農耕生態,或被遺棄或被取代,機器轟隆作響,附著其上的鋼鐵銹味帶領讀者決絕地沖入西門鬧投胎為“西門狗”、傳統與現代交接的一瞬,再次經歷初生時的創痛。而這種層級的痛感,在上述社會主義農場的故事因旅游業發展而被改寫到乾隆年間,在交織著常克勛奮斗、失意情緒的農場被出租改建為養貂場時攀至頂峰,這無疑是個體的歷史被商業消費的時刻。
(二)彌散于空氣中的權欲嗅景
嗅覺是欲望的感官,這種源自生命本能的力量,有直達個體生命欲望與自由意志的直覺。但長期以來,嗅覺被置于感覺體系的最下層,自柏拉圖時代以來,“嗅覺和所有的種類的氣味均被賦予負面意義”“如同性欲、欲望、沖動的感覺,嗅覺帶有動物性的戳記”[22],氣味接近原始、本能、快感的優勢如今成為眾矢之的,這與欲望、權力在我們的書寫和敘述中所遭遇的處境如出一轍。《嗅覺的符碼:記憶和欲望的語言》中指出,與影像相較,氣味更為“武斷、肯定”,人一生都在跟著嗅覺走。如今,藝術家們漸次發現了嗅覺的魅力,并重新審視嗅覺欲望所搭載的可靠的感性力量與直覺特性。老藤在《西施乳》《國家羊湯》中為食欲和權欲搭建文學橋梁時,就抓住了嗅覺的欲望屬性并重塑了這一載體。
“食、色,性也”,食欲是人的第一生本能,在中國官場文化場域中,食味與各種權力之間更是存在一種微妙的擺蕩關系,食味和權欲交互的敘事模式就發展為小說展現權力魔力的手段。由此,憑借嗅覺與權欲的特殊對應關系以及老藤在其小說中設置的特殊食香視角,書寫嗅覺在社會權力追求與個體生命意志之間的表現才顯得如此撩撥心弦。比方說,食思發達的古人就用“治大國如烹小鮮”譬喻國家治理,我們民族的審美意識也從“羊大為美”的體悟中初現輪廓。在這樣的文化心理氛圍的加持下,中國式官場世界也發展出一條“嗅/被嗅”的生存法則。老藤早期作品《西施乳》就將食欲和權欲交織纏繞的政治生態寫得活色生香。《西施乳》題目本身就是一道精細加工的美食,主人公鄭遠橋官場生涯里幾次重要變革都與這道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每每遇挫時,鄭遠橋敏銳的鼻子總能最先聞到空氣中神秘的味道,這味道提醒他三“嗅”而行,人的確是會用氣味進行思考的動物。整部小說最令人咂舌的地方是:制作西施乳的廚師尹五羊雖身不在官場,但儼然一位“食官”,更因其占有著制作西施乳香所需火候、時間等關鍵變量的秘訣,能神龍不見首尾地牽引藍城市長、書記等一眾食客職業場與人生場復雜交織的氣味紅線,在用食香撩撥人的權欲上他儼然是生殺予奪的嗅覺國王。同樣在以食設題的《國家羊湯》中,國家羊湯館是照鑒榆州縣政府機關官場世相的一面銅鏡。在這個小小的羊湯館里,有一群“不擔要職”的干部食客,他們常年利用公權力隨意簽單、欠單。因為久債積壓,店老板國老大決定討要欠款,但也“討”來了店鋪拆遷的封條。羊湯館關門之際,國老大留給唯一沒有掛過單的掛職副縣長“我”一段話,“國氏祖訓說,羊臉,五官俱全之物,五官即五味,五味調和才能出國之大羹。”[23]在現代與后現代的語境中,個體價值中心化、利己化,大有傾軋社群、集體價值信念之勢。就像羊肉湯的烹制過程內嵌的鮮活真理所顯示的那樣,“欲”將人內在的本能與外在的選擇通過氣味的隱喻來解釋,在羊湯充滿隱喻的氣味籠罩下,利與義、牧與治……凡此種種對權力的詰問成為盤桓在現代人價值判斷與道德選擇中濃稠難化的嗅覺情緒。
三
在文學創作的目的或旨歸上,莫言和老藤就故鄉與氣味的關系發表了相似的看法,前者認為:“作家的創作,其實也是一個憑借著對故鄉氣味的回憶,尋找故鄉的過程。”[24]后者亦宣稱:“我對故鄉的印象大都與味道有關。味道,是引領我回到故鄉的最好路徑。”[25]兩位作家的創作在這里匯合并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氣味認同在重構自我身份上具有重要作用。現代小說的敘事往往設計或內嵌著歷史與道德、理性與感性、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如將現代性焦慮具象化表征為地域身份、階層身份、文化身份焦慮,對人物內在精神的塑造往往趨向對抗、沖突的形式。老藤也摹寫人物身份問題,但他采取的是一種較為平和、正向的敘事策略。小說的創作,是一種在對外部世界氣息、殘骸、碎片吸入、消化后呼出的人與世界的均衡、連續、穩定的滿浸生命氣味的循環活動。氣味作為符號化的隱喻,在被吸入與被呼出之間“象征著人類精神中的價值和自我認同”[26]。
卡爾維諾在《美洲豹陽光下》一書的寫作前言中坦言,他正在通過穿透“五感”來呼喚一種新的寫作方法,嗅覺位列其中。“所有我們應該知道的東西,我們都首先用鼻子來獲得,而不是用眼睛:猛犸象,刺猬,洋蔥,干旱,雨水,它們首先是一些從其他氣味中脫離出來的氣味。食物,非食物,我們的山洞,敵人的山洞,危險,一切都是先由鼻子感覺到,一切都在鼻子里面,世界就是鼻子,我們是用鼻子來了解誰屬于我們這一群人,誰不是。……”[27]個人如何通過氣味的不同精細地辨別他人,也意味著他如何想象自我的氣味。在《名字,鼻子》這一章專述嗅覺的故事中,卡爾維諾讓花花公子、史前人類與吸毒的搖滾歌手皆因一位女士的體香展開了瘋狂的“尋找”,帶有氣味的女士顯然只是一個有香氣的符號能指,三位男士在尋找過程中追求的是對人的境遇的把控。聚斯金德的小說《香水:一個謀殺犯的故事》則展現了聞香識人的極端化情境,格雷諾耶這位擁有極靈敏嗅覺的“無香狂徒”,自出生就被家庭和社會棄養,而棄養的理由竟是因為他沒有香味,沒有被頒發作為身份識別的嗅覺護照!錯亂的身份感和犀利的識香能力,讓他不顧一切地寄希望于在殺人取香的過程中“重嗅”自我文化身份。致命的是,由香水偽裝而來的身份面具一戳即破,在最后一滴香水營造的迷狂盛宴過后,他也徹底失去獲得身份合法性的可能。不同于體香、香水賦予的反向身份特征,老藤更傾向于屈原式“香草美人”的正向身份特質的營構。以對王克笙和王明鶴這兩位主理九里的鄉紳身份的刻畫為例,作者分別賦予倆人“味”和“氣”兩種超拔躍升的品質:
王克笙站在酪奴堂庭院里,仰望著灰蒙蒙的天空對兒子鳴鶴說:“葦地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彌漫著一股干土味兒。”……他知道父親對味道異常敏感,這種干土的味道與干草的味道截然不同,給人以一種無邊的焦慮和憂患。……王明鶴沒有聞到父親所說的干土味,他敏感的是氣而不是味,在這個少雨的春季,他經常會感受到一種來自天空的磁力,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要把自己隨時撥到空中。[28]
對照來看,王克笙與王鳴鶴傾向于用味與氣形塑可能世界中超越性的“我”,不同的是,王克笙尋味的動力乃出于對“超我”的探詢與完型,臨終前仍念念不忘那縷指引他來到九里的野燕麥干草味,嘴里念念有詞:“我尋味去了。”[29]王鳴鶴并不追逐“味”,他最大的稟賦是在“氣”的沖、撞、推、撥的回旋中為他人尋找自識的出口。這是一種于他者氣味的識別中重塑己身的樸素辯證法。7歲時,他曾在葦地里迷路,正當父母和眾鄉親焦急萬分之時,他卻自己從蘆葦蕩里走出來。事后,王鳴鶴解釋道:“前后左右有三面在擠著自己,逼著自己往一個方向走,走著走著就走出了蘆葦蕩。”[30]這一嗅覺地景是隨著王鳴鶴身份意識的真正發生而覺醒的,但這種覺醒并不是“本我”的釋放,其仍處在現實自我與理性超我的相持之中。當王鳴鶴接過父親保護九里、建設九里的囑托后,葦地聚集的協同、互助的氣場正是他對自己鄉紳身份主動確認的努力結果。這兩位“有氣味的人”亦讓我們聯想起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式典型人物,他們身上散發的氣味可以窺見社會各行各業中具有神圣感召力與原初性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全貌。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學終結”的話題“甚囂塵上”,危言聳聽的批評之外是文學感覺的確在裂變、坍縮,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創作還會迸發出新的感覺嗎?老藤用文學作品實踐了嗅覺所具有的記憶感、欲望感、身份感、生命感乃至神圣感,用排列在瞳孔、唇齒、耳膜、發絲、肌膚、鼻腔和其他器官之上的感覺重建文學的、人本的風景。老藤的嗅景書寫不僅召喚出暗藏在白山黑水、綠葦紅灘中解構秩序感的膻腥味,也有心理地理、飲食滋味帶來的本能的、屬己的日常體驗。此外,眼睛看到的活火山、嘴巴嘗到的綠皮柿子、雙手摸到的碑文……都讓其文學故鄉暗香疏影。也許正如卡爾維諾所說:“假如我們的嗅覺失去了感知那些味道從而創造出豐富而珍貴的詞匯的能力,那么將無法用詞語來把這些香氣表達出來,它們也會因此變得模糊而又無法辨認。”[31]既然五感的鈍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那我們如何具體把握感受?如果不用文字去記錄火山噴發時彌散的氣味、馬匹舒張的鼻息、山羊厚重的膻氣,我們何以認識人所生活的寬廣無垠的世界?可行的方案是,作者不妨大膽地調動起所有的感官,去創造一篇呼吸、溫度、聲音與氣味俱存,并且感性綿延、思想閃耀的小說[32]。
注釋:
①“普魯斯特效應”是研究界對“嗅覺引發回憶”現象的命名。
②基姆·杜布尼克《嗅覺文化讀本》中收錄了由道格拉斯·波爾圖撰寫的論文《嗅覺地景》(《smellscape》),第一次提出“嗅覺地景”的概念。為行文方便,后文將“嗅覺地景”簡稱為“嗅景”。
③在傳統的感官意識研究中,視覺圖像被認為是人觀察和感受世界的主導性裝置,但在人的感覺系統中,嗅覺與人內心縱深的私密感的通聯,乃至于與外在世界的整合關系常常被忽視。實際上,嗅覺意象對人內心模糊甚至神秘感受的開掘能帶來身體感官的充分釋放,并形成一種“身體感意象”。關于“身體感意象”的論述,學者史言在《批評的召喚:文學啟示與主題思考》中指出,嗅覺意象有別于“感官意象”“感覺意象”或“知覺意象”,對嗅覺意象的定位,應超越記憶層面的“再現性喚起”,而強調創造性或預見性的想象層面,視之為“身體感意象”。
參考文獻:
[1]魯樞元.文學的內向性:我對“新時期文學‘向內轉討論的反省”[J].中州學刊,1997(5):88.
[2]劉軍茹.新時期小說的嗅覺書寫[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58.
[3][4][5]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J].小說評論,2021(1):63,61,63.
[6][24][32]莫言.小說的氣味[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4,2,4.
[7][10][11][28][29][30]老藤.刀兵過[J].中國作家,2018(4):16,21,47,38,51,33.
[8][22][美]派特·瓦潤,安東·范岸姆洛金,漢斯·迪佛里斯.嗅覺符碼:記憶和欲望的語言[M].洪慧娟,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110,16.
[9]林喦,滕貞甫.一部氣勢恢弘《刀兵過》,一部遼南底層民間史——與作家滕貞甫的對話[J].渤海大學學報,2019(4):11.
[12]李建東.無限廣闊的內在世界——論文藝創作的“內宇宙”[J].黎明職業大學學報,2001(1):14.
[13]王堯,牛煜.“東北—歷史—故事”:《刀兵過》閱讀札記[J].當代作家評論,2019(1):119.
[14]史言.批評的召喚:文學啟示與主題思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17.
[15]林翠云,張箭飛.嗅景與個人記憶的重建:以《生死疲勞》為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4):187.
[16][美]段義孚.戀地情結[M].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12.
[17][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M].趙京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23.
[18][英]紐拜.對于風景的一種理解[M]//美學譯文(2).王至元,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181.
[19]老藤.北地[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20.
[20][27][31][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美洲豹陽光下[M].魏怡,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89,89,84.
[21]莫言.生死疲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39.
[23]老藤.國家羊湯[M]//熬鷹(遼西往事).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5:84.
[25]老藤.文學是映在故鄉的影子[N].北京:光明日報,2023-03-08(15).
[26]林翠云.嗅覺地景與記憶——重思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D].武漢:武漢大學,2017:93.
作者單位:大連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