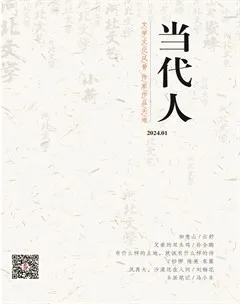“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的新思考
梁建中
筆墨在山水畫創(chuàng)作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國(guó)畫獨(dú)特的造型語言,是作品意韻和畫家精神情感的承載體。宏觀來看,它標(biāo)志著一個(gè)時(shí)代的繪畫風(fēng)格,同時(shí)又是對(duì)這個(gè)時(shí)代藝術(shù)環(huán)境的充分體現(xiàn)。作為中國(guó)山水畫家,對(duì)于筆墨要有正確的發(fā)展觀,要選擇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筆墨來繼承,要正確看待文化融合對(duì)筆墨語言帶來的影響,也要通過自身的實(shí)踐與研究創(chuàng)造新的筆墨語言來適應(yīng)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時(shí)代步伐。
無論何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從形成到發(fā)展的過程以及所要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都是對(duì)同時(shí)期文化的反映。筆墨語言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反映了在時(shí)代背景的變遷下中國(guó)山水畫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脫離文化來談藝術(shù),就像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進(jìn)而這種藝術(shù)形式也就不能稱之為藝術(shù),它的發(fā)展壽命也不會(huì)長(zhǎng)久,即“君子唯借古以開今也”。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隨著中國(guó)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中國(guó)向全世界打開了國(guó)門,隨之而來的各種西方文化思潮也涌了進(jìn)來。由于多元思想及文化的強(qiáng)勢(shì)注入,國(guó)內(nèi)的一些藝術(shù)家甚至一度放棄傳統(tǒng),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畫壇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創(chuàng)作方式和思潮,一些中國(guó)藝術(shù)家或多或少地缺失了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研究。
當(dāng)我們翻看中國(guó)的繪畫史,那些被留存史冊(cè)的作品,每一幅都能鮮明地體現(xiàn)出它們所處時(shí)代的文化內(nèi)涵。歷代畫家能夠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上有所建樹的,大都是創(chuàng)作者能把自己置身于所處時(shí)代文化的基礎(chǔ)之上,他們的作品既繼承了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又強(qiáng)烈地反映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
這時(shí)引發(fā)我們思考,那些經(jīng)典作品中的時(shí)代精神在哪里體現(xiàn)?為什么能對(duì)后世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
作品所要表現(xiàn)的時(shí)代精神就在“新”中得以體現(xiàn)。所謂的新,就是指創(chuàng)新精神。傳統(tǒng)的繪畫技法在每個(gè)歷史階段都會(huì)有創(chuàng)新,都有繼承和超越前人的繪畫技法及新的創(chuàng)作理論。而他們作品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創(chuàng)新”,是以當(dāng)時(shí)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為基礎(chǔ),深入生活,通過對(duì)社會(huì)的深刻認(rèn)識(shí)形成具有個(gè)人情感的創(chuàng)作觀,進(jìn)而形成具有獨(dú)立個(gè)性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的“新”是在古法、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不斷尋求適合自己的形式語言。
古語有云:“專其神,守其一。”只有投入全部的精力,才有可能創(chuàng)作出震撼心靈的作品。我們總是感嘆,古代交通不便利,信息閉塞,生產(chǎn)力落后。但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下古人卻創(chuàng)造出了大量的流傳后世的優(yōu)秀作品。其中奧妙,是古人能夠真正靜下心來研究體悟,能深刻地感受并試圖通過繪畫語言去解讀所處的時(shí)代,全身心地投入到繪畫創(chuàng)作中,那是對(duì)自然情感的真實(shí)流露。這種深度投入感情的創(chuàng)作不會(huì)受生產(chǎn)力的影響,反而是這種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使畫家能夠安心創(chuàng)作,少受俗世的打擾,因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是真正內(nèi)心情感的體現(xiàn)。
現(xiàn)在,我們所處的時(shí)代較之于改革開放之初,物質(zhì)更加豐富,信息唾手可得,展覽更是目不暇接,理應(yīng)是中國(guó)畫創(chuàng)作的黃金年代。但就作品而言,在某些方面遠(yuǎn)遠(yuǎn)沒有達(dá)到我們理想中的創(chuàng)作高峰。
藝術(shù)作品的作用及擔(dān)負(fù)的任務(wù)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解讀與抒寫,既是時(shí)代的需要,也是藝術(shù)家在作品中留給時(shí)代充分的、深刻的、明顯的印記。藝術(shù)當(dāng)隨時(shí)代,是作為一個(gè)有獨(dú)立思考藝術(shù)家的擔(dān)當(dāng)與責(zé)任。而當(dāng)我們放下作品來研究藝術(shù)家時(shí),他們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的方式是我們對(duì)藝術(shù)品之外的獨(dú)特個(gè)人感受。它是清醒又細(xì)致的,你可以稱之為靈感,也可以稱之為天分,其主要內(nèi)因一定是自發(fā)的強(qiáng)烈的感情,對(duì)他過往所認(rèn)知的觀念加以改造強(qiáng)化并最終作用到畫面中。過去許多關(guān)于繪畫發(fā)展的理論,即所謂的中國(guó)化的“底線”設(shè)置,其實(shí)是在某些方面給了關(guān)于中國(guó)畫藝術(shù)發(fā)展的界限,這如同是作繭自縛。當(dāng)我們回顧中國(guó)繪畫史,中國(guó)畫經(jīng)歷了不同階段的多種理論解讀和演變。從東晉顧愷之的《傳神論》,到南朝謝赫的《六法論》,再到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論》等,一直到今天所謂的“筆墨論”,比起古人其實(shí)并無高明之處,但就是在這樣的所謂總結(jié)與指引下,過分地解讀與重視了筆墨的趣味,而恰恰忽略了人作為主導(dǎo)的作品中所涵蓋的人生境界。以筆墨作為繪畫創(chuàng)作的底線,就是典型的重視表象的結(jié)果。正如吳冠中認(rèn)為的,脫離了具體畫面的孤立的筆墨,其價(jià)值必定等于零。筆墨是為畫面服務(wù)的。在新的時(shí)代我們不能墨守成規(guī),過分拘泥勢(shì)必會(huì)對(duì)繪畫的發(fā)展造成反向的影響。只有在繪畫發(fā)展過程中多方探索,無盡拓展,才能使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活力生機(jī)。大凡偉大的藝術(shù)家,一定是跳出了“厚古薄今”的思想,也破除了“崇古厚古”的世風(fēng),這其中需要極大的勇氣,也需要有極高的智慧,在遵循繪畫法則的過程中努力尋找表達(dá)的無限可能性。
傳統(tǒng)既是對(duì)過去的總結(jié),也是在不斷的融合中走來的,如中國(guó)的旗袍,原只是清滿族女子的服飾,后成為漢族女子的常服。一個(gè)民族所能產(chǎn)生的文化,不應(yīng)該把它稱之為“文化特色”,而應(yīng)該是“文化生命力”,從這一方面來說民族的便是世界的。如果一味地禁錮封閉,優(yōu)點(diǎn)就會(huì)慢慢轉(zhuǎn)變成缺點(diǎn)。對(duì)于繪畫而言更是如此,文化的生命力決定了它的競(jìng)爭(zhēng)力,同樣,繪畫的創(chuàng)造力促成了它的持續(xù)力。
關(guān)于“中國(guó)畫”這個(gè)定義也是近百年來才有的新名詞,是與“西洋畫”相對(duì)而生的,就像在西醫(yī)進(jìn)入中國(guó)之前,只有“醫(yī)術(shù)”而沒有所謂的“中醫(yī)”之詞。我們應(yīng)該有作為繪畫發(fā)展的基礎(chǔ)底線,但不能讓傳統(tǒng)成為“束縛”,如此才能真正地迎來百花齊放的藝術(shù)之春。這樣的繪畫發(fā)展道路,才能使傳統(tǒng)得以積累沉淀,并且歷久彌新,才不至于抹殺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光芒,就如同西方繪畫中的印象派、現(xiàn)代主義、未來主義在一段時(shí)期內(nèi)盛行卻從來沒有抹殺古典主義繪畫藝術(shù)的光芒。
清石濤有畫題跋曰:“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猶詩文風(fēng)氣所轉(zhuǎn)。上古之畫跡簡(jiǎn)而意淡,如漢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畫如初唐盛唐雄渾壯麗;下古之畫,如晚唐之句,雖清灑而漸漸薄矣;到元?jiǎng)t如阮籍、王粲矣,倪黃輩如口誦陶潛之句:‘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恐無復(fù)佳矣。”他的解讀有一定的時(shí)代局限性,但他提出了“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這一理念,如若石濤還在世,也許會(huì)有新的解讀,姑且由我等接過大道吧。在當(dāng)下這個(gè)時(shí)代,“開今”不僅需要“借古”,必要時(shí)還需要“借外”,這也是文化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這樣的筆墨,就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畫上筆墨了,它涵蓋了大千世界,涵蓋了人文歷史,是真正的“筆墨當(dāng)隨時(shí)代”,是對(duì)于筆墨在當(dāng)代繪畫發(fā)展中的最新解讀。
編輯:榮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