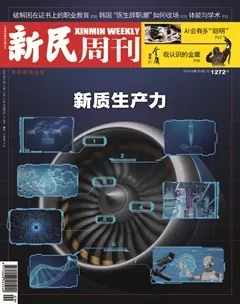戲劇“折射”真實
數十年來,我的戲劇創作之所以一直在變化,或以實驗作為手段,是因為我有意識不要演員以模仿現實的方式,來令觀眾認為或相信,他們的行為、感受,是完全等同真實的。從某個層面來說,這是為什么我更常以電影作為我的“聊天(靈感)”對象,而不是戲劇演出。
電影當然大多數也是以重塑的過程進行對真實的呈現,但在看電影和看戲劇時,最大的分別在于兩者的觀看方式,一個必然有著視點——鏡頭——的不停轉變。另一個,基于媒介性質,它的視點不能超越物理的局限,因而如何處理現場(空間)和當下(時間),讓真實被看見,既是戲劇藝術的創造性所在。但亦可能弄巧反拙,愈是追求,效果愈是虛假。
Pseudo(偽、假冒) ,是我最不希望出現在劇場里的空氣。但我毫不介意戲劇看上去很unreal(虛幻、不真實),甚至,它就是因此而存在。 Unreal,包含動機與表現上的脫離現實。在我的作品里,舞臺空間經常出現一景到底,便是方式之一。辦公室的戲沒有辦公室;又或,酒店的陳設,其實是“中陰”(陰陽之間);又或,廚房不因情節需要具有意義,而是在扮演“人與聲音”的交流場域。
故此,演員在架空了空間意義的“現場”,理論上,“現”便失去了“現在”的說服力。演員的演出,便不能著力于觀眾所見的當下,卻要繞過不存在的實景實物,以對過去經驗的心領神會,引領觀者進行同樣的參與。我把這過程定義為“打開自己給戲去觀照”。演員是媒介,媒介不負責提供(或還原)現實,但它應該以反射或折射現實的功能,協助觀者找到所見所聞的意義。

林奕華導演戲劇、寫作、電影
戲劇相對于電影,觀看的成份少了千變萬化,再加上先天性的距離因素,便更重于聆聽。
戲劇相對于電影,觀看的成份少了千變萬化,再加上先天性的距離因素,便更重于聆聽。常說舞臺演員對于吐字、發音,以致抑揚頓挫的操縱能力決定了一臺演出的力度,更是一部作品賦予觀眾感受的靈魂,是以如何“說話”成了演出與觀眾的契約,把話說好,幾乎等同把一部戲劇要傳遞的訊息,有效地達成了有素質的溝通。也就是,做到了呈現真實的目的。
如果舞臺上的演員只像鏡子般矗立在照鏡的人面前,這鏡像只是提供了直接的反射,即便反射出來的是照鏡的人的面貌,但那種真實,也只是照鏡的人最熟識的“正面”,不會同時讓這個人看見其(不同角度的)“側面”,遑論“背面”。以一個角度反映真實,不能與“說謊”同義,只不過,如此反映的真實,未必是客觀,更可能是主觀。
戲劇怎樣才能做到“折射”?很多劇場導演都會使用“即場攝錄”(Live Feed),把現場正在發生的事件,以多過一個角度,甚至多過一個時空(結合預錄),呈現在觀眾眼前。只是,在現場架起另外的“眼睛”(鏡頭),是否等于被呈現的影像就有“折射”的作用?觀眾就能在多角度的情況下,讓戲觀照了自己?抑或,另外的“眼睛”,也只是在建構欲望的放大多于真實。由于真實所代表的陌生感、隔異感,會讓觀者產生抗拒,一如走在商場里,忽然在某面反射物上看見有雙充滿懷疑的眼睛盯住自己,你是誰?充滿戒心的聲音,換來不大令人愉悅的回響:我就是你。
于我來說,那些讓人因懷疑、不舒服的對自己的感受而萌生的“猛然發現”,才是現代(藝術)戲劇存在的意義:隨著科技成了意識形態機器主宰多數人的思想與行為,真實只能存在于集團式的經營運作里,就像快餐、快時尚、快影像,“現實”比什么都重要,已經不再追求真實之于現實的差異——多數人相信的就是我們應該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