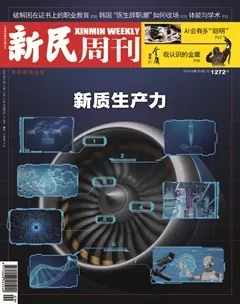對“媽校”的感情,強求不來的
今年櫻花還沒開,武漢大學提前火了,原因是武大校長張平文“喊你上武大”的招生視頻。張校長說:“我來到珞珈山已經三個年頭了,但實際上也就一年多。但是我熱愛武漢大學,因為這里特別像北京大學。”
短短的幾句話,每一個轉折都出人意料,特別是最后一句,真是把懸念放房梁上繞了三日,招生視頻很快就被網友套用了《甄嬛傳》里的典故,說成了“莞莞類卿”:“大胖橘”喜歡甄嬛是因為她長得像“純元皇后”。
張校長之前一直在北大學習、深造,之后在北大當領導,一年多以前才空降到武漢大學當校長。有人說,這位學數學的院士耿直,才會把心里話說出來。
其實,夢中喊出前任的名字還不是最有殺傷力的,最可怕的是婚禮現場,司儀那邊問:你是怎么愛上新娘的?你說:“因為她特別像我的前任。”我不相信新娘這時會夸一句,“我老公真是個耿直BOY”。
同理,這是一條武漢大學的招生視頻,而不是領導的即興發言,一個宣傳片從腳本撰寫、領導口播、后期制作,經手、過關的人還是很多的,但似乎都沒覺得這種“欲把西湖比西子,武大還是像北大”的恭維話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至少這么多工作人員就沒覺得母校被校長當成“替身文學”有什么不妥。

沈彬專欄作家假裝專家,低空觀察
高校不僅是發文憑的地方,而且是畢業生們深深的情感連結。
這些年來,大學的等級愈發固化,普本之上是211的人上人,211之上是985的人上人,然后就是各種細分:985“守門員”、中流985、C9俱樂部、TOP4以及王炸——清北,真是涇渭分明。說到TOP4想到一個笑話:如果一個人說自己是TOP4畢業的,他可能是復旦的、上交乃至南大、浙大的,但肯定不是清北的。
在這種微妙的比較之下,畢業生對母校的情感弱了,畢業高校徹底變成一種身份、資產乃至相親市場里面的資源要素。
其實大學之間難道不應該是平等的嗎?學校間的競爭不應該是參差不齊的嗎?回溯到20世紀80年代劉道玉校長的時代,大概沒有一個武大的學子自覺屈居北大之下,一如在謝希德校長領導之下,大概也沒有人覺得復旦和北大的關系是天然的“上下”關系。
也許當下賽道日益狹窄、競爭日益激烈,大家各種卷不動、躺不平,恰恰固化了大學之間的高低等級,而大學——特別是名校成了很多人扛了一輩子的蝸牛殼。
我曾經參觀過武大的校園,哪怕我是一個和武大沒淵源的陌生人,也被校園的深厚底蘊折服:櫻園宿舍建在山坡上,琉璃瓦灰墻,此間少年穿梭在迷宮般的民國老建筑里;一株橫柳匐伏在操場邊上,運動間歇,武大學子站在其間,夕陽的余暉灑進近百年前的宋卿體育館:這就是一所名校該有的樣子。
英語里母校并不叫mother school,而是沿用了一個古老的拉丁文單詞alma mater,意為“哺育的母親”,“母校”就是那個給奶喝的人。完善的高等教育離不開母校的哺育,高校不僅是發文憑的地方,而且是畢業生們深深的情感連結:某間教室里經歷了最摧殘人的考試,某株柳樹下曾牽過手,食堂里吃過紅燒大排……當時覺得平常,回憶時卻很美好。感情像良心一樣,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存在“發現”一說。
感情這個事,是強求不來的,對“媽校”的感情也是如此。雷軍給武漢大學捐了13個億,一定不是因為武大長得特別像北大。既然叫了“媽”,那就得不嫌母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