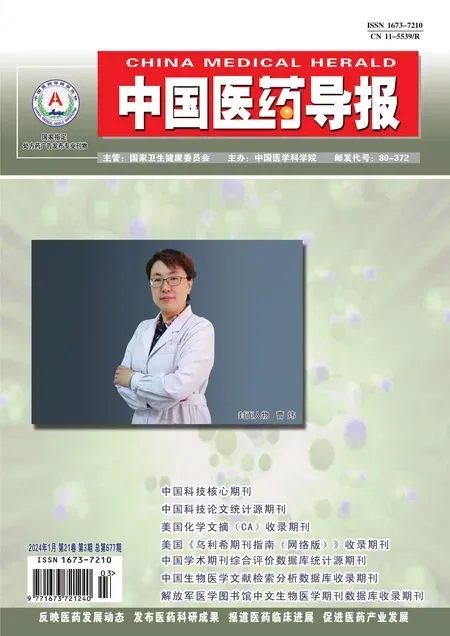健脾疏肝方顆粒治療肝郁脾虛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臨床效果及對腸道菌群的影響
施曉軍 侯秀娟 李軍祥 章 妍 姚玉璞 謝春娥 王允亮
1.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風濕病科,北京 100078;2.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脾胃肝膽科,北京 10007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 ease,NAFLD)是目前慢性肝病的主要病因之一。NAFLD發病率逐年上升,全球總患病率約為32.4%[1],一旦進展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將顯著提高肝硬化、肝衰竭和肝癌的風險[2-4]。目前NAFLD 發病機制仍未完全闡明,西醫缺乏特效治療藥[5]。中醫藥對NAFLD 的治療在改善臨床癥狀及肝功能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其作用可能與腸道菌群有關[6-7]。健脾疏肝方是臨床治療NAFLD/NASH 的效驗方,已獲專利授權(ZL201110042447.1)。本研究通過雙盲、雙模擬、隨機對照方法,觀察健脾疏肝方治療肝郁脾虛型NAFLD 臨床效果,以期為本方臨床應用提供更多證據支持。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9 年12 月至2021 年12 月來自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脾胃肝膽科門診NAFLD 受試者40 例,隨機分為中藥組與西藥組各20 例。中藥組男15 例,女5 例;年齡(43.75±8.14)歲,西藥組男15 例,女5例;年齡(42.70±10.05)歲。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JDF-IRB-2019034903)。
1.2 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標準:參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 年更新版)》[8]中NAFLD 診斷。中醫診斷標準:參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9]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意見》[10]擬定肝郁脾虛證。
主癥:①脅肋脹滿或疼痛;②倦怠乏力;③抑郁不舒;④腹痛欲瀉。次癥:①腹脹不適;②周身困重;③惡心欲吐;④食欲不振;⑤大便黏滯不爽;⑥時欲太息。舌脈:舌淡紅,苔薄白或白,有齒痕,脈弦細。證型確定:具備主癥2 項(第1 項必備)加次癥2 項,參考舌脈即可診斷。
1.3 納入及排除標準
1.3.1 納入標準
①符合NAFLD 診斷;②符合肝郁脾虛證;③GPT升高(<正常高線5 倍)>6 個月;④18~65 歲;⑤試驗前2 周內未接受同類藥品及益生菌治療;⑥自愿參加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2 排除標準
①伴主要臟器嚴重病變或精神疾病;②孕婦及哺乳期婦女;③對本研究藥物已知成分及輔料過敏。
1.4 脫落標準
①自行退出;②失訪。
1.5 剔除標準
①未曾使用研究用藥;②試驗期間,使用保肝降酶藥或微生態制劑等。
1.6 研究設計
本研究使用雙盲、雙模擬、隨機對照方法,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受試者隨機分配至中藥組和西藥組。
1.7 治療方案
中藥組:健脾疏肝方顆粒(華潤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批號:1910003,規格:8.4 g/袋),2 次/d,1 袋/次,溫水沖服;多烯磷脂酰膽堿膠囊模擬劑(浙江廣聚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號:20 170002;規格:24粒/板),3 次/d,2 粒/次,口服。
西藥組:健脾疏肝方顆粒模擬劑(華潤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批號:1 911005;規格:8 g/袋),2 次/d,1袋/次,溫水沖服;多烯磷脂酰膽堿膠囊[賽諾菲(北京)制藥有限公司,批號:9BJD266,規格:228 mg/粒],3次/d,2 粒/次,口服。
健脾疏肝方組成:炒白術、茯苓、澤瀉、白芥子、絞股藍、決明子、丹參、郁金、生山楂。治療12 周,統一進行飲食、運動教育。
1.8 觀察指標及療效判定標準
1.8.1 療效評價指標
①血清谷丙轉氨酶(glutamic-pyruvic transaminase,GPT):使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血清GPT 水平。②中醫證候評分:所有癥狀分為無、輕、中、重4級,主癥分別記0、2、4、6 分,次癥分別記0、1、2、3 分;舌脈不記分[9]。③肝臟脂肪含量:使用Fibroscan 檢測CAP。④肝臟B 超有效率:與基線比較,判定脂肪肝程度。痊愈:肝臟恢復正常,B 超顯示無脂肪肝;顯效:減少2個級別;有效:減少1 個級別;無效:無改善或加重[10]。
1.8.2 腸道菌群分析
使用糞便提取試劑盒提取菌群DNA,進行PCR擴增、純化、定量后,構建文庫。基于NovaSeq 平臺對文庫進行測序后分析菌群多樣性及組成。
1.8.3 安全性評價
血、尿、便常規,腎功能和心電圖。
1.9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間距[M(Q)]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 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隨訪中因失訪脫落3 例,因自行服用保肝中藥剔除1 例,最終受試者36 例。其中,中藥組19 例,西藥組17例。
2.1 兩組治療前后GPT 比較
治療前,兩組GPT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GPT 低于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組間GPT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治療前后GPT 比較[U/L,M(Q)]
2.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中醫證候積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中醫證候積分低于治療前,且中藥組低于西藥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分,M(Q)]
2.3 兩組治療前后CAP 值比較
治療前,兩組CAP 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中藥組CAP 值低于治療前,且中藥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CAP 值比較(±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CAP 值比較(±s)
注CAP:FibroScan 受控衰減參數。
2.4 兩組肝臟B 超有效情況比較
治療后,兩組肝臟B 超有效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肝臟B 超有效情況比較(例)
2.5 腸道菌群變化
2.5.1 Alpha 多樣性分析
治療后,Observed species、Shannon、Chao、Ace 水平高于治療前,Coverage 水平低于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前后,Simpson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

圖1 Alpha 多樣性指數比較
2.5.2 物種組成分析
2.5.2.1 門水平在門水平,中藥治療前后主要由厚壁菌門、變形菌門、擬桿菌門和放線菌門組成。治療前,其豐度依次為48.5%、18.2%、16.0%和4.4%;治療后,其豐度依次為54.9%、3.9%、32.7%和4.0%。
2.5.2.2 屬水平在屬水平,中藥治療前后主要由擬桿菌屬、棲糞桿菌屬、布勞特菌屬和普雷沃菌屬組成。治療前,其豐度依次為10.7%、9.2%、6.3%和3.0%;治療后,其豐度依次為19.5%、12.3%、6.5%和8.6%。見圖2。

圖2 屬水平相對豐度柱形圖
2.6 安全性評價
治療前后,所有受試者血、尿、便常規,腎功能、心電圖均在正常值范圍。治療期間,西藥組有1 例患者出現腹瀉,持續約1 周,后自行緩解。
3 討論
NAFLD 屬于中醫“積聚、脅痛、肝脹、肝癖(痞)”等范疇。李軍祥教授結合多年臨床經驗和歷代醫家論述,認為本病早期以肝郁脾虛為重,中后期以痰濕瘀熱等標實為先[11]。針對此病機,李教授創制了以健脾疏肝為主,兼顧化痰活血祛濕的健脾疏肝方。方用絞股藍健脾益氣化濕,郁金疏肝,白術、茯苓及澤瀉健脾祛濕,草決明清肝化濁,丹參、山楂活血降濁,白芥子溫化痰濕,全方配伍,共奏健脾疏肝、清熱化濕、祛痰化瘀之功。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以上諸藥可能參與調節肝臟氧化應激、改善糖脂代謝水平等多種機制治療本病[12-16]。
本研究結果顯示,健脾疏肝方顆粒與多烯磷脂酰膽堿膠囊均具有良好的保肝降酶作用,這與團隊前期的基礎研究結果一致[17-18]。在減少肝脂肪含量和改善臨床證候方面,健脾疏肝方較多烯磷脂酰膽堿膠囊臨床優勢更加明顯。遺憾的是,兩組在肝臟B 超改善上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該結果與其他研究不符,推測可能與本研究治療時間短、受試者數量較少有關[19-20]。
菌群紊亂可能是NASH 發生的機制之一[21-22]。諸多中藥可能通過調節腸道菌群紊亂,實現治療NAFLD 的目的[23-24]。健脾疏肝方治療后,受試者腸道菌群多樣性和豐富度得到改善,擬桿菌屬和普雷沃菌屬豐度增加最為明顯。兩菌可利用膳食纖維產生丙酸鹽,進入肝臟后,可改變代謝過程以降低肝臟脂質含量[25]。這可能是健脾疏肝方的作用機制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證明健脾疏肝方能有效降低NAFLD 患者GPT 及肝臟肝脂肪含量,改善脅肋脹痛、乏力等癥狀,其作用機制可能與調節腸道菌群組成有關。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