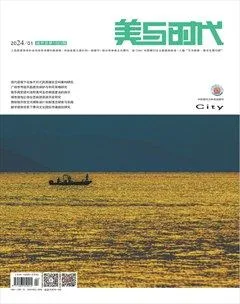“產、文、景”融合的上海城郊鄉村景觀更新策略研究
歐陽伊靜 浦靖璐 方智果
摘 要:在社會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傳統鄉土的景觀空間已不能滿足現代鄉村生活、生產功能的需求,鄉土景觀現代化轉型成為必然趨勢。探討受到城市化進程影響、物質空間變化的城郊鄉村所面臨的鄉村產業失活、傳統文化沒落和景觀風貌混雜的困境,提出產業、文化、景觀三者在城郊鄉村的發展與規劃中的聯系,構建“產、文、景”融合的上海城郊鄉村景觀更新策略,并以上海城郊月獅村景觀改造實踐為例,對“產、文、景”融合的景觀設計策略進行應用,以期為城郊鄉村景觀規劃研究提供助力。
關鍵詞:鄉村振興;地域文化;鄉村產業;景觀設計
我國鄉村與城市建設經歷了不同階段,鄉村的發展緩于城市發展進程[1]。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調好鄉村建設各方面利益[2]。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了系統的全面部署。當年還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旨在加快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進一步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水平[3]。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4]。上海市積極響應中央部署與安排,在2018年就發布了《上海市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打造“三園”工程,實施六大行動計劃、落實三大保障機制[5]。根據寶山區總體規劃,提出優化產業結構,加強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確保形成高識別度的特色文化風貌區,且將生態空間的重塑作為重要任務[6],從而實現產村融合。
一、上海城郊鄉村發展中的現存問題
由于城市與鄉村曾存在二元對立問題,各類資源涌向上海中心城區,導致上海鄉村發展緩慢,產業的活力逐漸消退,文化傳承出現斷裂,景觀陷入無序化狀態,使上海城郊鄉村的建設困境不斷加重。
從產業角度來看,上海城郊鄉村的產業結構在城市的影響下產生巨大變化,傳統農業占比下降,鄉村產業失活。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城郊鄉村的村民受到城市文化和生活模式的影響更深,地域文脈斷層嚴重,傳統文化沒落[7],且鄉村人口結構較復雜,存在文化資源挖掘不足、主題雷同等問題[8-9]。從景觀角度來看,上海城郊鄉村的鄉土景觀風貌混雜,日趨城市化,類似“別墅下鄉”,大拆大改模仿城市風貌,導致其現有風貌與鄉村原本肌理格格不入[10-11],造成了鄉村景觀同質化與單一化、空間缺乏可辨識性等一系列新時代的鄉村問題[12],使得當地傳統民俗與鄉土景觀逐漸消弭在城市化進程當中。
二、“產、文、景”融合的城郊鄉村景觀設計策略
產業、文化、景觀是鄉村空間的主要構成要素。“產”是城郊鄉村經濟提升的核心,也是支撐城市發展的重要基礎。城郊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不斷加深,聚落景觀與生產景觀交叉融合,產生復合功能[13]。“文”是由鄉村傳統文化、鄉村的公共精神以及城市文化的影響等多方面共同形成的特殊意識形態。其中,鄉村的公共精神是身處鄉村中的個體對共同利益的認同與維護,也是維系“鄉愁”的關鍵[14]。“景”即鄉村的景觀,是鄉村居民和游客在空間中能夠接觸到的自然景觀、建筑、民俗活動等多種自然和人類文化的復合體,兼具生態與經濟功能[15]。城郊鄉村的空間風貌則是在城市文化和鄉村傳統文化的共同影響下逐步形成的獨特景觀,城郊“產、文、景”三者之間互相促進,也互相制約。因此,對于城郊鄉村的更新與改造,應綜合考慮三者,協同發展。
(一)產業融合,激活內生動力
產業是鄉村發展和振興的重要基石,為各個方面的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目前,鄉村產業的升級迫在眉睫。其發展需要立足當地現有的資源優勢,借助城市的資本、科技、交通等要素對城郊鄉村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城郊鄉村在產業方面應更廣泛地使用現代科技和管理方式,延長農產品的產業鏈,以此提高農業附加值,具體可表現在現代化技術應用、可持續化生產、現代化宣傳及運營模式等。
(二)文脈延續,營造場景氛圍
歷史文化是鄉村的靈魂所在,挖掘研究并重續鄉村文脈是鄉村發展的重要手段。鄉村中的鄉風民俗、歷史事件以及文化內涵等都深刻影響著村落的形態、肌理和自然生長。鄉土歷史文化不僅能夠影響鄉村的整體風貌特征,也同樣是鄉村對于城市游客獨特的吸引力。因此,對歷史文化內涵的挖掘和提煉,是鄉村景觀更新的重要策略之一。
(三)空間重塑,提升鄉村景觀品質
鄉村的公共空間與鄉土文化、生產生活方式有機協調,承載了最真實的鄉村生活。自古以來,鄉村公共空間就是鄉村社會信息、物質媒介交換的場所,承載了當地諸多的集體記憶。對于鄉村公共空間的設計,應明確空間景觀所蘊含的內涵和承載的功能。在進行場所重塑時,應盡可能地使用鄉土材料、傳統工藝,塑造與當地鄉村整體風貌相適應的景觀。對鄉村的公共空間的重塑能夠提升鄉村景觀的品質,這對于村民和游客來說,也是鄉村記憶與現代生活方式的融合。
三、上海城郊鄉村景觀設計
——以寶山月獅村改造為例
(一)項目背景
1.區位條件
月獅村位于上海北部,地屬上海市寶山區月浦鎮,是典型的上海城郊融合類鄉村,總人口約3 500人,其中全村戶籍總人口846人,外來人口約2 600人。根據上位規劃,月獅村域的大部分用地將納入城市開發邊界內,屬于城郊融合型鄉村。本次項目基地屬于保留居民點,并已于2021年納入上海市第三批鄉村振興示范村。
2.上位規劃
在“十四五”期間,寶山區月浦鎮將奮力建設“生機勃發的經濟發展強鎮、生態美麗的花卉特色小鎮、生活美好的社會治理示范鎮”新三鎮,聚源橋村、月獅村、沈家橋村三村聯動,完善“鄉村會客廳”功能布局,以宜居精細管理引領鄉村高品質生活。
3.月獅村的社會情況
通過實地勘察,并結合調查問卷,了解到月獅村居民以房屋出租和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從事第一產業的比重相對較小,月獅村的常住居民以60歲以上的老年人為主。調查結果表明,村內約65%的居民對于鄉村目前人居環境呈正面評價,但還是希望能豐富文化活動項目,增加公共活動的空間和商業空間,以及引入和建設民宿、文旅產業。
(二)月獅村空間現存問題
1.處于花卉產業起步期,新業態融合不足
月獅村已形成以花卉種植為特色產業的發展道路,但仍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每年花卉節期間,游客流量達到頂峰,而后逐步下降,呈現明顯的周期性。植入的新興產業如旅游業、婚慶服務業、民宿產業等,與月獅村的基礎產業融合不到位,基礎建設不足,無法承接大量游客。
2.鄉村性喪失,文化向城市趨同
隨著上海城市的高速發展,月獅村的大部分村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青壯年勞動力大都進城工作,閑置的房屋和土地多被出租給外來人員,加劇了鄉村文化斷層。鄉村傳統歷史文化難以為繼,城郊鄉村居民意識形態逐漸向城市文化靠攏。
3.公共空間失序,建筑風貌混亂
新鄉村“別墅下鄉”的建設,造成了鄉村建筑風格上的混亂,大量仿歐式別墅紛紛涌現,取代了江南傳統民居粉墻黛瓦的典型特征,對我國傳統鄉村聚落形式和建筑風格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月獅村中的建筑風貌混亂,以近十年來自建的洋房別墅為主,間或有數棟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造的二層坡頂磚房,諸如此類的新建民居缺乏文化識別性與地域氣質,原有的場所文化精神消失殆盡。
(三)以“花”為主題的月獅村農旅產業一體化定位
1.特色產業轉型,植入新型業態
將月獅村的產業轉型方向定位為“文化農旅”:以花卉為主要經濟作物、水稻為主要糧食作物支撐鄉村產業,在此基礎上延長并完善產業鏈,發展特色農業,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此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植入民宿、特色活動等,完善城郊旅游體驗,滿足城市居民親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需求。
鄉村振興背景下,對月獅村的產業結構逐步進行調整。為實現與周邊村域協同和差異化發展,在月獅村基地著重強調鄉村旅游的農事體驗活動和配套服務,同時充分利用濱水優勢,塑造臨水空間景觀,發展月獅村的水上賞花、休閑垂釣等活動。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和舒適的旅游服務及多樣化的觀花體驗,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提升,推動當地的可持續發展。
2.歷史文化挖掘,塑造在地景觀
通過訪談調研,發現月獅村村民在閑暇時刻喜好欣賞昆曲,而且村莊也會定期舉辦業余昆曲大會,故而可將昆曲作為主要元素融入景觀設計中,將月獅村定位為昆曲文化科普基地,并結合種植的花卉,打造田園花海景觀,同時植入婚慶產業,實現產業的多元化生長。針對月獅村肌理混亂、建筑風貌混雜的現狀,對場地肌理進行重新梳理、整合以及規劃,依據現有條件將其劃分為不同片區,并植入相對應的功能,同時對當地建筑風貌進行整體統一的規劃設計。
3.構建環線路網,立體景觀層次
月獅村現有道路體系僅有一條主路,尚未形成環線,支路過窄,車輛與行人存在一定安全隱患,且游人無法全覽花田景觀。在原生道路體系上,以花為靈感,設計以南北向和東西向為主路的游覽主軸,建立合理的環線路網,進而對二級、三級道路進行梳理和細分,實現人車分流,以供村民、游客日常出行和全方位游覽。在水岸設計中,進行柔化處理,并設置沿河景觀步道,塑造河岸景觀,增加親水性,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挖掘項目基地的濱水優勢,同時植入各類水上活動,然后通過廊架串連不同功能片區的立體觀花流線,使之與項目基地內的主要場所以及濱水區域、游船碼頭相連接,最大程度地保持觀光線路的通達性,同時滿足環視觀花的功能要求,使觀花的視角更加豐富,增強游客的體驗感。
綜上所述,鄉村振興戰略在全國加速推進,城市與鄉村的差異性問題也日漸得到關注。城郊鄉村屬于城市與鄉村的交匯地帶,不僅有鄉村的田園景觀,也有城市便捷的交通,憑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空間特征,在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本文基于鄉村振興背景,提出以“產、文、景”融合的方式對城郊鄉村景觀空間進行更新,通過對上海城郊鄉村景觀現狀的深入分析,探究產業、文化、景觀三方面融合的改造策略,為我國城郊鄉村的研究延伸出新的方向,并結合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為城郊鄉村改造提供新的建議和策略。
參考文獻:
[1]許紅梅,郭炎,李志剛,等.大城市近郊農地流轉的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武漢蔡甸區為例[J].地理科學,2020(12):2 055-2 063.
[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公布提出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EB/OL].[2023-12-16].http://www.gov.cn/xinwen/2017-02/05/content_5165613.htm.
[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EB/OL].[2023-12-16].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5/content_5264056.htm.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EB/OL].[2023-12-16].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2/content_5675041.htm.
[5]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上海市鄉村振興實施方案(2018-2022年)》的通知[EB/OL].[2023-12-16].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720/046782b10d2145c0b201
c41aca762196.html.
[6]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同意《上海市寶山區總體規劃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17-2035)》的批復[EB/OL].[2023-12-16].https://www.shanghai.gov.cn/nw42844/20200823/0001-42844_57919.html.
[7]鄶艷麗,鄭皓昀.傳統鄉村治理的柔軟與現代鄉村治理的堅硬[J].現代城市研究,2015(4):8-15.
[8]栗小丹.上海鄉村旅游發展問題與對策研究[J].農業經濟,2020(8):62-63.
[9]黃國華.上海城郊旅游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及其對策:基于SWOT分析框架的研究[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10(5):78-79.
[10]王竹,范理楊,陳宗炎.新鄉村“生態人居”模式研究:以中國江南地區鄉村為例[J].建筑學報,2011(4):22-26.
[11]崔園園.上海大都市周邊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和模式[J].科學發展,2021(5):69-78.
[12]高春留,程勵,程德強.基于“產村景”一體化的鄉村融合發展模式研究:以武勝縣代溝村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19(5):90-97.
[13]楊亞東,羅其友,杜婭婷,等.鄉村振興背景下的“產—景—村”融合發展:現狀與對策[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1(3):232-239.
[14]田健,曾穗平,曾堅.重構·重生·重現:基于行動規劃的傳統鄉村“微”振興策略與實踐探索[J].城市發展研究,2021(1):60-70.
[15]仝曉曉,熊興耀.基于建筑類型學的蘇南新農村農居設計[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6):12.
作者簡介:
歐陽伊靜,上海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空間存量更新。
浦靖璐,上海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空間存量更新。
方智果(通訊作者),博士,上海理工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空間存量更新、鄉村振興和大數據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