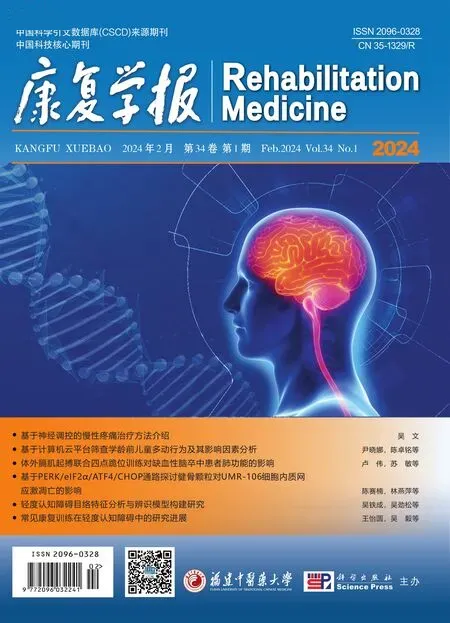體外膈肌起搏聯合四點跪位訓練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肺功能的影響
盧 偉,董朋霞,謝天培,范穎潔,仇 浩,劉昊宇,蘇 敏*
1 蘇州大學附屬第四醫院(蘇州市獨墅湖醫院),江蘇 蘇州 215000;
2 臺州學院附屬市立醫院,浙江 臺州 318000;
3 蘇州大學康復研究所,江蘇 蘇州 215000
在過去的30年里,缺血性腦卒中給世界范圍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負擔顯著增加[1-2]。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常出現肺功能障礙,臨床表現包括呼吸肌麻痹、肌力降低、肺通氣和換氣功能減弱等,存在加重腦卒中肺炎和復發的可能性[1]。因此,尋找有效的康復治療手段改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肺功能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目前,臨床上除了吸氣肌訓練和氣道清除技術等常規治療手段外,體外膈肌起搏已被廣泛應用于肺部康復。體位是控制呼吸的技術之一,通過改善呼吸肌功能,從而減輕呼吸困難[3]。研究發現四點跪式支撐改變了胸腹的形狀和運動[4-5],影響胸腹順應性和肺功能性剩余容量,從而改變呼出潮氣量的限制[6]。與有意識的俯臥位相比,四點跪式對改善胸腹呼吸輔助肌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有關于外膈肌起搏聯合四點跪位訓練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肺功能的臨床療效鮮有報道。本研究將探討體外膈肌起搏聯合四點跪位訓練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肺功能的影響,為體外膈肌起搏聯合四點跪位訓練的推廣應用提供依據。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選擇標準
1.1.1診斷標準 缺血性腦卒中符合《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8》[7]中的診斷標準,并經MRI或CT檢查確診。
1.1.2納入標準 ① 年齡18~65 歲,無嚴重認知障礙者;②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正常期望值80%者;③ 病程<3個月,無重癥肌無力或膈神經麻痹者;④ 生命體征穩定,可以配合訓練者;⑤ 患者臨床資料完整,簽署知情同意書,積極配合治療者。
1.1.3排除標準 ① 有肺部、胸部和腹部疾病史;② 有吸煙史;③ 合并重癥肌無力或膈神經麻痹;④ 合并嚴重心臟病、肝硬化、腎功能衰竭、嚴重全身性疾病和惡性疾病;⑤ 體內存在金屬植入物;⑥ 上肢-手-下肢的Brunnstrom評分低于Ⅲ-Ⅲ-Ⅲ。
1.2 一般資料
本研究為前瞻性、隨機對照臨床研究。選取2023 年1 月1 日—6 月30 日在蘇州大學附屬第四醫院康復科住院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70 例。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后,采用隨機數字表法以1∶1 的分配原則將其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每組35例。在治療過程中,2 組均有5 例患者因依從性不強、提前出院而脫落,最終每組納入30 例。2 組性別、年齡、療程及腦梗部位經統計學分析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研究已通過蘇州市獨墅湖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審批號:230068)。

表1 2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i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2 方 法
2.1 治療方法
2.1.1常規基礎治療 2 組均采取改善腦循環、保護腦細胞、維持水及電解質穩定性等常規藥物治療及呼吸肌運動訓練的常規基礎治療,包括腹式呼吸鍛煉、縮唇呼氣、阻力呼吸鍛煉,每次15 min,每天訓練2次,改善膈肌功能、動態肺順應性和肺通氣。
2.1.2對照組 使用體外膈肌起搏器進行常規肺功能康復治療。患者首先清潔皮膚,然后將治療電極片連接胸鎖乳突肌下端外緣1/3 處(平環狀軟骨水平處),輔助電極片置于鎖骨中線第2肋之間。起搏頻率12~18 次/min 或根據呼吸頻率/2 調整。刺激頻率為40 Hz,根據患者對電刺激的疼痛耐受性,盡可能加大刺激強度,刺激強度為10~15 U 或根據患者耐受水平調整。治療時間分別為4周和8周,每周5次,每次30 min。
2.1.3治療組 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四點跪位訓練。在該體位下,患者雙手掌和前腳掌置于地面,身體與大腿成90°夾角,膝關節成90°夾角,膝關節自由懸空,腹部收緊,背部伸直。根據患者的耐受性調整中間放松時間,治療時間分別為4 周和8 周,每周5次,每天30 min。
所有參與研究的人員都接受了標準化培訓,熟悉操作流程,并嚴格按照標準流程進行相關操作。數據由1 名治療師和1 名醫生記錄,交換數據進行審查,以確保數據輸入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數據分析由專業人員進行,確保數據分析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2.2 評定方法
2.2.1膈肌厚度及厚度變化率 采用新型Terason uSmart 3300 超聲系統評估患者治療前后健康側和患側平靜呼氣末膈肌厚度(calm end-expiratory diaphragm thickness,CEEDT)、最大吸氣末膈肌厚度(maximum end-inspiratory diaphragm thickness,MEIDT)。患者取仰臥位,囑其平靜呼吸,將探頭垂直放置于8~9 或7~8 胸壁輔助間隙,探頭標記面朝患者頭部。在二維超聲模式下,調整M 模式,將取樣線垂直于膈肌,分別測量CEEDT 和MEIDT,重復測量3次,取平均值作為最終測量結果。
2.2.2膈肌移動度 患者取相仰臥位,要求平靜呼吸。對于右半膈肌,將探頭放置在右鎖骨中線前肋下的區域。在二維超聲模式下,找到下腔靜脈及膽囊,當膈肌出現較粗的高回聲線時,調整傳感器的方向以確保其指向膈肌的內側、顱側和背側。然后將傳感器調整到M 模式。M 線放置在距顱-尾線約30°的位置,在平靜呼吸和深呼吸時測量治療前后健康側和患側的平靜呼吸膈肌移動度(quiet breathing diaphragm mobility,QBDM)和深呼吸膈肌移動度(deep breathing diaphragm mobility,DBDM)。對于左半膈肌,將探頭置于腋窩前中線之間,二維模式下進行橫向掃描,確定肺門與脾臟之間的最大距離,然后切換到M 模式進行膈肌運動測量,在平靜呼吸和深呼吸時測量治療前后健康側和患側QBDM和DBDM。
2.2.3肺功能評估 使用MasterScreen 肺功能儀進行肺功能測試。在坐姿情況下,指導患者快速呼氣,測量FVC、第1 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FEV1)、FEV1/FVC、最大呼氣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PEF)。重復測量3 次,取平均值作為最終測量結果。
2.2.46 分鐘步行距離 6 分鐘步行距離(6 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是指選擇平坦、有明確標識的走廊,讓患者盡力步行6 min,記錄行走的最長距離,重復測量3次,取平均值作為最終測量結果。
2.2.5Borg 評分 該評分范圍為0~10 分,評分越高提示患者呼吸越困難。
2.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使用SPSS 25.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服從正態分布以(±s)表示,進行t檢驗;不滿足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或等級資料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進行比較。以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 結 果
3.1 2 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CEEDT、MEIDT比較
2 組治療前健側和患側的CEEDT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對照組治療4周后健側的CEEDT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治療8 周后健側的CEEDT 提高(P<0.05);對照組治療4、8 周后患側的CEEDT 均明顯高于治療前(P<0.05)。與治療前比較,治療組治療4、8 周后健側和患側的CEEDT 均明顯提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第8 周后健側和患側的CEEDT均提高(P<0.05)。見表2。
表2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CEEDT比較(±s)cmTable 2 Comparison of CEEDT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表2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CEEDT比較(±s)cmTable 2 Comparison of CEEDT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2 組治療前健側和患側的MEIDT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2組治療4、8 周后健側和患側的MEIDT 均升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4、8 周后健側和患側的MEIDT均提高(P<0.05)。見表3。
表3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MEIDT比較(±s)cmTable 3 Comparison of MEIDT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表3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MEIDT比較(±s)cmTable 3 Comparison of MEIDT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3.2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QBDM、DBDM比較
2 組治療前健側和患側的QBDM 和DBDM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治療4、8 周后健側和患側的QBDM 和DBDM 均升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4、8 周后健側和患側的QBDM 和DBDM 均提高(P<0.05)。見表4、表5。
表4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QBDM 比較(±s)cmTable 4 Comparison of QBDM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表4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QBDM 比較(±s)cmTable 4 Comparison of QBDM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表5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DBDM 比較(±s)cmTable 5 Comparison of DBDM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表5 2組治療前后健側和患側DBDM 比較(±s)cmTable 5 Comparison of DBDM on unaffected side and affected sid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cm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3.3 2 組治療前后FEV1、FVC、FEV1/FVC 及PEF水平比較
2組治療前FEV1、FVC 和PEF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2 組治療4、8周后FEV1、FVC 和PEF 水平均升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4、8周后FEV1、FVC 和PEF水平均提高(P<0.05)。2 組治療前FEV1/FVC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對照組治療4、8 周后FEV1/FVC 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治療4、8 周后FEV1/FVC水平均明顯升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4、8 周后FEV1/FVC 水平均提高(P<0.05)。見表6。
表6 2組治療前后FEV1、FVC、FEV1/FVC及PEF比較(±s)Table 6 Comparison of FEV1,FVC,FEV1/FVC and PEF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表6 2組治療前后FEV1、FVC、FEV1/FVC及PEF比較(±s)Table 6 Comparison of FEV1,FVC,FEV1/FVC and PEF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3.4 2組治療前后6MWD比較
2 組治療前6MWD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對照組和治療組治療4、8 周后6MWD 均提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8 周后6MWD 明顯提高(P<0.05)。見表7。
表7 2組治療前后6MWD比較(±s)mTable 7 Comparison of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m

表7 2組治療前后6MWD比較(±s)mTable 7 Comparison of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m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3.5 2組治療前后Borg評分的比較
2 組治療前Borg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治療前比較,2組治療4、8周后Borg評分均降低(P<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治療8周后Borg評分明顯降低(P<0.05)。見表8。
表8 2組治療前后Borg評分比較(±s)分Table 8 Comparison of Borg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Scores

表8 2組治療前后Borg評分比較(±s)分Table 8 Comparison of Borg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Scores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4 討 論
肺部功能障礙是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在恢復期常見的后遺癥之一,會出現胸悶、氣短、呼吸困難、呼吸道感染,住院時間延長,嚴重者會對患者的生命安全帶來威脅[1-2]。研究表明,患者肺功能下降與膈肌功能下降、運動能力下降、胸廓擴張度減弱、呼吸肌功能受損、胸肌細胞數量減少、肌肉纖維化等有關[8]。其中膈肌功能下降、運動能力下降可致肺組織順應性和氧輸送能力下降,誘發肺功能惡化及心肺適應性下降,繼而進一步促使并發癥發生,嚴重影響患者功能的恢復[9]。患者發生缺血性腦卒中后,其患側膈肌明顯比健側薄[10-11]。因此,促進膈肌功能和運動能力提升對改善肺功能至關重要。
在本研究中,我們旨在制定一種簡單有效的康復訓練,通過促進膈肌活動,增強膈肌的厚度和活動性,促進呼吸功能恢復,從而進一步提高患者的整體功能。研究發現,俯臥位能夠改變橫膈的運動且減輕其他臟器對肺組織的壓迫,降低對肺的負擔而增大擴張程度來改善肺通氣,同時俯臥位也能夠改善氧合,說明體位改變能改善肺功能[12-14]。考慮到俯臥位的病理生理機制,四點跪位可能具有類似的生理作用,包括改善通氣不平衡和血液灌注比,促進肺復張,減少患者自身造成的肺損傷[15]。目前,四點跪位在康復練習中被廣泛使用。有研究表明,四點跪位時腹部橫肌和內斜肌的激活率高于仰臥位[16]。此外,四點跪位能夠提高膈肌長度-張力的關系和功能,減少胸鎖乳突肌和斜角肌的聚集,促進胸腹運動,減輕呼吸困難[17]。同時,四點跪式支撐可以改變胸腹形態和運動,影響胸腹順應性,從而影響潮氣量的限制和功能剩余量。因此,四點跪位具有改善肺功能障礙的潛力。體外膈肌起搏是目前臨床上廣泛使用的肺康復手段,其通過皮膚表面電極刺激膈神經引導膈肌有規律地收縮,增加胸氣量和潮氣量,改善呼吸肌疲勞和通氣功能,從而改善肺功能和臨床癥狀,并促進咳嗽和氣道廓清。基于以上研究,我們采用體外膈肌起搏技術結合四點跪位來改善膈肌和肺功能。本研究發現相對于單純體外膈肌起搏,體外膈肌起搏聯合四點跪位訓練能夠更有效地改善肺功能,治療第4 周后治療組的CEEDT、MEIDT、QBDM、DBDM、FEV1、FVC、FEV1/FVC、PEF、6MWD 及Borg 評分均出現明顯變化,治療第8周后上述指標變化更明顯,說明接受治療時間越長,改善越明顯,這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康復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因此,體外膈肌起搏聯合四點跪位訓練加速提高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肺功能。
但是,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樣本量小;研究周期不足;沒有確定外膈起搏技術結合四點跪位是否對所有肺功能障礙患者有效;相關的肺康復機制尚不明確。雖然本研究證實了四點跪位訓練對改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肺功能具有較好的效果,需要進行更多的相關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體外膈肌起搏技術結合四點跪位訓練可以改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肺功能,值得在臨床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