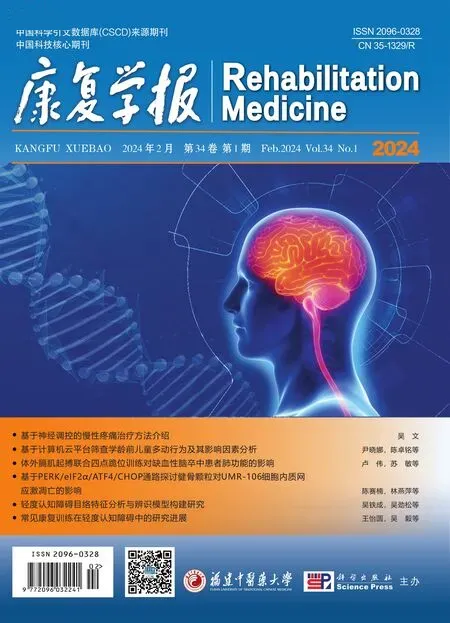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對(duì)腦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的影響
王子豪,胡 川,張海泉,王 欣*
1 山東體育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102;
2 山東大學(xué)附屬省立第三醫(yī)院,山東 濟(jì)南 250031
腦卒中在我國(guó)具有高發(fā)病率和高死亡率的特點(diǎn),數(shù)據(jù)顯示僅2019年我國(guó)新診斷的腦卒中案例就高達(dá)394 萬(wàn)例[1-2]。據(jù)統(tǒng)計(jì),只有5%~20%的腦卒中患者能夠完全使用上肢,25%的患者能夠部分使用,而60%的患者則完全不能使用,這嚴(yán)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限制其獨(dú)立生活所必需的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3]。隨著康復(fù)醫(yī)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基于神經(jīng)可塑性理論的中樞-外周-中樞的閉環(huán)康復(fù)理論逐漸應(yīng)用于臨床,并成為腦卒中后上肢及手功能障礙康復(fù)的研究熱點(diǎn)。該理論強(qiáng)調(diào)將中樞干預(yù)和外周干預(yù)相結(jié)合,形成“閉環(huán)”信息反饋傳導(dǎo)通路,提高神經(jīng)可塑性,強(qiáng)化肢體的運(yùn)動(dòng)控制模式,對(duì)腦卒中后上肢及手功能障礙的康復(fù)具有積極意義[4-5]。
互動(dòng)式頭針由互動(dòng)式針刺法發(fā)展而來(lái),為我國(guó)著名學(xué)者陳爽白所創(chuàng)建,提出針刺得氣后,患者可在針刺期間主動(dòng)運(yùn)動(dòng)相關(guān)部位[6]。頭針作為一種中樞干預(yù)方式,通過(guò)促進(jìn)大腦半球間功能重塑、改善局部腦血流量、增強(qiáng)神經(jīng)系統(tǒng)可塑性,從而促進(jìn)肢體功能恢復(fù)[7]。外骨骼機(jī)器人作為一種外周干預(yù)方式,可以為患側(cè)上肢提供密集、重復(fù)性、任務(wù)導(dǎo)向的肢體運(yùn)動(dòng)訓(xùn)練,有效地幫助患者恢復(fù)上肢的功能[8-10]。頭針與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在臨床上被廣泛應(yīng)用,但鮮有研究報(bào)道兩者結(jié)合所帶來(lái)的臨床療效。
因此,本研究以閉環(huán)理論為基礎(chǔ),采用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閉環(huán)治療模式,旨在為臨床實(shí)踐提供更為有效的上肢康復(fù)治療方案。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選擇標(biāo)準(zhǔn)
1.1.1納入標(biāo)準(zhǔn) ① 符合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神經(jīng)病學(xué)分會(huì)2018 年制定的腦卒中診斷標(biāo)準(zhǔn)[11],并經(jīng)CT 或MRI證實(shí)的首次缺血性或出血性腦卒中的單側(cè)偏癱患者;② 患者采用保守治療,未經(jīng)開(kāi)顱等外科治療;③ 腦卒中首次發(fā)病;④ 患者一側(cè)肢體運(yùn)動(dòng)功能障礙且上肢無(wú)過(guò)度痙攣(改良Ashworth量表≤1+);⑤ 患側(cè)上肢Brunnstrom分期≥Ⅳ期;⑥ 病程≤6個(gè)月。
1.1.2排除標(biāo)準(zhǔn) ① 合并嚴(yán)重的心、腎、肝、肺等內(nèi)科其他疾病;② 難以遵循和理解指令,不能配合治療患者;③ 同時(shí)參與其他康復(fù)試驗(yàn);④ 暈針或不配合針灸患者。
1.2 一般資料
本研究采用隨機(jī)、單盲、對(duì)照試驗(yàn)。本研究樣本量采用G*Power 3.1.9.7版本估算(G*Power 3.1.9.4版)。在計(jì)算樣本量時(shí),以Fugl-Meyer 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評(píng)估量表(Fugl-Meyer upper extremity motor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F(xiàn)MA-UE)的效應(yīng)量為指標(biāo)。根據(jù)汪軍等[12]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作業(yè)療法的研究,其試驗(yàn)組BrunnstromⅣ~Ⅴ期的患者FMA-UE 在干預(yù)前為(42.54±10.08)分,干預(yù)1 個(gè)月后為(51.00±7.82)分,以檢驗(yàn)水準(zhǔn)α=0.05,檢驗(yàn)效能(1-β)=0.80,得出本研究所需每組最小的樣本量為9 例。考慮到20%左右的退出率,本研究中每組招募了20例參與者,共40例。于2022年2月—2023年2月在山東大學(xué)附屬省立第三醫(yī)院招募40 例腦卒中患者,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shū),并自愿參加研究。使用隨機(jī)數(shù)字列表將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duì)照組各20 例,2 組一般資料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jiàn)表1。評(píng)估人員不知道組別分布情況,干預(yù)前后的評(píng)估由同一個(gè)治療師進(jìn)行。本研究已通過(guò)山東大學(xué)附屬省立第三醫(yī)院倫理委員會(huì)審批通過(guò)(審批號(hào):KYLL-2021009)。

表1 2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2 方 法
2.1 治療方法
2 組均接受腦卒中相關(guān)基礎(chǔ)藥物聯(lián)合常規(guī)康復(fù)訓(xùn)練。
2.1.1對(duì)照組 在常規(guī)康復(fù)基礎(chǔ)上接受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治療。外骨骼機(jī)器人使用模型為A6-2 康復(fù)機(jī)器人,由中國(guó)廣州一康研究院開(kāi)發(fā)。患者可通過(guò)電子顯示屏進(jìn)行任務(wù)導(dǎo)向性訓(xùn)練,并根據(jù)患者的功能調(diào)節(jié)難度等級(jí),對(duì)患者進(jìn)行循序漸進(jìn)的訓(xùn)練。訓(xùn)練模式包括肩部、肘部和腕部的主動(dòng)與被動(dòng)模式,以及進(jìn)行單關(guān)節(jié)以及多關(guān)節(jié)聯(lián)合運(yùn)動(dòng),并能夠提供三維、更真實(shí)的運(yùn)動(dòng)軌跡;對(duì)單個(gè)關(guān)節(jié)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精確控制,減少異常姿勢(shì)或運(yùn)動(dòng)模式。1 次/d,25 min/次,5 d/周,共4周。
2.1.2觀察組 在對(duì)照組基礎(chǔ)上接受頭針-外骨骼機(jī)器人相結(jié)合的中樞-外周-中樞閉環(huán)康復(fù)訓(xùn)練,在頭針留針期間配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進(jìn)行上肢運(yùn)動(dòng)訓(xùn)練,外骨骼機(jī)器人訓(xùn)練模式與對(duì)照組一致。頭針由針灸醫(yī)師實(shí)施治療,頭針穴位選取《針灸學(xué)》[13]中頂顳前斜線(xiàn)、頂旁2 線(xiàn)的定位標(biāo)準(zhǔn)。頂顳前斜線(xiàn)的中2/5 段,即督脈前神聰穴至膽經(jīng)懸厘穴連線(xiàn)的中2/5;頂旁2 線(xiàn),即督脈旁開(kāi)2.25寸,從膽經(jīng)正營(yíng)穴向后引約1.5寸的線(xiàn)至承靈穴。操作方法:局部消毒后,采用規(guī)格為0.30 mm×40 mm的華佗牌一次性無(wú)菌針灸針,針尖與頭皮呈15°快速進(jìn)針,針尖抵于帽狀腱膜下,至指下阻力感減少時(shí)將針身調(diào)整為與頭皮平行,緩慢刺入約25~35 mm,采用快速連續(xù)捻轉(zhuǎn)手法,頻率約200 次/min,留針共25 min,間隔5 min施行捻轉(zhuǎn)手法1 次,1~2 min/次,1 次/d,5 d/周,共4周。
2.2 評(píng)定方法
采用單盲法,評(píng)估治療師對(duì)患者分組不知情,2組干預(yù)前后的評(píng)估均由同一位治療師實(shí)施。
2.3 觀察指標(biāo)
2.3.1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 根據(jù)國(guó)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lèi)(International C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 Framework,ICF)的概念[14-15],使用FMA-UE 來(lái)衡量身體功能與結(jié)構(gòu)領(lǐng)域,得分越高說(shuō)明運(yùn)動(dòng)障礙越小,身體功能與結(jié)構(gòu)領(lǐng)域表現(xiàn)越好,該量表可以敏感地反應(yīng)上肢輕度至中度偏癱患者的運(yùn)動(dòng)功能及協(xié)調(diào)的提高程度[16]。
2.3.2上肢運(yùn)動(dòng)任務(wù)執(zhí)行功能 Wolf運(yùn)動(dòng)功能測(cè)試(Wolf motor function test,WMFT)用于衡量ICF 活動(dòng)領(lǐng)域,主要用于評(píng)估上肢執(zhí)行功能性任務(wù)的能力,分?jǐn)?shù)越高,活動(dòng)領(lǐng)域表現(xiàn)越好,該量表對(duì)于輕度至中度損傷的腦卒中患者具有更高的敏感度[17]。
2.3.3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 改良Barthel指數(shù)(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用于衡量ICF 參與領(lǐng)域,MBI主要用來(lái)評(píng)估患者完成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總分100 分是最高分,更高的分?jǐn)?shù)表明患者可以更獨(dú)立地完成日常生活,參與領(lǐng)域表現(xiàn)越好[18]。
2.4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采用SPSS 25.0版本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2組計(jì)量資料首先使用Shapiro-Wilk 檢驗(yàn)是否為正態(tài)分布,若呈正態(tài)分布,采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組內(nèi)比較采用配對(duì)樣本t檢驗(yàn);組間比較采用Mann-WilcoxonU檢驗(yàn),組內(nèi)比較采用Wilcoxon配對(duì)樣本非參數(shù)檢驗(yàn);計(jì)數(shù)資料采用(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yàn)。以P<0.05 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3 結(jié) 果
3.1 2組治療前后FMA-UE評(píng)分比較
與治療前相比,2 組治療后FMA-UE 評(píng)分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與對(duì)照組相比,觀察組FMA-UE 評(píng)分改善程度明顯更好,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jiàn)表2。
表2 2組治療前后FMA-UE評(píng)分比較(±s)分Table 2 Comparison of FMA-UE scro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Scores

表2 2組治療前后FMA-UE評(píng)分比較(±s)分Table 2 Comparison of FMA-UE scro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Scores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duì)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3.2 2組治療前后WMFT評(píng)分比較
與治療前相比,2 組治療后WMFT 評(píng)分有所升高(P<0.05);與對(duì)照組相比,觀察組WMFT 評(píng)分改善程度明顯更好(P<0.05)。見(jiàn)表3。
表3 2組治療前后WMFT評(píng)分比較(±s)分Table 3 Comparison of WMFT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Scores

表3 2組治療前后WMFT評(píng)分比較(±s)分Table 3 Comparison of WMFT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Scores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duì)照組比較, 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3.3 2組治療前后MBI評(píng)分比較
與治療前相比,2 組治療后MBI 評(píng)分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與對(duì)照組相比,觀察組MBI評(píng)分改善程度明顯更好,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jiàn)表4。
表4 2組治療前后MBI評(píng)分比較(±s)分Table 4 Comparison of MBI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Scores

表4 2組治療前后MBI評(píng)分比較(±s)分Table 4 Comparison of MBI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s) Scores
注:與治療前比較,1) P<0.05;與對(duì)照組比較,2) P<0.05。Not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2) P<0.05.
?
4 討 論
4.1 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可有效改善腦卒中患者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
腦卒中患者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障礙是ICF 身體功能與結(jié)構(gòu)領(lǐng)域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故本研究采用FMA-UE 作為主要結(jié)局指標(biāo)評(píng)估患者運(yùn)動(dòng)功能的改善程度。結(jié)果顯示,觀察組FMA-UE 評(píng)分在干預(yù)4 周后改善程度優(yōu)于對(duì)照組,表明將互動(dòng)式頭針與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相結(jié)合可有效改善腦卒中患者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這一結(jié)果可能與閉環(huán)理論的作用機(jī)制相關(guān)[19],互動(dòng)式頭針作為中樞干預(yù)方式,通過(guò)針刺頂顳前斜線(xiàn)、頂旁 2線(xiàn)對(duì)大腦運(yùn)動(dòng)功能區(qū)施加刺激,提高大腦可塑性,從而促進(jìn)腦組織重建及腦功能重組;并將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作為外周干預(yù)方式,強(qiáng)化腦卒中后患側(cè)肢體的運(yùn)動(dòng)控制訓(xùn)練,強(qiáng)化其感覺(jué)和運(yùn)動(dòng)控制模式,對(duì)大腦皮層產(chǎn)生正反饋,兩者相結(jié)合產(chǎn)生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jìn)的功能,從而從整體上改善腦卒中患者的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
此外,腦卒中患者運(yùn)動(dòng)功能障礙是由于大腦病灶周?chē)M織中殘存支配運(yùn)動(dòng)的皮層面積大小和/或興奮性大幅降低,但通過(guò)運(yùn)動(dòng)訓(xùn)練和增加運(yùn)動(dòng)感覺(jué)的體驗(yàn),可以調(diào)節(jié)患者病灶周?chē)窠?jīng)可塑性[20]。研究顯示,腦卒中患者經(jīng)過(guò)外骨骼機(jī)器人康復(fù)訓(xùn)練后,其大腦半球之間的運(yùn)動(dòng)誘發(fā)電位不平衡現(xiàn)象得到改善,從而對(duì)促進(jìn)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恢復(fù)具有重要意義[21]。而互動(dòng)式頭針作為我國(guó)傳統(tǒng)醫(yī)學(xué)與現(xiàn)代康復(fù)醫(yī)學(xué)的有機(jī)結(jié)合,強(qiáng)調(diào)針刺與康復(fù)同步,主張患者在對(duì)肢體功能障礙進(jìn)行功能性康復(fù)訓(xùn)練的同時(shí),實(shí)施頭針治療[22]。頭針可作為中樞干預(yù)方式,對(duì)神經(jīng)可塑性具有積極作用,如郎奕等[23]通過(guò)針刺頂顳前斜線(xiàn)發(fā)現(xiàn)其對(duì)腦卒中患者的神經(jīng)功能恢復(fù)具有促進(jìn)作用,促進(jìn)患者錐體外系運(yùn)動(dòng)調(diào)節(jié)中樞及部分感覺(jué)皮層灰質(zhì)結(jié)構(gòu)重塑,誘發(fā)相應(yīng)腦區(qū)功能代償。汪瑛等[24]采用經(jīng)顱彩超測(cè)定頭針對(duì)腦血流動(dòng)力學(xué)的影響,發(fā)現(xiàn)頭針可以提高大腦前動(dòng)脈、大腦中動(dòng)脈的血流速度和搏動(dòng)指數(shù),有助于改善患者神經(jīng)功能缺損。
因此,本研究充分利用互動(dòng)式頭針改善神經(jīng)可塑性的優(yōu)點(diǎn),將其與外骨骼機(jī)器人相結(jié)合,從而形成了中樞-外周-中樞閉環(huán)治療模式。我們的結(jié)果與以往研究一致,如李元進(jìn)等[25]將對(duì)照組進(jìn)行作業(yè)療法,觀察組采用頭針與上肢機(jī)器人結(jié)合訓(xùn)練,發(fā)現(xiàn)對(duì)改善患者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比作業(yè)療法具有更顯著的臨床療效。本研究在其基礎(chǔ)上深入探討互動(dòng)式頭針的作用,發(fā)現(xiàn)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外骨骼機(jī)器人在改善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方面較單純的外骨骼機(jī)器人具有更為積極的影響。
4.2 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可有效改善腦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
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觀察組治療4 周后WMFT 和MBI 評(píng)分改善更高,這表明互動(dòng)式頭針結(jié)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可有效改善患者上肢執(zhí)行功能性任務(wù)的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對(duì)于ICF 活動(dòng)與參與2 個(gè)領(lǐng)域均具有積極作用。這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guān):① ICF 活動(dòng)和參與領(lǐng)域雖然分別有不同的定義(任務(wù)或行動(dòng)的執(zhí)行及參與生活情境),但這2 種結(jié)構(gòu)通常被視為一類(lèi)[26],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中的進(jìn)食、修飾、穿衣、洗澡等功能性任務(wù)常常需要上肢來(lái)完成,意味著上肢執(zhí)行功能性任務(wù)的能力提升與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的改善正相關(guān)。② 日常生活環(huán)境中通常需要完成許多功能性活動(dòng)或任務(wù),在執(zhí)行這種運(yùn)動(dòng)任務(wù)之前,大腦產(chǎn)生運(yùn)動(dòng)電位的復(fù)性偏倚峰值,代表大腦在運(yùn)動(dòng)策劃/執(zhí)行時(shí)所需要的能力或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27]。而頭針可使大腦皮層突觸活動(dòng)減弱,大腦運(yùn)動(dòng)策劃/執(zhí)行時(shí)所需要的能量減少,從而提高現(xiàn)有神經(jīng)元群體在處理整個(gè)運(yùn)動(dòng)過(guò)程的效率,并激活受損腦區(qū)與運(yùn)動(dòng)相關(guān)皮層區(qū)域的神經(jīng)元,使得偏癱側(cè)肢體執(zhí)行運(yùn)動(dòng)任務(wù)的能力得到改善[28]。劉建浩等[29]還發(fā)現(xiàn),頭針具有即刻效應(yīng),即針刺10 min 后可以使腦卒中患者患側(cè)肌力提高2 級(jí)以上的即刻效應(yīng)。③ 當(dāng)患者上肢執(zhí)行以任務(wù)為導(dǎo)向的訓(xùn)練時(shí),可以產(chǎn)生皮質(zhì)重組及神經(jīng)可塑性方面的積極改善[30-31],而上肢康復(fù)機(jī)器人可提供的密集、重復(fù)、以任務(wù)為導(dǎo)向的訓(xùn)練,對(duì)患者損傷的腦組織恢復(fù)產(chǎn)生積極影響,可增強(qiáng)運(yùn)動(dòng)皮層的積極重組,并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32]。MILOT等[33]通過(guò)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提供的任務(wù)導(dǎo)向性訓(xùn)練,改善了患者皮質(zhì)脊髓束損傷的不對(duì)稱(chēng)性,將肢體功能改善結(jié)果轉(zhuǎn)化成功能表現(xiàn)的顯著改善。
5 小 結(jié)
本研究通過(guò)充分利用互動(dòng)式頭針的即刻效應(yīng),在利用頭針激活中樞的同時(shí)結(jié)合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的肢體訓(xùn)練,對(duì)閉環(huán)理論進(jìn)行了改進(jìn)。與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在腦卒中上肢康復(fù)閉環(huán)理論中引入了互動(dòng)式頭針作為中樞干預(yù)方式的研究,豐富了中樞干預(yù)方式的種類(lèi)。本研究結(jié)果表明將互動(dòng)式頭針與上肢外骨骼機(jī)器人有機(jī)結(jié)合,形成閉環(huán)式信息反饋通路對(duì)改善患者上肢運(yùn)動(dòng)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動(dòng)能力具有積極影響,進(jìn)一步豐富了中樞-外周-中樞閉環(huán)理論。
本研究同樣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樣本量相對(duì)較小,干預(yù)時(shí)間較短,這些初步結(jié)果應(yīng)該由未來(lái)有更多參與者、更長(zhǎng)干預(yù)時(shí)間的多中心研究來(lái)證實(shí)。其次,我們的評(píng)估指標(biāo)沒(méi)有對(duì)患者中樞神經(jīng)進(jìn)行量化評(píng)估,后續(xù)研究可通過(guò)磁共振或腦近紅外等技術(shù)運(yùn)用腦神經(jīng)學(xué)指標(biāo)深入探討該閉環(huán)訓(xùn)練模式對(duì)大腦皮層的機(jī)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