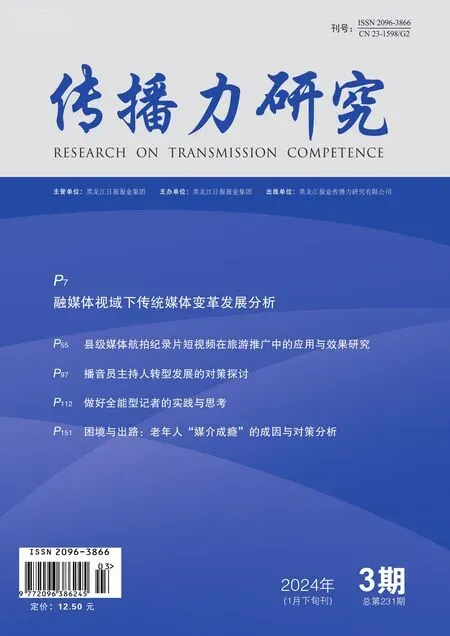困境與出路:老年人“媒介成癮”的成因與對策分析
◎喬如月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學院傳播系,北京 100872)
當前,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據測算,在“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進入到了中度老齡化階段,2035年前后達到重度老齡化。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到21 世紀中葉,我國超過60 歲的人口數量預計達到4.5 億。由此可見,我國老齡化的規模、深度和速度都相對較高,形勢較為嚴峻。
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更迭,人們的生活正在經歷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等一系列變革。互聯網不僅深刻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方式,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這一過程中,老年群體自然也深受影響。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67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5.6%。從網民年齡結構看,60歲及以上群體占比顯著提升,達到14.3%,即60 歲及以上老年網民規模達1.53 億。而在同一時間由國家統計局測算的我國60 周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為2.8 億,由此不難看出幾乎每兩個老人中就有一人接觸了網絡。
一方面,我們為老年人跟上時代的發展步伐而感到欣喜;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隨之而來的風險。當前,越來越多的新聞報道反映在如今的“手機控”“低頭族”當中,出現了很多老年人的身影,其行為特征包括終日手機不離身,沉迷于刷視頻、看直播、玩游戲、朋友圈分享點贊等。
不少老年人前腳剛越過“數字鴻溝”,后腳便陷入“媒介成癮”。在Quest Mobile 發布的《2022 銀發經濟洞察報告》中,有數據顯示,老年用戶對互聯網的使用程度呈現出持續加深的發展態勢,月人均使用時長達121.6 小時。特別是在短視頻、新聞資訊類APP 的使用頻率上,銀發人群甚至高于全網平均水平,具有明顯的線上娛樂化特征。
無節制的媒介消費甚至媒介成癮,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造成了不良影響,原有的生活節奏和作息規律被打破,甚至有的老人因給主播刷禮物致使家庭蒙受巨大的財產損失。由此可見,在數字化和老齡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轉型發展的重要特征的當下,我們需要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媒介生活,剖析部分老年用戶“媒介成癮”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協助老年群體養成更好的媒介使用習慣,幫助他們走出智能時代的“迷失”。
一、老年用戶媒介上癮的成因
老年人離不開智能手機和網絡,背后的成因復雜多樣。本文將從多個維度剖析影響老年人媒介依賴甚至成癮的因素。
(一)高危人群的健康焦慮
老年人群的健康情況脆弱,對于疾病防護、養生保健的需求較高。從客觀條件來講,我國的醫療衛生資源分布相對不均,老年人群的養老保障及健康服務面臨挑戰,再加上近幾年全球范圍內爆發的疾病問題,加劇了老年人的健康焦慮。從主觀因素來講,部分老年人接觸互聯網的時間較短,與“伴隨互聯網成長”的年輕人相比,老年人缺少對信息的辨別能力,更容易相信“健康謠言”。
基于此,老年群體會花費大量時間在媒介上搜索關注健康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在健康信息搜索的過程中,會更多地使用微信作為主要的搜索渠道。這是因為微信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扮演社交、娛樂的角色外,也是老年人與家人和朋友聯系的重要工具。微信朋友圈、訂閱號和微信群是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來源。此外,微信是熟人社交媒體,老年人在解讀微信傳播中的健康信息時,會天然地將信息內容與傳播者聯系起來,進而放大信息的重要性和價值,這種健康焦慮成為老年人媒介上癮的一個重要成因。
(二)老年群體的社會參與需求
老年人的社會參與需求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增加。由于老年人的社交圈子變小,社交活動減少,他們往往會感到孤獨和無助,渴望與他人進行交流和互動。以往在傳統媒體的傳播環境下,老年人只能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被動地接收信息,而在新媒體環境下,傳播狀態由一對多變成多對多,個體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具有雙重身份。
新的媒介為老年人提供了廣闊的社交平臺,通過網絡社交、在線游戲等方式,老年人可以與他人建立聯系,分享生活經驗和情感,再加上老年人身邊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性方式或社交資源,這導致他們對媒介的依賴越來越強烈。
在《2021 年中老年群體觸網行為研究報告》中,有數據表明,中老年群體的手機使用已經覆蓋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社交通訊、生活服務、健康醫療、娛樂資訊以及電商購物是最主要的五大類場景。社交通訊類APP/小程序使用頻次最高,其次是生活服務類APP。
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可以充分的了解、認識自己,對自己有很清晰的定位,通過對于自身的定位能夠確立生涯目標,隨著個人的不斷進步,職業生涯也會更加完善,進行職業生涯規劃也會更加健全。[4]
通過這些軟件,老年人的社交網絡被極大地拓展了,沒有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建立在朋友圈里的發送、反饋、分享的體系,讓空巢老人找到了歸屬感與團聚感。老年人自己的交際、評價體系,借助于社交軟件的幫助,得到了延伸與正向的反饋。因此,媒介的使用與滿足感增加了老年人沉迷于網絡媒體的時間。
(三)老年群體的情感需求
老年人時間充裕、經歷豐富,且大多子女不在身邊,對情感的需求比其他年齡段更為強烈。而恰好這個時間,互聯網發展的迭代升級,讓他們有了精神依托。
在抖音上,很多老年人開始“追星”,捧出了百萬粉絲網紅。其中一位名為“秀才”的男網紅,已積累了962.8 萬粉絲。其視頻以對口型唱歌為主,唱歌時會帶著害羞的表情,捂嘴、舔唇、挑眉是視頻必備三件套。在@秀才的賬號下,每天都會有老年粉絲傾訴自己的生活細節,比如家里老人做手術了、家里有喜事要辦酒席了、孫子孫女生病了、自己病了、牙又掉了、最近每天睡得越來越少等。甚至有一位72 歲的吉林老太太為了見“秀才”獨自坐火車到安徽亳州“追星”。
與“秀才”相對應的還有一個很火的賬號叫“一笑傾城”。主角是一位來自山東菏澤的農村女孩,擁有招牌式的甜美笑容,日常更新的內容是翻唱、跟唱一些熱門歌曲。該賬號同樣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愛,狂攬1 711 萬粉絲。這兩個賬號并不是個例,事實上,老年用戶已經成為抖音、快手等情感類賬號的主流粉絲群體。《2022 快手銀齡人群內容生態報告》顯示,快手上銀齡用戶最喜歡的內容是小故事。老年用戶在瀏覽短視頻時,喜歡點贊和轉發與自己有共鳴的內容,也喜歡使用正能量表情包和祝福。感同身受和情感共鳴是促進老年群體情感轉化的關鍵,也是一些老年網民迷戀短視頻的原因。
(四)媒介變革下的個性表達
如今,社交平臺越來越去中心化、個性化和場域化。因此,老年群體也得以從數字媒介浪潮的邊緣走到了前臺。同時,以抖音、快手為代表的短視頻平臺,不斷完善平臺功能,降低準入門檻,使得內容生成的方式短平快,于是越來越多的中老年博主在社交平臺脫穎而出,成為“銀發網紅”。
例如,同濟大學教授吳於人,退休后在抖音上注冊了賬號“不刷題的科學姥姥”,站在鏡頭前做趣味物理實驗,堅持科普18 年,目前賬號粉絲量已達486 萬;喜歡自駕的蘇敏,在抖音分享自駕游的視頻,其賬號“50 歲阿姨自駕游”粉絲已超過200 萬。還有通過變裝引發國風潮流的“時尚奶奶團”、分享日常搞笑生活的“我是田姥姥”以及教大家做家常美食的“陜西老喬”等,經過歲月的沉淀,他們將更優雅、更智慧、更率真的人生帶進社交平臺,在愉悅自己的同時,也給萬千網友帶來了知識和快樂。
一方面,老年人借助這些平臺探索了全新的生活,通過技術賦能,呈現出個性表達。另一方面,一些廣告主會與老年網紅合作,如在直播中穿插帶貨、種草和推廣。很多老人通過直播帶貨,走上了“脫貧致富”之路:陜西省安康市棗園村的“秦巴奶奶”曾一天賣出3 萬多瓶辣椒醬;貴州德江縣煥河村的張金秀奶奶,一個小視頻就賣了近5 000 單紫薯。短視頻平臺提供的巨大的流量、全新的舞臺以及潛在的商機,是吸引老年人的因素之一。
二、應對老年人媒介成癮的策略
(一)家庭成員的數字反哺與情感支持
傳統的教育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但在信息化社會中,自下而上的文化反哺模式更為有效。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和子女的數字文化反哺來學習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掌握微信等工具。然而,他們在信息的篩選、批判、評論、甄別、轉發等方面仍有欠缺。因此,家庭成員在老年人媒介上癮治療中起著重要作用。
首先,家庭成員可以通過數字反哺的方式,幫助老年人充分利用媒介的積極功能。例如,教授他們如何使用社交媒體與親朋好友保持聯系,如何獲取有益健康的信息等。家庭成員還可以與老年人共同參與媒介活動,提升他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度和參與度。其次,家庭成員還應給予老年人足夠的情感支持,滿足他們的社交需求和情感補償需求。定期陪伴、溝通交流以及組織社交活動等,可以減少老年人對媒介的依賴。
(二)適老化改造媒介基礎設施和內容社區
針對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需要對媒介基礎設施和內容社區進行適老化改造。首先,應優化媒介設備和軟件界面,使老年人更容易理解和操作。老年人對于技術的接受能力有限,因此界面設計應簡單易懂。在APP 的功能和界面設計上,要給老年人更多的數智“慢選項”。比如,設置大屏幕、大字版、語音版、簡潔版、一鍵達等,簡單的內容模塊,清晰明朗的標注,沒有惱人的彈窗、廣告,沒有讓人眼花繚亂的跳轉、推送,功能簡單,省力省心,可以有效解除老年人的閱讀障礙和操作障礙。
其次,與老年人沉溺網絡的現象相對應的是,能夠真正從關愛老人角度出發的電視內容和新媒體內容少之又少。媒介內容社區應提供多樣化、豐富且有意義的內容,以吸引老年人的注意力和參與度,這些內容可以包括老年人關心的與健康、生活、興趣愛好等相關的信息和活動。通過提供適合老年人的媒介基礎設施和內容社區,可以降低老年人沉迷媒介的風險。
(三)重塑媒體把關機制,加強內容審核
2022 年,抖音日活躍用戶達到了7 億,用戶數達到了8.42 億,人均單日使用時長超過2 小時,這只是平均數據,其中很多老年人刷抖音時間會超過3 個小時,且這個數據還有繼續增長的趨勢。在海量的短視頻內容面前,容易發生“把關缺位”的現象。為了確保老年短視頻內容的健康,平臺和有關機構均應優化媒體把關機制,加強內容審核。
首先,要合理利用算法推薦功能,特別是新聞類、健康訊息類短視頻,平臺在“算法把關”的基礎上,還應該過濾謠言、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優化算法推薦服務機制,積極傳播正能量,促使算法應用向上向善。其次,要警惕“信息繭房”與“內容窄化”,避免重復給老年用戶推薦單一類型視頻,造成思維固化,眼界短淺,在受眾喜好度、內容豐富度和新聞傳播速度之間尋找平衡點,構建健康向上的網絡空間。此外,相較于自媒體來說,主流媒體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與公信力,在新聞事實的探尋上也具有更大的還原能力。要加快主流媒體的新媒體化進程,擴大主流媒體在短視頻平臺的影響力,從而形成對內容的“反向把關”。
(四)政策助力老齡人口實現再社會化
在宏觀層面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可以為老齡人口實現再社會化提供支持和保障。首先,政府應加大對老年人媒介素養的培訓和推廣力度,提高老年人的媒介運用能力,包括舉辦媒介技能培訓班、推廣數字化知識等。
其次,政府還可以通過設立老年人媒介健康管理中心或者咨詢熱線等渠道,為老年人提供媒介使用指導和咨詢服務。這些機構可以提供老年人媒介使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項,引導他們健康合理地使用媒介。
另外,相關部門還應加強對媒介公司和平臺的監管,完善問責機制,推動其提供有益健康的內容和服務,定期審核、評估、驗證以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為主的內容生產和推薦機制、用戶數據和應用結果,通過完善問責機制,優化平臺推薦服務,保證老年短視頻內容的風清氣正,降低老年人媒介上癮的風險。
三、結語
在互聯網已經深刻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時代,無論是那些沒能找到智能時代入口的,還是那些已經接入了互聯網但卻沒有適應節奏、反而被有害信息帶偏沉迷上癮的老年人,他們都需要特別關懷,應幫助他們走出智能時代的“迷失”。
老年人媒介上癮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成因涉及高危人群的健康焦慮、社會參與需求、情感需求和個性表達等各個方面。治理老年人媒介上癮需要以更加全面、長遠的眼光系統謀劃,統籌應對。在微觀層面上,家庭成員可以加強數字反哺與情感支持;在中觀層面上,媒介基礎設施和內容社區的適老化改造,可以減少老年人對媒介的依賴;在宏觀層面上,要重塑媒體把關機制,加強內容審核,且政府及相關機構要助力老齡人口實現再社會化。通過這些應對策略的有效實施,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不斷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減少媒介成癮現象的發生。同時,老年人媒介成癮的問題在不斷發展和變化,需要深入研究和實踐探索,才能更好地滿足億萬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