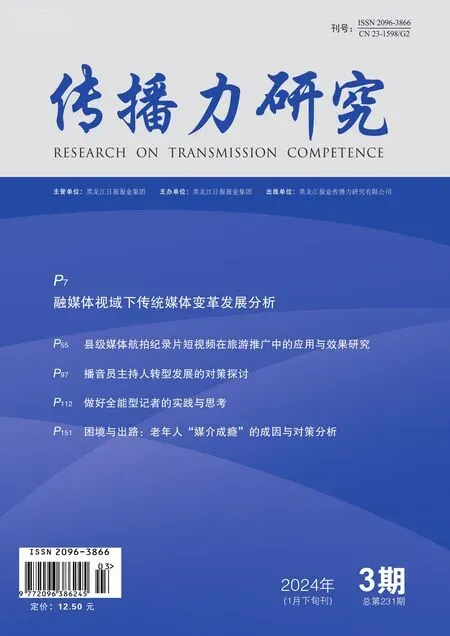從狂歡視角看彈幕模因
◎熊夢瑩 吳 瑤
(湖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隨著網絡技術和智能手機的普及,視頻分享平臺逐漸成為了人們獲取信息和娛樂的主要途徑之一。在這個過程中,彈幕作為一種新的交互方式出現并得到了廣泛應用。“彈幕”在最初是一種電腦射擊游戲。當大量子彈飛在屏幕上時,形成彈幕景觀。彈幕區別于網頁評論區中的用戶評論,使用者在觀看網絡視頻時,可以通過播放器實時發出文字和符號的評論,這些評論字幕會被保存起來,當視頻被(包括發帖人在內的所有用戶)再次點播時,評論字幕就會在播放器加載視頻文件的同時被載入,并在視頻中對應的時間點出現[1]。
一、理論基礎:狂歡理論與媒介文化研究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首次提出狂歡理論。狂歡理論的主要論述對象是人類社會中的文化現象,它強調了文化現象中的狂歡性和反常性。巴赫金認為,狂歡是一種超越了日常生活秩序的狀態,是一種解放的體驗,可以幫助人們打破常規、釋放情感、找到新的感受和價值[2]。
“在狂歡節進行當中,除了狂歡節的生活以外誰也沒有另一種生活,人們無從躲避它,因為狂歡節沒有空間界限……狂歡節具有宇宙的性質,這是整個世界的一種特殊狀態,這是人人都參加的世界的再生和更新。”“另一種生活”的前提是,對兩種世界、兩種生活的劃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嚴肅的、等級森嚴的秩序世界,統治階級擁有無限的權力,而平民大眾則過著常規的、謹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對權威、權力、真理、教條、死亡充滿屈從、崇敬與恐懼。而第二世界(第二生活)則是狂歡廣場式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顛倒的世界”,是無等級、民俗與解構的世界,是平民大眾的世界。
巴赫金所分析的狂歡化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第一,顛覆性,即狂歡節期間的人們可以在狂歡中重新構建自身的存在方式,推翻社會等級制度和現實規范的所有外殼;第二,無等級性,即與人建立開放、自由、親密的關系;第三,民俗性,即否定和破壞宮廷文化;第四,解構性,即利用狂歡節的意識形態范式來探索和建構世界,將人們的意識從被壓抑的現實中解放出來[3]。
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對生活現象進行了理論化,并將其解讀為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這一理論在多學科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引起了我國國內一陣巴赫金狂歡研究的熱潮,早期的國內研究者包括夏忠憲[4]、程正民[5]和陸道夫[6]等人。
狂歡理論在媒介文化研究領域的引入源于對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的研究。該理論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吉恩·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在其著作《消費社會》中提出,并在后來得到了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狂歡理論關注的是現代社會中的集體體驗、象征系統和消費文化,強調了大眾傳媒在創造集體認同和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在媒介文化研究中,狂歡理論被廣泛運用來分析和解釋大眾媒體和互聯網文化的現象。它提供了一種理論框架,可以揭示大眾傳媒和互聯網如何通過符號、象征和消費來塑造與影響社會。
從大眾娛樂產業和流行文化來看,狂歡理論被用來分析電影、電視劇、音樂和其他流行文化產品如何通過大眾傳媒和消費活動來營造集體狂歡和文化認同;從新聞傳媒和公共話語來看,狂歡理論被應用于研究新聞傳媒如何通過符號、象征和儀式來構建公共話語,并影響社會的輿論和意識形態;從廣告和消費文化來看,狂歡理論被用來研究廣告和消費文化如何通過符號、象征和儀式來創造和維持集體認同,并影響個體和社會的行為與價值觀;從社交媒體和網絡文化來看,狂歡理論則被應用于研究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用戶行為、網絡互動和虛擬社群,探討它們如何塑造和影響個體的身份認同與集體體驗。這些研究借助狂歡理論,從集體體驗、象征系統和消費文化的角度,探索和解釋媒介文化的各個方面。它們通過狂歡理論的框架,揭示了媒介在社會的塑造和個體的認同構建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作為表達的狂歡:彈幕模因
模因論是基于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解釋文化進化規律的一種新理論。新達爾文主義倡導者Dawkins 在其1976 年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中首次提到。作者在描述基因作為復制因子的特征的基礎上,構想了存在于人類社會文化傳遞的復制因子——模因。它是文化的一個元素,如一種傳統、信仰、思想、旋律或時尚,可以保存在記憶中并傳播或者復制到另一個人的記憶中[7]。模因的信息遺傳并不像基因那樣要求數字化的精確,它只要求模仿。
自然語言的模因(Meme)是指在文化傳播中具有傳承性的信息單元,可以通過語言、行為、符號等形式傳播。模因是一種文化符號,能夠在人群之間傳播和演化。在自然語言中,模因可以是詞語、短語、俗語、流行語等,具有被復制和傳播的特點。彈幕語言的模因是指那些在彈幕評論中被頻繁使用、傳播和模仿的特定詞匯、表達方式、符號或短語。這些模因在彈幕社區中得到共享和演化,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系統。
三、作為情緒的狂歡:彈幕模因的解構性與顛覆性
彈幕模因雖然可以承載信息,但其核心功能卻不在于高效地傳遞信息,而是通過“實時反饋”為用戶提供共享的觀看經驗,帶來主觀上的游戲般的愉悅[8],實現情緒的輸出。
(一)解構性情緒:對常規和傳統的解碼反叛
狂歡理論強調了對傳統社會規范和行為規范的反抗,認為狂歡是對常規和傳統的一種逃避和反叛。在彈幕中,觀眾可以通過發送實時評論和表情符號等方式對傳統的電視節目或視頻內容進行即時評價,表達對傳統觀看方式的集體批判或反叛。
弗洛伊德指出,實現本我的唯一目標是滿足欲望、追求快樂。人在面對現實社會中的壓力和約束時需要尋找一個能夠發泄的窗口,于是在虛擬世界中釋放壓力和惡搞玩樂成為一種有效且風靡的方式。比如,彈幕的參與者會從各個角度對語言進行解構和重構,生成模因。比如“awsl”,這四個字母表達的是“啊我死了”的意思,是從拼音縮寫的角度進行的解構,用來表達自己的興奮情緒。不過,它同樣也可以是“啊,是大佬,我死了”的縮寫,表示對強者的崇敬和贊美,還衍生出“阿偉死了”“阿偉輸了”“啊我是驢”等含義,是從諧音層面進行語義的重構。
官方性、嚴肅性的話語一般很少受到追捧和大量復制,即便出現官方的語言,也是對其的戲謔或反諷,是一種語言的變異。比如,當角色盲目自信地做出一個判斷時,“優勢在我”的彈幕會接連飄過。但“優勢在我”自此就成為了一個彈幕模因。每當有人盲目自信地作出并不符合實際、過于樂觀的判斷時,網友就會發送這則彈幕模因。這種語言變異會給予受眾很深的印象。變異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種“突出”。這里的“突出”,就是不尋常、不落俗套,引人注目[9]。
彈幕在解構“標準化”后重新促成了一種新的“標準化”。在當前傳播語境下,資本主義的邏輯導入創造出流量導向的傳播現狀,出現程序化和標準化的傳播內容。這種標準化是對于內容生產者的一種規訓,在需要創造力的領域引入了競爭機制。只有當內容符合這種標準化的傳播范式時,才能在數據顯示中得到良好呈現。但是在彈幕這樣一種特殊載體中,這種標準化實則是被打破了。彈幕不會顯示發布者的個人信息,因此其點贊量和模仿量不再能夠為發布者帶來經濟上的某些價值,由此資本化的邏輯被徹底打破。彈幕之所以能夠構成彈幕模因,看似是解構“標準化”后重新促成了一種“標準化”,但實際這種“標準化”的生成邏輯與資本主義邏輯完全背道而馳。看似的“標準”實則是完全服從個人內心的想法的表達,是對于內心聲音的一種放大和擴音,借助的是別人的語言,表達的卻是自身的內容和情緒。
(二)顛覆性情緒:線性不平等傳播模式的消解
一方面,彈幕這種表達載體本身的特點,原始影像與彈幕的平等使受眾的被動式傳播鏈條發生逆轉,作為主體參與彈幕視頻的二度創作,改變了傳統的影視傳播格局。彈幕出現之前,創作者與受眾之間是一種單向傳播;彈幕出現之后,受眾與創作者之間實現了多方面互動[10],例如“編劇你出來我絕對不打你”“小編該領盒飯了”等隔空示音。
另一方面,在以往的傳播載體中,實際上都隱含著顯性或隱形的顯示偏頗。無論是在視頻類內容還是文字類內容中,點贊評論量、付費推廣量都會賦予一則內容以流量分配上的優先權。這樣一種分配是在幕后進行的,因此很多時候不被受眾所察覺。但是在目前的彈幕機制中,受眾在不直接顯示身份和ID 的“面具”下發言,隨后不斷得到復制的彈幕模因將最初的發言者身份淡化,意見領袖的形象隨之消解,所呈現的只是完全一致的文字,不做任何身份的區分。
狂歡中的彈幕模因使“脫冕”和“加冕”的親身參與者無限擴大。普通的評論或者彈幕,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語出新裁,剝離權威者的權威性,成為造梗者,成為為奴隸或小丑加冕、為國王脫冕的人。彈幕模因這種特殊的形式則通過大批量的復制粘貼、重復發布,以一致的形態在彈幕中裂變式傳播,有時能形成一種壯觀的效果,強化儀式的狂熱感受。正是在這種平等的對話精神中,人們體會到了嶄新的感受。人仿佛為了新型的、純粹的人類關系而生,暫時不再相互疏遠。人回歸到了自身,并在人們之中感覺到自己是人,從而獲得了新生。平等的對話精神對于文化的發展、文化的新生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11]。
四、對狂歡化彈幕模因的反思
彈幕模因作為一種新興的網絡文化現象,展現了強大的社會互動性和情感表達性。然而,在其未來持續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和隱憂。我們需要認識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挑戰,以便能夠更好地引導和促進其發展。
(一)無關噪音淹沒內容本身
用戶受到彈幕模因噪音的影響,無法專注于內容本身,從而對內容的理解流于淺表化、娛樂化,喪失了獨立思考深度內容的能力。可以發現,在不同的視頻中,彈幕的內容可能幾乎是重合的,所有人都在玩“彈幕梗”。一樣的梗能夠嵌套不同的視頻,這本身就能夠說明,視頻本身并不受到關注,沒有成功地給受眾帶來信息量的增加和觀點的輸入。所有彈幕參與者都將注意力放置于何處能“玩梗”“抖機靈”,自己在何處能恰如其時地加入成為模因“大軍”中的一份子。
(二)成為誘生語言暴力的溫床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描述了群體情感的非理性,當個體進入到一個群體時,理性就會消失,“無意識”占據了理性。具有相同情感傾向的人聚集在一起之后,這種情感迅速發酵而走向極端化。群體中的情感動員和情緒傳染使得群體成員之間形成情感認同,左右了群體的決策,個體本能地處于情緒亢奮狀態,脫離了理智和冷靜。
在彈幕中,模因所承載的文字和情緒表達,通過群體動員的方式引發病毒式傳播。如果這是一種負面的情感框架,在“烏合之眾”的影響之下,負面的情緒更加膨脹和加速擴散,從而導致群體理性的喪失,甚至走向網絡民粹主義。《南方都市報》旗下南都大數據研究院在2020 年7 月梳理發現,在2 000 條低俗彈幕中,有不少內容常重復出現,部分來自同一用戶,其余部分來自多個用戶跟帖。這種不健康的彈幕模因誘生的語言暴力,不利于社會良好風氣的養成。
(三)生產人云亦云的復讀機器
彈幕模因以“自由”的命運自主理念制造同意,實則也是一種隱蔽的意識形態控制[12]。部分彈幕網站為激發受眾的彈幕表達欲望,在彈幕頁面中直接增設“+1”功能,受眾選中目標彈幕即可直接復制并發送一條內容一致的彈幕。這種增設功能直接激發了彈幕模因擴張。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設置不利于多元觀點的表達,會加劇迷群內部的回音室效應。
過于依賴彈幕模因可能使人們失去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只會不斷地重復、模仿或者傳播已有的彈幕內容。彈幕模因的重復性和傳播速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和深度。另外,彈幕模因的傳播速度極快,但其中的信息未必都是準確和可靠的。過于盲目地復讀彈幕內容可能導致錯誤信息和謠言的傳播,從而對個體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