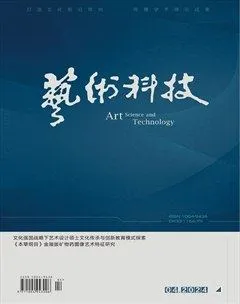海洋、地域文化與生命哲學
摘要:目的:蔡崇達的小說《命運》通過獨特的敘事手法和深入的主題思考,呈現了一個充滿韻味和思想內涵的世界,其為探索海洋在小說文本中被賦予的意象、獨特地域文化作為文本展開背景的意義及生命哲學的呈現而創作。方法:文章通過深入分析小說主題,揭示海洋、地域文化、生命哲學三大主題在小說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內涵,同時展現了蔡崇達作為一位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造詣。另外,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將內容與理論相結合,論述主題的意義和作用。結果:順應“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提出的時代潮流,從“南部以南”地區出發,完成了海洋敘事與文化敘事的結合。通過對海洋、地域文化的描繪,作者表達了對生命的獨特理解。他以海洋為象征,充分展現了海作為命運的載體在文中所承載的意蘊。以閩南地域作為故事開展的背景,為新南方寫作的發展提供典型的文學范本,從宗教與神明信仰及民俗文化兩個角度出發,揭開神秘的閩南文化面紗,拉近讀者與獨特地域文化之間的距離。《命運》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飽滿且層次豐富,透過阿太的人生傳遞了苦難中的生命哲學,即如何正常且有意義地死去。阿太在她百年的人生中交出了答卷。結論:《命運》是一部深入探討海洋、地域文化和生命哲學的作品,以深邃的主題和細膩的描繪手法,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來理解和審視我們的生活和文化。以海洋為象征,表現了生活的起伏波折,以南方地域文化為載體,呈現了人們對命運的堅韌和柔情。
關鍵詞:新南方寫作;海洋敘事;地域文化;生命哲學;? 《命運》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4-00-03
0 引言
“新南方寫作”近來被學術界頻繁提及,是指以南方地域為中心,成為新時代文學書寫的新文學潮流。然而,何為“新南方寫作”?學者在討論中提出了明確的地理位置定義,“如果將嶺南這個地理概念坐實,它包括福建、廣東、海南、廣西、香港、澳門,再擴大,就是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1]。南方立足于其地域的獨特性,包含了無盡可供挖掘的信息,“新南方寫作”期待更多符合其文學標準的作品填充。在“新南方文學”潮流來臨之時,泉州作家蔡崇達發布新書《命運》,透過作者的敘述,讀者能夠了解閩南地區神秘的神明信仰,體悟作品中的生命哲理。
作品以阿太的視角開展,敘述生命中的分離、生死以及神明在精神世界的支撐作用,平靜且輕松地講述悲苦的命運,直面死亡的主題,用溫暖且徐緩的話語回應當代人精神上的“懸浮”危機。《命運》展現了南方信仰的豐富性,帶領讀者走進神秘的閩南地區,打破了常規觀念中對非主流神明信仰的偏見,強調傳統文化在人生存之中具有的強大精神力量,充斥著豐富的生命意味,在視角選擇、地域文化展現等方面獨具匠心。正是這些使其作品的地域性與日常性、思想深度與平緩語言敘述、歷史感與當代性處理得恰當、巧妙,呈現出“新南方寫作”的新氣象,為“新南方寫作”提供了典型范例。本文主要從作品的海洋敘事、閩南地域文化書寫、苦難命運中的生命哲學三個方面探析蔡崇達筆下的閩南世界。
1 海的意象
縱觀世界發展史,發達國家的興起無不與海洋貿易的興盛有關。“海水的流動性,決定了海洋文明超越大地限制的自由性、開放性。”[2]因獨特的地理風貌,廣闊的平原占據了祖國版圖的大部分地區,文學書寫自古以來以大陸文化為特色,這種文化以保守、穩健和中式傳統價值觀的特質而著稱。然而,這種視角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沿海地帶人們的生活與文化。縱觀整個中國文學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漫長的海岸線周邊,人們的生活與情感被嚴重忽視[3]。“南部以南”的沿海地區居住著并不算少的人民,沿海地區氣候多變,地形復雜,水文資源豐富,生態環境多樣化,這些環境條件為沿海居民提供了獨特的生存資源。與大陸文化相比,海洋文明強調的是一種與自然和諧共處、尊重自然規律的文化特質,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沿海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蔡崇達在《命運》中將海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海的存在也被賦予了獨特的意義。大海的寬廣、無限、永恒,浸染著蔡崇達的文學創作。
在西方文學中,大海一直被視為一種原型意象,象征著無邊無際、神秘莫測的精神世界,象征著死亡和再生,象征著永恒不朽[4]。“討大海”還是“討小海”?這是每一個閩南地區成年男子所要直面的選擇,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獨特的地理環境使沿海地區不適合依賴土地生產農作物發展,這種獨特的生存方式隨著文本的書寫進入讀者的視野。而無論是選擇“討大海”還是“討小海”,不僅僅是生計的選擇,也是命運的選擇,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命運:一種是闖蕩天涯、尋求冒險和挑戰的命運;另一種是安分守己、尋求現世安穩的命運。《命運》中所描繪的海洋體現了蔡崇達獨特的藝術風格,其以細膩的筆觸和深情的語言,將閩南地區的海洋風情和人物情感融為一體。同時,巧妙地運用海洋意象來表達人物的內心情感和思想變化,通過海洋敘事展現了閩南地區獨特的魅力。
2 閩南地域文化書寫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國家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地理不是一個惰性的容器,也不是文化史‘發生的盒子,而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它彌漫整個文學的領地并對其深度塑形。”[5]地方的獨特性決定了作家創作內容的獨特性,作為一位擁有自覺地域文化意識的作家,蔡崇達將家鄉泉州石鎮浮現于紙上,不斷地將創作的觸角伸向文化深處,閩南小鎮的獨特文化為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內容,不僅描寫了當地的文化風俗,更試圖挖掘文化之下流傳百年的精神文化遺產。這是一片充滿神明信仰和沿海地區獨特生活習俗的土地,文化精神是人們心中的歷史。而《命運》則隨著阿太的生命歷程,敘述了這片土地的百年歷史。
2.1 宗廟與神明信仰
“天上的神與心中的神,既理想化,亦世俗化。而神化了的人,既具最高形上疑惑的‘精神我,又成為每個人心中的至上神。”[6]書中描繪最多的便是閩南地區的宗廟,數量多便是其最突出的特征。當人的心中有困惑,想要尋求答案之時,便會去宗廟祭拜,將心中的問題訴之,并堅定神明會在生活中給出答案并解決困難,指引并庇護信徒。受阿母的影響,阿太堅信神明是真實存在的。即便在極端反對宗教信仰的年代,阿太仍將神明的雕塑悄悄藏在隱秘的地方,她與神明在百年的生命中相伴。阿太經歷如此之多的苦難,神明是支撐她活下去的動力。作品賦予神明形象活力,使神明更平易近人,宗教也不再蒙上神秘的面紗。神明在小說中的形態和安放的空間都具有世俗化特征,神明愛美、斗嘴,會在業務繁忙時兵荒馬亂,廟宇是人們與神明講話、召開集會的普通空間,另外,神明也會被藏在廁所、被窩、骨灰盒等地方。
神婆作為能夠與神明溝通的人,象征著信仰的力量,是一個充滿智慧和神秘的人物。每當人們向神明求得指引無果后都會到神婆這里,想要神婆問問神明的意思。神婆不僅了解神明,也了解人性,她通過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幫助阿太解決了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同時,神婆又代表著一種智慧和精神的傳承,其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通過言行傳授給阿太。這種傳承不僅使阿太在生活中找到了指引,也使阿太成為一個更有力量的人。此外,神婆還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一種傳統文化的智慧力量、信仰宗教對人的力量,這種力量對人們的生活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在作品中,宗廟與神明的信仰情節貫穿始終。阿太在宗廟燒香、祈禱,與神明交談、解惑,她的抗爭、堅韌以及對神明的信仰體現了她對生命、命運、價值的探索和思考,也反映了人們對自然、宇宙、存在的敬畏與崇拜。
2.2 民俗文化
民俗在長期的傳承與擴布過程中會展現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與符碼[7],民俗文化是一個民族或社會群體的生活經驗和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不僅能反映當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傳承,還豐富了國家文化內涵。邁入現代化進程后,都市的興起、外來生活方式都在不斷沖擊傳統的地方特色民俗。蔡崇達在作品中多次對閩南地區的生活習俗有詳細描寫,不僅增強了讀者的在場感,更激發了對傳統習俗的重新重視。“葬禮等民間儀式是農民文化實踐的載體。農民在文化實踐中習得并傳承著這個古老民族的人生理念、生存智慧和做人之道。”[8]作品從開頭就寫了閩南地區的葬禮,寫了阿太的“死亡摩觀團”。當一個老人預感到死亡降臨時,會通知家人將床板放在神明面前,在神明的注視下完成死亡這件事,如此便會使靈魂去往好的歸處。人在走后還要“做功德”,即各方上臺唱戲、不間斷燒香并擺桌設宴,“遠遠就立滿了密密麻麻紅紅火火的拱門。西洋樂隊、南音團、耍猴子、踩高蹺……”由此可窺見葬禮習俗的煩瑣。盡管時間在不斷推移,但人生中的大事,結婚、死亡等仍在按照傳統習俗進行。這些民俗反映了閩南地區民眾的社會心理狀態,是他們生活、情感和信仰的集中體現。
3 苦難命運中的生命哲學
苦難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經歷,有時恰恰因為有了苦難,所以人才得以成長。如何面對生命中的苦難,阿太用她的生活經歷告訴了讀者。她所經歷的痛苦,雖然刺激了她女性意識的覺醒,但并沒有讓她僅僅以自我宣泄或隱藏自我來加以應對,而是將所有的個人經驗和記憶轉化為一種深刻的洞察和同情來理解。“阿太特別喜歡站在入海口,往陸地回望。她瞇著眼睛,好像看得見匯入大海的每條河流,以及匯成河流的每條小溪。”[9]阿太命運中的歡喜與苦難、來到的人與已逝的人,如同終會匯入大海的小溪般,源源不斷、未曾停歇,最終構成完整的阿太。命運是文學藝術永恒而偉大的母題,《命運》通過多個脈絡的聚合和分散,展現了在歷史混亂中對意志頑強和深厚情感的執著追求。這種尋求無盡止的追求和始終無法實現的目標的主題,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悲劇悖論,強烈地激發了人們對命運的感知和回應。蔡崇達以神明為媒介,將命運的安排視為注定,使生命的苦難變得必要而又神秘。死亡僅是生命旅程中的一站,應積極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和困難,以樂觀的態度面對人生的終點。
人生像果子的生長過程,最好的死亡就像成熟的果子,不用掰就自然脫落了。阿太的生命哲學也是直面死亡、自然死亡。活了百年的阿太送走了自己的長輩、朋友還有子女,太多的意外死亡讓阿太感慨自然死亡的難能可貴。死亡不值得懼怕,人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將自己的命運完成得像“成熟的果子”,如何讓果子成熟。老人們會聚在一起琢磨身體的各種特征,切磋各種可能預示死亡的線索,就像在百米沖刺起跑線旁的運動員,豎起耳朵,隨時聆聽命運發出的槍聲。在數個對葬禮細節的描寫中,人的死亡帶來的是親朋歡聚的宴席,還有熱鬧的戲劇表演。作者以寫實的筆法描繪了生命的終點,書寫死亡的真實存在和不可逆轉。不過,蔡崇達并沒有讓死亡成為故事的終點,相反,他通過描述阿太和其他人物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展現了生命的韌性和無限可能。生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但存在的價值是永垂不朽的。
4 結語
蔡崇達將故鄉泉州的文化帶入大眾視野,將寫作角度轉向沿海地區,完成了有關海洋的書寫。他經常說一句話,“其實,作家都是土地的農作物,寫作之前作家一定得回到他的來處,就是他的家鄉”,順應了“新南方寫作”的潮流,揭開了閩南地區神秘的面紗。《命運》以南方之南的泉州為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還兼顧了流傳已久的地域文化的歷史感與時代發展的現代感,更有方言表達和海洋敘事。蔡崇達成功地為新南方敘事提供了典型作品,顯現出新南方寫作的超越性。海的意象作為生命哲學思想的載體,呈現了作者對生命和命運的思考,代表了生命的起源、命運的無常以及人類對自由與解放的渴望。從《皮囊》到《命運》,阿太一直存在于蔡崇達的作品之中,透過阿太的命運,也體現出蔡崇達的生命哲學,“再爛的活法,也算活法”,只要堅強地活下去,一切便都有余地。
參考文獻:
[1] 袁捷.新南方寫作:地緣、文化與想象:第十二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紀要[J].南方文壇,2023(5):80-98.
[2] 朱山坡.我的南方,我的暴風雨[EB/OL].傳媒內參-傳媒獨家,(2020-10-07)[2023-10-18]. https://mp.
weixin.qq.com/s/2YwLXLkb3tbr6Ys3mpEwxg.
[3] 賀仲明,黃鈺淳.在歷史與現實對話中建構“新南方文學”:評熊育群《金墟》[J].南方文壇,2023(4):128-130.
[4] 蔡云琴.水一樣的柔韌與海一般的剛強:沈從文的《邊城》與康拉德的海洋小說中水∕海意象比較[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19(4):43-46.
[5] 莫雷蒂.歐洲小說地圖集1800—1900[M].倫敦:韋爾索出版社,1998:003.
[6] 施議對.文學與神明:饒宗頤教授論文藝觀[J].江海學刊,2008(5):209-219.
[7] 周鵬.新世紀鄉土小說中的民俗書寫與鄉村文化變遷[J].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5):82-87.
[8] 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041.
[9] 蔡崇達.命運[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011.
作者簡介:王思佳(2001—),女,安徽阜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