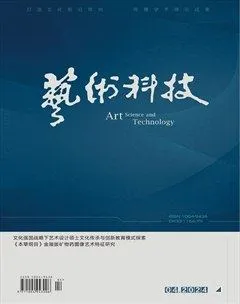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文化可視化創新模式構建探究
吳媛媛 劉政藝 張梓瑩 任雨辰 庹立弘

摘要:目的:鄉村文化振興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文化可視化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文章探析鄉村文化可視化的意義,研究鄉村文化可視化設計存在的問題。方法:通過分析當下鄉村文化可視化的常見方式,選擇國內外的典型案例進行研究,運用元素歸納、符號提取、意蘊抽象等設計方法,對鄉村地區的地形景觀、自然資源、傳統技藝等元素進行挖掘,提煉出圖形、符號、色彩等視覺元素,為當下鄉村文化傳播和鄉村形象建構提供借鑒。結果:通過對鄉村地區的顯性地域文化和隱性地域文化的提煉總結,共設計出三個鄉村標志,打造個性鮮明的鄉村形象。結論:將地域文化元素應用于鄉村標志設計中,能夠避免鄉村形象的同質化和單一化。鄉村文化的可視化設計應以地域文化為核心,以地方精神為引領,注重對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多維度挖掘,使優秀的傳統文化重新擁抱當代人的生活,喚起人們的鄉愁記憶,增強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激發鄉村文化發展的動力,提升鄉村形象的可識別性,實現鄉村文化的活態傳承和創新發展,也為未來鄉村文化的設計實踐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文化;文化可視化;設計創新
中圖分類號:G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4-0-03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1]。文化振興是發展鄉村文化的客觀需要,也是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本文通過文獻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對鄉村文化可視化的意義作出解釋,梳理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文化可視化存在的問題,提煉出文化可視化的創新路徑并進行設計實踐,為鄉村文化可視化設計提供新的策略和思考。
1 鄉村文化可視化相關概述
1.1 鄉村文化可視化的定義
鄉村文化可視化是指將鄉村地區的優秀傳統文化,通過設計創作活動向大眾進行傳播。在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文化的可視化設計不僅注重物質文化建設,更注重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通過挖掘鄉村優秀文化資源,利用圖像、符號、色彩等,對文化信息進行圖形化處理、可視化表達,使鄉村文化變得更加直觀、生動,使其在現代社會中得以發揚光大。
1.2 鄉村文化可視化的意義
我國鄉村地區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在現代文明發展的沖擊下,鄉村傳統文化逐漸消亡。如何使即將被遺忘的鄉村文化重新回到大眾視野,是當前鄉村文化振興進程中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文化可視化為記錄、傳承和發展鄉村文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途徑。
首先,通過可視化的設計手段,能夠對傳統的鄉村文化進行清晰的記錄和解讀。鄉村文化歷經千百年的流傳和發展,許多傳統習俗、“非遺”技藝逐漸流失,鄉村自然景觀、古建筑等遭到破壞,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需要得到保護和傳承。以方言文化可視化為例,太原市和佛山市在2021年下半年相繼開設了方言博物館,還有設計師針對閩南方言文字進行了可視化設計,通過對方言文字的形、音、義進行圖像化設計,制成了方言文字折頁、書籍設計等,讓更多的人有機會領略方言文化的魅力[2]。可見,結合現代設計手法和當代人的審美趣味展示優秀的地域文化,能夠使傳統文化重新擁抱大眾,最終實現文化的記錄與保存。
其次,通過可視化的設計手段,能夠使鄉村文化得到有效的傳播與弘揚。長期以來,鄉村地區由于地理位置與交通工具等因素,鄉村文化發展較城市相比具有滯后性和封閉性的特征,一些優秀且獨具特色的鄉村文化鮮為人知。隨著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傳統手工藝的傳承不再滿足于當下的發展。例如,四川省的滎經砂器通過虛擬仿真技術實現了砂器制作的真正實踐,并制作成在線課程進行展示[3]。這種寓教于樂的傳播方式拉近了觀者與文化的距離。因此,應充分發揮現代科技的優勢,將文化與科技結合,擦出絢爛的火花。
最后,通過可視化的設計手段,能夠促進鄉村文旅產業快速發展與壯大。過去,我國鄉村以農耕文化為主,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無論是農耕文化還是新興產業,都應創新發展模式,因地制宜地建立符合鄉村產業發展和滿足消費需求的機制,促進各類產業振興,推動鄉村經濟快速發展。例如,侗族融合文化和旅游產業的“月也”節為侗族傳統民俗文化的現代化發展構建了一個新的模式[4]。圍繞地域特色和消費需求,開發出了觀光產業、飲食產業等,還以“月也”節的文化習俗為靈感,提取相應元素進行品牌包裝的創新、插畫及周邊產品設計。將節慶文化與現代產品設計相結合,使人們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對該地區的文化產業振興和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2 鄉村文化可視化的現狀及問題
2.1 鄉村文化可視化的常見方式
在鄉村文化振興背景下,國內外許多地區都圍繞鄉村文化進行了公共空間藝術改造和可視化設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墻繪藝術。墻繪藝術是改善鄉村風貌最直觀、清晰的藝術形式。這種藝術最初由美國紐約的街頭涂鴉藝術發展而來,而后在中國的上海、廣州等城市流行開來。當下,墻繪藝術也滲透到了鄉村文化建設中。例如,韓國甘村利用地理位置優勢,用墻繪涂鴉將居民樓打造成色彩斑斕的色塊,吸引了眾多游客前去觀賞、拍照,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藝術鄉村。
二是標語標牌展示。鄉村公共空間的標語標牌能夠傳播鄉村文化振興的政策理念,宣傳當地民俗文化,提高鄉村居民的思想覺悟,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當下傳播媒介的變遷使鄉村標語標牌出現了新的形式。在設計的介入下,鄉村標語標牌的展示不僅以文字形式感染著大眾,其生動的畫面還能給觀者帶來情感上的共鳴。
三是景觀墻形式。鄉村的景觀墻根據鄉村地理特征、文化元素進行相應的設計與開發,能夠使墻繪景觀與自然風貌融為一體。湖北公安縣圍繞自身文化特色進行多元化的文化展示,還有設計者以作家陳應松出生地公安縣為依據,打造了文化景觀墻,宣傳作家陳應松及其著作。
2.2 鄉村文化可視化存在的問題
第一,文化資源缺乏整合。在鄉村振興的推動下,鄉村文化建設雖有成效,但總的來說鄉村文化資源并沒有得到合理的挖掘和利用。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鄉村居民的思想認識不足,逐漸淡化了對傳統技藝、“非遺”的傳承;二是在鄉村建設方面,只注重物質文化建設,忽視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對此,鄉村居民應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探索本地區的優秀文化,與政府、企業、藝術家合作,共同創新鄉村文化的形式,激發鄉村文化活力。
第二,文化可視化形態單一。對文化資源的挖掘不夠充分,反映在文化可視化方面,出現了單一化、同質化的現象。當前許多鄉村在進行文化建設時,只是隨波逐流地進行墻繪和涂鴉,創作水平參差不齊,缺少美感;在鄉村品牌形象設計方面,logo的運用過于同質化,元素的提取不能體現鄉村面貌;在農產品的包裝方面,缺乏對包裝形式的創新和對鄉村文化符號的利用。鄉村文化可視化設計應展現地方文化特色,充分體現其多樣性。
第三,模式化、商業化嚴重。鄉村文化振興歸根結底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雙重振興。當前,鄉村文化可視化設計存在嚴重的過度模式化和商業化的問題。一些先致富的農村,丟棄了對家鄉的認同感和審美觀,盲目模仿城市,對鄉村進行城市化改造,出現了羅馬柱歐式雕花與中式龍鳳戲珠等傳統元素混雜堆砌的建筑,加上現代材料的胡亂堆砌、建筑色彩的任意涂刷拼湊,致使傳統的村落形象和鄉村文化日漸衰退[5]。從長遠來看,這種商業化、模式化的設計不利于鄉村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3 鄉村文化可視化的創新路徑
3.1 提煉地方精神文化,重塑鄉村文化形象
無論鄉村社會如何變遷,千百年來人們形成的文化傳統和精神思想是不變的。鄉村文化可視化應根植于地方歷史文脈進行轉化提煉,在激活鄉村文化資源的同時,增強人們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例如,臺灣土溝村通過對鄉村公共空間進行藝術改造,建立了鄉村美術館、舉辦了主題藝術展等,將傳統的鄉村打造成全新的充滿藝術氣息的公共空間,改變了人們以往對鄉村的土味印象[6]。
3.2 挖掘地域文化元素,傳遞鄉村文化符號
文化可視化設計離不開對地方傳統和特色元素的挖掘,應注重從文化元素到設計符號的轉譯,使轉譯后的設計符號既能體現傳統的文化形態和觀念,又能與現代設計的要求相一致[7]。當前,許多鄉村都基于自身的資源優勢,打造出各具特色的鄉村品牌形象。以鄉村標志設計為例,筆者選取了湖北省和浙江省的土家寨村、橫坑村、舍米湖村三個村莊進行實踐創作,通過對鄉村顯性地域文化和隱性地域文化的挖掘,共設計出三個標志(見圖1)。
首先是基于顯性地域文化的標志設計,以橫坑村和土家寨村為例。橫坑村在自然景觀中呈現出村落、梯田、山水等多樣的田園格局,毛竹林則是該村的產業基礎。通過對地形景觀和自然資源的符號提取,對山坡、房子進行抽象化排列組合,最終形成“竹筍”形象的標志設計。這種扁平化的設計風格使鄉村形象的呈現更加簡潔,也有利于標志的延展應用。而土家寨村的礦產資源和林業資源豐富,尤其以古楓樹最為著名。為充分彰顯該村特色,筆者選取楓葉作為標志設計的主視覺形象,兼顧山林、村莊等顯性文化元素進行表達;標志設計形似“土”字,與“土家寨村”的村名相呼應。
其次是基于鄉村隱性地域文化的標志設計。筆者選取了湖北省的舍米湖村作為案例。該村的擺手舞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標志上方的屋檐形狀代表當地特色建筑擺手堂;標志的中間部分模擬了村民跳擺手舞的姿態;標志下方結合擺手堂地面的石頭變形而成。整個圖形的組合又變成“舍米湖村”的“舍”字。基于隱性地域文化元素的標志設計能夠打造差異化的鄉村形象。從文化可視化的角度出發,該標志設計巧妙地融入了舍米湖村的“非遺”,并且迎合了當代人的審美趣味。
4 結語
當前,鄉村文化振興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文化可視化設計豐富了鄉村文化的傳播方式。在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文化可視化設計應以地域文化為核心,以地方精神為引領,將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相結合,從而迸發新的火花。通過對鄉村標志的設計實踐,能夠打造鄉村文化品牌,塑造鄉村文化形象,激活鄉村文化產業,增強人們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從而推動鄉村文化振興。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總書記《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J].新生代,2022(6):2.
[2] 張文化,蔡信弘.閩南方言文字的信息可視化設計探析[J].藝術百家,2021,37(6):149-158.
[3] 何毅華,李克難.基于陶瓷文化科普的滎經砂器的可視化研究[J].包裝工程,2023,44(10):429-437.
[4] 宋冬慧,楊曦.地域性文化在少數民族節慶品牌中的可視化生態應用:以廣西侗族“月也”節為例[J].包裝工程,2022,43(16):442-450.
[5] 顧小玲.農村生態建筑與自然環境的保護與利用:以日本岐阜縣白川鄉合掌村的景觀開發為例[J].建筑與文化,2013(3):91-92.
[6] 陳可石,高佳.臺灣藝術介入社區營造的鄉村復興模式研究:以臺南市土溝村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6,23(2):57-63.
[7] 李倩.鄉村文化遺產與鄉村振興:基于設計視角的創新思考[J].文化遺產,2021(4):144-151.
作者簡介:吳媛媛(2001—),女,河南鄭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文旅融合與品牌形象設計。
劉政藝(2003—),女,湖北恩施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
張梓瑩(2003—),女,湖北武漢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
任雨辰(2002—),女,河北承德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
庹立弘(2003—),男,湖北宜昌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23年度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藝術點亮鄉村——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文化可視化創新模式構建”成果,項目編號:2023105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