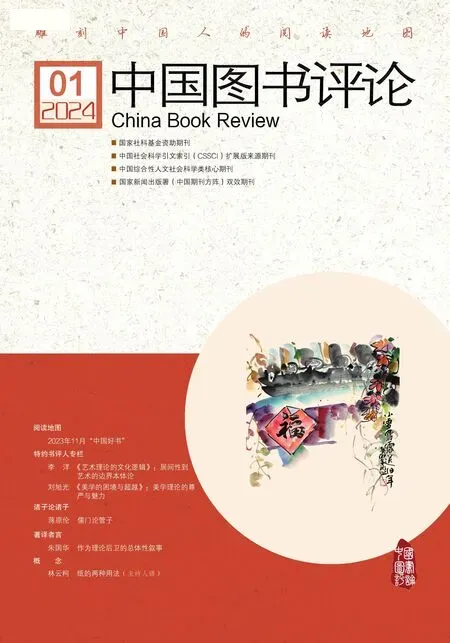“行動—影像” 與好萊塢類型電影
□周厚翼
【導 讀】 德勒茲的“行動—影像” 詮釋了20 世紀美國好萊塢類型電影里“情境”與“行動” 之間的二元生成機制。 “行動—影像” 理論將好萊塢電影類型轉碼為相關的結構性形式, 從哲學層面把握了類型電影的構成與運作規律。
“行動—影像” (L’image-action)是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 在《電影1: 運動—影像》(Cinéma1,L’Image-mouvement, 1983)一書中提出的關鍵概念。 通過勾勒德勒茲在《電影1: 運動—影像》 以“行動—影像” 的固有結構對好萊塢類型電影的詮釋思路, 或可見出德勒茲視域中“行動” (A:action) 與“情境” (S:situation)、 “電影” 與“哲學” 的內在張力, 從哲學層面理解20 世紀美國傳統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構成形式與運作規律。
一、 定義“行動—影像”——德勒茲的問題域與錨點
在《電影1: 運動—影像》 開篇, 德勒茲即指出: “一個事物的本質從來不會在一開始就顯現出來,而是在中間(Mais au Milieu), 在其發展過程中, 在當它的力量得到保證時。”[1]11這一 “中間” 在德勒茲哲學里表現為 “Becoming” 指代的“生成” (Le devenir)[2]狀態, 這一狀態被德勒茲用連字符“—” 體現出來。 德勒茲以“—” 連接“運動”與“影像”, 而非用“運動” 修飾影像(“運動—影像” 不是“運動的影像”), 旨在強調 “運動” 與 “影像” 間的互動關聯: 并非揭示“運動” 與“影像” 二者互動的結果,而是關注二者如何互動, 如何生成。作為“運動—影像” 所存在三種變體(Variétés)[3]之一的“行動—影像” 亦是如此。 “行動—影像” 這一關鍵詞亦置身于 “Becoming” 的問題域, 旨在揭示“行動” 與“影像”之間存在的動態聯系。 參考英國經驗主義(Empiricism) 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 的影像觀, “行動—影像” 直接指向了“二戰” 前以美國為中心的傳統類型電影所呈現出的“情境” 與“行動” 之間內在的二元“生成” 結構。 “行動” 與“影像” 如何在一種動態的關系中相互“生成”? ——這是德勒茲嘗試回應的核心問題。
在《電影1: 運動—影像》 中,德勒茲反諷、 揶揄地定義道: “行動—影像”, 即好萊塢式的“現實主義” (Réalisme) 電影。 或可從以下幾方面對德勒茲所謂的“現實主義”電影(“行動—影像”) 的所屬范疇做一個界定。 時間階段上, 參考大衛·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 和克里斯汀·湯普森(Kristin Thompson)所著的《世界電影史》 (FilmHistory:AnIntroduction, 1994), “行動—影像” 所探討的美國好萊塢類型電影應集中在1930 年左右好萊塢制片廠制度逐步完善, 到戰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 (Le Néo-réalisme) 和“新浪潮” (La Nouvelle Vague) 電影產生之前的這段時期[4]; 如果一定要給出確切的分期, 這一討論主要涵蓋三個階段: 美國電影初創時期(1895—1929)、 經典好萊塢時期(1930—1945)、 經典好萊塢后期(1945—1965)。 但實際上, 德勒茲并未給 “行動—影像” 框定某個封閉的時空范疇, 或可將“一戰” 與“二戰” 作為德勒茲所謂的好萊塢類型電影的轉折點, 但是, 它們只是一個曖昧的時間節點。 此外, 在空間意義上, “行動—影像” 的范疇也并不嚴格局限為美國(德勒茲也提到了大量給美國好萊塢制片體系帶來影響的歐洲電影、 蘇聯電影、 日本電影等), 它所涵蓋的是一種大寫的“美國” 觀念。 在電影工業意義上, “行動—影像” 主要指稱的是好萊塢制造的電影, 并且集中于宣傳美國中心主義的某種“主流” 院線電影, 可以理解為常識意義上的“經典好萊塢電影”。
德勒茲以“現實主義” 定義好萊塢類型片有其合理性, 因為“行動—影像” 所涉及的影片內容與美國現實主義電影的題材大致重合;好萊塢類型片確實反映了美國的現實, 見出了好萊塢的歷史觀念和美國的意識形態, 這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美國”。 但是, 德勒茲本意并非如此, “現實主義” 并非他真正要去關注的內容, 而只是他的一個語詞游戲。 好萊塢類型電影被德勒茲以揶揄的態度歸為一個“容易界定的領域”[1]196, 因為其大眾性往往也與便利性和通俗性密切相關。 “現實主義” 的構成模式在德勒茲眼中是十分簡單且刻板的: “環境” (營造的幻覺) + “行為” (表現的行為) →“行動—影像” (“環境” 與“行為” 之間的關系及其所有變式)。德勒茲斷言: 美國電影的模式均無法逃離行動—影像的變式, “這也是美國電影稱霸全球的秘密”[1]226。 并且, 這一“現實主義” 的揶揄是相對于“新現實主義” 提出的, 這也為他在《電影1: 運動—影像》 末章以及《電影2: 時間—影像》 (Cinéma2,L’image-temps, 1985) 的第一章里分析“新現實主義” 電影如何超越“運動—影像” 埋下了伏筆。
“行動—影像” 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結構性”, 即“行動—影像” 所指向的電影應該具有特定的“Genre”(“類型”, 亦可譯為 “流派”)。[5]在電影中, “類型” 作為一個專業術語可指代電影制作中不同領域囊括的范疇, 如歷史片、 動作片、 喜劇片、 懸疑片等。 屬于一種特定類型的電影或多或少呈現出某種特定風格, 正如人人皆有自身性格。 “類型” 亦可類比為電影的特定 “性格”, 這些性格由故事類型、 場景、道具、 服裝、 社會環境、 視覺表征等多種元素綜合而成, 而非完全被給定的先驗圖式。 誠如法國學者樊尚·阿米埃爾(Vincent Amiel) 和帕斯卡爾·庫泰(Pascal Couté) 所著的《美國電影的形式與觀念》 (FormesetObsessionsduCinémaAméricainContemporain, 2003) 導言中所述: “面對當今大量不同風格的影片公司、多樣化的制作方式、 相互交叉和融合的藝術標準, 給美國電影下一個準確的定義還是很難的。”[6]進一步, “類型” 自身的劃分也是靈活的、 相對的。 當然, 這并不意味著對“類型” 的某種嚴格劃分無其必要, 相反地, 這些分類和結構的剖析將引導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美國電影所揭示的美國文化和美國社會的真實圖景, 以及這套成功的好萊塢電影體系的生成機制與推廣形式。
二、 何種“行動—影像”?——好萊塢電影與類型機制
對“類型” 的某種約定俗成的沿用來自電影市場中種種取得顯著票房成績與觀眾反響的成功電影,而“類型機制” 在好萊塢的統治也是好萊塢電影“稱霸全球” 的一個重要因素。 學者霍頓斯·鮑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 以 “夢工廠” (Dreamworks) 形容好萊塢, 這一比喻揭示了好萊塢類型電影最為核心的本質矛盾: 它既是一種藝術類型, 又是一套工業體系。 一方面,好萊塢使得電影工業成為名副其實,可類比汽車工業的一套成熟工業,它充分利用了集中生產、 分工勞動、流水線裝配等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手段, 并通過“制片廠體制” 聯合了制片人、 導演、 編劇、 明星、 攝影師、 電工等一眾人員, 依靠 “資本運作機制” 下高度細分的制作系統和傳播手段。 另一方面(這也是好萊塢最為悖謬之處), 它的流水線機制并非用于生產汽車或香皂, 而是造“夢”: 依靠影像、 人物、 情境、行動的綜合, 制造一段又一段持續120 分鐘左右很快變化為回憶的無形愉悅經驗。
正如哥特、 文藝復興、 巴洛克等藝術歷史時期都形成了各自鮮明的風格, 好萊塢經典類型電影也擁有自己的一套敘事風格。 1910—1920 年, 美國批量化生產的類型電影已經自發或自覺地有了一套流暢、自然、 便利的敘事模型。 透過一系列明晰、 簡單、 系統、 經濟、 平衡的約定俗成的原則, 故事可以被毫不費力且高效率地講述給觀眾。 在《美國電影美國文化》 (AmericanCinema,AmericanCulture, 1994) 一書中, 學者約翰·貝爾頓(John Belton)認為: “這種風格總的來說是無形的, 一般觀眾難以察覺。 它的隱蔽性, 很大程度是美國電影熟練技巧的產物, 猶如一部講故事的機器。”[7]32一方面, 這種“隱蔽性” 體現出好萊塢電影的某種“透明性”, 通過隱匿它們的運作技巧和刻意建構的所有痕跡, 好萊塢電影坦然地鼓勵我們去“看透” 和 “看清” 它們——似乎我們看到了什么, 它們就是什么。 另一方面, 這種 “隱蔽性” 所呈現的“透明性” 實際上只是一種“幻象”, 它是高度技巧和復雜運思的綜合產物, 它們盡量避免用突如其來的符號、 雜多的暗示破壞流暢敘事, 從而暴露出其本身就是刻意營造的產品。 這種自好萊塢誕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本質悖謬所呈現的“表里不一” 的 “雙重性” 和 “左右互搏” 的“平衡性”, 深深地根植于它的類型片敘事結構之中, 時至今日都在對當代國際國內的電影工業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而這種悖謬又解釋了其本質的某種 “復雜性”和“曖昧性” ——它的明晰是 “希望” 被我們發現的, 而它的“曖昧”則是隱而不顯的。 這也是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商業導向所決定的——畢竟“觀眾看得懂的電影就是好電影”, 這或許是好萊塢電影賣座的原因, 也是好萊塢電影盡可能地隱匿其內在的多義性, 使電影的核心主題盡可能明晰曉暢的原因。
“商業性” 和“藝術性” 是好萊塢類型電影的雙重本質。 很多好萊塢類型片導演如大衛·格里菲斯(D.W.Griffith)、 查理·卓別林(Charles Chaplin)、 約翰·福特 (John Ford)也是極具創造力和創新意識的藝術家, 他們的作品兼具商業效應和藝術價值。 如今的工業化電影和作者電影、 商業片和藝術片之間也并無一道明確的界限。 類型的劃分是靈活的、 相對的, 影片的模式亦是多變的。 美國電影風格的多樣化和流動性賦予其內容豐富的特征, 好萊塢電影的自身標準也在不斷跟隨時代的需求和敘事體系的更迭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 故而, 與其說“戰前好萊塢” 這一前綴對于 “電影” 而言是一個時空范疇或邏輯范疇上的界定, 不妨說“戰前好萊塢”是一種開放的觀念, 而這一觀念在當時的歷史階段主導全球的電影體系, 并且時至今日都對國際國內的電影工業生產不斷施加著復雜的影響力。
此外, 需要強調一下作為德勒茲關注對象的“類型電影” 與德勒茲提出的核心概念 “行動—影像”所規定的電影領域所存在的微妙區別。 這種區別或更偏重于情感態度和學科進路, 而不是其內容之邊界的框定與分殊。 一言以蔽之, 雖然德勒茲研究“類型電影”, 但他并非在進行“類型批評”。 譬如, 德勒茲在《電影1: 運動—影像》 的 “行動—影像: 大形式” (“L’image-action: La Grande Forme”)對主要的好萊塢電影類型如 “社會—心理片”(Le Film Psycho-social) “西部片”以及“歷史片” 等均有提及, 并且他以此為材料, 分門別類地進行分析, 最終證明了它們的內在本質均為“SAS” (大形式)。 雖然, 行動—影像的“S-A” 結構在德勒茲看來是一種強敘事機制, 但是, 這個結構下也潛藏一些可以呼吸、 可被打破的場域。
我們可通過德勒茲對黑澤明(Akira Kurosawa) 的“氣韻—空間”(Espace-souffle) 分析窺見大形式間細碎的裂縫。 黑澤明的影像敘事結構的確存在非常純粹的 “S →A”(由“情境” 到 “行動”) 的公式,但是, 黑澤明拓展了大形式里“S→A” 公式所能延展的范疇, 使其進入了一個較之“情境” 而言更加深邃的、 極具獨特性的 “意境” 領域,這可能是日本本土敘事傳統和黑澤明的個人天賦共同塑造出來的。 黑澤明的《影武者》 (TheShadowWarrior, 1980) 講述了三雄之首武田信玄與其“影武者” 之間的“決斗”,《七武士》 (TheSevenSamurai, 1954)則講述了農民與武士之間的 “決斗”。 在這些講述日本戰國時代戰爭故事的作品中, 穿透了“決斗” 的“氣韻”, 這種“氣韻” 在黑澤明的影像敘事中表現為一種獨特的筆觸,它構成了影片的“綜合符號” (Synsigne) 和作者的“個人簽名” (Signature Personnelle)。 黑澤明的電影里, “橫軸” 與“縱軸” 的設定非常重要, 它們將影片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 一是, 對于 “情境”構成緩慢的展示; 二是, 展開人物的緊張和突然的“行動”。 譬如, 影片《七武士》 中, 拍攝角度通常是一個扁平畫面, “決斗” 的氣韻似乎表現為某種流動的、 無休止的“橫向運動”; 與此同時, 瓢潑大雨從天而降, 又構成了斷斷續續的“縱向垂線”。 在“行動—影像” 所提供的封閉的、 二元的 “S-A” 結構之內,黑澤明通過制造“橫向” 與“縱向”的交錯運動生成了潛能的、 生機的“氣韻—空間”。 通過“氣韻” 的流動, 空間不再是一個封閉的情境,而是擴大成一個有呼吸、 有靈韻、有缺口的“大循環”。
總結而言, “行動—影像” 的指稱對象可被大致概括為: “新現實主義” 運動(1958) 前的美國好萊塢主流類型電影。 “戰前” “好萊塢”“類型” 等關鍵詞并非一種嚴格的概念限定, “行動—影像” 的 “S-A”結構也并非完全僵死的范式(雖然我們致力于批判它) ——德勒茲及此前的美國類型電影研究學者亦未采用此做法; 畢竟, 若將行動—影像的指涉對象嚴格框定在某個“好萊塢” 的論域里或許又掉進了“行動—影像” 自設的陷阱。 如果我們到達了 “行動—影像” 理論更讓人驚喜的部分, 則會發現“框定” 這一影像的邊界意義不大, 因為它不斷在擴展自己的邊界, 并且在時間性和空間性意義上提供了極大的詮釋空間。 “行動—影像” 理論的創新之處在于, 它提供了一套對于美國類型電影的全新的分類方法, 這套方法可以將美國電影的內在結構和運作規律進行嚴格的整合與編碼。
三、 “影像” 何以“行動”?——德勒茲的研究進路
正如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 將他的電影形容為“一片薄薄的蛋糕” 而非生活的一瞥, 電影并非對生活簡單的截取、記錄或轉譯, 它必須經過復雜的藝術加工和特定的環境推動。 我們在兩種層面作為觀眾凝視一部影片的放映。 在第一層面, 我們會在智識中知曉所看到的影片是由每秒24 幀的電影膠片組成的。 正常而言, “一部90 ~120 分鐘的影片由600 ~800個鏡頭和5 ~40 個獨立片段組成”[7]38, 而這些作為組成元素的底片是在不同的布景和場面調度中進行拍攝, 進而通過鏡頭、 剪輯等手段組合起來的。 但是, 當我們真切置身于一部賣座影片的觀影環境中,會發現電影是連貫的而不是割裂的,敘事是天衣無縫、 行云流水的延續,而非支離破碎的情節拼貼。 基于此,傳統電影研究已經發展出一套較為成熟的結構分析的手段, 這種方法通常被稱為“分解” (Segmentation),即將電影本身拆分成若干獨立的基本敘事單元, 在從細節上剖析電影中單獨的某一場, 甚至某一場中的各個部分, 進而見出電影的敘事結構與敘事技巧。 基于這兩個層面,可見出傳統電影類型的研究文獻呈現出兩條線索。 首先是“歸納法”,上溯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歷史發展,具體地、 分門別類地將其安置于各自的類別中; 其次是“演繹法”, 將電影類型作為一個宏觀的文化研究對象。 作為電影類型研究的傳統進路, “歸納法” 以作品為首要研究對象, 從經驗現象出發, 進而總結、歸納、 提煉出相關的內在運作原則和結構特性。 近年來, 第二條線索下也出現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譬如,文集 《類型定義的變化: 對電影、電視節目和媒體進行分類的文章》(TheShiftingDefinitionsofGenre:EssaysonLabelingFilms,TelevisionShows andMedia, 2008)。 該文集遵循的編輯結構則是典型的類型研究邏輯——在第一部分考察了類型的含義與歷史, 在第二部分通過特定的電影考察各種類型電影的殊異, 第三部分則側重類型感知與歷史、 記憶的互證關系, 以此見出類型所體現的社會歷史性。
然而, 德勒茲的方法異于傳統電影研究的兩條進路: 它完全不同于“歸納法”, 也比“演繹法” 更為激進。 不同于傳統的電影理論家、電影史學家對于美國類型電影的剖析方式, 德勒茲無意整理、 總結和歸納浩如煙海的影像材料, 也對條分縷析地挖掘其隱匿的敘事邏輯和敘事模式不感興趣。 他 “獨斷” 地將好萊塢類型電影揶揄為一個 “容易界定的” 領域。 一方面, 德勒茲并非從電影的 “發明史” 出發, 而是從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在 《創造進化論》(L’évolutionCréatrice,1907) 一書中提出的 “電影幻覺” (L’ illusion Cinématographique) 出發。 在電影真正被發明出來之前, 柏格森在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就預料到了一種可能的電影影像, 并以其作為某種幻覺的移印抑或復制。 柏格森將“電影” (Cinématographique) 定義為一種古老的、 由虛假運動所造成的影像的幻覺, 他說: “用某個抽象的、統一的、 不可見的變化將它們串聯起來……我們只能開動某種內心電影機了。”[8]由此可見, 我們好像在無意識中制造電影。 一個世紀后,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所言的“意識猶如電影” (Le Cinéma de La Conscience)[9]或許亦是此論斷的某種延伸。 柏格森這一“電影” 概念, “以預言的方式預測電影的未來或本質”[1]12, 暗示著電影在其本質上就是一個由概念創造出的實體, 所以, 在德勒茲看來, 電影不僅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材料存在, 還是一種哲學本體的化身。 另一方面, 德勒茲也不遵循以往電影研究學者提出的 “類型”概念——雖然他在《電影1: 運動—影像》 中多次提及該詞, 但是他僅僅將其作為“佐料”, 并不賦予其與“結構” 同等地位。 區別于“類型分析” 的某種開放性(開放性同時意味著 “隔靴搔癢”), 在德勒茲的“結構分析” 體系里, “情境” 和“行動” 兩極成為商業大片的固有結構, 好萊塢式的“現實主義” 電影結構被框定在“情境” 與“行動” /“環境” 與“行為” 間的關系及其所有變式里。 他雖然從休謨切入“運動—影像”, 但并非從經驗層面分析“電影幻覺” 如何產生, 這種方法在他看來過于工具化。 他選擇通過批判吸收柏格森 “靜態分切” (une Coupe Immobile) 和 “動態分切”(une Coupe Mobile) 理論, 勾勒出一種作為抽象機制的“元電影” (Metacinéma) 的“運動法則”。
在《電影1: 運動—影像》 的導言中, 德勒茲認為: “這項研究并不是電影史, 而是分類學 (Taxinornie)。”[1]7德勒茲對美國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分類受到諾埃·伯奇 (Noёl Burch) 的啟發, 他按照“大形式”(SAS) 和“小形式” (La Petite Forme,ASA) 將 “行動—影像” 粗略分為兩類, 目的則是構建他在導言里所暢想的一種全新的“影像分類學”,并通過這一分類學重新發現影像的本體。 德勒茲從法國哲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 ( Claude Lévi-Strauss) 《結構人類學》 (AnthropologieStructurale, 1958) 這一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的哲學史背景進入對“行動—影像” 的概念分析, 并且試圖提出一種以好萊塢電影為對象的結構主義電影觀。 首先, “結構” (Structure) 區別于傳統藝術史意義上的“形式” [如海因里希·沃爾夫林 (Heinrich W?lfflin) 的 “形式分析”]; 其次, “結構” 亦區別于“程式” (Formula) [如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 的 “情念/激情程式” (Pathosformel)]。 在德勒茲看來, “結構” 不是局部的規定、 規律或程式, 它也不屬于藝術史范疇,它聚焦更為宏觀的立場, 試圖提出某種元歷史的敘事模式。 與其將結構主義狹義地歸類為某一理論、 某一流派, 不妨說結構主義是作為某種現代方法論存在。
不難理解為何德勒茲提出S (情境) 和A (行動) 這兩個錨點作為好萊塢類型電影穩定敘事的依托——他的策略可以被理解為: “立靶子—打靶子。” 德勒茲以結構分析的方法, 將好萊塢電影類型轉碼為相關的結構性形式, 然后再松動并顛覆這一形式, 進而達到對整個美國好萊塢類型電影內在機制的把握和批判。 在《電影1: 運動—影像》中, “形式” (Forme) 一方面作為“結構” 的另一種說法(根據不同的情境可理解為 “模式” “形態”等); 另一方面, 又被德勒茲賦予了一種由柏拉圖“理型說” 流變而來的哲學內涵。 與此同時, 探析 “行動—影像” 這一結構的建制與統治,以及厘清好萊塢類型電影“稱霸全球” 的原因這兩條線索在德勒茲的行文中互為表里, 相伴而行。 進一步, 德勒茲對此結構的批判, 以及瓦解此結構的嘗試, 同樣是從 “結構主義” + “符號學” (Semiotics) 的立場切入, 他引入美國邏輯學家、 實用主義 (Pragmatism) 創始人查爾斯·S. 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 提出的松動“第二性” 的“第三性”,進而以希區柯克的 “關系—影像”(L’image-Relation) 瓦解了 “大形式” 與“小形式” 的二元結構建制。希區柯克的 “關系—影像” 脫離了“行動—影像” 的固有結構, 它具備了“行動—影像” 的“第二性” 無法提供的意義, 進而作為 “時間—影像” 的前奏昭示了“行動—影像”所面臨的這場危機之結局。
四、 結語
“行動—影像” 理論所呈現的某種“二元性” 原則不僅可以作為分析美國好萊塢類型電影的總體方法論, 整個美國社會的二元意識在文化表現和行為習慣中也體現為某種結構化的內在構造及運行特征。 某種長期的斷裂曾持續存在: 類型批判缺少理論的譜系, 而結構主義則缺少具體、 現實的,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材料。 不同于傳統的電影理論批評家們以“類型” 為切口層層剖析, 以求解決此問題的答案,德勒茲從一開始就試圖將好萊塢類型電影“編碼” 為二維的固定結構,進一步地厘清 “行動—影像” 的內在機制, 在結構層面找到扭轉這一癥結的關鍵錨點。 無論是好萊塢電影內在運行機制這一研究對象, 還是德勒茲這一異于其他學者的研究方法, 都對解決學界此前遭遇的電影史、 哲學史問題, 以及目前面臨的現實問題有積極意義——它不僅提供給我們一種觀照當下電影發展的獨特視角, 也指出了一條理解電影內在的哲學性變革訴求的全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