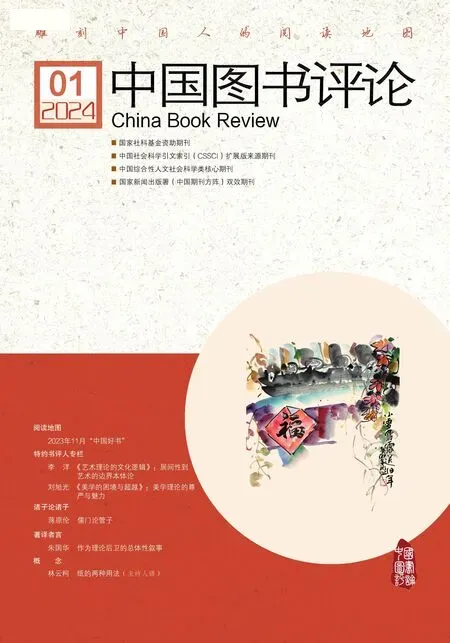打破學科界限的知識史
——評介彼得·伯克 《什么是知識史》
□路雅鑫
【導 讀】 知識史這一新的學術領域正在形成。 彼得·伯克作為其中最權威的先行者, 既置身其中又超然思考, 為之回溯歷史, 繪制藍圖。 溯源其理論基礎, 在各學科的具體語境下體悟知識史的思考路徑, 正可深化對知識縱深與整體的認知。
2020 年, 全世界創造、 復制、傳播的數據總量達到59ZB, 即59 萬億GB。[1]這一天文數字直觀地呈現了我們在信息時代所面臨的數據、信息乃至知識的“爆炸” 增長。 訴諸學術, 中世紀晚期部分知識精英憂慮的“信息過載” 問題終于發展到如今幾乎全民面對的“知識爆炸”現狀。 知識在小到個體、 大到國家命運中漸趨重要, 亦成為人類發展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們開始思考——數據、 信息與知識可以等同嗎? 知識應當如何保存? 知識的更迭與遺失是革新還是災難呢? 知識是如何生產傳播的? 知識的意義是什么? 唯有深入認識知識發展的歷程與內在理路, 才能理解信息時代的知識狀況在人類歷史中所處的位置, 判斷如今知識狀況的特殊性抑或是普遍的連貫性。 知識史的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
一、 彼得·伯克與知識史的新趨向
《什么是知識史》 (Whatisthe HistoryofKnowledge?) 是著名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 應Polity 出版社之邀, 為WhatisHistory?叢書撰寫的一本知識史大綱, 近已有中文譯本問世。[2]不同于該叢書中彼得·伯克的另一本《什么是文化史》 清晰呈現了該學術領域的發展歷程與研究路徑[3], 新興的知識史研究尚未形成統一范式與積累足量學術成果, 因此該書并非后來第三者視角的總結提綱, 而是作者作為知識史領軍者, 置身其中提倡知識史研究, 以及對其未來發展的建議。我們在此書中尋找到的“什么是知識史” 的答案也是相對模糊的。
知識史研究雖是新興, 但與知識有關的研究與思考并不少見。 在數千年前, 尚無學科分界與專門學術的年代, 哲人、 思想家便開始了對“知” 與“智” 的探索。 因此彼得·伯克希冀借整理 “知識及其歷史”, 來展示知識史研究的大致范圍。 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為開端, 近代對知識整體及其歷程有研究自覺的學者不在少數,此為廣義的知識研究。 直到近年,大體從彼得·伯克2000 年出版《知識社會史(上卷): 從古登堡到狄德羅》 開始[4], 專門的知識史研究漸有起色, 英、 法、 德、 瑞典等國已有專門研究機構以及著作問世。
但若要回答“什么是知識史”,甚至單是界定其基本概念, 已是困難之極。 而在定義與理解 “知識”的概念上達成共識, 又是知識史研究開展的基礎。 因此, 彼得·伯克指出這個定義不能狹隘, 亦不可過于嚴格, 在與原生的直接的 “信息”對比下, “知識” 可以指經過一定階段處理、 相對成熟的內容。 這般寬泛的概念, 并無學科邊界, 雖稱之為“史”, 卻也并非歷史學專屬。 在面對實際研究對象中的“知識” 時,彼得·伯克考慮到要強調“知識” 的復數特性 (plural), 提前規避 “知識” 單一性的漏洞。 不同文化中的知識、 不同群體所掌握的知識、 不同類別的知識, 甚至不同語言與國度中對于“知識” 的定義, 在歷史過程中都是并存的, 它們的競爭與沖突正是知識史研究所要關注的問題。 這所吸取的正是20 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均曾普遍出現過的將研究對象簡單化、 視為不變的單一整體的經驗教訓。
知識史研究當前所能使用的概念術語, 也大多來自相鄰學科的較為廣泛的知識研究, 這些概念工具為探索知識史研究提供了多維度的思考視角。 彼得·伯克基于個人學術視野進行判斷, 選擇了19 組概念名詞。 它們分別為權威和壟斷(authorities and monopolies)、 好奇心(curiosity)、 學科 ( disciplines)、 創新(innovation)、 知識分子與博學者(intellectuals and polymaths)、 跨學科性 ( interdisciplinarity)、 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y)、 知識秩序 (orders of knowledge)、 實踐(practices)、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 無知體制(regimes of ignorance)、 情境中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 思想方式(styles of thought)、 被壓制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s)、 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 知識的工具(tools of knowledge)、 傳統(traditions)、 翻譯知識(translating knowledges)。 來自各學科的概念內涵, 投射在知識問題的研究中, 為之提供了足夠豐富的認識視角。 理解與運用這些概念, 是閱讀、 書寫、 思考知識史研究的關鍵。
在明晰知識史研究對象及可參考的概念工具后, 彼得·伯克從認知論的角度, 提煉知識的歷程, 嘗試為知識史研究制定可供實踐的研究路徑。 彼得·伯克認為普遍意義上的知識制造可概括為“系統化” 過程,即人們從信息獲取到將之轉化為知識并付諸應用。 由此, 所有的知識過程大體均可分為四個階段: 收集、分析、 傳播和應用。 彼得·伯克在這一最具實踐性的關鍵章節中, 用上述概念審視與檢驗知識生涯的四個階段, 展示了知識史研究所能涵蓋的大量議題, 收集知識指的是觀察、委派考察、 保存與保護信息 (遺失)、 檢索, 分析知識包括描述、 量化、 分類、 比較、 解釋、 驗證、 發現事實真相、 批判的歷史: 懷疑論者和史料、 批判主義、 敘述, 傳播知識包括口頭傳播、 表演知識、 檢驗知識、 派遣傳教士、 印度經歷、移居他鄉者、 通過物體傳播、 構建文人共和國、 翻譯知識、 通俗化、審查、 隱藏與揭露、 獲取方式, 應用知識則涉及反宗教改革、 官僚化、商業上的知識運用、 再就業、 誤用等知識問題。
正如彼得·伯克強調要避免知識的復數特性一般, 他亦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前警告了知識史研究中即將面臨的其他問題。 這些問題并非歷史學專屬, 而是廣泛存在于20 世紀以來的人文與社會科學中。 彼得·伯克逐一分析了這些共同的新舊問題投射在知識史研究時所呈現的面相,提前規避研究傾向有所偏頗的風險。在內外史的問題上, “內部” 方法可以從內部的增長或下降來解釋知識順序的變化, “外部” 方法將知識秩序內的變化與外部世界的變化聯系起來。 在革命與演化上, 通過越加深入的具體研究, 我們可以認識到此前所簡單理解的革命性知識事件中, 實則包含著連續性的歷史進程。在當下研究中, 要警惕以現代的知識詞匯與觀念審視過往, 亦要警惕過度反思以西方為中心的知識系統后, 轉而矯枉過正地認為在歷史時期所有知識都擁有平等的地位與意義的相對主義。 也有一些新思潮或將影響知識史的思考視角, 對勝利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反思, 將提醒研究者注意相較于掌握知識而言更易被忽視的知識遺失, 以及在發現與發明客觀知識之外還存在對知識的主觀建構。 個體行動者與社會結構對知識狀況的整體影響, 以及性別視角下對不同類型知識的彰顯與隱去等問題, 都是知識史研究中所要警覺的二分法式的陷阱問題。 作者建議選擇中間的某個位置, 作為觀察對立觀點及其局限性的有利位置,避免研究淪為任意單一話語的附庸。最后作者展望了知識史的發展前景,應當是在地理學層面的全球轉向、 社會學層面的社會轉向與年代學層面的長時期這三種視角下的綜合觀察。
概言之, 《什么是知識史》 以十分扎實的歷史學及相關學科的實證研究與理論成果為基礎, 梳理與整合了自培根以來近代知識研究的成果與趨勢, 由此提出知識史的主要研究課題, 并從理論上提醒了研究者知識史研究可能存在的問題。
在此書之前, 尚無其他系統整理與介紹知識史基本概念與路徑的研究著作。 因此, 在知識史的學術脈絡中, 《什么是知識史》 當屬開先河之作。 但若將此書置于彼得·伯克個人學術史中, 這本出版于2016 年的知識史導論并非石破天驚的新作。彼得·伯克本是研究歐洲 “近代早期” (early modern) 文化史的學者,由此衍生出其對知識史的認知與思考, 是在20 世紀末。 出版于2000 年的《知識社會史(上卷): 從古登堡到狄德羅》 才是真正的知識史先行者。[4]彼得·伯克在該書中已經探討了知識史研究的可行性, 并從知識的階層、 學術機構、 分類、 權力掌控、 銷售、 獲取等方面呈現出印刷術以來的歐洲近代知識發展的大體狀況。 此書的時間斷限以及所涉研究主題仍然可見作者出身于“近代早期” 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而2012年出版的《知識社會史(下卷): 從〈百科全書〉 到維基百科》 則將文化史的束縛拋棄得更為徹底一些[5],也基本確立了知識史研究的規范與體系。 《知識社會史》 (下) 將“知識實踐” 劃分為“收集知識” “分析知識” “傳播知識” 三個階段。 除未專門討論 “知識應用” 外, 這與《什么是知識史》 中知識生產的其余三個階段完全一致。 第二部分“進步的代價” 集中討論了知識丟失與分類兩大狀態下的知識現象, 涉及本書中知識管理、 分類、 博學、 隱性知識、 復數的知識等內容, 是本書中知識概念、 進程、 問題各章所論的交叉內容。 第三部分“三維視角下的知識社會史” 所指的知識地理學、 知識社會學、 知識年代學與本書最后展望的知識史研究的全球、社會、 長期三大轉向正一一對應。概言之, 《什么是知識史》 出版于2016 年, 四年間, 彼得·伯克并未再次大幅度推進其對知識史路徑的思考, 而是基本沿襲了同一出版社出版的《知識社會史》 (下) 的基本框架, 并整合了《知識社會史》 (上)中所梳理的知識史研究的學理基礎。
了解彼得·伯克在《什么是知識史》 中展示的知識史研究內容與路徑, 結合其從文化史轉向知識史歷程中的其他研究, 大體可初步了解知識史這一新的研究趨向。 需要強調的是, 《什么是知識史》 確為史學叢書中的一本, 且彼得·伯克的知識史研究也著重關注知識的歷史維度,從這一角度看, 尚在形成中的知識史固然可以視為歷史研究的一個新的分支。 此外, 知識史研究所吸收的學術經驗、 面臨的理論問題以及即將展開的研究等, 并不完全歸屬于歷史學的學科范疇之中。
二、 知識史的多學科理論來源
面對互聯網技術的沖擊, 彼得·伯克認識到在這個重建知識體系的年代, 定位自身知識狀況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諸歷史。 但這并不意味著知識史研究是以現實為導向的應用性與政策性的學問。 知識史的誕生有其深厚的理論基礎。 而這理論來源, 正揭示了知識史打破學科界限的基本屬性。
彼得·伯克在多本著作中均將知識史的理論追溯至20 世紀初德國的知識社會學研究。 知識社會學的思想源頭是馬克思主義、 尼采哲學與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的歷史主義傳統[6], 其先天便與歷史學有密切聯系。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將意識形態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境中解放出來, 轉化為更具普遍意義的認識論與歷史社會學的問題, 奠定知識社會學這一分支的基礎。[7]知識社會學建立起知識與其所在社會環境之間的系統關系。 這種社會環境既是社會性的, 也是歷史性的, 因此知識社會學天然具備社會與歷史取向的多重內在屬性。 彼得·伯克最初被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吸引, 才開始思考歷史時期的知識與社會的關系, 兩大本《知識社會史》 的研究與寫作計劃的開端正是知識社會學的理論。[4]11此后, 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 與托馬斯·盧克曼 (Thomas Luckmann) 將“知識” 進一步普遍化為個體所獲得的一切認知, 提出知識社會學這門學科是要“把人類現實理解為社會建構的現實性”[6]235。 知識社會學在此次研究范圍擴張后, 幾乎成為社會學理論本身, 他們不再重點關注理論性知識與社會的關系。[8]20 世紀后半期至今, 社會科學學科整體呈現歷史轉向的同時, 知識社會學與歷史研究的直接關聯卻在減弱。此后, 知識史研究的進展, 受益于整個社會科學理論的進步。
彼得·伯克認為, 在社會學之外的人類學、 科學史、 哲學研究的刺激下, 知識社會學復興, 并形成了新的知識社會學。[4]78但實際上, 在他所列舉的上述成果中, 無論是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evi-Strauss) 由原始文化研究帶來的正視社會結構決定意義的研究路徑、 托馬斯·塞繆爾·庫恩 (Thomas Sammual Kuhn) 闡述的科學史上的范式革命、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建立起整套話語體系來探討知識與權力的關系, 抑或是文化理論專家對知識問題的關注, 所建立起的“科學建制理論” “公共空間” “文化資本” “場域” 等理論, 都可視為社會科學研究理論的整體推進。 它們程度不等, 卻廣泛地影響著所有社會科學在20 世紀后半期以來的轉向, 自然也可為知識研究提供理論支撐。 但這些是否已被完全吸收,貫通為新知識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尚有爭議。
與此同時, 知識社會學衍生出來的更具專門性的科學社會學反而迅速擴張[9], 與衍生自哲學的科學哲學合流, 推動了科學史研究的發展。 科學史研究中雖然也不乏具體科學事件、 技術史與學科史之類的研究成果, 但自古典時代開始, 哲人對有關科學與自然哲學的思考就是一同進行的, 如亞里士多德對宇宙結構、 物質本性、 運動原因等問題的解釋, 共同構成其自然哲學。這就要求自然哲學在任一次革新時,都需要為諸門具體科學提供新的基本概念。[10]換言之, 科學的變革,本就是以宏觀科學整體為對象的,而非某一自然科學學科。 科學史研究既解決了相應自然科學學科發展史的問題, 亦可視為自然科學的知識史。 在此視角下, 科學史確為其他類型的知識史研究提供了典范。[2]4同時, 科學史學者逐漸關注到非科學范疇內的人文、 技藝以及希臘、印度、 中國等非近代西方的內容,以此發展出他們的知識史研究。[11]這與本書認為科學史為了應對所面臨的挑戰, 正自行擴展研究視野,轉向更為寬闊的知識史研究領域的想法基本契合。[12][2]5
對知識史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有書史研究。 知識史研究試圖呈現長時間段的知識演變狀況, 但就歷史資料而言, 書籍畢竟是保留至今的最主要的知識載體——印刷時代以來尤甚。 現代書史的專門研究, 常以1958 年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 與亨利-讓·馬丁 (Henri-Jean Martin) 合著的《印刷書的誕生》 為開端。[13][14]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 無論是年鑒學派自身對書史研究的推進[15], 還是全世界的書史研究, 都正從書籍貿易的經濟史取向轉向兼具乃至更為強調社會史與知識史視野下的閱讀實踐。[16]書籍這一物質實體, 承載著知識與社會的互動。 不同書籍的書史研究, 彰顯的不僅是該書本身的歷史, 更能揭示其所在歷史時期的歷史問題, 其中當然也不乏知識史議題。 如對工具書的研究呈現的是近代“知識過載” 背景下的知識與信息管理問題[17], 腳注歷史的研究實為知識生產的規范問題[18]。
概言之, 書史提供了對知識物質載體的研究路徑, 書籍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 也彰顯了知識與社會的互動。 科學史與書史的快速發展, 從整體與具體的兩種視野共同推動了知識史研究。[2]5此外, 尚有不同學科牽涉知識研究, 如經濟學、地質學、 考古學、 人類學、 政治學、法學等[2]9-14, 這些相鄰學科中對知識問題的研究, 以及某一理論、 研究成果的新生, 對知識史相關議題的討論也有重要影響, 在此不復贅述。
上述相鄰學科對知識史研究的推動, 說明在當下的分科體系下,知識史作為一門較為理論性與探索性的歷史學分支, 明顯是具備跨學科特質的。 因此, 知識史研究的意義之一便在于打破分科畛域。 若以歷史學的眼光來審視, 則無論是始自古典時代哲人對于知識的思考,還是近代早期培根的知識研究, 都誕生于現代分科體系確立之前。 如此, 以后出的知識體系來分割本身具備整體性的知識研究, 多少有些不合時宜。 進言之, 知識史研究致力于認識知識發展的進程, 還原不同時期的知識狀況, 而各歷史時期的知識, 本身便是相互聯系的整體。因此, 無論各領域學者的知識史研究是以何學科為根基, 以何視角為出發點, 知識史研究都明確具備一種知識的整體史傾向。
三、 歷史學視野下的知識史
彼得·伯克歷時數十載對知識史的宏觀思考, 基本體現在該書及兩本《知識社會史》 中。 又以該書后出, 且為提綱挈領的導論性質。 對于這一新興的知識史的領航與奠基之作, 如何肯定其在知識史上的學術意義都不為過。 該書介紹知識史的基本內容及相關概念, 尤其是將知識實踐明確劃分為四個階段, 確實為知識史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思考與研究路徑。 但是, 在彼得·伯克的知識體系中, 知識主體似乎被置于次要地位, 無論是此書還是兩本《知識社會史》 中都沒有專門討論。[19]
知識實踐的四階段論, 很難不使人聯想到書史研究中的階段論。托馬斯·亞當(Thomas Adams) 與尼古拉·巴克(Nicolas Barker) 總結出“出版—制造—發行—接受—流傳”作為文本生命歷程中的 “五件大事”[20], 讓-多米尼克·梅洛 (Jean-Dominique Mellot) 表示法國書史的生產(production)、 發行(diffusion)和接受(reception) 的三菱鏡式的架構[21], 這些對書籍歷程的認識或對彼得·伯克劃分知識實踐有所啟發。傳統書史研究受目錄學與經典文本研究影響, 對作者十分重視; 現代書史受文本社會學與文學理論影響,綜合考察文本前端生產者、 中間經手者以及終端接受者。[22]總之, 在新舊書史研究中, 人的主體性一直是其中關鍵。 影響較廣的書史專家羅伯特·達恩頓 (Robert Darnton),正是以人與文本的互動為標準, 確定了影響極廣的 “作者—出版者—印刷者—販運者—圖書銷售商—讀者” 的書籍“交流圈” (communications circuit) 模型。[23]在知識實踐的每一階段, 也都有人這一主體的參與。 彼得·伯克多年來致力于溝通歷史學與社會理論[24], 明確指出書史研究推動了知識史研究, 且著有述論年鑒學派歷史的專著, 對書史專家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研究十分關注。[25]因此, 該書缺少對知識主體的分析理解, 頗令人費解。 退一步講, 在彼得·伯克所有的知識史理論著作中, 也僅有《知識社會史》 上冊論及知識階層的崛起與讀者獲取知識的途徑。
如本書所呈現的, 去除掉知識主體的知識史, 是更為簡潔流暢的敘述模式。 知識實踐的四階段, 確實客觀清晰。 知識史的社會維度表明作者關注社會環境對知識的影響,但因缺乏對知識主體與知識實踐的對照分析, 在知識實踐的每一個階段, 作者大多列舉近代早期的知識狀況作為代表, 實則抹殺了知識主體的歷史差異性。 知識采集中既有早期探險家、 博物學家的記錄, 也有古代社會耕織漁獵的生活經驗與技藝, 亦有現代實驗室中無數實驗與信息時代的數據收集。 在現代邏輯思維體系與科學驗證法則確立之前, 在批判與反思理論尚未成型之前, 知識分析已然存在數千年了。最為復雜的是, 如近代多數知識原產地的西方視為知識傳播的現象—— “翻譯”, 實際是經被傳入國家學人篩選、 整理、 譯介、 編輯、整合、 重新闡發的過程, 這在被傳入國更接近于知識采集與知識分析的階段。 由此構成該國家的知識體系, 此后才進入傳播階段。 也就是說, 即使是同樣的知識, 在不同知識主體視野也可能完全不同。 至于知識應用, 確與廣泛的 “閱讀史”有更多的交叉空間。 總之, 知識主體的復雜性, 并非社會結構足以涵蓋。
強調知識主體的另一用意在于兼顧知識實踐以及知識觀念, 筆者認為二者共同構成了知識主體, 亦是知識史書寫的多重維度。 彼得·伯克曾在《什么是文化史》 中指出近年來各學科領域廣泛存在的“文化轉向”, 在那些曾堅定不移的理性認知中, 加入了對特定時期特定人群的價值觀的考察。[3]2相較于政治史、經濟史, 知識史本就是更為抽象更具思想觀念特質的學科, 但知識史也仍舊存在思想觀念的維度。 作為理性行動者, 知識主體在知識采集、分析、 傳播、 應用任一階段中的知識實踐, 都是其知識觀念的投射。他們對知識或系統深入或零碎簡樸的認識, 至少包括何為知識以及知識有何效用的判斷。 而這又反過來影響著他們的知識生產與獲取, 最終塑造而成我們所探索的實踐層面的知識史。
彼得·伯克在本書與《知識社會史》 (下) 中都展望了知識史在時間、 空間、 社會三種視角下的面貌。依筆者所見, 或可在此基礎上增加知識觀念的維度。 如此, 知識史研究的目標在于繪制一張四維的知識全景圖。 據此, 我們可定位任一時空、 任一社會階層程度的知識狀況與知識觀念。
在此基礎上, 筆者想從歷史學視角進一步闡發知識史研究的意義與研究空間。 其一, 知識史視 “知識” 為整體, 在這張四維圖景中,我們能更為客觀立體地認識某一事件、 技術、 創見、 學科在知識史中的坐標系, 打破各學科、 社團、 國家敝帚自珍式的學科史與學術史的研究。 其二, 知識史將為各學科的研究對象提供新的認知視角。 例如,在知識史的視角下, 圖書館是新舊知識體系交接下知識的儲存、 分類、傳播中心; 大學、 研究所、 學會的建立是新知識生產的體制基礎; 教科書則代表著將時代前沿知識整理、規范、 簡化為普通知識, 塑造國民共同認知的努力。 其三, 知識史亦可為傳統歷史研究提供背景依托。知識在不同時代的重要性不同, 知識史研究的意義亦有所區別。 但在中國近代——即使再反思西方中心論亦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中西相遇、知識轉型的年代, 幾乎所有重要人物、 事件研究中的思想來源均取自時代的“知識倉庫”。[26]如在溯源日本對梁啟超思想的影響研究中[27],若有中日此一時期前后的知識狀況研究, 那么認知歷史人物的思想來源也不是難事。
概言之, 《什么是知識史》 是一理論性著作, 筆者對此書的介紹與進一步思考, 亦維持在理論層面,而非具體研究。 在此書之后, 彼得·伯克連續出版了其對流亡者、 博學者和無知的研究成果[28], 仍在踐行其對知識史的倡導, 開拓知識史研究的空間。 紙上得來雖不覺淺, 但推動知識史發展確需躬行。 無獨有偶, 本文完稿不久, 恰逢本書中文版以及一本知識史專題的著作上市[29][30], 或將有更多讀者關注到知識史研究。 放眼全球, 知識史研究都尚在起步階段, 無論是理論性的討論還是具體課題的研究, 都尚有極大的探索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