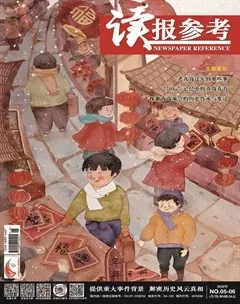靠微短劇“翻身”的演員們
孫雅蘭
這兩年,大量混跡橫店多年的無名演員靠微短劇翻了身,他們終于有了挑選劇本和角色的權利,然而,他們并不覺得自己更靠近影視圈了……
微短劇演員的“自我修養”
“我進入影視行業8年了,第一次接觸微短劇的時候,突然開始懷疑自己,是我太長時間沒拍戲了嗎?好像跟不上這個時代了。”張震在錄音室忙了一上午,為自己參演的作品配音,錄完嗓子就啞了。她是最早一批涉足微短劇的演員之一。從2022年9月到現在,她最忙的時候一個月能演四五部,在橫店的片約很少斷檔,八千元一天的片酬也是一般演員的兩三倍。
站在片場,她首先感受到的是快速運轉的節奏,無論哪個環節,都至少快過傳統影視劇一倍的時間。演員進入任何狀態或情緒都要快,說臺詞也要快,只需要調動夸張的動作或表情,目的是讓觀眾一眼看出人物標簽化的性格。一個微短劇演員的“自我修養”通常是快速入戲和出戲的能力。將時間一再壓縮,是微短劇片場的最高準則。
微短劇的表演方式,對演員提出了新的要求,張震的方法是逼迫自己建立表演時的信念感,尤其是演戰神題材時。張震演過女戰神,每次熟悉臺詞前,她都要不停給自己打氣“我是戰神,我是戰神”,這樣她才能念出那些又狂又拽的臺詞,淡然接受所有人在自己面前磕頭、下跪的場面,“否則很多臺詞根本說不出口,自己都覺得尷尬”。
張震回憶自己以前參演影視劇,拿到劇本后需要認真分析故事背景、人物關系和人物心理等,甚至提前一個月進行劇本圍讀、進組訓練,在片場還要經常跟導演或攝影師溝通。輪到演微短劇時,只能是導演讓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導演指令以外的自我發揮都屬于多余。但張震并不敢全然信任導演,許多拍攝微短劇的導演都是新手,以前多在傳統影視劇組擔任副導演、燈光師、演員或美術,甚至是從婚紗攝影、宣傳片導演轉過來的。她搭戲的對象也跟從前大不一樣,短視頻達人、信息流廣告演員、純素人,有些是帶資進組,有些是資方的裙帶關系,“他們連臺詞都說不清楚”。
現在的橫店已經很少能見到影視劇組開機,取而代之的是遍地開花的豎屏微短劇,專業影視人紛紛轉戰豎屏,其中也包括大量像張震這樣的在橫店求生的演員,他們大多以配角、特約演員、群眾演員的身份輾轉影視圈多年,微短劇使他們搖身一變升為主角,有了源源不斷的片約。
新人也不缺通告。努爾在2023年1月來到橫店,出演微短劇之前,他的全部行業經驗僅限于群演。努爾來自新疆,濃眉大眼、棱角分明,身高也接近一米八,這為他贏得了機會。最初的一次,是他去朋友的微短劇劇組探班,劇組的導演和制片人相中了他,鼓勵他出來拍微短劇,并承諾要將他培養成男主角。盡管努爾從未受過任何科班訓練,在此之前甚少有演戲的經驗,臺詞功底更加棘手,但沒人介意。有時候,努爾還很羨慕一些爆款演員一部劇的片酬能達到兩三萬,而他只有一萬。
出生于1998年的徐藝真和大她一歲的搭檔孫樾,兩人頻繁以配對搭檔的形象出現在不同的微短劇中,相似的劇情和固定的陣容可能會讓普通觀眾暈頭轉向,但這也是演員以量取勝的方式。制片人惠祥意曾與徐藝真合作過一部微短劇,此后他只要一跟投資方聊項目,對方都會流露出只想找爆款演員、爆款團隊的意愿,惠祥意認為這多少有些盲目,“現在微短劇的資方90%都是圈外人,只認爆款團隊,從來沒人去研究他們為什么能火,其實完全可以復制的”。
投資方對爆款演員的依賴,意味著傳統影視劇演員入局微短劇沒有太大優勢。可以說,豎屏主動與橫屏劃清了界限,分界的標準是流量與數據。張震就曾經推薦過一個朋友拍微短劇,對方經常出演電視劇中的男二、男三號。等到張震把資料推給片方,換來的卻是一句質疑:“他演過爆款微短劇嗎?”
“沒人把它當成藝術搞”
張震記得,自己剛開始接微短劇時,身邊認識的演員沒有多少愿意跟風的。作為橫店最早一波入局微短劇的演員,張震承認自己吃盡了紅利,與她同一時期入局的幾位演員都是如此,從來不愁沒戲拍,“每個人起碼不下10部爆款”。
張震接演的角色都是女一號,但她并不將其視為打開事業運途的一扇窗戶,“豎屏出不了作品,微短劇不能叫作品,只能算是對我職業能力的一種考驗”。她所指的考驗,聽起來更像是在耐力上逼近極限。初期,張震接拍的大多是戰神題材,平均3-5天拍完一部,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張震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有挑不完的劇本和角色。演得多了,張震開始體味到其中的副作用——拍戲拍麻了。
演員安欽夫管拍微短劇叫“下海”。安欽夫從拍兒童劇和喜劇開始出道,入行已經10年。一開始,他對微短劇充滿抗拒。從去年3月開始,不停有人邀請他拍微短劇,他糾結了半年,直到發現很難再接到影視劇項目,便鼓足勇氣“下海了”。安欽夫于是從2023年9月開始拍微短劇,一共參演過5部微短劇,拿到的全都是男一號。“把我的心氣都養高了,我都已經干了自己不喜歡的事,還去演配角嗎?沒必要。”只是做男主的代價是比其他演員辛苦得多,拍戲過程中,安欽夫每天只能睡4個小時。
隨著微短劇市場急速增長,對演員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橫店開始出現搶演員的局面。安欽夫告訴記者,以前很多影視項目在北京建組和面試演員,現在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橫店的微短劇劇組為了節省經費,大多會選擇在橫店片場挑選演員。很多演員專門搬來橫店住下,就是為了提高接戲的效率。安欽夫的第5部微短劇就是這樣定下的。
短短3個月里,安欽夫觀察到專業影視人紛紛擁入,服化道也越來越講究,但劇本仍然和傳統影視劇相去甚遠,他認為這是由微短劇的基因所決定的。微短劇的基本邏輯是一分鐘一集,動輒拍至100集,每一集最重要的是“埋鉤子”,吸引人往下看,再怎么變化,也很難呈現飽滿的人物形象、展現人物完整的心路歷程,這就決定了微短劇的人物普遍臉譜化、模式化、標簽化,一個劇里的人物改個名字就可以拍成另一部劇了,甚至不同劇的劇名都很相似。“別說我了,包括導演、制片團隊,他們都門兒清,拍這個東西就是為了生存,沒人把它當藝術搞。”
微短劇未來會朝什么方向發展?張震心里沒底。去年,張震接演了優酷的首部自制微短劇,雖然她很滿意其專業的劇本和團隊,但仍然掩藏不住內心的擔憂,“專業影視人下沉到微短劇,不一定能作出爆款”。她跟記者提了幾個微短劇觀眾愛看的元素,呼來呼去的巴掌、動輒下跪的人馬、開著豪車的少爺等,主打一個爽感。如果要再進一步研究規律,只能看概率,“靠命、靠運氣”。
聽說橫屏影視劇并不認可微短劇演員,安欽夫擔心對自己的演藝事業造成負面影響,他甚至不好意思像以前那樣,在自己的社交平臺上更新劇組的花絮,并且要求劇組不要在演職員表中露出自己的名字。有時候,他和其他業內人士聊起,都認為微短劇的風口最多持續到今年下半年,就像當年網絡大電影 的發展軌跡一樣,迎來內容監管的同時也將告別野蠻生長的勢頭,“大家都在趕最后一波風口,再掙一波錢”。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