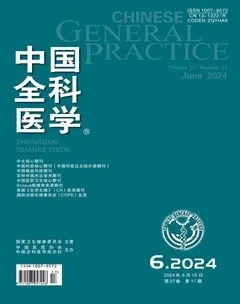中國中老年人C 反應蛋白累積升高次數與軀體和非軀體抑郁癥狀的關系:前瞻性隊列研究
趙檸煊,姜琳,胡美婧,姚強,毛一能,朱彩蓉*
1.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 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
2.637199 四川省南充市,川北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
中老年抑郁癥是全球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1]。中國老年人抑郁癥患病率呈上升趨勢[2-3]。研究顯示,2020 年中國老年抑郁癥狀總體患病率為20%,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負擔[4-6]。
基于“心理-神經-免疫功能障礙”的老年抑郁癥“炎癥假說”廣受關注[7-9]。C 反應蛋白(CRP)是常用的炎癥生物標志物[10],但目前關于CRP 與抑郁癥狀之間縱向關聯的研究結論不一致[11-13]。兩項基于英國老齡化縱向研究數據庫(ELSA)探索CRP 與抑郁癥狀縱向關聯的研究中,AU 等[14]采用CRP 的單次測量,BELL等[15]則集中于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持續升高的累積效應,但其結果不一致,提示探索CRP 和抑郁癥狀關聯時,是否考慮CRP 在多次測量中升高的累積效應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
抑郁癥狀分為軀體癥狀(疲勞、厭食、身體障礙等)和非軀體癥狀(認知改變、焦慮、易怒)兩個維度[16]。臨床研究發現軀體癥狀可以通過與炎癥相關的抗抑郁治療進行控制,而非軀體癥狀卻對該治療方式未有明顯反應,提示不同維度抑郁癥狀的發生機制可能存在差異[17]。此外,基于疾病行為理論,有研究提出炎癥的發生更可能導致疲勞、睡眠問題和運動放緩等軀體抑郁癥狀[18]。因此,探索炎癥與抑郁癥狀不同維度的關聯很有必要。
中國關于CRP 與軀體和非軀體抑郁癥狀縱向關聯研究[19]僅使用了CRP 的單次測量結果,未對CRP 持續升高累積效應進行探索。因此,本研究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數據庫探索中國中老年人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抑郁癥狀及其軀體和非軀體癥狀之間的關聯,以期為預防中老年人群抑郁的發生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數據來源于CHARLS 研究2011—2018 年公開數據庫。該研究獲得了北京大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IRB00001052-11015),所有受試者提供了書面知情同意。CHARLS 是一項基于中國45 歲及以上人群的前瞻性調查,研究對象來自28 個省份、150 個地區、450個村莊/社區。基線調查數據在2011 年通過計算機輔助的面對面個人訪談收集,并于2013 年、2015 年和2018 年完成隨訪。基線血液檢查數據于2011 年采集,并在2015 年進行隨訪。有關CHARLS 的其他詳細信息已在其他研究說明[20]。
2011年共有11 847名研究對象參與基線血液檢查,本研究排除標準:(1)年齡<45 歲;(2)沒有基線或2015 年或2018 年抑郁癥狀測量數據或患有精神、記憶或精神類相關疾病;(3)沒有基線或2015 年CRP 測量數據或CRP 測量值>10 mg/L 且<0.1 mg/L(CRP>10 mg/L 被認為是急性感染[21],CRP 的有效檢測下限為<0.1 mg/L);(4)基線協變量缺失。經上述排除標準,最終納入3 868 例樣本(圖1)。由于軀體和非軀體抑郁癥狀評估未有明確的閾值判斷標準,為盡可能保留樣本信息,因此本研究并未排除2011 年及2015 年患有抑郁癥狀的參與者,在后續分析中將基線抑郁癥狀得分作為協變量進行調整。

圖1 研究對象篩選流程圖Figure 1 Flow chart of participant selection
1.2 研究變量及定義
1.2.1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血液樣本中的CRP 水平是由免疫比濁法測量的,檢出范圍為0.1~20 mg/L,變異系數為5.7%[20]。CRP 以3 mg/L 作為測量閾值判定慢性低度炎癥狀態[22],并通過2011年與2015 年兩次測量計算慢性低度炎癥發生次數,即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范圍:0~2)。其中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2 次表明研究對象在2011 年和2015 年均存在慢性低度炎癥狀態。
1.2.2 抑郁癥狀:抑郁癥狀通過10 項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10)進行評估,反映過去1 周的抑郁癥狀。CESD-10 量表分為“軀體抑郁癥狀”(條目2、4、7、10)和“非軀體抑郁癥狀”(條目1、3、5、6、8、9),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3]。每個條目的評分范圍從“很少或沒有時間=0 分”到“大多數時間=3 分”,求和計算抑郁癥狀總分(范圍:0~30 分),其中得分≥10 分被認為表現出有臨床意義的抑郁癥狀[24-25]。
1.2.3 協變量:本研究所納入的協變量包括基線人口學特征(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相關行為(吸煙、飲酒、社會活動)、代謝指標(BMI、高密度脂蛋白、三酰甘油)和健康狀況(高血壓、糖尿病、癌癥、心臟病、關節炎、卒中和肺部相關疾病)。
受教育程度劃分為小學以下、小學、初中、高中及以上。婚姻狀況定義為已婚、離異、喪偶和未婚。吸煙和飲酒狀態分為從不吸煙/飲酒、現在吸煙/飲酒和曾經吸煙/飲酒。社會活動由調查者前1 個月內參與的10 項活動的頻率評分相加并分為0、1~2 分和≥3 分。BMI 根據參與者的身高和體質量依據標準公式計算。血液樣本采用酶比色法檢測高密度脂蛋白和三酰甘油。高血壓定義為收縮壓≥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Hg;或服用抗高血壓藥物;或自我報告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定義為空腹血糖≥126 mg/dL(7.0 mmol/L)和/ 或糖化血紅蛋白(HbA1c)≥6.2%;或使用任何控制血糖的治療;或自我報告糖尿病病史。此外本研究也納入了基線時自我報告的健康狀況,包括癌癥或惡性腫瘤(不包括輕微的皮膚癌)、心臟病(包括心肌梗死、冠心病、心絞痛、卒中和其他心臟問題)、關節炎或類風濕關節炎、卒中及肺部相關疾病。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使用SAS 9.4 和Stata 16.0 軟件進行,檢驗水準設置為α=0.05。根據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的次數對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進行描述,連續性變量符合正態分布時采用(±s)表示,分類變量采用頻數和構成比表示。連續性變量的組間差異性檢驗采用方差分析,分類變量的組間差異性檢驗采用χ2檢驗和Fisher's 確切概率法。
本研究采用多重線性回歸模型分析CRP 在2 次連續測量(2011 年、2015 年)中升高的累積效應與2018年抑郁癥狀總分/軀體抑郁癥狀得分/非軀體抑郁癥狀得分之間的縱向關聯并計算回歸系數及其95%置信區間(CI)。此外本研究也采用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的累積效應與2018 年抑郁癥狀患病情況(是/否)之間的關聯性,計算OR 值及95%CI。參照既往相關研究及單因素分析的結果[14,26-27],本研究共建立5 類回歸模型,初始模型針對結局變量的基線水平進行調整,剩下每個回歸模型則在前一個模型的基礎上依次添加社會人口學因素、健康相關行為、代謝指標和健康狀況。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一般特征
納入本次分析的3 868 名參與者,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0 次的參與者共計2 918 人,1 次共計763 人,2 次共計187 人;平均年齡(57.2±7.8)歲;男1 812人(46.85%),女2 056 人(53.15%);BMI(23.9±4.0)kg/m2;基線CESD-10 平均得分為(7.99±6.08)分。CRP 累積升高0 次、1 次、2 次者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吸煙情況、社會活動評分、癌癥、心臟病、高密度脂蛋白、三酰甘油、基線CESD-10 平均得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CRP 累積升高0 次、1 次、2 次者BMI、飲酒情況、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炎、肺部相關疾病、卒中患病情況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不同的3 組研究對象一般特征比較Table 1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episodes of CRP elevations over two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2.2 CRP 累積升高次數與抑郁癥狀得分的縱向關聯
以2018 年抑郁癥狀得分作為因變量,多重線性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在調整了基線抑郁癥狀的情況下,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2 次相對于0 次,與2018年抑郁癥狀得分存在正向關聯(β=1.20,P<0.05)。在調整所有協變量的模型中,正向相關關系仍未改變(β=1.22,P<0.05)。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1次相對于0 次,與抑郁癥狀得分的關聯在所有模型中均未發現相關性(P>0.05)(表2)。

表2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2018 年抑郁癥狀得分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Table 2 Associations between repeated episodes of CRP elevations over two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2018
2.3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的累積效應與軀體抑郁癥狀/非軀體抑郁癥狀得分的縱向關聯
以2018 年軀體抑郁癥狀為因變量,2011 年和2015年CRP 升高的累積次數為自變量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中,在調整了所有協變量的全模型中,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2 次相對于0 次,與軀體抑郁癥狀得分存在正向關聯(β=0.51,P<0.05)。在研究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持續升高的累積效應與非軀體抑郁癥狀的分析中,CRP 升高2 次相對于0 次,與非軀體抑郁癥狀得分也存在正向關聯(β=0.71,P<0.05)。不管是軀體抑郁癥狀還是非軀體抑郁癥狀,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1次相對于0次,在所有模型中未發現相關性(P>0.05)(表3、4)。

表4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2018 年非軀體抑郁癥狀得分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Table 4 Associations between repeated episodes of CRP elevations over two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and non-somatic depressive symptoms in 2018
2.4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抑郁癥狀患病情況(是/否)的縱向關聯分析
當2018 年抑郁癥狀得分≥10 分時認為患有抑郁癥狀,本研究以2018 年抑郁癥狀患病情況(賦值:是=1,否=0)作為因變量,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調整基線抑郁癥狀得分的情況下,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2 次相對于0 次的參與者,3 年后患有抑郁癥狀的風險更高(OR=1.58,95%CI=1.15~2.18)。在調整所有協變量后的模型中相關性仍未改變(OR=1.64,95%CI=1.18~2.29)( 表5)。 進一步, 本研究將CESD-10 量表的10 個條目單獨分析,回答為“很少或沒有時間”則認為不存在該條目對應的抑郁癥狀,其余回答則認為存在該條目對應的抑郁癥狀。以調整所有協變量的模型5 對抑郁癥狀不同維度下各個條目進行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與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0 次的參與者相比,CRP 升高2 次是軀體抑郁癥狀中“我覺得做任何事都很費勁”(條目4)發生的危險因素(OR=1.54,95%CI=1.11~2.13),同時也是非軀體抑郁癥狀中的“我不愉快”(條目8 反向計分)發生的危險因素(OR=1.54,95%CI=1.12~2.13)(表6、7)。

表5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2018 年抑郁癥狀患病情況的關聯分析Table 5 Associations between repeated episodes of CRP elevations over two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and developing hig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2018

表6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2018 年軀體抑郁癥狀各條目的關聯分析Table 6 Associations between repeated episodes of CRP elevations over two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and developing items of somatic depressive symptoms in 2018

表7 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2018 年非軀體抑郁癥狀各條目的關聯分析Table 7 Associations between repeated episodes of CRP elevations over two successive determinations and developing items of non-somatic depressive symptoms in 2018
3 討論
本研究利用具有代表性中國中老年縱向數據庫,分析了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累積升高次數與抑郁癥狀及軀體和非軀體癥狀之間的縱向關聯,結果提示CRP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2 次相比于0 次的中國中老年人抑郁癥狀(β=1.22,P<0.05)、軀體抑郁癥狀得分(β=0.51,P<0.05)及非軀體癥狀得分(β=0.71,P<0.05)發生風險更高。
CRP 持續升高的累積效應可能是中國中老年人群抑郁癥狀發生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探索CRP 與抑郁癥狀之間關聯的研究僅考慮CRP 的單次測量,且均未發現炎癥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聯[19,28]。既往關注CRP持續升高的累積效應的研究只集中在西方人群,本研究補充了來自中國人群的證據,在不同人種中研究結論一致[15,22]。在探索炎癥與慢性疾病關聯的流行病學研究中,考慮炎癥反應的慢性和持續性是至關重要的[29]。對炎癥的單次測量,因其無法區分個體的暴露是否持續,可能導致誤分類的發生。
本研究發現,CRP 持續升高與中國中老年人軀體抑郁癥狀之間存在正向關聯。本研究結論與荷蘭一項多中心隊列研究一致,提示軀體抑郁癥狀與炎癥標志物存在關聯[30]。炎癥與軀體抑郁癥狀的病理生理學機制研究提示,胰島素、空腹血糖、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脂質標志物可以通過降低細胞代謝功能和加劇炎癥反應來影響軀體抑郁癥狀[18,31]。此外,CRP 等促炎蛋白水平異常可能延續“病態行為”(即疲勞、活動減少等),并對與情緒調節相關的大腦區域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導致軀體抑郁癥狀[32-33]。
CRP 持續升高的累積效應也是非軀體抑郁癥狀發生的危險因素。是否考慮CRP 在多次測量中升高的累積效應可能是導致既往CRP 與非軀體抑郁癥狀之間關聯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34-35]。同樣采用CHARLS 數據庫的一項中國研究[19],在僅考慮CRP 單次測量的基礎上,并未發現CRP 與非軀體抑郁癥狀之間存在關聯。一項來自英國的研究,在對抑郁量表的條目單獨分析時發現,CRP 在2 次連續測量中升高2 次相比于0 次的參與者在抑郁癥狀量表的某些非軀體癥狀條目下均存在正向關聯[15],本研究結論與之一致。目前關于炎癥與非軀體抑郁癥狀的相關機制尚不明確,仍需更多的生物學研究進行補充。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由于CHARLS 數據庫的測量點有限,本研究通過CRP 超過閾值的測量點數進行分析。在有多個測量點的縱向研究中,本研究建議可以采用軌跡分析等方法,更準確地捕捉CRP 的動態和持續變化[36]。其次,本研究抑郁癥狀的評估是基于CESD-10 量表,而不是依賴專業醫療人員,不能準確反映臨床診斷。
4 小結
長期暴露于慢性炎癥不僅是中國中老年人抑郁癥狀的危險因素,也是軀體抑郁癥狀及非軀體抑郁癥狀的危險因素,建議及時治療中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慢性炎性疾病,避免處于長期的慢性炎癥狀態,以降低中老年抑郁的發生。
作者貢獻:趙檸煊提出研究理念,負責數據整理,統計分析,論文撰寫;姜琳負責數據整理,提供統計學設計思路,協助論文修改;胡美婧負責數據整理,分析可行性;姚強負責數據整理,統計學設計;毛一能負責數據整理;朱彩蓉負責思路指導,編輯與修改論文,對文章監督管理和審查。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