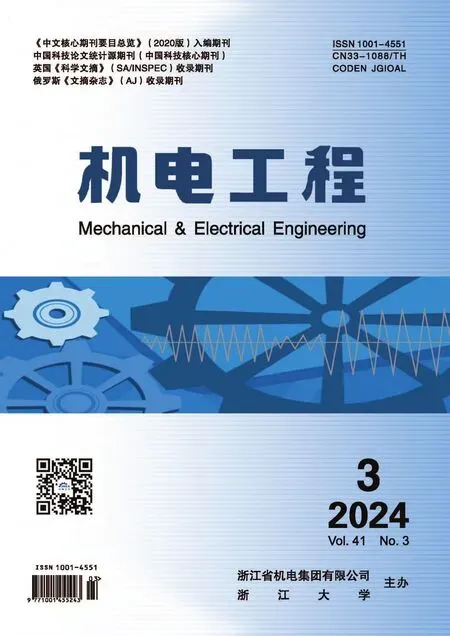考慮點蝕情況的雙漸開線齒輪動態特性研究*
沈 成,姜 宇,姜春雷,潘 毅,樊智敏
(青島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學院,山東 青島 266061)
0 引 言
齒輪作為機械傳動系統中的核心部件,點蝕與磨損是其失效的主要形式。齒面一旦發生點蝕,齒輪的傳動精度、承載能力、工作壽命和效率就會降低。點蝕坑數量增加,會導致接觸線長度發生變化,從而影響齒輪的嚙合剛度,其動力學特性也會隨之變化。
因此,開展點蝕對雙漸開線齒輪的接觸線長度與嚙合剛度影響的研究,對研究其動力學特性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點蝕情況下齒輪的時變嚙合剛度及動力學特性進行了不同深度的研究。
馮松等人[1]研究了齒面磨損對齒輪嚙合剛度的影響,考慮輪齒彎曲變形、剪切變形等,計算分析了微觀點蝕及宏觀點蝕下的嚙合剛度及發展規律。林騰蛟等人[2]研究了裂紋故障對斜齒輪的時變嚙合剛度及振動響應的影響,采用能量法建立了齒根裂紋故障的懸臂梁模型,并對齒輪動力學特性進行了研究。趙鑫等人[3]基于能量法建立了輪齒懸臂梁模型,研究了不同點蝕位置、深度、數量對嚙合剛度的影響。陳勇等人[4]研究了不同點蝕程度對斜齒輪動力學特性的影響,建立了齒輪多體動力學模型,并通過實驗研究了點蝕對齒輪振動加速度的影響。QIN Wei-jie等人[5]基于多疲勞機理的方法,在考慮摩擦的基礎上,研究了轉速對齒輪應力分布的影響,并預測了齒輪產生疲勞裂紋的加載規律。馮偉等人[6]利用鐵譜分析和振動分析,模擬了點蝕故障齒輪嚙合過程中的磨損與振動的關系。MA Rui等人[7]推導出發生齒面點蝕剝落的遏制齒輪的時變嚙合剛度計算式,研究了齒面點蝕對其時變嚙合剛度的影響。李紀強等人[8]探討了工程中微點蝕與熱膠合發生的損傷原理,分析了潤滑油膜厚度和瞬時嚙合溫度的影響。涂旭欣等人[9]研究了點蝕發生時齒面剝落形狀及分布對齒輪時變嚙合剛度的影響。HAN Lin等人[10]以齒面點蝕剝落的斜齒輪為研究對象,給出了發生點蝕后的斜齒輪時變嚙合剛度計算式。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在發生點蝕失效情況下,齒輪動力學特性的研究大多針對目前工業體系中的常見齒輪,對雙漸開線齒輪的研究較少。
雙漸開線齒輪是一種綜合了雙圓弧齒輪優點和漸開線齒輪優點的新型齒輪,目前對雙漸開線齒輪動態特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樊智敏等人[11]提出了一種基于有限元法建立的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剛度計算模型,求解了雙漸開線齒輪時變嚙合剛度,發現了雙漸開線齒輪綜合時變嚙合剛度變化趨勢與普通漸開線齒輪相似。陳亮等人[12]基于赫茲接觸理論和分形理論,建立了考慮分形齒面粗糙度的雙漸開線齒輪時變嚙合剛度模型,分析了摩擦系數、分形維數以及粗糙度幅值等對雙漸開線齒輪時變嚙合剛度的影響。
但目前尚未有學者對雙漸開線齒輪發生疲勞點蝕情況下的嚙合剛度及動力學特性進行研究。
筆者建立輪齒載荷和輪齒變形的比值關系,研究發生點蝕時的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剛度,并其與有限元法結果進行對比,以驗證該方法的準確性;建立發生點蝕時雙漸開線與普通漸開線齒輪的動力學模型,在不同點蝕情況下,研究雙漸開線齒輪與普通漸開線齒輪動態嚙合力及振動加速度的時域變化規律。
1 齒輪點蝕動力學模型
齒面點蝕是齒輪傳動中常見的失效形式之一。點蝕可分為幾個階段。點蝕狀態分為均勻磨損、微點蝕、宏觀點蝕;宏觀點蝕又分為初期點蝕、擴展性點蝕、片蝕或剝落。
早期的點蝕多是由于嚙合初期齒面存在微小凸起,接觸時產生較大的應力,從而產生點蝕;在齒輪多次嚙合之后,多數均勻磨損變為微點蝕;在早期微點蝕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雙齒嚙合沖擊,在靠近節線的位置出現宏觀點蝕[13]。
雙漸開線齒輪基本齒廓如圖1所示。

圖1 雙漸開線齒輪基本齒廓
雙漸開線齒輪是以普通漸開線齒輪齒廓為基準齒廓,對齒根進行切向正變位,對齒頂進行切向負變位,其基本齒廓包括齒根過渡圓弧AB、齒根直線BC、半徑為ρg齒腰過渡圓弧CD、齒頂直線DE。
齒根過渡圓弧與齒根直線在B點相切,齒腰過渡圓弧CD與齒頂直線DE相切于D點、與直線BC相交于C點[14]。
為了更加直觀地分析齒輪嚙合過程,筆者將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平面沿基圓柱展開,考慮發生宏觀點蝕情況下,接觸線長度隨時間變化情況如圖2所示。

圖2 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平面沿基圓柱展開圖

考慮宏觀點蝕發生在節線靠近齒根附近,為5個沿齒面方向的圓形點蝕,在該工況下不同時刻的接觸線長度可表示為:
(1)

其中,tB2C=lB2C/rb1ω1,tB2P1=lB2P1/rb1ω1,tB2E=(lB2E-l_)/rb1ω1,tB2E1=(lB2E1-l_)/rb1ω1,并依次計算tB2X、tB2D1、tB2E3、tB2E4、tB2B1、tB2F、tB2G、tB2H。
為使研究方便,假設均勻分布的5個直徑為1 mm圓形點蝕坑,在這里設置的初期點蝕為5個沿齒向方向的點蝕坑,稱為點蝕1情況;齒輪經長時間嚙合初期點蝕變為沿齒向方向10個點蝕坑,稱為點蝕2情況;又經長時間嚙合,其在齒面沿齒向方向變為15個點蝕坑,稱為點蝕3情況。
3種齒面點蝕情況如圖3所示。

圖3 雙漸開線齒輪的不同點蝕情況
不同點蝕情況下的雙漸開線齒輪接觸線長度如圖4所示。

圖4 不同點蝕狀態下的雙漸開線齒輪接觸線長度
從圖4可以看出:在3種不同點蝕情況下,在主動輪齒進入嚙合時,雙漸開線齒輪單齒接觸線長度逐漸增大,其未受到點蝕坑影響出現突變;嚙合進行到齒腰分階位置時,接觸線長度因點蝕坑影響發生2次突變,接觸線長度減小;隨著嚙合的進行,主動輪進入嚙合向齒頂嚙合區移動,接觸線長度逐漸增大并在達到最大值后保持不變,此時點蝕情況最為嚴重,接觸線長度共發生3次突變;隨著輪齒退出嚙合,接觸線長度逐漸減小,期間未受點蝕坑影響,整個嚙合過程中接觸線長度共發生5次突變,這與數學模型變化一致;點蝕坑對接觸線長度的影響主要發生在主動輪輪齒進入嚙合時,在3種不同點蝕情況下,隨著點蝕坑數量的增加,接觸線長度突變值增大[15]。
2 點蝕情況下雙漸開線齒輪時變嚙合剛度
剛度激勵是指齒輪在嚙合過程中由于嚙合剛度的時變性而產生的動態激勵。作為齒輪系統內部激勵的重要激勵形式,剛度激勵對齒輪系統的動態性能有著很大的影響。
嚙合剛度可以用來表征輪齒抵抗變形的能力,通常將單齒抵抗變形的能力稱為單齒嚙合剛度,將參與嚙合的各對輪齒之間的綜合效應稱之為綜合嚙合剛度。綜合嚙合剛度與輪齒的綜合彈性變形、輪齒嚙合對數以及齒輪的材料等因素有關[16]。
筆者考慮點蝕情況發生時,點蝕坑對齒輪接觸線長度的影響,研究不同點蝕數量對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剛度的影響。
假設在齒輪嚙合過程中,輪齒上所受載荷在接觸線上呈均勻分布,并且輪齒變形也是沿接觸線方向呈均勻分布,則兩者的比值即嚙合剛度,可近似認為其只與接觸線的長度有關,并且呈正比關系,計算公式如下[17]:
kt=k0lt
(2)
式中:kt為時變嚙合剛度;lt為總接觸線長度;兩者均與時間有關,具有時變性;k0為比值系數。
由式(2)可知,嚙合剛度的時變性主要與接觸線的時變性有關,接觸線的時變性主要是由嚙合齒對的交替變化所致,三者的時變周期一致,都為輪齒的嚙合周期T。
根據ISO 6336—1:2006圓柱直齒輪和斜齒輪疲勞強度與彎曲強度計算國際標準,斜齒輪單齒嚙合剛度的最大值為:
(3)
式中:CM為理論修正系數,CM=0.8;CR為輪坯結構系數,CR=1;CB為基本齒廓系數,CB=1;β為齒輪螺旋角,β=8°6′34″。
(4)
(5)
齒輪嚙合剛度均值的計算公式為:
cγ=(0.75εα+0.25)c′
(6)
式中:εα為端面重合度。

不同點蝕情況下的雙漸開線齒輪時變嚙合剛度如圖5所示。

圖5 不同點蝕情況下的雙漸開線齒輪時變嚙合剛度
由圖5可知:輪齒嚙合期間,齒輪嚙合剛度隨著時間變化不斷增加,在點蝕1與點蝕2情況下,單齒嚙合剛度差別不大;相較點蝕1、點蝕2,點蝕3情況發生時,點蝕坑擴展至靠近齒根位置,單齒嚙合剛度明顯減小。
觀察齒輪嚙合時嚙合剛度的變化,可以發現點蝕坑增加,即輪齒在嚙合過程中接觸面積減小,導致齒輪嚙合剛度降低。
假設一對齒輪在節點均勻接觸,將齒輪接觸單位面積的法向載荷與輪齒齒面法向綜合變形量的比值稱為對輪齒的單齒嚙合剛度kf,公式為:
(7)
式中:Fn為齒面法向載荷;b為齒寬;δ為輪齒齒面法向綜合彈性變形。
齒輪從上一輪齒退出嚙合開始到下一輪齒進入嚙合的過程稱為一個嚙合周期,在此期間主動輪轉過的角度被稱為轉角,其值:φ=2π/z1。
筆者建立3種點蝕情況下的雙漸開線齒輪嚙合有限元模型,將每對齒輪20等分,生成21個不同角度的仿真模型,并進行瞬態動力學分析。
因為在ANSYS中提取各輪齒變形量存在誤差,且計算過程比較復雜,所以筆者采取一種快捷方法,首先提取主動輪的角變形量,利用公式求得齒輪的扭轉嚙合剛度,再根據扭轉嚙合剛度與嚙合剛度之間的比值關系求出齒輪的嚙合剛度。
齒輪扭轉嚙合剛度kt為:
(8)
式中:T1為主動輪輸入轉矩;Δθ為主動輪角變形量。
單齒嚙合剛度kn為:
(9)
筆者在齒輪中一個輪齒的齒面建立符合圖3的3種點蝕坑,將齒輪嚙合模型導入到ANSYS中的Transient Structural模塊,并進行仿真設置,求得雙漸開線齒輪主動輪的角變形量Δθ與嚙合剛度,如表1所示。

表1 雙漸開線齒輪有限元仿真數據
雙漸開線齒輪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圖6所示。

圖6 雙漸開線齒輪有限元分析模型
筆者將雙漸開線齒輪與普通漸開線斜齒輪在3種點蝕情況下的有限元仿真數據、雙漸開線齒輪接觸線長度計算的單齒嚙合剛度矩陣導入MATLAB軟件,對三組數據進行曲線擬合,得到兩種齒輪的單齒嚙合剛度,點蝕1、點蝕2、點蝕3情況,即雙漸開線-普通漸開線齒輪點蝕情況下單齒嚙合剛度對比情況,如圖7所示。

圖7 雙漸開線-普通漸開線齒輪點蝕情況下單齒嚙合剛度對比
由圖7可知:接觸線長度法與有限元法求解齒輪嚙合剛度的變化趨勢大體相同;點蝕情況發生時,兩齒輪嚙合剛度值均減小,隨著點蝕坑的增加,齒輪嚙合剛度變化明顯,接觸線長度法計算出的齒輪嚙合剛度大于有限元法計算出的剛度;點蝕1與點蝕2情況發生時,兩種方法計算的嚙合剛度變化趨勢相同,點蝕3情況發生時,點蝕坑的位置不斷向齒根位置靠近,有限元法求解的嚙合剛度小于接觸線長度計算的嚙合剛度。
對比雙漸開線齒輪與普通漸開線齒輪的嚙合剛度,在一個嚙合周期內其變化規律大致相同;在點蝕情況下,雙漸開線齒輪由于齒根增厚,其單齒嚙合剛度要大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剛度。
綜上所述,兩種方法計算齒輪的嚙合剛度總體變化趨勢相同,總體數值在同一量級,且均表現出點蝕情況下的齒輪嚙合剛度變化。
3 點蝕情況下雙漸開線齒輪動力學特性
在考慮點蝕的情況下,筆者建立同參數、同工況的雙漸開線齒輪與普通漸開線齒輪的柔性多體動力學模型,研究點蝕發生對兩齒輪動力學特性的影響。
雙漸開線齒輪齒面點蝕模型,即發生點蝕1、點蝕2、點蝕3情況的齒輪輪齒模型如圖8所示。

圖8 雙漸開線齒輪齒面點蝕模型
3.1 雙漸開線-普通漸開線齒輪傳動動態接觸力
筆者對同參數、同工況下的雙漸開線-普通漸開線齒輪進行動力學仿真分析(為防止啟動時轉速的突變,驅動與負載均采用Step漸進函數施加),綜合分析不同點蝕故障對齒輪動態嚙合力的影響。
點蝕1情況下齒輪動態嚙合力時域圖如圖9所示。

圖9 點蝕1情況下動態嚙合力時域圖對比
點蝕2情況下齒輪動態嚙合力時域圖如圖10所示。

圖10 點蝕2情況下動態嚙合力時域圖對比
點蝕3情況下齒輪動態嚙合力時域圖如圖11所示。

圖11 點蝕3情況下動態嚙合力時域圖對比
由圖9~圖11可以看出:隨著點蝕程度的不斷加深,雙漸開線齒輪與普通漸開線齒輪的嚙合力幅值波動越來越大,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力最大值1.24×105N,普通漸開線齒輪嚙合力最大值為1.01×106N,對比兩齒輪整體嚙合力均值與最大幅值,可發現普通漸開線齒輪在點蝕坑增加時,其嚙合力的變化范圍、嚙合力均值及增加值均大于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力的變化范圍、嚙合力均值及增加值。
綜上可知,點蝕常發生在節線靠近齒根位置時,由于雙漸開線齒輪齒腰的分階特點,齒根厚度大于普通漸開線齒輪,在點蝕發生時,其動態嚙合力最大幅值及均值小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動態嚙合力最大幅值及均值;點蝕情況下,雙漸開線齒輪抵抗嚙合沖擊的能力更強,承受動態沖擊的能力要優于普通漸開線。
3.2 雙漸開線-普通漸開線齒輪傳動振動角加速度
齒輪通過嚙合輪齒間的接觸來傳遞動力,齒面點蝕導致齒輪在傳動過程中產生振動沖擊,進而導致齒輪動態嚙合力幅值的波動。齒輪嚙合時,接觸力的變化會影響傳動過程中角速度、角加速度的波動。
筆者將根據不同點蝕情況分析雙漸開線與普通漸開線齒輪振動角加速度的變化情況。
點蝕1情況下從動輪角加速度時域圖對比如圖12所示。

圖12 點蝕1情況下從動輪角加速度時域圖對比
點蝕2情況下從動輪角加速度時域圖對比如圖13所示。

圖13 點蝕2情況下從動輪角加速度時域圖對比
點蝕3情況下從動輪角加速度時域圖對比如圖14所示。

圖14 點蝕3情況下從動輪角加速度時域圖對比
從圖12~圖14中可以看出:普通漸開線齒輪角加速度整體波動大、峰值高,最大值為3.012×107°/s2;雙漸開線齒輪在0~0.02 s內呈加速上升狀態,角加速度波動較穩定,最大值為2.66×106°/s2,不會產生過大的沖擊,速度變化整體優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速度變化;齒面點蝕由點蝕1擴展為點蝕3,兩齒輪的振動角加速度最大值均有所增加,雙漸開線齒輪振動角加速度的幅值變化小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幅值變化,角加速度幅值分布集中,未有較大突變值。
因此,點蝕發生時雙漸開線齒輪抵抗沖擊的能力較強,動力傳遞的穩定性優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穩定性,傳動過程較平穩。
4 結束語
筆者研究了雙漸開線齒輪不同點蝕情況下接觸線長度及時變嚙合剛度的變化規律,用有限元法驗證了接觸線長度計算嚙合剛度的準確性;建立了點蝕情況發生時雙漸開線與普通漸開線齒輪柔性多體動力學模型;分析了不同點蝕情況對兩齒輪動態嚙合力及振動加速度的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
1)點蝕發生時,雙漸開線齒輪輪齒進入嚙合后接觸線長度發生變化,在輪齒退出嚙合時接觸線長度不發生變化;
2)隨著點蝕程度的加深,兩種類型齒輪嚙合剛度均不斷減小,其中雙漸開線齒輪在點蝕影響下的嚙合剛度變化穩定,抵抗沖擊能力優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抗沖擊能力;
3)同工況條件下,隨著點蝕程度的加深,兩種類型齒輪動態嚙合力及振動角加速度幅值增加,雙漸開線齒輪嚙合力最大值為1.24×105N,角加速度最大值為2.66×106°/s2,普通漸開線齒輪嚙合力最大值為1.01×106N,角加速度最大值為3.012×107°/s2;可見,雙漸開線齒輪的加速度幅值波動較平緩,動力傳遞穩定性優于普通漸開線齒輪的穩定性。
筆者后續的研究方向為:1)不同工況下雙漸開線齒輪的齒面形貌,安裝誤差等的動力學特性;2)研究雙漸開線齒輪瞬態接觸下的齒面油膜壓力分布、摩擦因數等瞬態接觸特征量的提取方法,及其對動載荷的影響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