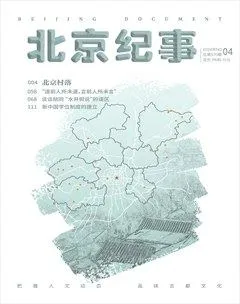“土城” 記憶
石建

北京北三環外的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是個獨特的公園,它的地理結構十分特殊,延綿十余公里,最寬處卻不過二百米,橫跨朝陽和海淀兩區,是京城最狹長的公園。它還集歷史遺跡保護、改善生態環境于一體 ,為市民提供了一個游春賞秋、健身休閑的好場所。這個公園惠及了周邊數十萬民眾的生活和休閑,而它原來的名字“土城”在人們的記憶里卻漸漸變得陌生了。
60年前,我就住在離土城不遠的北太平莊,而且就讀的小學就在土城的邊上。那時這一帶荒涼落寞,不僅雜草叢生、遍地荊棘,更是人煙稀少。可以用李清照“憶秦娥”來形容昔日土城的境況:“臨高閣。亂山平野煙光薄。煙光薄。棲鴉歸后,暮天聞角。斷香殘酒情懷惡。西風催襯梧桐落。梧桐落。又還秋色,又還寂寞。”
寂寞的土城上長滿了荊棘和酸棗樹,城墻周邊樹林茂密,里面有很多亂墳崗子。許是那個朝代戰亂頻發沒錢建造磚石的城墻,是用土壘起的,因此經不住歲月的侵蝕,幾百年間就徹底崩塌了,崩塌后的墻體形成高矮不一的小山,這就是“土城”名稱的由來。在土城腳下的小月河是原來的護城河,由于長久得不到疏通,土城上的土不斷坍塌進來,護城河只剩下小溪一般的涓涓細流。
當時的北京市政府已經提出了保護古都遺址土城,學校離得近,常組織我們到土城種樹、修路,因此“土城”不僅伴隨我度過了快樂的童年,也留下了它是亟待保護的歷史遺跡的記憶。
學校音樂教室的后窗外是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稻田里不知藏有多少青蛙,此起彼伏的蛙鳴如同演奏雄壯的田園交響曲,而那些蛐蟀、蟈蟈、秋蛉子也不甘示弱,它們的鳴叫清脆悅耳。稻田的北邊就是土城了,稻田里經常落著成群的鷺鷥,據說北京曾是鷺鷥的棲息地,如今很難再見到它們的身影了。鷺鷥長著長長的腿、尖尖的嘴,雪白的羽毛,姿態十分優美,時而落在水中覓食,時而飛上藍天繞著土城翱翔。此情此景讓我難忘,可惜我們的孩子再也見不到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景象了。
記得是在四五年級的時候,學校多次組織我們到土城植樹造林,并在樹林中開辟了一條土路。后來我去找當年種樹的地方,那里綠樹成蔭,合抱粗的參天大樹遮天蔽日,一群孩子在樹下盡情嬉戲,徜徉其中十分愜意。我突然想到一句老話:“前人種樹后人乘涼。”不禁從心底生出一絲滿足的笑意,我種的樹不僅后人乘涼,連我自己也享受其中,這大概應算是一種福報吧?只不知哪棵樹是我種的了。
我上小學的年代鼓勵大家養蠶,學校里很多同學都在養,養的人多了,桑葉成了問題,有錢也沒處買。有同學發現土城有幾棵桑樹,我們就利用中午吃飯休息的時間去采桑葉,誰想到這么荒涼的地方居然還有人居住,這家人養了一條很兇的大狗看著桑樹,狗見有人采桑葉就汪汪狂吠,要想采到桑葉,要冒被狗咬的風險,或是趁它睡著時。后來知道的人越來越多,這幾棵桑樹很快變得光禿禿的了。
從北太平莊往北到花園路,現在是一條熱鬧繁華的大道叫北太平莊路,這條路就是當年音樂教室外的那片稻田。現在成了通衢大道,道路兩旁聚集了不少大單位:有色金屬研究院、遠望樓賓館、牡丹電視機廠、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可能沒有多少人記得,沒修這條路之前,這里是以土城小月河上的一座小橋得名,叫牤牛橋,到上個世紀70年代,牤牛橋地區還是河溝港汊密布,人跡罕至,蘆葦和野草長得比人高的濕地。
我們的小學是鐵路子弟學校,班上的幾個同學住在一個樓里,每天一起上學、一起放學、一起寫作業,放學后互相串門玩耍,整日形影不離。有一天有個同學提議,每天放學從土城繞道回家,從小鍛煉體魄和意志,長大報效祖國,這個提議得到我們的一致同意。
于是,放學后我們幾個同學從花園路方向迎著夕陽登上土城。崎嶇不平的土城上有一條羊腸小道,走在上面,酸棗棵子的尖刺不斷撕扯著衣褲。不知從何年代土城開了很多豁口,便于行人通過。豁口處寬達幾米,斷面幾乎是直上直下的土墻,我們就從一個豁口拽著酸棗樹爬下去,再從另一個豁口處攀援上來,手上被酸棗刺扎破,腿上也刮出道道血口。走到黃亭子(現在叫薊門橋)往東向北太平莊的方向回家,這時太陽已經落在身后,天也黑了。這一圈對于孩子來說可不近了,大約要多走3至4公里的路。
“鍛煉”沒堅持幾天就終止了,每天回家這么晚,還渾身傷痕累累,家長很快就發現了我們的秘密。
因為土城太過荒涼,當時一般人家根本不敢讓孩子去土城玩,我們上述的行動自然驚動了家長,后來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大事,土城更沒人敢去了。
大約是1966年一個周六的晚上,土城邊上的解放軍“535”印刷廠在操場免費放映電影,周邊的孩子都去觀看。我們院有一個十來歲的男孩,當晚看完電影沒有回家,他平日很淘氣,家里也沒當回事,結果第二天在土城發現被人殘忍地殺害了。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陰影,以致很多年再也不敢去土城了。
看著“土城”一天天變得漂亮起來,既高興又感慨。它就像一串美麗的項鏈將京城北部諸多人文景色串聯起來,形成了北京最宜居、最美麗、最繁華、最有情調的地方。當年如此荒涼的地方如今成了繁花似錦的人間天堂,人們可以在公園里晨練、唱歌、遛鳥……享受著時代進步帶來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