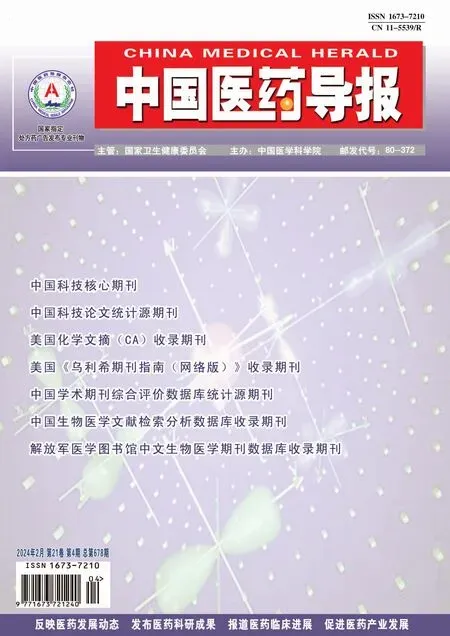胃癌干細胞表面標志物的研究進展
馬 嬌 鄭小影 張易青 趙慧珍 冶俊玲
1.青海大學臨床醫學院,青海西寧 810000;2.青海大學附屬醫院病理科,青海西寧 810000
據統計,胃癌(gastric cancer,GC)的發病居全球癌癥發病率的第五位,且其發病更趨于年輕化[1]。即使現已擁有先進的治療措施,但GC 根治后的復發率及轉移率仍然很高。直到推動實體腫瘤發生、發展、轉移及耐藥最相關的是腫瘤干細胞(cancer stem cell,CSC)這一觀點的提出。CSC 是一種具有自我更新、分化能力,啟動腫瘤生長及轉移潛能的獨特亞群[2];胃癌干細胞(gastric cancer stem cell,GCSC)亦是如此。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證據也說明包括GC 在內的多種實體腫瘤中存在由正常干細胞轉化而來的CSC,進而推動腫瘤的發生、發展、耐藥、復發及轉移[3-4]。現如今醫學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就是尋找靈敏度高、特異性強的分子標志物并探索其機制。本文就GCSC 表面標志物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GC 的靶向治療提供更多參考。
1 GCSC 表面標志物
傳統觀念認為,治療GC 的手段有手術切除及放化療等,但近年提出的假說將GCSC 作為治療GC 的靶點,從源頭消除腫瘤,切斷其復發、轉移的途徑,為GC 的診斷及治療提供了新的設想。CD44 是第一個被鑒定為具有GCSC 潛能的表面標志物,這一結果首次支持了GCSC 假說,也為GC 的診治打開了新思路[5]。相較于普通GC 細胞而言,GCSC 具有更強的侵襲、致癌及耐藥性,其擁有的遷移及血管形成能力更強,對于促進GC 的發展及轉移更加有利[6]。因此,探尋更新、更特異的GCSC 表面標志物,已成為新的研究趨勢。
1.1 CD44
CD44 是一種分布廣泛的多分子形式的膜整合蛋白,也是能夠介導細胞與基質、細胞間黏附性的黏附因子。有學者將CD44+GCSC 定義為具有啟動腫瘤生長和維持腫瘤自我更新能力的獨特亞群,且其具有更強的致瘤性及干細胞自我更新特性[5-7]。CD44 的變異亞型CD44v6 也可以預測GC 患者的預后和治療反應,CD44v6 增加了GC 細胞中順鉑處理的細胞存活率,CD44v6+表達的增加提示了GC 患者預后可能更差[8-9]。USP22 是泛素特異性蛋白水解酶的一員,Yang等[10]分離出具有CSC 特性的CD44+GC 細胞,構建出CD44+抗體偶聯的USP22 siRNA 納米脂質體,發現其可顯著抑制CD44+GCSC 的增殖和比例,且能夠選擇性靶向清除CD44+GCSC。表明針對CD44+的靶向治療將是GC 的有效方式。CD44 是最早發現、也是目前為止研究較為成熟、經典的GCSC 表面標志物,針對CD44 的變異異構體及其偶聯物質的靶向治療是目前研究的一大熱點。
1.2 CD133
CD133 抗原來自造血干細胞表面的一種5 次跨膜糖蛋白,是調控干細胞功能的關鍵分子。Ni 等[11]發現,CD133+/CD166+GC 細胞亞群具有CSC 特性。然而也有學者研究了CD133 在GC 及非腫瘤性正常胃黏膜中的表達,發現CD133+雖然可以在GC 細胞中檢測到,但其在組織學正常的胃黏膜中同樣表達[12]。因此,CD133 作為GCSC 的特異性標志物尚存爭議,其獨特的機制需進一步探究。
1.3 重復含G 蛋白偶聯受體5(recombinant leucine rich repeat containing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5,Lgr5)
Lgr5 富含亮氨酸,能夠增強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進而刺激CSC 自我更新及增殖[13]。Lgr5 在結直腸隱窩底部的柱狀細胞中高表達,并標志驅動腫瘤生長和轉移的結腸癌干細胞同樣在GC 中高表達[14]。Lgr5 在胃幽門腺中標記了具有自我更新的GCSC,通過Wnt 信號通路驅動了遠端GC 的形成[15]。此外,突變的Lgr5+細胞能夠促進浸潤性腸型GC 的生長和增殖,而敲除Lgr5+細胞能夠明顯抑制GC 的生長[16-17]。由此可見,Lgr5+細胞具有GCSC 樣特性,能夠作為GCSC 表面標志物,這意味著Lgr5+細胞可以作為GC治療的又一潛在靶點。
1.4 SOX2
SOX2,一種轉錄因子,是SOX 區域Y 蛋白家族成員之一,在胚胎發育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前,SOX2已被發現在肺癌、胰腺癌、乳腺癌及結腸癌等多種腫瘤中高表達[18];能夠調節腫瘤細胞的增殖、凋亡、侵襲、遷移及耐藥性,并通過維持腫瘤細胞的干性來調節腫瘤的進展和轉移[19]。SOX2 也在GC 等腫瘤中充當腫瘤抑制因子,其在GC 細胞中表達下調,通過誘導細胞周期停滯從而對GC 細胞產生抗增殖作用[20]。有實驗發現,Rho 鳥苷酸交換因子家族成員(FGD5)敲低抑制了GCSC 樣特征,確定了一種新型FGD5/SOX2軸,其與SOX2 蛋白相互作用,通過增強SOX2 蛋白穩定性發揮GCSC 樣特性[21]。總之,SOX2 有望成為GCSC標志物,但其在GC 中的調控機制還需進一步明確。
1.5 醛脫氫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ALDH)
ALDH 基因位于人類12 號染色體上,通過將維生素A 氧化為視黃酸,在干細胞的早期分化中發揮作用。近幾年逐步發現ALDH 除能夠調節自我更新、分化、擴增及耐藥性相關的細胞功能外,還可以富集來自腫瘤起始干細胞樣細胞中的腫瘤細胞群,它的表達與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的不良預后相關[22]。ALDH 的同工酶之一(ALDH1)是一種參與細胞分化和耐藥性的解毒酶,在正常細胞和CSC 中高表達。比如其在GC 中高表達,而GC 細胞的生長因ALDH1 表達的抑制而受到抑制,且有藥物通過抑制ALDH1 的表達來抑制GC 的生長和逆轉耐藥性[23]。其另一同工酶醛脫氫酶-3A1 在GCSC 樣細胞中高表達,且與GC 的異型增生、分化、分期及轉移密切相關[24]。因此,推測ALDH1+細胞及醛脫氫酶-3A1 具有干細胞潛能,ALDH 及其同工酶值得深入研究。
1.6 AQP5
AQP5 是一種跨膜水通道蛋白,能夠進行水分轉運、參與腺體分泌,可能影響腫瘤細胞的增殖及凋亡,促進腫瘤發生、發展[25]。Tan 等[26]發現,AQP5 在胃幽門腺基底部表達。此外,AQP5+GC 細胞可以在體外沒有外界因素刺激的情況下連續增殖,表明該細胞群含有潛在的GCSC,這一結果為AQP5 作為GCSC 標志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27]。
1.7 NME/NM23 核苷二磷酸激酶2(NME/NM23 nucleoside diphosphokinase 2,NME2)
NME 家族蛋白質由十種亞型構成,這些亞型參與了包括增殖、分化、發育等在內的多種生理病理過程[28]。其家族成員之一NME2 也被確定為一種潛在的腫瘤抑制因子,比如有學者證明了NME2 過表達減少了胃癌細胞向細胞基質的遷移和侵襲。因此,NME2的表達與胃癌分化良好且侵襲性較小的組織學表型相關,提示其可作為預測GC 侵襲性的潛在標志物[29]。也有學者發現,將NME2 敲除會導致GCSC 樣細胞的活力和數量顯著降低,致使細胞周期停滯在G1期,由此推測NME2 可以通過增強抗凋亡基因的表達維持GCSC 的特性[30]。那么NME2 是否可以作為GC 的潛在標志物,是否可以作為基因治療的潛在靶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2 總結及展望
本文綜述了不同GCSC 標志物的研究機制及現狀,隨著這些標志物逐漸被發現,將更快鎖定GCSC,進而得以從蛋白或基因方面分析GCSC 的表達機制,以期找到更好的治療靶點。目前,GC 的發病機制雖尚未闡明,但已報道的如CD44、CD133、Lgr5 等GCSC表面標志物,無疑為GC 的探究躍出了一大步。同樣,隨著對GCSC 相關信號通路機制愈深的探索,研究者們對GC 的發生、轉移、耐藥性及預后等相關研究已有較為深入的了解。比如一些分子及蛋白的上調或下調通過某信號通路對于GCSC 進行調控,或者一些藥物能夠通過阻斷或抑制信號通路的信號傳導,從而成為GC 診治的潛在靶點。總之,人們對GCSC 內外機制及細胞多能性的轉錄機制等還需更深入的研究。由于GCSC 標志物的復雜性及多樣性,在腫瘤中具體的調控機制還未明確,因此尋找抑制GCSC 相關標志物及其靶點藥物,以及尋找GC 診治的新方向、新思路,仍然是目前臨床醫生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重難點。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