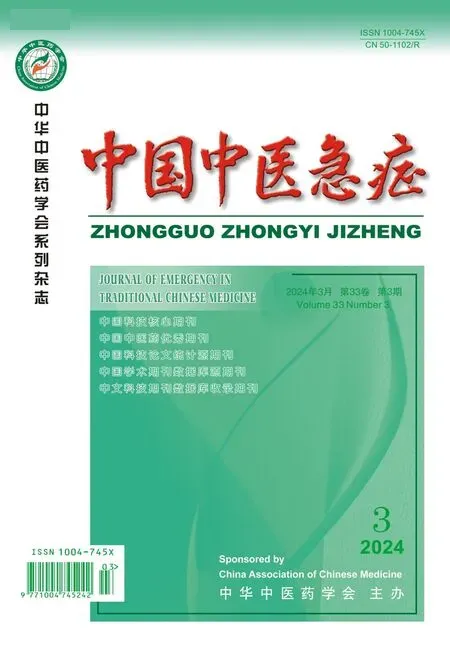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中醫證型分布及預后危險因素研究*
嚴文金 曹旺梅 范榮榮 周耿標 韓 云△
(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030;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廣東 廣州 510030;3.廣東省中醫院晁恩祥學術經驗傳承工作室,廣東 廣州 510145)
重癥肺炎是由肺組織(細支氣管、肺泡、間質)炎癥發展到一定疾病階段,惡化加重形成,引起器官功能障礙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1]。盡管重癥肺炎得到了早期識別和治療,但30 d 和1 年死亡率仍然很高(分別為27%、50%)[2]。隨著惡性腫瘤放化療、自身免疫性疾病診斷的增加及艾滋病發生率的升高和免疫抑制劑的使用率不斷增加,免疫缺陷患者也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罹患有肺炎風險的免疫缺陷患者的數量也在增加[3]。但既往開展的肺炎相關臨床研究,納入研究對象往往排除了這部分患者,而免疫缺陷并發肺炎的患者病情可能會迅速惡化,在幾小時內從輕癥肺炎發展為需要重癥監護的重癥肺炎[3],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已成為現代醫學危重癥治療領域的難點。
根據臨床癥狀,重癥肺炎歸屬于中醫學“暴喘”“肺炎喘嗽”“風溫肺熱病”等范疇[4]。目前中醫藥治療重癥肺炎已積累一定的經驗和優勢[5],但缺乏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的中醫證型、病原學特征及預后危險因素研究。本研究擬通過回顧性分析入住ICU 的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的中醫證型分布、病原學特征及預后危險因素,以期為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的辨證施治與預后提供臨床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對象及分組
采用回顧性分析方法,納入2021 年1 月至2022 年12 月在廣東省中醫院ICU 住院,且符合免疫缺陷標準的重癥肺炎患者,根據第28 天結局狀態分為生存組和死亡組。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2019 年版《美國胸科學會(ATS)/感染性疾病學會(IDSA)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治指南》[6]及《中國成人醫院獲得性肺炎與呼吸機相關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18 年版)》[7]相關診斷標準:1)醫院或社區發病;2)肺炎相關臨床表現:新近出現的咳嗽、咯痰或原有呼吸道疾病加重,伴或不伴膿痰、胸痛、呼吸困難及咯血;發熱;肺實變體征和/或聞及濕性啰音;外周血白細胞計數>10×109/L 或<4×109/L,伴或不伴細胞核左移;3)胸部影像學檢查顯示新出現的斑片狀浸潤影、葉或段實變影、磨玻璃影或間質性改變,伴或不伴有胸腔積液。符合及第1、3 條及第2條中任何1項,并除外肺結核、肺部腫瘤、非感染性肺間質性疾病、肺水腫、肺不張、肺栓塞、肺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癥及肺血管炎等后,可建立臨床診斷;其次符合重癥肺炎相關診斷標準:符合以下1 項主要標準或≥3項次要標準者確診為重癥肺炎。主要標準:1)需要氣管插管行機械通氣治療;2)膿毒癥休克經積極液體復蘇后仍需要血管活性藥物治療。次要標準:1)呼吸頻率≥30 次/min;2)PaO2/FiO2≤250 mmHg(1 mmHg ≈0.133 kPa);3)多肺葉浸潤;4)意識障礙和(或)定向障礙;5)血尿素氮≥7.14 mmol/L;6)收縮壓<90 mmHg 需要積極的液體復蘇。
1.2.2 免疫缺陷標準 根據2020 年《免疫缺陷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的初始治療策略共識聲明》[8]制定免疫缺陷標準:1)原發性免疫缺陷性疾病;2)活動性惡性腫瘤或惡性腫瘤1 年內合并CAP,除外局限性皮膚癌或早期癌癥(如Ⅰ期肺癌);3)癌癥接受化療;4)HIV 感染者CD4+T 淋巴細胞計數<200 個/μL,或百分比<14%;5)實體器官移植;6)造血干細胞移植;7)接受激素治療潑尼松20 mg,≥14 d 或累積劑量>600 mg(或等效劑量激素);8)接受生物免疫調節劑;9)接受改善病情的抗風濕藥或其他免疫抑制劑(如環孢素、環磷酰胺、羥氯喹、氨甲蝶呤)。
1.2.3 中醫辨證標準 參照《社區獲得性肺炎中醫診療指南(2018 修訂版)》[9]對于重癥肺炎的中醫辨證標準,將本病分為4 個證型。1)痰熱壅肺證:主癥為咳嗽,痰多,痰黃,痰白干黏,胸痛,舌質紅,舌苔黃、膩,脈滑、數。次癥為發熱,口渴,面紅,尿黃,大便干結,腹脹。2)痰濁阻肺證:主癥為咳嗽,氣短,痰多、白黏,舌苔膩。次癥為胃脘痞滿,納呆,食少,痰易咯出,泡沫痰,舌質淡,舌苔白,脈滑、弦滑。3)熱陷心包證:主癥為咳嗽甚則喘息、氣促,身熱夜甚,心煩不寐,神志異常,舌紅、絳,脈數、滑。次癥為高熱,大便干結,尿黃,脈細。4)邪陷正脫證:主癥為呼吸短促,氣短息弱,神志異常,面色蒼白,大汗淋漓,四肢厥冷,脈微、細、疾促。次癥為面色潮紅,身熱,煩躁,舌質淡、絳。
1.3 納入標準
1)臨床診斷符合重癥肺炎標準;2)符合免疫缺陷標準;3)2021 年1 月至2022 年12 月在廣東省中醫院ICU 住院治療;4)有關病原學、肺部影像學、血常規、血氣分析、呼吸支持方式等臨床資料完整的患者。
1.4 排除標準
1)臨床資料不完整的患者;2)年齡<18 歲的患者;3)ICU住院時間<24 h的患者;4)孕婦或哺乳期婦女。
1.5 研究方法
收集入住ICU 的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的基本信息及臨床觀察指標,分析患者中醫證型分布、臨床特征及預后危險因素。資料采集通過住院病歷系統、檢驗系統、臨床影像系統、DoCare 重癥監護臨床信息系統及電話隨訪獲得。中醫辨證分型由2 位副高及以上職稱的中醫或中西醫結合醫師分別獨立進行,如兩者辨證結果不一致,則指定由第3 名正高級中醫師進行判斷。
1.6 觀察指標
患者一般信息及入住ICU 24 h內輔助檢查指標,包括:性別、年齡、免疫功能缺陷診斷類型、重要基礎病史(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呼吸系疾病、肝膽系疾病、腎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肺炎患病環境、第28天生存狀態、中醫辨證分型、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評分系統Ⅱ(APACHEⅡ)、SOFA 評分、是否有創機械通氣、有創機械通氣時間、無創機械通氣時間、呼吸道病原學檢測結果、肺部影像學表現、白細胞計數(WBC)、中性粒細胞(NEUT)、淋巴細胞(LYM)、單核細胞(MONO)、血紅蛋白(Hb)、血小板(PLT)、C反應蛋白(CRP)、降鈣素原(PCT)、動脈血酸堿度(pH)、PaO2/FiO2比值、血乳酸(Lac)、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白蛋白(ALB)、球蛋白(GLB)、總膽紅素(TBIL)、尿素(Urea)、血肌酐(Cr)、估算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凝血酶原時間(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纖維蛋白原(FIB)、D-二聚體(DDi)、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FDP)。
1.7 統計學處理
2 結 果
2.1 研究對象一般信息
見表1、表2。本研究共納入104例患者,其中生存組有46 例(44.2%),死亡組有58 例(55.8%);男性71例,女性33 例,年齡19~93 歲。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患病環境、重要基礎疾病、免疫功能缺陷病史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年齡分布比較[M(P25,P75)]

表2 兩組一般信息比較[n(%)]
2.2 兩組中醫證型分布情況
見表3。研究納入的患者中,痰熱壅肺證32 例(30.8%),痰濁阻肺證32 例(30.8%),熱陷心包證15 例(14.4%),邪陷正脫證25例(24.0%)。兩組患者的中醫證型分布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兩組中醫證型分布比較[n(%)]
2.3 兩組肺部影像學表現情況
見表4。本研究納入的患者肺部影像表現以雙肺炎癥居多,少數患者同時伴有中-大量胸腔積液、肺淤血和(或)肺水腫等表現。兩組患者肺部影像表現分布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4 兩組肺部影像學表現分布比較[n(%)]
2.4 兩組肺部病原學分布情況比較
見表5。研究納入的患者中,細菌感染有67 例(64.4%),真菌感染有34 例(32.7%),病毒感染有13 例(12.5%)。其中,細菌感染以鮑曼不動桿菌、肺炎克雷伯菌、銅綠假單胞菌、嗜麥芽窄食單胞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為前5 種最常見的致病細菌;真菌感染以耶氏肺孢子菌、白念珠菌、熱帶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煙曲霉復合群為前5 種最常見的致病真菌;病毒感染以巨細胞病毒、EB病毒、細環病毒、人類皰疹病毒為最常見。

表5 兩組肺部病原體分布情況比較[n(%)]
2.5 兩組各項觀察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的觀察指標中,有創機械通氣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APACHEⅡ評分、SOFA 評分、pH、CRP、ALB、FIB 符合正態分布(P>0.05),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aO2/FiO2比值、ICU 住院天數、有創機械通氣時間、無創機械通氣時間、Lac、WBC、NEUT、LYM、MONO、Hb、PLT、ALT、AST、GLB、TBIL、Urea、Cr、eGFR、PT、APTT、DDi、FDP 不符合正態分布(P<0.05),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表6~表8 結果顯示:死亡組的有創機械通氣率、APACHE Ⅱ評分、SOFA 評分、Lac、ALT、AST、TBIL、Urea、PT、APTT、DDi、FDP 高于生存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的pH、CRP、ALB、FIB、PaO2/FiO2、有創機械通氣時間、無創機械通氣時間、WBC、NEUT、LYM、MONO、Hb、PLT、PCT、GLB、Cr、eGFR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6 兩組有創機械通氣情況比較[n(%)]
表7 兩組觀察指標比較(±s)

表7 兩組觀察指標比較(±s)
指標APACHEⅡ評分(分)SOFA評分(分)動脈血pH CRP(mg/L)ALB(g/L)FIB(g/L)生存組(n=46)24.09±7.17 7.43±4.30 7.41±0.08 117.79±85.71 30.26±5.50 4.85±1.93死亡組(n=58)32.10±10.23 10.17±4.16 7.39±0.09 134.64±77.22 29.71±5.30 4.51±2.00差值及95%CI-8.02(-11.41~-4.63)-2.74(-4.39~-1.08)0.02(-0.02~0.05)-16.31(-48.06~15.44)1.06(-1.56~2.66)0.39(-0.44~1.11)t值4.692 3.283 1.017 1.019 0.514 0.857 P值0.001 0.001 0.312 0.311 0.608 0.394

表8 兩組觀察指標比較[M(P25,P75)]
2.6 兩組28 d預后危險因素分析
見表9。在單因素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以第28 天結局狀態為因變量(生存=0,死亡=1),是否有創機械通氣、APACHEⅡ評分、SOFA 評分、Lac、ALT、AST、TBIL、Urea、PT、APTT、DDi、FDP 為自變量。結果顯示,APACHEⅡ評分對28 d 預后具有統計學意義[OR=1.132,95%CI(1.047-1.223),P<0.05];APTT 對28 d 預后具有統計學意義[OR=0.937,95%CI(0.886-0.991),P<0.05]。

表9 兩組28 d預后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 論
因腫瘤、血液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原發病以及化療、移植手術、服用糖皮質激素等醫療手段對正氣的損耗,免疫缺陷患者機體處于正氣虛損的狀態。肺為嬌臟,與外界相通,易受外邪的侵襲而發為“風溫”“肺熱病”等,即如《素問·評熱病論》所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10]。國醫大師晁恩祥教授主張“正氣虧虛、熱毒傷肺”為重癥肺炎的主要病機,正是機體正氣虛弱,御外作用減弱,使得邪氣外襲深入肺部乃至全身,致氣血、陰陽受損,發為此病,治療上強調扶正祛邪、補益正氣[11]。故而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的本虛標實病機貫穿始終,痰熱壅肺證、痰濁阻肺證、熱陷心包證以邪實為主,邪陷正脫證則是正氣虛脫為主。本研究顯示生存組與死亡組的中醫證型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各證型患者病情均可進展至正氣虛脫而引起死亡,亦有經積極救治正氣存續而存活者,這提示中醫藥治療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可能需要全程扶正,同時結合辨證論治佐以祛邪。
本研究納入的104 例患者病死率為55.8%,為既往研究免疫功能正常患者重癥肺炎病死率的2 倍左右[2,8],與顧瑩的研究結果一致[12],故入住ICU 的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有著高死亡率,應引起高度重視。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入院時24 h內APACHEⅡ評分、APTT 是28 d 預后獨立危險因素。APACHEⅡ評分、綜合急性生理評分、年齡評分與慢性健康評分多個生理指標,目前廣泛應用于ICU 危重患者的預后評估,既往的研究證實較高的APACHEⅡ評分是危重癥患者預后的危險因素[13]。本次研究顯示生存組與死亡組患者在年齡、慢性健康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合APACHEⅡ評分是預后獨立因素,且其中急性生理評分占比最大,進而考慮急性生理評分部分可能是患者預后的主要影響因素。近年來,重癥肺炎患者凝血功能紊亂受到廣泛關注。本研究結果顯示生存組與死亡組在PT、APTT、DDi、FDP 等凝血指標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APTT 是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與多項臨床研究[14-16]結果相符。
本研究結果顯示,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的肺部病原體方面,細菌感染居多,且約三分之一患者存在真菌感染,檢出的病原體同國際共識聲明[8]列舉的病原體較為相近。結合此類患者病情危重、死亡風險高的特點,應早期進行全面的微生物學檢查,以精準指導抗感染治療。
綜上所述,本研究納入的104 例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中,28 d 死亡率達55.8%;中醫辨證分型以痰熱阻肺證和痰濁阻肺證居多,但各證型預后無明顯差異,需注意患者證型的動態演變;檢出病原體種類數量較多,建議早期行全面微生物檢查指導抗感染治療;APACHEⅡ評分和APTT可作為預測患者預后的指標。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僅納入廣東省中醫院ICU 的重癥肺炎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樣本例數較小,且因病歷資料不完整,需剔除部分患者,也未能將T 淋巴細胞亞群、免疫6 項等反映免疫功能的指標作為觀察指標,部分統計結果的顯著性可能受樣本量的影響。期望未來開展高質量的前瞻性多中心大樣本研究,為免疫缺陷并發重癥肺炎患者的中西醫結合診治策略的制定提供高級別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