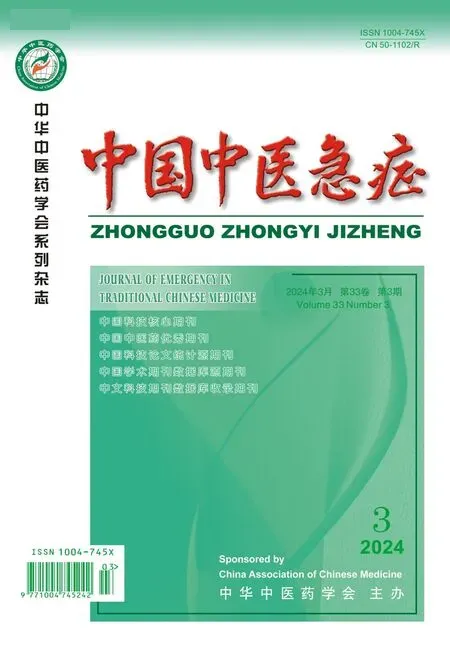溫針灸治療暴聾臨床觀察
徐海蓉 張 蕊 劉 瑜 曾雪花 陳凌杰
(1.中國中醫(yī)科學院廣安門醫(yī)院,北京 100053;2.陜西省精神衛(wèi)生中心,陜西 西安 710061;3.陜西省腫瘤醫(yī)院,陜西 西安 710000;4.福建省明溪縣總醫(yī)院,福建 明溪 365200;5.福建中醫(yī)藥大學附屬三明市中西醫(yī)結合醫(yī)院,福建 三明 365000)
暴聾又稱為“風聾”“卒聾”“厥聾”等病名[1],相當于現(xiàn)代醫(yī)學中所述之突發(fā)性耳聾(SD),又可稱之為感音神經(jīng)性聾,一般以短時間內(nèi)出現(xiàn)耳內(nèi)悶脹、聽力下降、頭暈頭痛等癥狀為主要癥狀,并以病因不明、發(fā)病急驟、進展迅速等為特點[2]。在我國其發(fā)生率受多方面社會因素影響,在60 歲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其發(fā)病率在30%左右,亦有逐年遞增且年輕化趨勢[3]。雖然SD 的發(fā)病機制尚未明確,但絕大多數(shù)的學者均認為其病因多與病毒感染、局部微循環(huán)障礙、免疫反應、膜迷路積水、情緒障礙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關[4-6]。SD 的治療以糖皮質激素、營養(yǎng)神經(jīng)、改善微循環(huán)等多種方法為主,雖然經(jīng)鼓室內(nèi)灌注激素類藥物的療效相對確切,但依然存在長期應用導致患者血糖升高、骨質疏松、消化性潰瘍等多種副作用,同時在伴有多種基礎性疾病患者的臨床應用上受一定程度限制[7]。隨著中醫(yī)、中藥、針刺等研究與應用不斷深入,針灸治療SD 的效果顯著[8-10]。本研究選用溫針灸治療暴聾(氣滯血瘀證)患者,并觀察患者治療前后的癥狀變化,從而為臨床應用提供依據(jù)。現(xiàn)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診斷標準:符合《突發(fā)性耳聾診斷和治療指南(2015)》[11]對SD 的診斷標準;符合《中醫(y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12]對暴聾(氣滯血瘀證)的診斷標準。2)納入標準:符合上述標準;有相關體格、聽力學、影像學等檢測結果支持;病程<72 h;最少2 個相鄰頻率的下降程度大于20 dBHL;年齡>18 歲,且<70 歲;神志清楚;自主簽署《知情同意書》。3)排除標準:能夠影響正常聽力的疾病者;存在嚴重的臟器功能障礙,且無法逆轉者;內(nèi)耳道或腦內(nèi)存在占位病變者;存在糖皮質激素過敏史或禁忌證者;施術局部皮膚破損者;未完成全部治療,或發(fā)生嚴重不良反應者。
1.2 臨床資料 選擇2021 年1 月至2022 年12 月筆者所在醫(yī)院治療的SD 患者總計74 例,按隨機數(shù)字表法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37 例,兩組臨床情況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本研究經(jīng)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表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
1.3 治療方法 1)對照組:參考文獻[11]進行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給予患者醋酸潑尼松片(天津力生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chǎn),國藥準字H12020123,規(guī)格為5 mg×100片),每天1 mg/kg,最大劑量60 mg,晨起頓服,每日1次,連續(xù)治療3 d;銀杏葉提取物注射液(悅康藥業(yè)集團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70226,規(guī)格為5 mL∶17.5 mg×10支)10 mL劑量溶于0.9%的氯化鈉注射液250 mL之中,靜脈滴注,每日1 次,連續(xù)治療14 d。2)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溫針灸療法。穴位選擇聽宮、聽會、翳風、耳門為主穴,交替選用。再以外關、合谷、足三里、三陰交、太沖為輔穴,對主穴采用瀉法,對輔穴采用平補平瀉法,留針20 min,且在主穴與足三里穴、三陰交穴上使用溫針灸,小艾粒點燃后將其置于針柄處,溫度不宜過高,以施術部位局部皮膚潮紅為度,每日1次。兩組以5 d為1個療程,需3個療程。
1.4 觀察指標 1)中醫(yī)證候評分[13]。以聽力減退、耳鳴、眩暈、耳悶脹感、局部疼痛、舌質暗紅為基礎癥狀,并按照病情的嚴重程度由輕至重分為4 個等級,分別計為0 分、2 分、4 分、6 分,評分范圍在0~36 分,所得分數(shù)越低表示患者中醫(yī)證候越輕。2)純音聽閾(PTA)測試[14]。給予受試者氣導耳機,由健側開始,依次進行1 000 Hz、2 000 Hz、4 000 Hz、8 000 Hz、250 Hz、500 Hz、1 000 Hz,雙耳氣導之差大于40 dB,需掩蔽操作后進行骨導測試,依然從1 000 Hz開始,若氣導與骨導之差大于10 dB,依然需進行掩蔽操作,最后讀取純音聽閾測試結果。3)血液流變學指標。采用血液流變學全自動測定儀檢測,其中包括全血黏度高切(WBV-H)、全血黏度低切(WBV-L)、紅細胞比容(HCT)等。4)凝血功能指標。采用免疫比濁法檢測,其中包括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凝血酶時間(TT)、血漿凝血酶原時間(PT)。
1.5 療效標準 痊愈:癥狀與陽性體征完全消失,受損的聽閾值恢復正常。顯效:癥狀與體征明顯緩解,受損的聽閾值恢復≥30 dB。有效:癥狀與體征有所改善,受損的聽閾值恢復≥15 dB,且<30 dB。無效:癥狀與體征無變化,甚或加重,受損的聽閾值恢復<15 dB[15]。
1.6 統(tǒng)計學處理 應用SPSS22.0 統(tǒng)計軟件。計量資料以(±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shù)資料以“n、%”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不同時間多項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法進行比較。P<0.05 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評分與PTA 值比較 見表2。與對照組相比,完成每個療程的治療時,觀察組的中醫(yī)證候評分與PTA 值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P<0.05);同時兩組比較的干預主效應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其時間主效應差異亦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提示各項評分隨時間推移而降低,且干預因素與時間因素存在交互作用(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評分與PTA值比較(±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評分與PTA值比較(±s)
注:與對照組同時期比較,△P <0.05。
組 別觀察組(n=37)對照組(n=37)PTA值(dBHL)49.91±7.71 39.73±6.21△32.16±5.39△25.79±5.31△50.14±7.83 43.42±6.55 37.63±5.69 31.91±5.58時間治療前第1療程第2療程第3療程治療前第1療程第2療程第3療程中醫(yī)證候評分(分)25.13±4.57 15.06±2.14△10.59±1.58△5.15±0.48△24.92±4.73 18.67±2.39 14.12±1.75 9.52±1.14
2.2 兩組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指標比較 見表3。治療前相比,兩組WBV-H、WBV-L、HCT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0.05);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的降低程度更為顯著(P<0.05)。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指標比較(±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指標比較(±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 <0.05;與對照組同時期比較,△P <0.05。下同。
組 別觀察組(n=37)對照組(n=37)時間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WBV-H(mPa·s)7.51±2.42 3.72±1.29*△7.25±2.43 4.83±1.71*WBV-L(mPa·s)18.23±4.28 8.75±2.31*△17.91±4.46 11.19±3.82*HCT(%)55.71±6.54 38.78±4.46*△56.13±6.59 44.92±5.71*
2.3 兩組治療前后凝血功能指標比較 見表4。與治療前相比,兩組APTT、TT、PT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P<0.05);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的提高程度更為顯著(P<0.05)。
表4 兩組治療前后凝血功能指標比較(±s)

表4 兩組治療前后凝血功能指標比較(±s)
組 別觀察組(n=37)對照組(n=37)時間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APTT 37.42±4.31 52.53±6.52*△37.29±4.36 42.19±5.44*TT 10.72±2.29 16.83±2.95*△10.96±2.37 13.37±2.61*PT 12.63±2.43 19.27±3.14*△12.79±2.55 16.04±2.88*
2.4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5。觀察組總有效率與痊愈率較對照組高(P<0.05)。

表5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3 討 論
暴聾最早見于《素問·厥論篇》之中,曰“少陽之厥,則暴聾”。其病因多與肝膽疏泄不利相關,在《針灸甲乙經(jīng)·卷十二》《備急千金藥方·卷六下》《太平圣惠方·卷三十六》等古籍均有記錄,在“風聾”“卒聾”“厥聾”等范疇內(nèi)均存在與之相關的描述,其中以暴聾(氣滯血瘀證)與SD 的描述最接近[1]。雖然暴聾(氣滯血瘀證)在病因分類上應歸類于“外因”的范疇,多因外感風熱邪毒經(jīng)患者口鼻而入,直接侵襲肝膽之經(jīng)脈,氣血壅滯于局部,閉塞關竅而最終發(fā)為本病。但在臨床實際的治療過程中,絕大多數(shù)臨床就診患者均存在一定的體虛基礎,有多種氣血陰陽虧虛之“內(nèi)因”,因此治法既要以行氣活血之法疏通經(jīng)絡,又要以補虛強壯之法鼓邪外出。
在穴位的選擇上,以聽宮、聽會、翳風、耳門為主穴,以外關、合谷、足三里、三陰交、太沖為輔穴。其中聽宮屬于手太陽經(jīng),并與手足少陽經(jīng)相交,是治療耳疾的常用之穴,聽會屬于足少陽經(jīng),是治療耳疾常用之穴,翳風與耳門均屬于手少陽經(jīng),兩穴配合共治耳鳴、耳聾、眩暈等諸多病癥,能夠起到生清降濁、聰耳通竅、散內(nèi)泄熱等諸多作用;外關屬于三焦經(jīng),是治療五官科疾患常用之穴,同時善于治療熱性疾病,合谷屬于大腸經(jīng),是治療熱病、耳聾、頭痛等諸多癥狀的常用之穴,足三里與三陰交,前者屬于胃經(jīng),后者屬于脾經(jīng),兩穴配合以達健脾和胃、調暢氣機、疏經(jīng)通絡等作用,且臨床中常以兩穴配合來達到引導上焦之熱下行之力;太沖屬于肝經(jīng),是治療頭痛、眩暈、耳鳴等諸多病癥的常用之穴,以起到平肝息風、清熱利濕、通絡止痛等功效;上述諸穴遠近配合,以達行氣活血、疏肝清熱、調肝理脾之效[16]。溫針灸療法與普通針刺療法相比,不僅能夠增強針刺部位的針刺作用,而且能夠起到顯著的行氣活血、疏經(jīng)通絡、散寒燥濕之效,此種功效對于局部氣血停聚所引發(fā)的疾病療效顯著,能夠有效抑制局部的炎性反應,達到抗炎、鎮(zhèn)痛、改善局部血液循環(huán)等目的[17-18]。
中醫(yī)證候評分與PTA值可全面評價患者聽覺能力的整體情況。本次研究兩組中醫(yī)證候評分、PTA 值均較治療前改善,觀察組改善程度更顯著,且臨床療效顯示觀察組的總有效率與痊愈率更高,提示中西醫(yī)結合治療方案能夠有效改善SD 患者的臨床癥狀。凝血功能指標APTT、TT、PT,血液流變學指標WBV-H、WBVL、HCT 與SD 的存在與進展有一定相關性。本次研究兩組血液流變學指標較治療前均有降低,且觀察組的降低更為顯著,提示中西醫(yī)結合治療方案能夠明顯改善SD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狀態(tài)。
綜上所述,采用溫針灸療法的觀察組,在各療程中醫(yī)證候評分、PTA值、凝血功能指標、血液流變學指標、臨床療效的比較上,均優(yōu)于對照組,提示中西醫(yī)結合溫針灸的治療方案能改善SD患者聽覺異常,同時可改變患者凝血功能與血液流變學指標異常,值得臨床推廣。但本次研究依然存在單中心低樣本量、缺乏遠期數(shù)據(jù)觀察等問題,仍需在今后的研究中繼續(xù)擴大樣本量,進行量、時、效等問題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