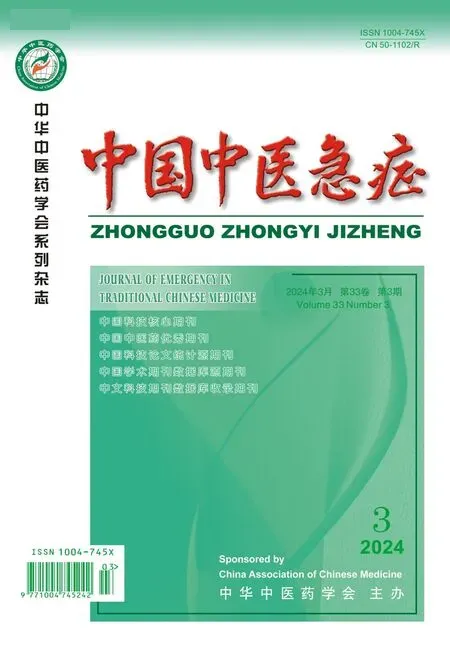清腸飲加味聯合美沙拉嗪治療活動期潰瘍性結腸炎(大腸濕熱證)的療效觀察*
陳敬博 厲 馨 王 雯 曾斌芳
(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1;2.新疆醫科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1)
潰瘍性結腸炎(UC)是一種非特異性的炎癥性腸病,患者癥狀主要表現為腹痛、腹瀉以及膿血便等,臨床治療困難大,病程周期長,易復發,且存在癌變風險[1]。UC 的病機紛繁復雜,臨床仍缺乏可治愈療法,美沙拉嗪為其常用治療藥物,可顯著抑制腸黏膜的炎癥反應,減輕癥狀體征,然而長期使用可誘發較多的不良反應,甚至導致肝炎[2]。中醫治療UC 的效果確切,尤其是應用中西醫結合療法可取長補短,發揮各自優勢,提高UC 的療效及患者的臨床預后[3]。UC 在中醫學中歸屬“痢疾”范疇,基本病性證素包括濕、熱、氣虛、氣滯、血瘀等,以濕、熱為主,在急性期以大腸濕熱證常見[4]。據此,中醫治療UC 常采取清熱化濕、調氣和血為主的治法。清腸飲是具有清熱化濕、消積導滯、調和氣血的功效。本研究探討了清腸飲加味聯合美沙拉嗪對活動期UC(大腸濕熱證)患者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西醫診斷標準:根據炎癥性腸病診療共識[5],并結合鏡檢與病理性檢查擬定。2)中醫辨證標準:大腸濕熱證辨證標準依據UC 中西醫診療共識[6]。主癥:腹瀉黏液膿血便、腹痛、里急后重。次癥:肛門灼熱、身熱不揚、口干口苦;小便短赤,舌質紅苔黃膩,脈滑數。3)納入標準:滿足上述相關診斷條件;輕中度活動期UC;年齡18~70 歲;無腸管手術史;自愿受試及簽訂同意書。4)排除標準:存在其他類型腸道疾病者;存在全身性感染疾病者;(準備)妊娠、哺乳期者;對本組受試藥物過敏者;合并嚴重基礎疾病或惡性腫瘤者。
1.2 臨床資料 選擇2021 年6 月至2023 年6 月我院確診的UC(大腸濕熱證)患者88 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44例。觀察組男性19例,女性25 例;年齡33~65 歲,平均(44.09±4.90)歲;UC 病程4~13 d,平均(7.04±0.79)d;UC 類型[5]為初發30 例,復發14 例;UC 嚴重分級[5]為輕17 例,中27 例;病變范圍為左半結腸18 例,廣泛結腸26 例。對照組男性22 例,女性22 例;年齡34~64 歲,平均(44.14±5.34)歲;UC 病程4~12 d,平均(7.11±0.82)d;UC 類型[5]為初發28 例,復發16 例;UC 嚴重分級[5]為輕19 例,中25 例;病變范圍為左半結腸20例,廣泛結腸24例。兩組臨床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兩組UC 病例參考診療共識[5]予常規措施,如優化調節、營養支持以及對癥補液和糾正電解質紊亂等。對照組予美沙拉嗪緩釋顆粒劑(上海愛的發制藥,批號14200623779,規格:0.5 g/袋),每次1 g,每日3 次。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予清腸飲加味治療,組成:葛根9 g,黃芩12 g,焦檳榔12 g,白芍9 g,藿香15 g,黃連12 g,木香9 g,生甘草6 g,炮姜3 g,車前草15 g,大黃9 g,當歸6 g。每日1 劑,本院中藥房代煎,分裝2袋,每日服2次。兩組療程均為2周。
1.4 觀察指標 1)Sutherland 疾病活動指數(DAI)[7]:治療前后對腹瀉、出血、腸黏膜病變進行評價,按正常、輕、中、重記為0、1、2、3 分。總評分12 分,≤2 分為癥狀緩解;3~5分為輕度活動;6~10分為中度活動;11~12分為重度活動。2)腹痛改善情況[6]:治療前后以視覺模擬量表(VAS)評定,0~10 分,得分越高,疼痛越嚴重。3)生活質量改善情況[6]:治療前后以炎癥性腸病問卷(IBDQ)評定,包括生活腸道癥狀(10 條目)、全身癥狀(5條目)、情感能力(12條目)、社會能力(5條目),每個條目均按7等級分級記1~7分,總評分32~224分,得分越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改善更優。
1.5 療效標準[7]治愈:患者癥狀基本消除,療效指數95%及以上。顯效:患者癥狀顯著好轉,療效指數70%及以上但未達治愈標準。好轉:患者癥狀有一定好轉,療效指數30%及以上但未達顯著標準。未愈:患者癥狀未見好轉,療效指數30%以下。療效指數=(治療前DAI 評分-治療后DAI 評分)÷治療前DAI 評分×100%。總有效率采取治愈、顯效、好轉進行統計。
1.6 統計學處理應用SPSS21.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s)表示,行t檢驗;計數資料以“n、%”表示,對比行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1。治療后,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總有效率明顯提升(P<0.05)。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2.2 兩組治療前后DAI 評分比較 見表2。治療后,兩組病例DAI 評分顯著下降,且與對照組病例同時點相比觀察組分別下降更明顯(均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后DAI評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DAI評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 <0.05;與對照組同時點比較,△P <0.05。下同。
治療2周1.79±0.26*△2.55±0.34*組 別觀察組對照組n 44 44治療前8.31±0.94 8.18±0.92治療1周4.30±0.52*△6.22±0.71*
2.3 兩組治療前后VAS 評分比較 見表3。治療后,兩組病例VAS 評分顯著降低,且觀察組病例降低更明顯(P<0.05)。
表3 兩組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分,±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分,±s)
組 別觀察組對照組n 44 44治療前6.14±0.69 6.06±0.68治療1周3.16±0.40*△4.43±0.53*治療2周1.81±0.27*△2.39±0.33*
2.4 兩組治療前后IBDQ 評分比較 見表4。治療后,兩組病例IBDQ評分顯著升高,且觀察組病例升高更明顯(P<0.05)。
表4 兩組治療前后IBDQ評分比較(分,±s)

表4 兩組治療前后IBDQ評分比較(分,±s)
組 別觀察組對照組n 44 44治療前81.49±9.03 81.63±9.06治療1周136.04±15.93*△122.03±14.03*治療2周171.46±18.93*△155.41±17.09*
3 討 論
UC的病因復雜,涉及先天遺傳、生存環境、飲食偏嗜、心理情緒異常等,已知的發病機制有基因、腸道菌群紊亂、免疫損害、機體高凝狀態、腸上皮細胞凋亡、細胞自噬-伏毒-UC以及毒損腸絡等[8]。故探尋UC的多靶點及安全可靠的治療措施或藥物已成為臨床亟待解決的醫學問題,而中醫藥憑借多環節、多層次、多靶點的防治優勢,其對UC 的綜合治療也獲得較廣泛認可[9]。UC 的中醫病因復雜,如先天稟賦、外感邪氣、內傷飲食、情志所傷、藥物濫用等,均可損及太陰脾經,以致濕邪內生,濕聚成熱,內侵腸道,濕熱蘊蒸,損傷大腸脂膜血絡,并與氣血相搏結于腸腑脂膜,內潰成瘍,導致本病[10-11]。《丹溪心法》中述“赤痢……白痢……皆濕熱為本”。因此,中醫治療UC建議采取清熱化濕、調氣和血作為治法。
清腸飲加味方以葛根、藿香合用,起到疏肌達表、宣化濕濁的作用;黃芩、黃連合用可清熱燥濕。木香、焦檳榔疏利腑氣、消積導滯;白芍養血和營、緩急止痛,配以當歸養血活血,體現了“行血則便膿自愈”之義,且可兼顧濕熱邪毒熏灼腸絡,傷耗陰血之慮;大黃苦寒沉降,合黃芩、黃連則清熱燥濕之功著,合當歸、白芍則活血行氣之力彰,其瀉下通腑作用可通導濕熱積滯從大便而去,體現“通因通用”之法;車前草分化濕熱;炮姜佐黃芩、黃連,可寒熱并治、防苦寒傷胃;生甘草補脾,調和諸藥。全方合用,使濕去熱清、氣血調和,從而諸癥自悉。
本組數據顯示,與對照組相比,治療后觀察組病例的總有效率明顯提升(P<0.05);治療后,兩組DAI 評分、VAS評分顯著下降、IBDQ 評分顯著升高,且與對照組同時點相比,觀察組改善更明顯(P<0.05)。藥理學研究證實,清腸飲加味方中主藥葛根提取物能減少結腸黏膜巨噬細胞浸潤,減輕結腸黏膜炎癥因子所引起的反應[12];藿香活性成分藿香醇具有抗炎、抗消化道潰瘍、預防結腸炎、抗氧化應激等作用[13];黃芩苷具有抗炎、調節免疫、抗氧化等作用,通過調節免疫細胞、免疫活性因子、信號通路等途徑治療炎癥性腸病[14];小檗堿通過調節腸道平滑肌鈣通道、穩定腸道微生態、抑制腸道炎癥、調節膽汁酸吸收等途徑參與腸道保護,緩解腸道炎癥反應[15]。
綜上,清腸飲加味聯合美沙拉嗪對活動期UC(大腸濕熱證)患者的療效顯著,有利于病情的控制,減輕疼痛,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是治療UC 的有效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