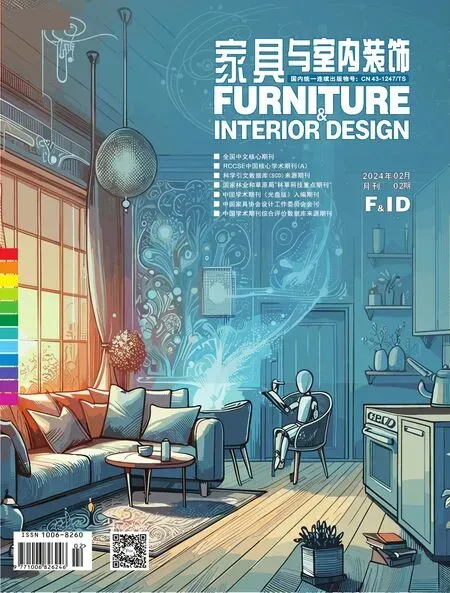維特根斯坦哲學視角下的商周青銅器紋飾研究
■齊秀芝,賀雪梅
商周青銅器紋飾充滿獰厲的美,長鼻、雙目圓瞪、卷角的獸面紋;尖鉤喙、長冠羽,逶迤尾羽的鳳鳥紋,云雷紋為底,三層花裝飾和沖出器表的浮雕詮釋出多重內涵,從哲學符號學角度分析青銅器紋飾的邏輯結構及符號意義的嬗變過程,能豐富符號學在商周文化和考古學中的實踐表達。
1 符號學理論引入與青銅器紋飾的社會意義
索緒爾和皮爾斯是當代兩大符號學理論的代表,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符號展開研究[1]。索緒爾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和結構性[2],突出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任意性。符號的意指過程形成不同層次的語言結構,表達世界上的各種意義。皮爾斯基于實用主義哲學、范疇論和邏輯學,認為符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整體,從感情符號到邏輯符號,永無止境[3]。他提出了“符號三元關系”論,強調符號活動是人類認知的過程。相較之下,維特根斯坦是重要的哲學家和數理邏輯學家,側重符號系統的原則和語言中詞與事物關系的重要性。他的觀點適用于研究古代器物符號邏輯結構。
符號學理論能夠解釋社會儀式。比如,商代以來,祭祀一直是國家的重要儀式,《禮記》指出商人尊崇神明,率領民眾奉獻祭品。青銅禮器在幫助巫覡通神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九鼎成為象征合法王權和天命的神圣物品,通過祭祀成為王權權威的象征。在西周時期,青銅器不僅是祭祀的供品,還演變成權力和社會等級的標志。青銅器成為家族祭祀、日常宴飲和墓室陪葬的必備之物,突顯使用者在社會身份和地位中的象征意義。青銅器紋飾與祭祀緊密相連,作為“犧牲之物”和“彝器之量”的結合體,它的任務是輔助巫覡溝通天地,協調人與神的關系。在祭祀中,青銅器不僅僅是實用物品,更是承載著天命授達精神意義的物質載體。
本研究將從維特根斯坦的符號學理論入手,梳理青銅器紋飾的邏輯結構,解讀其符號學關系及發展。
2 維特根斯坦哲學與青銅器圖像符號分析
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不僅有邏輯目的,更追求實踐,即“觀看”人類問題的本質[4]。青銅器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代表物質文化。研究者從哲學視角分析青銅器,剖析其歷史“語境”。維特根斯坦強調有意義的詞與使用規則緊密相關,而青銅器分為禮器、容器、兵器、樂器,各有不同的使用規則和場景。商代的鼎代表國家王權,周代的鼎反映社會等級秩序。紋飾作為圖像在社會環境中存在,其構成法則反映了社會等級劃分的規則。維特根斯坦的圖像和邏輯理論與青銅器紋飾的層級有對應關系,有助于揭示其邏輯結構。這一哲學視角深化了我們對青銅器及其文化意義的理解。
青銅器是中國傳統藝術的代表,其紋飾是多層次、復雜的文化符號。早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多與石器時代的绹紋有關,但隨著王朝的建立、宗教巫術的發展和禮制的強化,發生了美學風格質的變化[5]。藝術成為歷史的媒介和載體時,圖像母題不再是獨立發展的個體,而是一個涵蓋所有元素的綜合體[6]。母題最早源于英文“motif”,吳光正先生認為母題是民間文學中反復出現的最小敘事單元[7],可在不同文體中重復或復制,構成新的主題。母題不僅存在于文學,考古和藝術中也有提及。基本元素如圓形、三角形構成藝術形態,如圖1、圖2所示寶雞竹園溝墓地出土的圓鼎BZM4:77,展示了西周早期的典型圓鼎器型,以弦紋、乳釘紋為代表,抽象的圓形、直線成為主要裝飾元素。

■圖1 圓鼎 BZM4:77線圖

■圖2 圓鼎 BZM4:77
1972年岐山縣京當村出土的窖藏云紋分襠鬲,屬于商代前期,如圖3所示紋飾拓片,頸部飾一周以連珠紋為界隔的雷紋,連珠紋是由單個圓圈排列構成,雷紋是由最簡單的曲線反復構成的。圓圈和單組雷紋屬于母題的基本形式,后來在時間的演化中變化出眾多如饕餮紋等復雜紋飾。

■圖3 云紋分襠鬲(IA.104)紋飾拓片
“原型”源于母題與主題在紋飾發展中的溯源。符號邏輯理論揭示了母題的原發性,形成了“原型”,在歷時發展中演化為多個相似的母題。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共識母題不斷吸收新元素演變,成為融入新元素的母題或母題群。這些融入新元素的母題在不同時期作為主題表達,具有研究意義的母題與主題必須是歷時持久的。鳳鳥紋是青銅器中典型的紋飾,與盤古開天辟地的傳說有關。東周時期的元素如采桑、射侯、宴樂按照一定結構組合形成內涵豐富的主題。圖像中的母題以一定結構組合形成隱喻,成為文本或圖像主題的基礎,具備敘事性主題。青銅器紋飾母題運用陰陽結構關系,對空間的把握呈現虛實結構。不同時代、地域的青銅器呈現出不同的主題和母題變遷。藝術通過對母題的價值判斷傳遞主題的闡釋,達到對某種思想高度的認知。母題與主題之間存在因果聯系,在考察源流中追蹤它們的演變關系和淵源,青銅器紋飾邏輯層級分為原型、母題、母題群和主題。
■圖像的意義在歷史語境中生成,存在于歷史主體的觀念和行為中。圖形的意義是歷史主題在人的理解和解釋中生成和流動的結果。青銅器紋飾作為圖像和宗教觀念的物化形態,其意義隨時代和文化變化而演變,反映不同時期、族群的文化認知方式。中國傳統造物藝術中的圖案,如饕餮紋、花紋、鳥紋等,具有歷時性譜系特征[8]。商周社會文化主題下存在青銅器紋飾演變的主題譜系,其中近似的母題可能源自同一原型。在商代和周代,不同統治者運用母題呈現出與原型的差異,甚至出現了借用相同母題表達不同意義的主題,構成了青銅器造型和紋飾變遷的重要原因。通過紋飾的演變,可以窺視青銅器紋飾圖形變遷的因果關系和史學規律。
3 青銅器紋飾的歷史、文化與語義綜合分析
3.1 歷史與文化語境的結合
在商代,青銅器作為禮器廣泛用于祭祀和宗教儀式,政治結構以王室為核心,青銅器上的紋飾如饕餮紋、龍紋體現了王權威嚴。
西周時期,政治變革導致青銅器紋飾演變為以鳳鳥紋為主,反映時代變遷和統治者理念。青銅器在政治上彰顯統治者威嚴和地位,在宗教上連接人與神明。紋飾如獸面紋反映社會對神靈的崇拜,而鳳鳥紋則代表對祥瑞和權力象征的追求。
青銅器在宗教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紋飾不僅是裝飾品,更是宗教儀式和信仰的表達。文化符號延伸體現在青銅器紋飾的多樣性和變化上,以及其社會功能中。商周青銅器歷史與文化語境的結合揭示了其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和文化內涵,通過多樣紋飾和社會功能傳達了當時社會的價值觀、信仰體系和審美取向。
3.2 語義分析拓展
商周青銅器的紋飾是連接古代文化和觀念的橋梁,深刻的語義內涵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信仰和審美趣味。獸面紋象征神靈,鳳鳥紋傳達對繁榮和權威的追求,而抽象幾何紋飾反映社會對秩序和規范的追求。動植物紋飾承載了神話傳說和宗教信仰,連接人與神明之間,傳遞對神圣力量的渴望。紋飾的組合方式呈現更為復雜的意義,強調統治者的神圣地位和國家繁榮。器型演變反映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的變革,紋飾與器型協調關系強化祭祀和宗教功能。地域差異在紋飾和形態上的體現,反映當地文化和宗教影響。青銅器融合繪畫和雕塑元素,與音樂、文學、建筑等互動,展現多重藝術角色。紋飾演變反映社會演進,承載深厚的宗教內涵,從神秘向往到對祥瑞和權力的追求,彰顯社會對秩序和規范的演進。
4 符號轉義體系的構建
4.1 語境與語言集合
在構建符號轉義體系時,我們著眼于“語境與語言組合”,將商周時期的社會文化視為一個獨特的語境,而商周青銅器的紋飾則被看作是這個語境中的一種語言組合。這一概念扎根于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強調語言和符號的使用是緊密嵌入于特定社會背景和文化共識中的實踐。
商周時期的社會結構、宗教體系、禮制等方面為這個語境提供了基礎。這一時期的人們在這個獨特的文化共識下進行交流和理解,而青銅器的紋飾則是他們語言集合的一部分。這些紋飾不僅僅是裝飾性的元素,更是在這個語境中構建和傳遞意義的方式。
商周青銅器的紋飾被視為一種語言集合的組成部分,其中每一種紋飾都可以被看作是語言組合中的一個“詞語”。這些紋飾的具體形式、圖案、組合方式等構成了符號的語法規則,類似于語言中詞語的排列和組合形成語法結構。因此,我們可以將商周青銅器的紋飾理解為這個時期人們在特定社會共識下進行的一種獨特語言組合,通過這種組合來表達、傳遞、共享特定的文化內涵。這種觀點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青銅器紋飾的語境化含義,以及它們在商周時期社會文化中的角色和意義。
4.2 符號的建構
在構建符號轉義體系的過程中,我們將商周青銅器的紋飾視為符號的構建,借鑒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語言邏輯理論。這一理論強調語言和符號的使用是嵌入于特定社會背景和文化共識中的實踐,因此商周青銅器上的紋飾成為一種獨特的符號,其建構涉及多層次的意義。
首先,我們將青銅器的紋飾作為符號,將每一種紋飾視為語言組合中的“詞語”。這些紋飾的形式、圖案以及它們之間的組合方式,構成了符號的語法規則。就像語言中的詞匯和語法一樣,青銅器的紋飾通過特定的排列和組合形成獨特的符號體系。這一構建過程突顯了紋飾作為符號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每一種紋飾都是一種特定的符號,有其獨特的語法和表達方式。
4.3 社會共識的體現
在符號轉義體系的構建中,社會共識在商周青銅器紋飾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首先,我們考察了商周時期的歷史文獻、宗教儀式、社交禮儀等方面,以挖掘社會成員對于青銅器紋飾的共同理解和共鳴。這些文化元素構成了商周時期社會的共識基礎,對青銅器紋飾的意義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特定的紋飾可能在宗教儀式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成為神靈的象征,同時在社交場合中可能代表特定的社會身份或地位。
其次,符號的意義在于其在特定社會共識中的象征性作用。青銅器紋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于商周時期的社會認知框架之中。特定圖案可能代表著神靈、權威或特定的社會價值,這些意義的賦予不是個體行為,而是整個社會對于紋飾的共同解讀。
4.4 符號的演變與變遷
首先,符號的演變可以從商周時期的歷史劃分進行考察。在商代晚期,獸面紋飾占據主導地位,這與當時社會崇拜神靈的風氣和對自然力量的敬畏有關。隨著商代的滅亡和西周的興起,鳳鳥紋飾逐漸嶄露頭角,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祥瑞和權力象征的追求。到了西周末期,重環紋、環帶紋等幾何抽象的紋飾成為主流,顯示了商周時期紋飾走向更加抽象和規范的趨勢。因此,符號的演變與商周時期歷史階段的變遷緊密相連,呈現出多樣而有序的發展軌跡。
其次,符號的演變也受到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的影響。在商代時期,獸面紋飾所體現的神秘和崇拜表達了當時社會對于神靈力量的向往。而在西周時期,隨著禮制的確立,鳳鳥紋等更為抽象的圖案強調了社會秩序和統治者的權威。至西周末期,紋飾趨向規范和幾何化,反映了社會對于秩序和規范的追求。因此,符號的演變不僅僅是形式的變化,更是社會觀念、文化價值觀在符號上的投射和演進。
4.5 符號的語義解讀
首先,不同的紋飾可能承載著不同的語義。以獸面紋飾為例,其在商代晚期占主導地位,一般被解讀為對神秘和自然力量的崇拜。這種解讀可以從當時社會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動中找到支持,獸面紋飾作為一種象征,傳達了人們對神靈的敬畏和對神秘力量的追求。
區域構造特征十分復雜,主要為斷裂構造和褶皺構造。褶皺構造在礦區南部發育,發育于古元古界金水口巖群中,表現為一系列的背形和向形構造,其走向順地層NWW向展布。斷裂構造主要呈NW向、近EW向、NWW向及NE向,其中NW向和NWW向斷裂構造具明顯的多期活動性,是重要的控巖、控礦構造。
其次,隨著歷史的演進,鳳鳥紋飾在西周時期逐漸嶄露頭角。鳳鳥在商周文化中被賦予祥瑞和權力的象征,因此鳳鳥紋飾往往被解讀為對權威和祥瑞的追求。
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青銅器的紋飾逐漸趨向抽象和規范。重環紋、環帶紋等幾何抽象的紋飾成為主流,其語義解讀更側重于社會秩序和規范的追求。這種演變體現了商周時期社會對于秩序和規范的強烈需求,紋飾的語義逐漸從具體的神秘象征轉向對社會制度和文化規范的表達。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構建了青銅器紋飾符號轉義體系,它是紋飾邏輯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如圖4所示。

■圖4 青銅器紋飾符號轉義體系
5 維特根斯坦哲學符號學思想下青銅器紋飾邏輯系統分析
在論述青銅器紋飾符號系統之前,先區分記號和符號,記號和符號是構成符號系統的基礎,一個記號因表意方式不同而成為不同的符號[9],單一一個豎短線代表一個記號,在不同的器物上表達含義不同,即構成了不同的符號。如圖5所示為陜西姜寨遺址出土的紅陶缽,缽體刻劃符號,姜寨遺址共發現129處刻劃符號,筆畫均勻流暢,粗細不一。新石器時代的諸多文化中都能見到類似半坡紅陶上的刻劃符號。如圖6所示半坡文化刻劃符號,大多為長短不一的豎線或斜線組成,具有一定規律和共性,不是無意識留下的痕跡,而是表達了某種含義。

■圖5 刻符彩陶缽T254W158:1

■圖6 半坡文化刻劃符號
前期維特根斯坦對使用的解釋:“使用”是符合邏輯句法的使用,與后期他所提到的日常用語中的完全不同。意義是“使用”造成的,也就是因為有邏輯句法的使用(構造),一個句子才有意義。記號只有結合其符合邏輯句法應用才能決定一種邏輯形式,也可以說,符號等于一個記號加上邏輯句法的使用。青銅器器表分布長短不一的直棱紋構成與陶器上不同表意方式的符號,青銅器和陶器上的符號和直棱紋是按照一定使用規則分布的,體現了一定的符號使用的邏輯表達。如圖7所示是1966年岐山出土的史逨方鼎,口沿下飾長尾鳥紋,腹中部飾直棱紋,周邊布置兩排乳釘,腹部四面紋飾相同,直棱排布整齊。鼎上直棱紋與長尾鳥紋、乳釘紋的搭配,分布具有一定意義,直棱紋、乳釘紋飾在口沿、腹中部,腹下部不同部分的“使用”,使鼎紋飾具有了表達的意義,也蘊含了鼎上紋飾排列布局的邏輯句法。邏輯句法的使用決定了句子的意義,青銅器作為一種物理感知可視為一種記號,在商代和周代通過祭祀的這種形式(邏輯句法)的使用后,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禮記·表記》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10]。青銅器中的各種紋飾,如饕餮紋、夔紋、龍紋、鳳紋等動物紋樣,是“殷人尊神”、殷人“率民以事神”的具體體現,是當時巫師溝通天地的助手和工具,青銅器具有莊嚴、神秘、恐怖的氣氛,是天上諸神和人間奴隸主貴族相結合的產物[11]。《禮記·表記》:“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12]。決定了青銅器這個“句子”的使用具有了商代“事神”,周代“尊禮近人”的意義。邏輯句法也可稱為“深層語法”,自然語句的語法或結構組合方式只是“表層語法”[13],自然語句的物理感知是記號,自然語句的語法或結構組合方式只是“表層語法”,對應在青銅器系統中,青銅器上的紋飾即記號,青銅器上的紋飾和不同部位的紋飾組合是表層語法。青銅器和青銅器的組合使用構成的整體等于一個符號,九鼎八簋等青銅器組合形式相當于邏輯句法中的深層語法。

■圖7 史逨方鼎(七二199)腹部正面拓片
在文學中,語言是由句子組成的集合,是一組記號所構成的集合;而形式是某些符號串按照一定規則的構建方式。形式語言就是在不考慮語義和語用,只從語法這一側面來講的語言[14]。維特根斯坦建構的語言邏輯空間,是將句子放置于一定語境原則下的研究方法,是基于一種整體認識論的。只有被語言所建構和解釋,客觀事物才成為人之對象而被明晰地感知并被賦予意義,顯現出明晰的特征,才可能成為符號。離開語言,其他任何符號也就不可能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是符號之母。從具象和抽象的角度分析,形成了語言系統和符號系統的邏輯對應關系。根據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語言學語境下,關于句子和符號表達的論述:“句子具有本質特征和偶然特征。偶然特征是隨同產生命題記號的特定方式而來的特征,本質特征則是命題為了能夠表達其含義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特征”。一個句子中本質的東西,是所有能夠表達相同意義的句子共有的東西。同樣的,一般來說,一個符號中本質的東西,是所有能夠達到同一目的的符號共有的東西。更直白地講,維特根斯坦認為表達式(是符號,句子部分)或句子(也是符號)具有形式和內容。由此可知,語言包括了基本句子、復雜句子等不同層次的類型,最終構成了句子的總和即語言,維特根斯坦建立了一套語言和符號的對應層級關系,對符號不同層級的邏輯句法抽象概括為邏輯符號,邏輯符號是形式概念的抽象符號,形成了符號邏輯和語言哲學的哲學符號學理論,和青銅器圖像結構一樣存在不同層次類型和特征,存在邏輯哲學關系。
每一件事物都具有一定內涵,都可以看做是一個符號。就青銅器來講,每一件青銅器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都可認為是一個句子。就句子而言的青銅器具有本質特征和偶然特征。青銅器按照使用功能的不同分為禮器、容器、兵器、生活器等,禮器又包括食器、酒器和水器。每類器中細分為鼎、簋、鬲、甗、盆、壺、爵等器類。不管青銅器器類、器形如何差異,不同器類青銅器作為體現商周時期文化的物質文化,折射出的文化內涵是一致的,即青銅器的本質特征是一致的。偶然特征便是每件青銅器上不同紋飾和器型的差異,即每件青銅器上不同的紋飾、鋬、器身、器形的區別,體現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特征。各種器型的青銅器裝飾著各種各樣的紋飾,由牛、羊、虎、鹿等動物的部分特征組成的獸面饕餮紋,羽冠飄飄的夔鳳紋等都展現了在青銅器上的不同形式。
維特根斯坦搭建的邏輯空間是置于新語境原則下的。在經維特根斯坦校譯的第二版中原子事態被翻譯成“state of affirs”,它不是代表了靜態的一個名詞,而是意指一種集合、一種關系。人們如何把邏輯必然性(語言、思想和世界的邏輯結構)跟偶然的(事實的存在)聯系起來?在這里邏輯的必然性指的是維特根斯坦指出的對象、原子事態、事態、原子命題等及其邏輯關系。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是事實的存在,在這里指邏輯必然性相對的偶然,包含了青銅器及其上的紋飾、紋飾的分類、構成等的邏輯關系。一個原子事態,作為初始的材料,已經是一種對象的結合,對于事物來說,重要的是它可以成為原子事態的構成部分。如果一個原子事實被盡可能地(指理論的而不是實際的可能性)完全分解,最終達到的成分就可稱為“簡單物”或者“對象”[15]。青銅器紋飾按照層級可以分為原型、母題、母題群、主題,這些均可以稱之為對象,構成了原子事態的組成部分。按照青銅器紋飾的邏輯結構系統和維特根斯坦的符號學邏輯架構,語言邏輯、邏輯符號、青銅器紋飾系統之間對應的邏輯層次如圖8所示[16-18]。

■圖8 青銅器紋飾系統的邏輯符號對照
6 案例研究與實例展示
本節將通過兩個具體的案例,對符號轉義體系進行驗證與應用,從而更全面地揭示這一古代文化的深層含義。
6.1 案例一,青銅爵分析
青銅爵出土于商周時期文化較為繁榮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是盛裝酒的容器,是商代等級地位的代表,廣泛應用于商代社會的宗教儀式和社交場合,具有較高的時代代表性。1976年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父辛爵76FZH1:96(圖9-圖10),屬于西周中期穆王段,寬流尖尾,圓腹圜底,傘狀柱近流,三刀形足外撇,獸首半環鋬。流下、尾下飾蕉葉紋。腹部中間飾直棱紋,上下各飾一周小鳥紋。小鳥紋屬于鳳鳥紋中體形較小的一種。

■圖9 陜西扶風莊白一號父辛爵

■圖10 扶風莊白一號父辛爵線圖
青銅爵作為一種重要的禮器,在祭祀儀式和社交場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商代的歷史文獻中對爵的記載,如《禮記》《周禮》等,提供了關于商代禮制和宗教儀式的詳細信息。
首先,應用符號轉義體系,對青銅爵的紋飾與符號進行解讀。考慮青銅爵的紋飾所處的特定語境。通過對商周時期社會結構、宗教儀式、禮制等方面的研究,將爵的紋飾視為一種語言組合,參與者是當時的人們,他們共享一系列文化共識。將青銅爵上的紋飾看作符號,每一種紋飾都是語言組合中的“詞語”。紋飾的具體形式、圖案、組合方式等構成了符號的語法規則。通過研究商周時期的歷史文獻、宗教儀式、社交禮儀等,挖掘社會成員對于爵紋飾的共同理解和共鳴。爵的符號意義在于其在特定社會共識中的象征性作用,例如特定圖案可能代表神靈、權威或特定社會價值。青銅爵上不同的紋飾,在不同語境中具有特定的含義。例如,爵上的鳳鳥紋與權力、祥瑞有關,見表1。

表1 青銅爵主要紋飾及其描述
其次,利用邏輯符號對照,對青銅爵的語言邏輯結構進行解析。基于青銅爵的整體邏輯空間,著眼于爵上紋飾表現的事態形式,不同的圖案呈現出不同的情境,通過對事態形式的解讀,揭示商周時期人們對于特定事物的態度和看法。分析爵上紋飾中各個對象的配置方式,了解商周文化中對于特定對象之間關系的理解。通過對事態和事實的研究,還原商周時期的某些歷史事件或文化實踐。
然后,通過語義解讀,揭示青銅爵的深層文化內涵。比如,通過對爵上的紋飾進行逐層解析,了解每個元素的具體含義,通過關注符號的排列和組合,推斷紋飾的更深層次含義等。
通過分析,提出的符號轉義體系能對青銅爵及其紋飾提供正確解釋并與實際相符。具體如下:
符號轉義體系解讀了青銅爵上的紋飾,明確了各個符號的語境、建構方式和社會意義。對于每一種紋飾,成功地揭示了其在商周時期特定文化環境下的象征意義,為青銅爵紋飾的語義提供了清晰的解釋。
通過比較和驗證,我們發現符號轉義體系提供的解釋與實際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記載相符。青銅爵紋飾的解釋在多個方面得到了印證,使得我們對商周時期社會的文化符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青銅爵的分析中,符號轉義體系的應用效果顯著。它幫助我們建立了一個系統性的框架,連接了青銅爵的紋飾與商周時期的文化語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理解商周文化的工具。
通過該符號轉義體系,不僅能更好地理解青銅爵紋飾本身的含義,還進一步深入理解了商周時期整體文化的內涵。這對于研究者把握商周時期社會結構、宗教觀念、禮制規范等方面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6.2 案例二,青銅觚分析
青銅觚出土于商周時期的殷墟,是商代青銅器酒器中的典型代表,其在商代社會的社交場合和宗教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1953年岐山縣京當鄉禮村征集的父乙觚(圖11),侈口,束腰,中腹略鼓,高喇叭形圏足,四條棱脊將器腹和圈足分成四等份,頸部飾蕉葉紋,腹部和圈足飾獸面紋,是西周早期觚的代表形態。青銅觚主要紋飾及其描述見表2。

■圖11 陜西岐山京當鄉禮村父乙觚
通過與青銅爵類似的分析方式,我們構建出對應的符號轉義體系框架,對青銅觚及其紋飾提供正確解釋并與實際相符,具體如表3所示。

表3 兩種青銅器的符號轉義體系特征分析總結
基于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語言邏輯理論構建的符號轉義體系,是一種嵌入于特定社會背景和文化共識中的實踐。通過分析語境、符號建構、社會共識等方面,能夠建立完整而內在一致的分析框架。通過該符號轉義體系的應用,能夠有效揭示青銅觚紋飾背后的文化內涵,讓我們在語境解讀、符號建構、社會共識、演變變遷、語義解讀等方面對青銅觚有更深入的認識,驗證了體系的可靠性。所揭示的青銅觚紋飾的意義不僅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還在更深層次上解釋了當時社會的文化、宗教、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現象。
7 結語
本文借助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語言理論框架,對商周青銅器紋飾的符號轉義體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利用符號轉義體系方法,對語境與語言組織的關聯、符號的建構過程、社會共識的體現以及符號的演變進行了強調。其次,通過對青銅觚紋飾的分析,揭示了背后的文化內涵,強調了其在不同語境下的意義表達。第三,在商末周初至西周末期的紋飾演變中,觀察到了獸面紋、鳳鳥紋、重環紋、環帶紋等母題的嬗變,這種變化反映了紋飾系統的層級和意義的發展。最后,通過符號學方法,對青銅器紋飾的不同層次類型和組合特征進行深入分析,并解釋了它們的使用規則和文化內涵。我們的研究不僅為商周青銅器紋飾提供了哲學思考,也為符號學在考古學領域的應用提供了有益的實踐經驗。期望這一研究為深入理解商周文化、發掘符號學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推動文化符號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