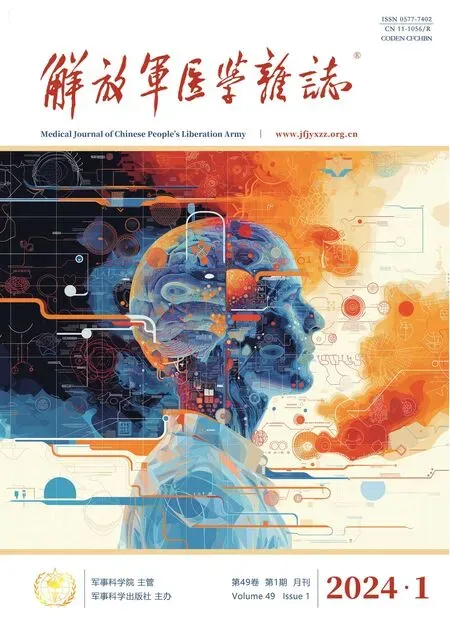早期胃癌內鏡下黏膜剝離術及幽門螺桿菌根除后異時性胃癌的發生機制研究進展
胡馨月,王斌,王濤,劉凱軍,文良志,陳東風
陸軍軍醫大學陸軍特色醫學中心消化內科,重慶 400042
胃癌是我國常見的惡性腫瘤[1],2021 年的數據顯示其發病率在惡性腫瘤中排第5 位,病死率排第3位,胃癌發病率在不同國家及地區存在明顯差異,日本、韓國、中國、東歐及中南美洲國家胃癌發病率較高[2]。胃癌與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持續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癥密切相關[3‐4],從慢性胃炎、萎縮性胃炎(atrophic gastritis,AG)、腸上皮化生(intestinal metaplasia,IM)、腸上皮異型增生發展至胃癌的Correa學說路徑已得到業界認可[5‐6]。HP也被世界衛生組織(WHO)確定為胃癌的Ⅰ類致癌因子。2015年,《京都全球共識報告》提出,除有制衡因素以外,所有感染HP的人群都應接受根除治療[7],成功根除HP可以明顯降低胃癌的發生率。數項隨機對照試驗及薈萃分析也證實,根除HP可減少胃癌的發生,然而學者們發現,即使在早期胃癌內鏡下黏膜剝離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后根除HP,仍有2.7%~6.1% 的患者會發生異時性胃癌(metachronous gastric cancer,MGC)[8‐13]。MGC為早期胃癌(early gastric cancer,EGC)患者行ESD后1年或更長時間在原病灶以外部位發生的胃癌。根除HP 后,胃癌的發病率每年約為0.3%,其發生因人而異,甚至成功根除HP后10年以上者仍有可能發生胃癌[14]。本文就根除HP 后MGC 的發病機制進行綜述,以期為MGC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1 HP根除后AG與IM不能完全逆轉
以往學者們認為胃癌前病變中AG 及IM 一般不能逆轉,但最近研究報道顯示,部分患者根除HP后其胃黏膜萎縮及腸化生可以逆轉[15]。另有研究顯示,羔羊胃提取物維生素B12膠囊及塞來昔布單藥均能逆轉AG及IM,且在羔羊胃提取物維生素B12初始治療的基礎上加用塞來昔布挽救治療可進一步提高IM的消退率,達85.93%[16]。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根除HP雖然可以延緩AG 及IM 的進展,但不能完全逆轉腸化生及異型增生的發生,這可能是由于根除HP后胃黏膜異常的局部微環境仍持續存在,以及胃黏膜上皮細胞遺傳及表觀遺傳重編程的累積改變。因此,相關臨床指南建議在發生胃黏膜萎縮前就進行HP根除治療,以降低胃癌發生風險[17]。
1.1 細胞周期與IM 胃黏膜上皮細胞發生IM 時,細胞凋亡與增殖的比例明顯降低,這有利于細胞損傷及突變的積累。50%的胃癌旁IM有p53基因突變,Ⅲ型IM中P53蛋白積聚更明顯[18]。IM所致的黏膜屏障功能障礙可導致胃內各種物質不斷跨上皮滲透,促進免疫應答局部微環境改變,參與腫瘤的發生。根除HP 后不能完全逆轉的胃黏膜損傷及IM,與MGC的發生發展關系密切。
1.2 DNA異常高甲基化與IM 根除HP后,盡管IM上皮細胞異常高甲基化有所下調,但仍遠高于正常胃黏膜,這些異常DNA甲基化在胃黏膜干細胞中仍能檢出,均與胃癌發生相關。有研究還觀察到根除HP 并不能阻止表觀基因組的重編程,癌前病變的DNA甲基異常賦予了細胞持續突變的潛能,這些表觀遺傳印記變化可致基因表達的永久性改變,促進腸化上皮向MGC演進[19‐20]。
2 胃黏膜上皮細胞過度增殖可獨立于HP感染
有研究發現,慢性胃炎及胃癌的胃上皮增殖率增高與HP感染無關[21]。組織病理學檢查顯示,胃竇HP 密度高于胃體,同時其炎癥程度也較重。除菌后,胃竇上皮細胞的增殖指數有所降低,但與除菌前比較無明顯差異[22],表明根除HP后,胃竇的炎癥仍可持續存在,提示HP感染并不一定是胃黏膜炎癥的唯一原因。持續存在的炎癥反應及炎癥介質可引起胃黏膜上皮細胞損傷,一方面,氧自由基等引起細胞增殖過快,而增殖活躍的細胞DNA 合成旺盛,易受基因毒性致癌物質的損傷,導致基因不穩增加而發生上皮內瘤變乃至癌變。若增殖速度超過凋亡速度時,增殖與凋亡失衡,可促進上皮內瘤變發生。另一方面,HP 感染可刺激胃黏膜炎性細胞釋放C‐X‐C 族的炎性因子,此炎性因子中的ELR 片段(谷氨酸‐亮氨酸‐精氨酸序列)可刺激細胞分裂增生、促進血管生成。當根除HP后,持續存在的炎癥反應可能繼續促進胃黏膜上皮細胞發生過度增殖,引發惡變。
3 胃黏膜上皮細胞遺傳異常的累積
HP 感染可導致胃黏膜上皮細胞增殖自穩態受損,如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體細胞突變負荷(mutational burden,MB)及點突變,這些改變很難通過根除HP來逆轉[23]。
3.1 胃黏膜上皮細胞MB 累積 早期胃癌ESD 術后實施根除HP治療,在鄰近的非癌黏膜中,發生異時性進展的患者MB往往高于未發生早期胃癌的患者。研究發現RECQL4、JAK3、ARID1A及MagiC1基因的突變與MB 結合可促進異時性癌癥的發生。ARID1A及MAGI1基因與胃癌的發生有顯著相關性[24]。對GC外顯子進行序列分析發現,83%的MSI患者存在ARID1A 的高頻失活突變或蛋白表達缺陷,并與PIK3CA 突變及MSI 相關[25]。在胃癌細胞中干擾ARIDIA后,Akt磷酸化水平上升,p21表達減少,細胞周期S 期增多,G2 期減少,細胞體積變大,葡萄糖消耗量增加。這些結果提示ARID1A 通過影響Akt的磷酸化水平及細胞周期來調控細胞增殖。ARID1A還可通過影響E‐cadherin 的轉錄從而調控腫瘤的遷移、侵襲。且ARID1A的缺陷與MSI相關聯,腫瘤抑制基因ARID1A的體細胞突變常在MSI高的胃癌中可以檢測到[26]。攜帶ARID1A 變異體的胃早癌患者在鄰近非癌黏膜中有高的MB,與根除HP 后仍可發生MGC有關。
3.2 胃黏膜上皮細胞點突變及基因擴增累積 HP感染相關的胃癌有相似的遺傳學改變,即體細胞點突變及基因擴增。“非可控性炎癥”(如持續或低強度的刺激、靶組織處于長期或過度反應狀態)產生的細胞因子通過誘導基因突變、改變癌基因及抑癌基因表達、抑制細胞凋亡,炎癥信號傳導通路異常,誘導血管新生;并且“非可控性炎癥”可通過募集多種免疫抑制性細胞(M2 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骨髓來源抑制細胞、調節性T細胞等)促進免疫抑制狀態的腫瘤微環境建立,最終導致腫瘤發生,這種現象被稱為廣義的炎癌學說。“非可控性炎癥”通過點突變或基因擴增激活已知的癌基因,如ErbB2及PIK3CA,進而活化下游信號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PKB,Akt)/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及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APK)途徑,抑制細胞凋亡,促進腫瘤血管再生,增強腫瘤細胞的侵襲力[27]。這些變化在HP根除后的非癌黏膜中可持續存在,可能參與了MGC的發生。
4 表觀組穩態失衡
表觀遺傳學是一系列影響基因表達而不影響DNA一級序列的染色質改變,如異常甲基化。DNA異常高甲基化與不適當的轉錄沉默及基因功能缺失密切相關[28]。正常組織中表觀遺傳學改變的積累將會形成表觀組穩態失衡,可能與HP相關胃炎及胃癌發生密切相關。研究表明胃癌患者的正常胃黏膜在根除HP 后的甲基化水平可反映胃黏膜干細胞的DNA異常甲基化,與MGC的發生風險顯著相關[29]。
4.1 DNA 異常甲基化持續存在 HP 感染后胃黏膜DNA甲基化的改變可持續存在并累積,暫時性甲基化很可能在祖細胞或分化細胞中被誘導,這些改變觸發凋亡,引起胃黏膜上皮細胞脫落更新。永久性DNA甲基化很可能在胃黏膜干細胞中被誘導并終身存在。根除HP后,胃黏膜上皮細胞的甲基化水平沒有明顯下降,可能與MGC的發生有關。端粒的縮短及DNA 甲基轉移酶1(DNMT1)的高表達是根除HP后胃黏膜異常甲基化誘導的重要機制。除此之外,甲基化水平與炎性細胞浸潤密切相關,即使根除HP,胃黏膜間質的炎癥仍會存在,可持續誘導DNA甲基化。吸煙、飲酒等不良生活習慣及激素也可以誘導異常的DNA甲基化,長期接觸煙草增加了DNA甲基轉移酶3B(DNMT3B)的表達,并招募DNMT3B到BUB1、HDAC2等基因的啟動子區域,促進這些基因的高甲基化,導致胃黏膜上皮細胞突變[30]。
4.2 CpG 島啟動子異常甲基化 DNA 甲基轉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的差異表達也可能誘導哺乳動物細胞中CpG 的整體DNA 低甲基化向DNA 高甲基化演進,導致表觀遺傳不穩定[31]。CpG島啟動子的異常甲基化導致包括腫瘤抑制基因在內的多個基因如RUNX3、LOX、PTEN及CDH1的表觀遺傳沉默,這些基因參與DNA 修復、調節細胞周期、信號轉導等多個細胞生理過程,是腫瘤發生的重要機制之一[32]。PTEN 蛋白對P13K/Akt 信號通路有負性調控作用,當PTEN 失活時,PIP3 不能去磷酸化為PIP2,過多的PIP3 積聚會激活Akt 通路,通過調控P27、BAD、FOXO、mTOR、GSK‐3 等下游分子,發揮抑制細胞凋亡、促進細胞存活及增殖的作用。除調控Akt通路外,胞質內的PTEN還可抑制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刺激引起的原癌基因Shc磷酸化,進而抑制Ras/MAPK 通路的活化;亦可通過FAK 脫磷酸化等途徑抑制細胞遷移、伸展及黏附。胞核內的PTEN 具有重要的生物學功能,核內的PTEN可下調cyclin D1水平,誘導細胞G0‐G1 期阻滯,抑制腫瘤生長。還可通過非磷酸酶依賴的方式與著絲粒蛋白CENP‐C 結合,維持著絲粒穩定;也可與E2F1 協同,激活Rad51 轉錄,調控DNA 雙鏈斷裂(DNA double‐strand breaks,DSBs)的修復,抑制因DSBs 引起的染色體不穩定。RUNX3可以通過上調miR‐30a 的表達從而抑制上皮‐間充質轉 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中 關 鍵的間質標志分子波形蛋白的表達,從而抑制EMT的發生及胃癌細胞侵襲轉移。
CpG 島啟動子異常甲基化導致多個抑癌基因的表觀遺傳沉默,將會破壞細胞穩態,影響細胞增殖與凋亡、遷移及黏附。當腫瘤抑制基因下調,胃黏膜微環境中可觸發一系列炎癥反應,包括釋放促炎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IL)‐1、IL‐6、IL‐8 及腫瘤壞死因子(TNF)‐α,激活核因子(NF)‐κB 途徑。IL‐8 上調是甲基化炎癥的共同特征,IL‐6 又可反向誘導DNA甲基化,這些途徑的激活導致黏膜微環境中持續的慢性炎癥,共同促進MGC的發生。
4.3 DNA異常甲基化導致腫瘤抑制因子表達下調異常甲基化可引起miR‐124a 表達下調,特別是腫瘤抑制因子miR124a‐3,它是預測MGC 發生風險的標志分子[33]。SPHK1是miR‐124 的靶基因,miR‐124 直接與SPHK1的3'‐UTR 結合并下調其表達,發揮抗增殖作用。當miR‐124異常甲基化時,SPHK1的過度表達導致AKT激活,進而導致FOXO1的抑制,并因此下調細胞周期蛋白抑制分子p21Cip1 及p27Kip1 的表達。miR‐124還可通過NF‐κB信號通路阻斷EMT,抑制腫瘤細胞浸潤及轉移。異常甲基化導致腫瘤抑制因子SOCS3功能障礙,促進STAT3信號轉導的持續激活[34],SOCS3 異常甲基化的胃黏膜中P‐STAT3 表達較高,可促進細胞的異常增殖。根除HP 后,在SOCS3 甲基化活躍的早期胃癌患者的非腫瘤性胃黏膜 中,P‐STAT3 及Ki‐67 的 表 達 水 平 仍 較 高[35]。STAT3 還可通過與COX‐2 啟動子結合上調COX‐2,其產物PGS 可進入核內,反向調節IL‐6/STAT3 信號轉導,形成正反饋[36],從而促進胃黏膜上皮細胞異常增殖。
5 機體免疫系統異常
HP感染胃黏膜后,可遷徙至胃淋巴結,影響與慢性胃炎相關的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有助于MGC的發生。根除HP 后,HP 抗體滴度的緩慢降低提示侵入淋巴結的HP 并未被迅速清除,這可能增加了MGC 的發生風險。細胞毒素相關蛋白A(cytotoxin associated protein A,CagA)深易位可能與CagA抗體滴度的緩慢下降及胃癌的發展有關。根除HP 0.5~2.0年,較多患者仍有高滴度的HP 抗體,提示HP 陰性患者可能存在假陰性可能。定植于胃黏膜上皮細胞外的HP 主要毒力因子CagA 及空泡毒素(VacA)可通過多種方式抑制自噬上游信號活化及自噬溶酶體成熟,使癌前病變胃黏膜細胞的自噬受到抑制。這一變化可導致HP 無法通過自噬被有效清除,CagA 及VacA持續存在引起胃黏膜上皮細胞過度增殖及凋亡異常,從而增加了DNA損傷的機會,并促進胃黏膜組織的炎癥[37]、氧化應激、凋亡及增殖異常等一系列惡性生物學過程。HP感染還能夠誘導以Thl為主、調節性T細胞(Treg)及Thl7混合的T淋巴細胞免疫反應,有利于感染的慢性化過程。上述環節通過激活活性氧(ROS)、上調DNA 突變酶胞苷脫氨酶(activation‐induced cytidine deaminase,AID)的 轉 錄、誘導DNMTs 錯誤定位等,導致腫瘤相關基因突變、染色體錯配、異常DNA甲基化,從而導致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活、DNA修復失調及染色體不穩定等。即使HP 感染已被根除,癌變過程仍然繼續進展。HP感染所致的炎癥介質釋放還可促進胃黏膜化生或異型增生,如IL‐8 是EMT 的誘導因子;IL‐6 可以誘導DNA甲基化,增強COX‐2誘導,促進細胞增殖及血管生成;NF‐κB 的激活可誘導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因子1(TRAF1)的表達上調,而TRAF1具有抗凋亡作用;活化的NF‐кB 可結合在許多靶基因的啟動子上,通過增強子與啟動子之間的作用,迅速誘導mRNA 的合成,這些改變與MGC 的發生密切相關。
6 胃黏膜干細胞異常
有研究發現,HP可激活胃黏膜干細胞并增加上皮細胞的分化及轉歸[38],HP不僅感染胃小凹頂端的胃上皮細胞,也可侵入到胃底腺的深處,此處也是胃腺體的干細胞區域[39]。HP根除后,干細胞的持續增殖可能參與了MGC的發生及發展。
6.1 胃黏膜干細胞Axin2+/LGR5‐細胞信號轉導異常激活 Wnt/β‐catenin 信號轉導在許多組織中對干細胞穩態調節及上皮細胞的再生有重要作用[40]。經典的Wnt靶基因Axin2主要表達于胃底腺及胃幽門腺的下峽部,此處也是胃干細胞存在的區域。HP感染增加了胃腺體間質R‐spondin3 的表達,Axin2 及LGR5的表達都需要基質來源的R‐spondin3 來維持干細胞池的微環境。R‐spondin3是胃黏膜上皮Wnt信號的調節因子,可促進胃干細胞特異性Axin2+/LGR5‐細胞信號轉導的效應及Axin2+細胞的增殖,并形成Axin2+細胞池,發揮胃小凹上皮細胞由基底向小凹頂端有序增殖并遷徙的調節作用。Axin2+/LGR5‐細胞構成了一個高度增殖、無分化的區域,維持胃腺體的再生,其中R‐spondin3 作為一個關鍵的特異性調節因子來協調干細胞的穩態及增殖動力學[39]。即使根除HP后,干細胞特異性Axin2+/LGR5‐細胞信號轉導途徑可能持續激活導致過度增殖,促進MGC的發生。
6.2 胃黏膜干細胞Wnt/β‐catenin 信號通路異常激活 有研究表明,HP 感染可通過CagA 以細胞間質上皮轉換因子(cellular‐mesenchymal 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c‐Met)和(或)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Akt)依賴的方式介導C 端Ser675 及Ser552 殘基β‐catenin 磷酸化,并以此激活Wnt/β‐catenin信號通路。Nanog及Oct4是Wnt/β‐catenin 信號通路的下游靶基因,是腫瘤干細胞(cancer stem cells,CSCs)自我更新、特異性標志物表達及多能性維持所必需的[41‐43],具有誘導CSCs 產生及增強EMT 的能力[44‐45]。HP 可通過Wnt/β‐catenin 信號通路上調Nanog 及Oct4 的表達,促進CSCs 的自我更新并上調CSCs 標志物的表達,其啟動子活性在HP 感染過程中增強。EMT 可誘導具有干細胞特性的CD44+細胞出現,CD44+信號激活后通過STAT3 導致胃黏膜上皮化生及異常增生性病變。除此之外,CagA 蛋白可直接與GSK‐3β 結合,抑制β‐catenin 降解[46],還可促進以C‐Met 和(或)Akt 依賴的方式誘導Ser552 及Ser675 處的β‐catenin 磷酸化,導致β‐catenin 在胞質中的大量聚集并入核與淋巴細胞增強因子/T細胞因子結合形成異二聚體,啟動相關癌基因及有絲分裂原基因的轉錄等。HP感染還可通過NF‐κB 依賴性機制誘導RAS 蛋白激活劑2(RASAL2)表達,NF‐κB 直接與RASAL2 啟動子結合,激活其轉錄,通過基因沉默及異位過表達,上調β‐catenin 轉錄活性。根除HP 后,CSCs 的異常持續增殖更新與MGC的發生密切相關。
6.3 胃黏膜干細胞DNA 雙鏈異常斷裂 DNA 雙鏈斷裂(DSBS)是HP 依賴于Ⅳ型分泌系統(T4SS)由XPF/XPG 核酸內切酶引入導致,進而引發NF‐κB 靶基因激活及細胞增殖。DSBS 通過經典途徑激活的NF‐κB,將會發生異二聚體p50 及RelA/p65 的核位移,激活與炎癥、細胞存活、生長等相關基因;通過非經典途徑激活的NF‐κB,促使淋巴樣器官形成、B細胞存活。HP長期感染會導致胃黏膜細胞不精確修復,發生遺傳不穩定性及頻繁的染色體畸變,從而參與胃癌的發生。在不同細胞系及胃底或下峽部的干細胞中,DSBS 以時間及劑量依賴的方式積累,在根除HP 后可能會繼續保持誘變特性[47]。除此之外,此前有研究在增強子上發現了一種DSBS轉錄耦合修復機制,這種耦合修復機制支持致癌超級增強子的激活。超級增強子是基因組中的獨特區域,區域大,密集地與轉錄因子/輔助因子結合,可控制多種癌癥驅動因素的超轉錄,是相關癌基因高表達所必需的,幾乎參與所有腫瘤的進展。上述研究提示HP 感染引起DSBS 修復可通過超級增強子的重塑參與MGC的發生。
7 染色質可及性、染色體重塑及染色體重塑子的改變
染色質可及性提供轉錄因子結合的結構,以調節與腫瘤進展及侵襲相關的多個基因的激活。染色質重塑可被遺傳及表觀遺傳的改變所破壞,并作為驅動因素參與表觀穩態缺陷的形成[48]。染色質重塑子通過調節染色質可及性及染色體重塑參與轉錄調控,如ARID1A、SMARCA1、SMARCA2及SMARCA4在胃癌中常常發生突變,參與胃癌的發生發展。SMARCA1及SMARCA2還是胃癌的抑癌基因,SMARCA1或SMARCA2突變在胃癌細胞系中會促進其生長。SMARCA1在正常胃組織中表達豐富,其表達可能因暴露于HP而暫時受到抑制,從而導致對異常甲基化誘導的易感性增加。根除HP后,胃黏膜干細胞中異常甲基化而沉默的SMARCA1 可能促進了MGC 的發生。DNA 甲基化及組蛋白修飾相互關聯,并在胃癌發生過程中影響表觀遺傳修飾,共同作用于染色質重塑[49]。在HP相關性胃炎的IM中,EZH2的表達明顯高于非IM 組,而EZH2 可催化組蛋白及DNA 的甲基化。BET 家族含有能夠識別乙酰化組蛋白賴氨酸殘基的蛋白質,可作為活性啟動子或增強子積聚在高乙酰化染色質區域上,作為支架招募轉錄因子及多蛋白復合物促進靶基因的轉錄,從而可能改變全局染色質的可及性[50]。高表達的EZH2 還可通過與PTEN 啟動子結合來誘導胃癌細胞獲得上皮‐間充質轉化表型,下調E‐cadherin 的表達,從而增強癌細胞的遷移及侵襲能力,特別是EZH2 可增強胃癌細胞的成球能力,說明其在腫瘤干細胞富集過程中具有促進作用。HP根除后,發生在干細胞中的DNA 甲基化及組蛋白修飾是相對“永久性的”,因此癌旁胃黏膜及化生上皮可能存在這些表觀遺傳穩態缺陷,參與MGC的發生。
8 總結與建議
早期胃癌ESD 術后根除HP 后MGC 受到臨床越來越多的關注,HP 根除及定期內鏡監測是預防MGC 發生的有效措施,根除HP 能降低MGC 發生率,但不能完全消除其風險。根除HP后,胃黏膜上皮細胞仍可通過持續異常增殖、遺傳及表觀遺傳重編程的累積改變、干細胞突變轉化及染色體可及性異常調節等環節逐漸演進發生MGC。因此,建議接受ESD 治療的早期胃癌患者于術前、術后常規檢測HP,發現感染后盡快進行根除治療。在早期胃癌ESD 術后根除HP后建議患者每年進行1~2次內鏡隨訪,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可適當縮短隨訪間隔,便于早期發現及治療MGC。大部分MGC 是分化良好的黏膜內癌,可繼續選擇內鏡ESD 治療,少數進展期胃癌可選擇外科手術、化療、靶向或免疫治療,長期預后良好。MGC的發生機制及相關標志物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