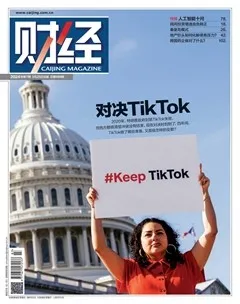構建新熟人社會
說起熟人社會,總是讓人們感覺有點前現代,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社會的運行很多時候是在正式的規則和書面的法度之外,因此會有人情的讓渡和規則的妥協,進而不利于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這種理解有正確的一面,也有片面之處。
熟人社會自有其規則,而且也并非全與現代法規相捍格的“潛規則”,很多也體現了公序良俗,也深入人心,且因彼此相熟,信息不對稱情形較少,因此在維護社會秩序、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可以實現自治型低成本運作。
在應對包括校園霸凌在內的諸多社會治安問題上,熟人社會自有其諸多優點和長處。在霸凌一詞尚未風行的時候,校園內外青春期孩子間的以強凌弱便屢見不鮮,這或許本身就是人性使然,可能也是人們成長的必經階段。使其不至于演變成社會熱點問題的,是熟人社會的各種制約和緩釋機制。
熟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學生、家長和校方處于一個共同的網絡和知情圈內,家校之間的互動、家長之間和學生之間的來往也都比較頻密,加之當年班級規模比較小、獨生子女也相對較少,這些都有利于學生身處一個網格相對密集的社會安全網內,留下的死角和灰色地帶比較少。如此一來,不僅有利于提前遏制一些霸凌事件的發生,還能在霸凌事件發生后讓被霸凌者告訴有門,相關方處置迅速,而且多無需勞煩公權力介入。
數十年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大規模推進,中國社會像其他發達社會一樣發生了巨大的形態和生態的改變,主要標志之一便是從熟人社會走向非熟人社會。涉及校園霸凌問題,便意味著不少之前在熟人社會能夠發揮作用的安全網絡、緩釋機制和應對手段,面臨一定程度的缺失。
此消彼長的是,隨著城鄉融合力度加大,一些鄉村中學撤并,導致不少超級中學的出現,班級數目、規模和住校生的規模都同步大幅擴大。這些學生中又有不少是獨生子女兼留守兒童。這些都給家校互動和家長之間的互動帶來一些困難。此外,近年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學校和社會之間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隔膜”,令學生的成長環境出現這樣那樣的死角。種種原因之下,校園霸凌現象有所抬頭,霸凌事件發生后有時也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置,為個別事件的升級惡化埋下了伏筆。
在重新念及熟人社會的種種好處的同時,人們也深刻意識到重回熟人社會不可能。為今之計,在于加快構建新熟人社會,讓學生置身于升級版網格密集的社會安全網絡之中。新熟人社會的重建當然首先離不開家庭網絡的重建,因此盡量為外出打工者創造各種便利條件,盡快縮小留守兒童規模是當務之急。也因此,近來有不少人士呼吁為農民工子女隨遷入學創造方便。除此之外,大力振興縣域經濟,加快推進美麗鄉村建設,讓更多農民工就地擇業,也是必由之路。總之,無論是成為新市民,還是離土不離鄉,盡快實現農民工階層家庭團聚,是構建新熟人社會、打造新社會安全網絡的根本。
構建新熟人社會需要假以時日。在這之前,為更有效應對學校霸凌,除了校方更加重視和加大投入之外,各地應積極引入社會力量,比如積極發揮社會志愿者組織的力量,積極主動為留守兒童在校生提供各種心理咨詢和法律救助服務,讓他們敢于把問題說出來擺出來,既防患于未然在前,又及時處置在后。
除了學校社會積極聯手形成網絡效應之外,學校內部也應積極為學生減負,推動他們在埋首學習之外組成各種社團,讓他們置身于各種有形無形的網絡之中,提升自治、自助和自救能力,從而減少校園治理死角和灰色地帶的產生。
與校園霸凌相關的惡性事件發生后,呼吁加以嚴刑峻法,加大懲治和矯正力度的呼聲不絕于耳,也有其合理之處。而標本兼治之道還是構建新熟人社會,改善社會生態,打造新社會安全網絡,從而以相對較低的社會治理成本維護社會秩序,從而真正體現巨大規模人口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