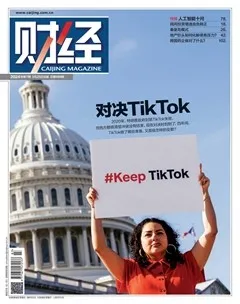韓國的斯密型增長
包茂紅

《是什么締造了漢江奇跡》
(韓)俞正鎬 著
方菊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戰后東亞創造了發展奇跡,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韓國創造了漢江奇跡。與日本的第二次崛起相比,韓國的發展基礎甚為薄弱;與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相比,韓國的密度和強度更大;與其他三個小龍相比,韓國的發展更具發展型國家的特點。因此,韓國的經濟高速增長被稱為“人為的奇跡”,即政府引領的韓國人,在最不可能成功的韓國創造了經濟奇跡。韓國的經濟起飛主要發生在樸正熙執政時期,他認為,在與朝鮮已經開始的“千里馬運動”的競賽中,韓國必須通過人的革命來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經濟自主,進而通過重建社會實現民族統一。隨著樸正熙遇刺身亡和隨后開始的韓國民主化,對韓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的認識逐漸多元化。就其側重點不同,大體可分為三種: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強調儒家文化在韓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的多元現代性理論,強調全要素生產率(TFP)和投資回報的協同作用對韓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貢獻的經濟學理論。這三個流派大體上與對東亞奇跡或東亞模式的主流認識相對應。
所謂發展型國家主要指發展型政權通過政商合作和實施產業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發展型國家主要包括四方面內容:發展優先的理念,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經濟官僚機構,密切合作的政商關系,以及有所選擇和側重的產業政策。
樸正熙政府就是典型的發展型政權,他以軍人的管理方式,通過發揮技術官僚的作用,成功實施了重點各不相同的多個五年計劃,創造了韓國經濟的發展奇跡。尤其與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相比,韓國的這個特點格外突出。韓國經驗也成為其他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學習榜樣。但在戰后的第三世界,許多國家都曾形成了類似于韓國的官僚威權政府,但都沒有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類似于漢江邊上的奇跡那樣的亮眼成就,于是學者們不得不把關注點轉向韓國文化和社會的底色方面,探討儒家文化和宗教對韓國現代化的重要影響。這個思路無疑受到了馬克斯·韋伯的影響,因為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強調了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儒教與道教》中否定了在儒家文化中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多元現代性流派順著韋伯的思路,反過來在韓國發展中尋找儒家文化和宗教的積極作用及不利影響。
韓國的世襲制親屬關系、宗教信仰、對權威的尊崇、對合法秩序的遵守等文化特點,都有利于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屢次創造出人意料的經濟增長率。毫無疑問,這種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文化傳統是經過選擇和適應的新儒家思想,或亞洲價值觀,而不是真正傳統的儒家思想。新儒家的道德價值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但并不能引發工業革命。在東亞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后,新儒家能夠融會資本主義并推動韓國經濟發展。不過,從經濟學入手探尋經濟增長的奧秘似乎更為專業。通過對多國增長的計量經濟學分析,發現是較高的TFP增長率和較高的資本存量增長率共同作用,使得韓國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韓國在這兩方面之所以能一馬當先,不在于政府采取出口導向工業化等改革政策,而在于在改革開始時相對較高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改革的有效性。顯然,這種觀點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的觀點完全相反。克魯格曼認為,東亞奇跡只是一個神話,因為東亞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的。
這三種不同的觀點都是從比較視野出發,采用排除法,找到了自認為的、韓國高速發展的動力和秘密。然而,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更不等于漢江奇跡。因為經濟增長是一個可以用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的單一因素,而經濟發展不僅涉及GDP的增長,還包括用基尼系數和恩格爾系數等來衡量的經濟全面進步,漢江奇跡更是一個反映韓國整體轉型和各方面快速變化的概括,甚至還具有與朝鮮進行競爭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
《是什么締造了漢江奇跡》就是從經濟學的視角來探討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并在對相關觀點做出回應的基礎上提出見解。本書作者俞正鎬在研究時首先明確了一個前提:市場經濟并不是一點都不要國家的規制,相反,國家通過制定符合市場規律的政策來規范和監管市場經濟的運行。換言之,規制市場不等于政府干預,某些規制市場的措施雖然也是政府制定并執行的,但那是為了維護市場秩序或為市場正常運行創造條件。例如,韓國政府保證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對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進行投資,保持經濟政策的外向性等。在此基礎上,政府對不同行業和市場的干預才是需要研究的重點。
針對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因為韓國政府推行出口導向戰略的主流觀點,作者發現,在韓國政府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之前,其出口已經從1961年開始大幅度增長。另外,外貿在帶動韓國經濟增長方面并沒有突出作用,因為進口保護政策仍然沒有廢除,兩項相抵,只能說韓國出口是在類似于自由貿易環境中進行的經濟活動,而不是通過提供額外的優惠來促進出口。為什么出口會先于出口導向戰略實行而高速增長,關鍵在于政府通過外匯管理制度改革消除了阻礙出口的障礙,同時發揮了韓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換言之,韓國政府只是掃清了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從而釋放出經濟增長的潛力。
針對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迅速升級是由政府實行的重化工業政策帶動的主流觀點,作者發現,1973年實行的重化工業促進計劃(鋼鐵、有色金屬、電子、化工、通用機械和造船)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產業結構,但它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大,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末韓國出口和投資的雙雙負增長,最終迫使樸正熙政權不得不在1979年4月頒布全面穩定計劃,終止重化工業運動。具體而言,政府對重化工業的保護和鼓勵政策抑制了韓國最具出口競爭力,也是出口主力的輕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來自出口的所得和外國貸款被迫流向制造業,雖然使制造業的固定資本投資率的迅速上漲,但生產和獲利周期長的制造業并未能迅速帶動經濟高速增長,因為人為保護的、幼稚的韓國重化工業并不能迅速搶占國際市場份額。相反,終止重化工業運動后,韓國的輕工業和服務業迅速恢復了投資和出口雙雙增長的強勁勢頭。
那么,真正帶動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呢?韓國的經濟潛力和比較優勢只有在廣大的世界市場上才能轉化為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先發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在經濟增長時其外貿在某種程度上是利用殖民主義體系、在另外的程度上是利用世界市場進行的。如果以1990年國際美元計算,根據麥迪遜的統計,1820年世界出口總額是73億美元,英國占15.5%,是11億美元,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1%。到韓國經濟迅速增長的1961年,世界出口量比1820年增長了100多倍,而韓國出口只有4090萬美元,占國內總產值的1.8%。到1973年,世界出口總額增長到17970億美元,韓國出口為79億美元,占世界出口總額的0.4%,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這說明市場規模的擴大,是韓國出口擴大以及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另外,一國工業化開始時的市場規模每增加1%,該國工業化所用年數就減少0.35%。這足以說明為什么荷蘭和丹麥等國完成工業化花費了大約一個世紀,而韓國只用了大約20年。因此,后發國家利用世界市場規模擴大,不但增加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的出口,還提高了生產率,從而有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顯然,俞正鎬通過反駁國家干預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和觀點,重回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同時也暗示韓國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就是斯密型增長。具體而言,生產率的提高取決于通過分工發揮比較優勢,而分工的程度取決于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規模。反過來,國際市場規模的擴大成就了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不能忽略的是韓國政府奉行積極推進國際貿易的政策,但這不是政府干預,而是為市場有效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和提供保障。如此一來,漢江奇跡就不是漢江奇跡,東亞奇跡也不是東亞奇跡,它們都是20世紀的奇跡。
俞正鎬采用這種層層剝筍式的研究方法,直達促成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核心,其邏輯關系非常清晰,也有數據支持,觀點得以削尖,但很容易造成片面的深刻,尤其是在把韓國經驗普遍化時。具體而言,把漢江奇跡擴而廣之到東亞奇跡,把漢江奇跡和東亞奇跡轉化為20世紀的奇跡,都會出現過度普遍化或過度簡單化的問題。歷史發展是非常復雜的,并不是用排除法就可以簡單解析的。面對俞正鎬過度普遍化的觀點,人們還是要問,同樣面對規模擴大的世界市場,其他國家,例如無論是工業化基礎還是與國際市場的聯系都比韓國強的菲律賓等,為什么沒有像韓國一樣形成經濟高速增長?毫無疑問,經濟增長是歷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個重要領域的分析不能孤立進行,需要放在整體史的框架中進行研究,需要與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聯系起來進行綜合分析,需要把外部因素和內部動力結合起來進行全面認識。也只有在進行綜合分析之后,其歷史經驗和教訓才具有更大的借鑒意義。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世界環境史研究中心主任;編輯:許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