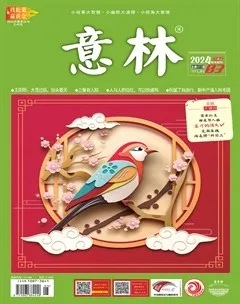我們正在成為一種很新的窮人
薛巍

屢次看到有人在談論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的一本書,《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這本書很薄,不到200頁,很多人讀這本書,可能是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消費主義的俘虜,算不算新窮人。看完之后很多人可能稍微松了一口氣:自己大概還不是新窮人,但是肯定被消費主義裹挾了。
鮑曼提出,在現代性的工業階段,每個人在擁有其他身份之前,必須是一個生產者。在現代性的第二階段,即消費者的時代,人首先要成為消費者,才能擁有其他特別的身份。
在后現代社會,人們仍然從事著各種工作,有的是做簡單的體力勞動,有的是高薪的管理階層。工作是否高級、誘人,不是看它對社會的貢獻、對人的技能的要求,而是看它能不能不斷地給人帶來刺激。人們在購物時不僅是滿足生理需求,還有很多心理需求。有錢人是消費潮流的引領者。拿高薪的人則是一邊拼命工作,一邊通過瘋狂消費來犒勞自己,因為“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義的源泉。曾經由專業能力帶來的自豪感,現在可以從(以合適的價格)購買精美商品中獲得——在迷宮般的大型購物中心發現最好的店鋪,發現推車上最好的衣服或貨架上最好的商品”。
消費主義的問題在于,我們以為我們的購買欲是自發的,挑選是自由的,是按照自己的審美去選購的,市場上商品琳瑯滿目、不斷推陳出新是好事。鮑曼則認為,消費者其實并不主動,并不自由,“是市場選擇了他們,并把他們培養成消費者,剝奪了他們不受誘惑的自由,但每次來到市場,消費者都覺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們可以評判、評論和選擇,他們可以拒絕無限選擇中的任何一個——除了‘必須做出選擇之外。尋求自我認同,獲取社會地位,以他人認為有意義的方式生活,這些都需要日復一日地到訪消費市場”。
購物時,我們希望買了之后立刻就能享用,但新東西帶來的滿足感又很快就會消失,于是繼續買,購物帶來的暫時滿足感讓人們習慣了超前消費。
向消費者社會的轉變導致窮人的處境也發生了變化,新的貧窮并不僅限于物質匱乏和身體上的痛苦,也是一種社會和心理狀況。每個社會都有“體面生活”的衡量標準,如果無法達到這些標準,人們就會煩惱、痛苦、自我折磨。貧窮意味著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著“達不到標準”,從而導致自尊心受到打擊,產生羞愧感和負罪感。窮人無法履行消費者義務,就會被拋棄、被剝奪、被貶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會盛宴之外。在生產者社會,窮人的生活很苦,但他們一起苦,他們還是儲備的勞動力,社會還需要他們。在消費者社會,窮人之間的紐帶也消失了,要么是孤獨的消費者,要么成為無力消費的新窮人,他們的處境成了對其他人的一種警示。
有些人努力想擺脫消費者身份,還原購物的原始目的。不過消費主義的力量過于強大,美國作家凱爾·查卡在《渴望更少》一書中說:“在網上用信用卡購買不必要的物品能迅速、輕松地對不確定的環境施加一種掌控感。各種品牌向我們出售汽車、電視機、手機等產品,好像它們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通過書籍、播客和周邊產品,極簡主義觀念本身也被商品化了,成了利潤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