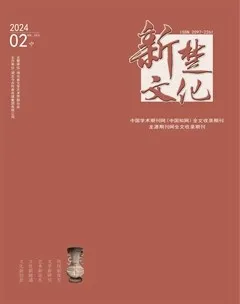賡載傳統,多維承繼:非遺語境下舞火狗的傳承與發展路徑研究
【摘要】“舞火狗”是龍門縣藍田瑤族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文化發展價值。經文獻研究、田野作業,從民間傳說詮釋歷史形成,從儀式過程凝練出認同標識、傳統美德、自然共識、對歌風俗等文化意義。繼而立足現代“非遺”語境,分析傳承現狀,結合藝術人類學理論提出傳承與多維發展路徑,為充實舞火狗文化的學理經驗,推動舞火狗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予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藍田瑤族;舞火狗;非遺傳承
【中圖分類號】J722.2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05-0084-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5.027
【基金項目】2022年廣東省教育廳教育規劃項目“文化共生視域下廣東民族舞蹈融入高校美育建設的轉化”(項目編號:2022GXJK251)。
2021年,文旅部在《“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指出“加強非遺區域性整體保護,加大非遺傳播普及力度和服務社會經濟發展”[1]。聚焦嶺南少數民族沃土,惠州市龍門縣唯一少數民族鄉即藍田瑤族鄉,以“舞火狗”聞名。它作為廣東省首批非遺項目,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本研究旨在追溯舞火狗的神話歷史,分析儀式步驟、文化意義和傳承現狀,賡載舞火狗傳統本位基礎上,探索它在非遺語境下的發展多維路徑,希冀強化民族文化認同,拓寬非遺文化資源新用途,促進廣東民族區域治理,并促進文化和諧交流。
一、瑤遷傳舞,星火相承:舞火狗的歷史形成
藍田瑤族鄉位于惠州市龍門縣北部,地處群山環抱之地。其備受推崇的瑤族少女成年禮“舞火狗”,廣泛分布于藍田瑤族鄉的藍田、上東、倒流、紅星、小洞、社前等7個村委會,共82個自然村和1個居委會。
“南嶺無山不有瑤”,經瑤族人民的世代遷徙,惠州龍門縣已形成一片瑤風濃郁、獨具特色的“藍田瑤”之鄉。清朝咸豐元年《龍門縣志》卷三風俗中記載“十八堡地較廣有唐魏風,上建、高明、鐵岡多土著,俗雖樸野尤推淳”。“上建”是藍田的古稱,記載中的“土著”就是今日龍門縣所在的瑤族。據傳,瑤族祖輩自明代時期從粵北韶州的瑤山遷徙至惠州龍門縣。古時藍田(原名上建峒)的土著人種植火棉、苧麻,利用藍靛染衣料,形成一片藍色景觀。村寨設有染缸、染房,尤以圩田附近產藍豐富,因此后人將“上建峒”改名為“藍田”。舞火狗一直延續至今,其形成與藍田瑤民間傳說有著密切的聯系,而“舞火狗”也成了瑤民心中神話信仰的儀式載體。
(一)對祖先“峒主爺”的崇拜
《禮運·大同》載:“人道親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藍田瑤族以劉、楊、譚、李、林、朱、黃七姓為主,共敬譚仙公。傳說自明朝弘治年間,瑤族受壓迫起義,譚觀福率義軍抵抗明軍,英勇無畏但最終失敗。為紀念譚軍,瑤民建起“譚公廟”。另一傳說稱譚姓為藍田瑤族主要姓氏之一,與七大姓氏有血緣和姻親關系,“譚仙公”為始祖與拓荒英雄。由傳說而來,“譚仙公”既是祖先崇拜又是英雄崇拜的象征。隨著地域共同體形成,“譚仙公”由血緣神演變為地域信仰。瑤族人民通過對共同祖先的崇拜消除家庭內部人與人間的精神隔閡,完成整個家族的親和維系。
(二)犬系傳說的圖騰崇拜
龍門縣藍田瑤族鄉的舞火狗傳統根植于中秋節,源自瑤族對狗的崇敬。古代瑤族人視狗為重要伙伴,傳說中,一勇敢之犬破解懸賞榜,從而成為神犬大將軍,后瑤族先祖公主愿意嫁給神犬大將軍,便形成了女子扮演火狗起舞的起源。另外,傳說瑤族峒主爺小時候失母,被父親用狗奶撫養長大,崇敬狗視為“再生之母”。每年中秋夜,鄉村舉辦舞火狗活動,少女們身著火狗裝,象征狗是繁衍之力,意喻著少女成人后的為母之性。舞火狗除了慶祝成年,還有驅邪避災、消弭瘟疫之意。瑤民通過舞蹈儀式與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的結合,表達瑤族少女對祖先的緬懷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幸福人生的追求。
二、圍火起舞,成人之儀:舞火狗之展演復現
舞火狗在龍門縣藍田瑤族鄉已有300多年歷史,是瑤族少女的“成人禮”,也是八月十五“打歌堂”的重要部分。“打歌堂”包括祭祖、祭拜峒主公和青年男女對歌等,而舞火狗則是核心環節,由未婚少女扮演火狗。每位少女需連續參與三年,方可謂成年。
完整儀式有以下幾個流程:
第一,采葉。參演女孩的家屬在山上采集山滕、黃姜葉等做準備。黃姜葉一般春季種植,夏季八月十五左右茂盛,可采摘做衣服裙擺,有驅蚊辟邪作用。
第二,扮“火狗”。瑤族少女由兩名備受尊敬的中年婦女打扮,穿戴儀式簡潔而富有特色,如黃姜葉裹腰、腿、手臂,斗笠草帽,頭頂點三炷香,扮演“火狗”。裝束完成后,她們邁開腳步,投入一年一度的舞火狗活動。
第三,拜祠堂。少女們先獻上狗糧和香火,然后從大門到祭臺祈禱。龍門藍田瑤族深信“峒主爺”,在祠堂獻上狗糧和香火,表達感恩之情,祈求順風順水。祭拜時,每人手持三炷香,三拜恭敬,唱舞火狗歌,隨后依次進行一系列祈福動作。
第四,拜地堂(曬谷場)。少女拜地堂以祈求風調雨順、來年豐收,并唱舞火狗歌。祭拜完畢后,邊歌邊舞穿街過巷去灶堂,遠遠看上去,隊伍在行走和圍圈跳舞時像一條長長的火龍。
第五,拜灶堂與菜園。隨后,隊伍走到灶堂前祭拜,祈求火神庇護、平安順利。在歌唱方面,少女們連續并反復唱三遍歌曲,每首歌三段,并看著香根識別儀式的剩余時間。爾后隊伍在菜園舞拜,祈愿蔬菜長得茂盛、豐收并唱抓蟲歌。
第六,驅瘟逐疫。整個活動約一個半小時,每次舞蹈不超過十分鐘,男孩們圍觀并放鞭炮助興。據傳承人解釋,改革開放后祭拜已無需祭品;每人持香祭拜三下即可。最后,少女們穿過巷道,走向村旁的河流,將身上捆扎的黃姜葉、山滕、竹斗笠、香火等全都扔到河里去,讓河水帶走;然后濯洗手腳,象征沐浴全身,祛除病邪,驅除往日的霉運和病疫,迎來吉祥。
舞火狗的動作及儀式過程有著豐富的民俗意蘊,承載著身份認同、美德教育、信仰傳承等文化意義。
第一,藍田獨有,點綴族群身份的認同標識。藍田瑤以“藍靛”之源成為獨具特色的瑤族分支。獨特的少女祭祀禮儀、藍色為尚的傳統服飾、黃姜葉群的盛產與制作、美好的觀念意義匯聚成本民族獨有的文化符號,即“舞火狗”。這一文化符號如星星點燈般點綴藍田瑤的民族身份,同族人見此而共鳴,強化彼此之間的民族認同感。
第二,弦舞不輟,繼承瑤族傳統美德。祭拜先祖儀式由村里德高望重的男性長輩主持,體現儀式敬上、賢下之禮。于祠堂、地塘、灶頭等地的祭拜、舞蹈過程,是長者和儀式構成的教育場域,對少女們傳授成年后家族女性仁慈母愛、尊老愛幼、賢能儉樸的美好品德。在每年定期儀式的身體操演和舞動過程中,女孩們將美德內化于身心,薪火相傳。
第三,崇敬自然,達成萬象互饋的虔誠共識。在禾堂、灶堂、菜園等的祭拜動作,意喻著人們在汲取自然給予的營養物質、稻谷臻糧的同時,也應勤勞務實、知恩圖報,用儀式敬仰、保護家鄉環境等回饋自然萬物。族民祈求豐收的美好寄望也傳達一種崇尚自然的自然敬意,并將這份虔誠共識融入儀式以育后代。
第四,男女對歌,保持和諧交往的美好風俗。在“驅瘟逐疫”過后,青年男女來到溪河兩岸,選擇意中人與之對歌。男青年等待少女上岸,選擇意中人與之通宵對歌,表達彼此心中的愛慕之情。兩岸歌聲此起彼伏,一來一往,直至天明。對歌也傳達了藍田瑤族傳統的族內聯婚、族民自由戀愛的觀念。
三、經濟催變,文化沖擊:舞火狗的傳承困難
經濟基礎的變化影響著扎根于原生民俗文化的承載者,出現“民俗藝術的主體從農村向城市遷移或流動”[2]的局面。文化生態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民俗文化的轉變,經對相關人員的訪談了解,舞火狗目前面臨以下主要困難。
第一,鄉村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扶持仍在路上。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經濟增長滯后,限制了傳統舞火狗演出的資金支持。從服裝制作到道具購買和人員調配等成本對于欠發展的鄉村村民來說難以承擔。因此,原生態舞火狗傳承在經濟壓力下仰賴政府文化政策的支持與生存。
第二,長者記憶遺忘,原生儀式面臨失傳。經訪談90歲的傳承人譚松娣,發現老一輩對舞火狗中的許多動作及其象征性意義記憶逐漸消退。老一輩傳承人隨年歲逝去,帶走了對舞火狗的生命記載。此外,缺乏專業團隊對原生態舞火狗沿襲,傳承斷層和技藝流失。現代表演偏向程序化,觀賞性勝過文化與民俗的本質,令原生儀式文化逐漸瓦解。
第三,多元互動文化的沖擊,傳統崇族觀念及交友功能淡漠。隨著娛樂多樣化和多媒體的發展,年輕人更偏向流行文化和融媒體交互,以致傳統舞火狗儀式因程序較繁多漸失吸引力。繁忙的經濟考量、外出活動和文化選擇削弱了宗族血親和傳統崇祖關系。很多人無暇顧及舞火狗復雜的祭拜儀式,其傳承壓力隨著崇祖紐帶松弛而減弱。加之,現代文化價值觀對“舞火狗”傳統民俗意識以內在沖擊。年輕一代群體有了更便捷的多渠道交流方式,以靈活搭建自己與族內、族外人群的互動結構關系。藍田瑤族存在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排外性婚姻觀念[3],以族為界、圈內互動的舞火狗,無法與新一代年輕人交友結伴需求契合,儀式中青年男女交友功能淡化。
四、“非遺”活化:舞火狗文化的多維發展路徑
方李莉從人類學視角提出“非遺”保護的路徑應具有“整體性、歷時性、動態性、主體性和未來性”[4]。基于“五大特性”的發展理念,通過政府、學校、社會及傳承人等多主體聯動,提出多維路徑推動舞火狗的傳承與發展。
第一,文化歸檔的系統建構,堅守舞火狗的原生本色。舞火狗的祭祀儀式、舞蹈、歌謠、服飾、道具和表演程序等,至今仍繼承和保持著瑤族民俗文化的傳統“本位”。因此,保護“舞火狗”非遺文化,必須保護其原生態性,才能扎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政府在場的社區場域下,整合校園志愿組織、社區文化站、信息技術人才等,廣泛收集藍田瑤族史料、影視圖片和相關文獻。建立電子檔案平臺和專館設施,并確立保護政策和法規,以全面展示藍田瑤舞火狗文化。多方主體記錄,深入傳遞舞火狗的原汁原味,加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保持傳統本色的基礎上,促使其文化符號實現“傳統”本位上的發明再造。
第二,挖掘美學價值,建構非遺文化的審美空間。審美意識的參與將“非遺舞蹈”從生活經驗記憶向美學價值的轉換與形塑,使傳統藝術在當代呈現出“原生態、次生態與再生態并存而不相悖的諧美局面”[5]。“舞火狗”這一文化符號下衍生出許多具有審美性、風格性的子符號,例如藍靛綠葉與香燭構成的獨特服裝,藍綠相間、樸實協調;舞火狗歌謠,明亮悠轉,編制成曲;多彩織帶仔,提煉元素設計成民風文創;民俗舞蹈,大眾展演吸引游客融入其中。諸如此類,在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深耕與挖掘舞火狗的文化子符號,將舞火狗所承載的文化符號結構編織為多樣一體的中秋佳節“舞火狗”的文化空間。同時,關注當代大眾對傳統審美特征的發展趨向,保留“舞火狗”系列文化符號原生性的基礎上融合傳統美學、精練技術和裝飾藝術,打造原生“舞火狗”文化場景。在這個空間中,服裝租借和舞蹈演出共同構成豐富的文化體驗,讓各年齡層次主體沉浸式感受舞火狗的魅力,領悟其民俗和文化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曾言:“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舞火狗”正是在特具觀賞性的文化符號建構中形成動態性、創新性及其當代審美價值可持續性的發展。
第三,善用多模態媒介,拓新舞火狗傳播路。從傳媒角度講,多模態為“信息容器與設備,也涵蓋特定的傳播組織形式或社會機制”[6]。非遺傳播至活躍于大眾文化視野,需要多方協助,通過各種融媒體的渠道,如網絡新媒體(公眾號、短視頻等)、電視節目、公共廣告牌、學校、文化工作室等文化場域中擁有的多模態媒介進行廣泛宣傳、素材征集激勵策略及項目合作。再者,以符合現代審美心理的平面或多面設計,向公眾呈現舞火狗非遺舞蹈的文化及價值,增強社會大眾對其的文化記憶和興趣。其次,政府扶持下,民間組織、地方學校合力組織傳統文化節日演出和展覽,同時鼓勵相關文化機構和社區組織自發開展舞火狗非遺舞蹈的交流路演等。通過多模態媒介的有效運用,從線上與線下交互方式,提升舞火狗社會知名度,也為藍田瑤地方宣傳提供豐富的素材,由此拓寬舞火狗的傳播途徑,以星星之火續航傳承動力。
第四,特色非遺融校園,潛移默化傳精髓。加強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推動傳承創新的關鍵途徑。將“舞火狗”的傳統以文化資源形式融入地方或校本課程,引導青少年了解和欣賞“舞火狗”。通過“非遺進校園”政策支持,邀請傳承人和專業展演者帶領學生學習舞火狗動作程序,塑造年輕一代對家鄉非遺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信念,提升家鄉文化認同感。
第五,聯動多方主體發展,非遺語境立體化。在藍田瑤族鄉,積極貫徹“一村一品,一戶一韻”政策,社區展現了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地方各方需抓住政府推動的文旅發展契機,構建“舞火狗節日儀式的旅游發展線”。利用旅游產業,將舞火狗表演與瑤鄉民宿、景點建設、農景觀光等結合,創造多元旅游體驗與發展機遇。通過整合資源,讓舞火狗文化經濟賦能,發揮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促進非遺文化和鄉村發展。同時,將其他傳統文化如“男女對歌”“不落夫家”與舞火狗聯動,形成豐富的文化情境,吸引各方游客,推動非遺文化傳承與發展,煥發文旅社區生機。
舞火狗作為非遺傳承的典范,以保留傳統為主體,挖掘美學價值為動力,融合多元文化為特色,通過“五大特性”共振的多維路徑,為藍田瑤族的非遺文化注入新活力。
五、結語
“舞火狗”習俗對研究瑤族的歷史來源、宗教信仰以及文學藝術、生產生活等都有其重要的歷史價值[7]。未來,文化工作者更應在窺探現狀時,追溯形成過往,知其源以溝通瑤族整體變遷發展脈絡,站在民族歷史的肩膀上提出廣東少數民族共進、共謀、共融、共生的發展對策,活用與傳承并進,讓“舞火狗”等藍田瑤民間非遺成為經濟賦能、文化賦能和鄉村治理的瑰寶,為鄉村振興貢獻瑤族的文化力量。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關于印發《“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通知[A/OL].(2021-05-25)[2023-12-12].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fwzwhyc/202106/t20210609_925092.html.
[2]毛巧暉.非物質文化遺產語境下民俗藝術研究之嬗變[J].民族藝術,2020(04):47-54.
[3]戴朝.“舞火狗”的傳承與保護研究[J].荊楚理工學院學報,2020,35(01):16-19.
[4]方李莉.人類學視角下的“非遺”保護理論、方法與路徑[J].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0(01):54-62.
[5]仝妍,曹露露.“非遺舞蹈”的歷史性觀念、現代性本質與審美建構[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21(06):80-85.
[6]王建民,曹靜.人類學的多模態轉向及其意義[J].民族研究,2020(04):61-73+139-140.
[7]潘多玲.廣東龍門縣藍田瑤族“舞火狗”傳承現狀研究[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0(03):63-66.
作者簡介:
魏彥華,女,漢族,廣東河源人,廣東技術師范大學音樂學院2022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舞蹈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