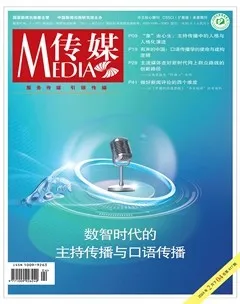媒介偏向與融合:數智時代口語傳播具身性的回歸與強化
姚爭 徐學明

摘要:口語時代,人與人的交流需雙方同時“在場”,紙質媒介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狀態,使得人在傳播過程中得以“離場”;及至大眾媒介時代,廣播傳播人聲、電視呈現人像,“面對面”的溝通再次回歸;而數智時代,AI主播以及ChatGPT、文心一言等軟件的大規模應用,讓真實的人“再離場”。但正是由“再離場”所引發的人類隱憂,使得口語傳播活動對于具身性的原初關懷再次得到凸顯和呼吁。“具身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歸與強化,真人之間的在場交流感更加不可替代。人們更多地期待身體的“在場”。
關鍵詞:具身性 口語傳播 在場 播音員主持人
在數字智能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無論新聞寫作還是語音播報,AI技術都可以部分甚至全部獨立完成。我們是否還需要傳統意義上的“播音員”“主持人”?如果僅從文字信息和視聽信息轉譯的角度來看,視聽內容的創制工作已經可以由AI完成;但從當前的傳播實踐來看,各種類型的主持人并沒有被AI大面積取代。反之,面對“冰冷”的科技感,人們愈發期待在場交流所帶來的親近感。由此,一些在場感更強,更加符合原始口語傳播形態的視頻內容大量出現。口語傳播活動中的具身性特點和優勢,在數智時代再度成為一把標尺,測度著傳播活動的溫度和質量。在數智時代,重新關注“肉身人”的意義,也是對作為言說主體的“人”的再度標舉。
一、媒介偏向與異化過程中的口語傳播
媒介偏向常被與時間、空間聯系在一起,但這一概念最重要的意義不是重新劃分媒介,而是改變了人對世界認知的既有建構方式。延續媒介偏向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媒體在強化傳播效率的同時,剝奪了人最原始具身傳播的身體感官體驗性。隨著社會深度媒介化,媒介偏向最終改變的是社會形態和作為傳播主體的人。人的意義是否已“退化”為媒介的肉身銘刻對象?回顧媒介與人的互動歷程,我們認為媒介“異化”人類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
從報紙到廣播電視再到新媒體的媒介技術演進是一個從文字書寫重回影像化的過程。如同沃爾特·翁及其后繼學者所指出,相較于廣播,電視直播并未增加信息傳遞速度,但電視直播創造了一種在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行交流的場景,且這種交流無限接近于“面對面”交流。當下的智能媒介中的AI主播相較于此前的電視媒介中的播音員主持人,固然擁有許多優勢,但亦缺乏真實性和情感共鳴,沒有顯示出口語傳播活動的人際交往性質和情感表達功能,此即真實人的“再離場”。
數智化強調的是數據的智能化,通過數據挖掘、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數據和信息的深度挖掘,從而驅動業務和決策的創新。數智化媒體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泛媒化,萬物互聯,萬物皆媒。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媒介突破了既有形態,擴展到了各個物體和領域,這意味著任何物體都可以成為信息傳遞的介質物,使得信息的傳播和交流更加廣泛和便捷,推動了信息傳遞和社會交往的快速發展。二是場景化,精準畫像,場景傳播。這在移動傳播中被精準運用,基于場景的服務,進行精準感知和信息適配,制定用戶畫像,通過對用戶所處場景的理解和把握,提供更加個性化、精準的信息和服務,以滿足用戶的需求。三是臨場化,沉浸體驗,虛實融合。通過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方式使用戶置身于環境之中,提供更加沉浸式的體驗。
然而,數智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具身化暫未得到足夠關注。大眾傳播時代,技術造成的媒介偏向和異化使得身體經常處于分離和缺席狀態。受此影響,現有智能媒體的運用方式嚴重忽視了物理人形的具身意義。換言之,如果從效率層面考量,智能媒體完全有更好的表達形式,但“仿真機器人”和“腦機接口”等技術,仍然執著地追求著智能數據與肉身人的連接。這一技術演進路線與傳統媒體時代(報紙—廣播—電視)的技術演變路徑無異,均凸顯著人形的重要價值。因此,從智能技術的發展歷史和趨勢來看,數智時代將使傳播的“具身化”得到前所未有地回歸與強化。在數智化時代或許我們也要重溫梅洛·龐蒂等對“身體”的定義,虛擬世界里的身體并非現實世界里的“肉身”,但作為肉身與意識統一體的身體,在虛擬世界中仍然具有重要價值,甚至因為愈發稀缺而彌足珍貴。
二、具身性:數智時代口語傳播的本質要求
現代口語傳播學脫胎于西方修辭學,而西方修辭學發源于“口頭文化”盛行的古希臘時代。口語傳播的基礎情境是人際傳播,從具身性的視角看,人際傳播是人形和人性高度統一的肉身人之間的對話,這是口語傳播最為本質的特征之一。相對于文字信息,人可以通過口語的音調、語速、語氣等傳遞更為豐富的信息。由此,口語傳播中的有聲語言表達更具有人情味和親和力,能夠更好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身體缺席和時空壓縮“使現實和傳播者同時不在場也成為可能”,對傳播研究造成的直接影響是“‘以技術為中介的大眾傳播研究和‘無需中介的人際傳播研究的相互割裂”,注重媒介技術的“主流傳播學”研究都或多或少且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身體。雖然媒介技術使得人的肉身得以“離場”,但在數智化場景下我們依然在追求“人”的形態和與“人”交流的慣習。在這個被5G、VR/AR、AI、機器人、自動駕駛等名詞所包裹的時代,重訪口語傳播及其具身性特征具有兩點重要意義。
第一,人機共生的媒介生態下,“人性”“人聲”的研究依然重要,不可偏廢。在數字時代的口語研究中——無論是AI主播和人形機器人的語言、表情、動作研究,還是ChatGPT等軟件的生成內容研究——口語傳播理論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口語傳播有著語言傳播和非語言傳播要素相互匹配的優勢。當下,AI技術的一項重要攻關課題就是盡可能使其信息輸出方式貼近自然人的信息表達風格。為此,各個AI技術團隊都在努力研究人類語言的規律和特點,甚至發音方式和習慣,從而更好地模擬和生成人類語言,實現更高水平的自然語言處理和生成能力。即便是如ChatGPT般的最新AI技術,其本質上仍是海量汲取既有人類語言成果的技術物。概言之,AI不可避免地具有類人的邏輯與慣習。
第二,無論媒介技術如何迭代,口語傳播對于具身性的原初關懷應始終貫徹于技術的開發和使用過程中。美國實用主義先驅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認為,人的心理活動都有生理構造基礎,生理上的隔絕可以導致心理上的隔絕;而試圖破除人與人之間的生理隔絕,則必須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才能實現。口語傳播是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之一,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人類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傳播載體。正因如此,傳播學在現代社會科學中才占有一席之地。AI主播和人形機器人的技術形態正是源于人在溝通中對于“人形”的期待,因此可以說,無論媒介技術如何迭代,口語傳播對于具身性的原初關懷應始終貫徹于技術的開發和使用過程中。
三、數智時代口語傳播的具身回歸與角色遷移
媒介的發展有兩種演化方向。一種是人的逐漸離去,甚至消失,如口語媒介時代過渡至印刷媒介時代后,面對面的口語溝通變為紙張上的文字讀寫,紙張在空間上的可運輸性,帶來了人在傳播過程中的“離場”;另一種是人的回歸,亦即原始口語傳播場景“具身性”的回歸,如書籍、報紙等紙媒上最初只有文字,后來出現帶有人形的圖片、照片,再到后來廣播中出現的人聲,電視中呈現的人像。

隨著數智化程度不斷加深,口語傳播活動的具身化特征不斷得到回歸與強化,這或許可以歸因于人類對“人形”和“人性”兩方面的孜孜求索。其一,人類本身就抱有對“人形”的親近和期待。縱觀目前被設計出的機器人,大多數都具有“人形”,即便不具有“人形”,多數也具有“人聲”。但這種仿真有時也會有相反效果,甚至帶來“恐怖谷效應”。有研究表明,當一個物體看起來足夠像人類,人們在開始時會對其產生親近感和喜愛。然而,當這個物體的外觀和行為與真人非常相似,但并不是完全相同時,人們的情感反應會突然變得消極,甚至產生恐懼感。因此,越是在數智時代,越要重視“人”的回歸,同時把握其回歸尺度。其二,人類從未放棄對“人性”的關注和探析。口語傳播是一門與人相關的社會科學,人性是其繞不開的話題。口語傳播始終關注人,長久以來,它的基礎假說是人類的傳播行為無論透過什么媒介,信息傳遞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人。這種觀點在AI已經可以自主創作的今天看來,似乎顯得有些過時。但是,當我們深入了解AI的設計研發與推廣使用后就會發現,其所有的程序都源于人類工程師的編寫,所有生成內容的原始數據庫都是現有人類社會的智慧成果,AI的自我進化也依賴于人類社會提供的基礎材料。“人性”依然是數智媒體時代口語傳播學的基礎關懷。
在數智時代,真人主播的角色意識更加凸顯。傳統廣播電視時代,主播的角色按功能可分為播音員、主持人、解說員等,而數智媒體時代主播則以各種身份出現。在口語傳播理論中,人的角色與角色意識也是重要議題。在戲劇五要素、幻想主題分析等傳統的修辭分析方法中,人物主題和人物設定都是重要的研究內容。
在社會表演學中,口語傳播行動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表演,即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人們通過語言交流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態度。數智時代的社會是深度媒介化的社會,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中介化的語言(天然的或合成的)進行語音交互、信息交換、情感交流。傳統的媒介口語傳播者,如廣播電視的新聞主播更多地扮演媒介機構發言人的角色。這一角色定位在數智時代仍然不可或缺,但其作為大眾媒介時代的一項傳統職業與崗位的屬性色彩將不斷減弱。網絡主播等口語傳播主體的話語實踐,已經從傳統的廣播電視媒體挪移至新媒體平臺。按照戈夫曼的擬劇理論,人們通過扮演不同角色來展示自己的社會身份和角色定位。數智時代,口語傳播者的角色遷移是必然的,選擇合適的角色定位才能達到最佳的傳播效果。這種角色遷移通常具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是角色的多元化。數智時代,傳播者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在不同的媒介平臺上有不同角色定位,與之相關的“前臺”和“后臺”以及“戲班”亦各不相同。二是角色的虛實轉換。在虛擬現實技術的支持下,傳播者可以更加自由地切換角色,并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之間進行轉換。這將帶來更多的創意和表現機會,但也需要傳播者在表演和行為上更加精準。三是角色的交互性。數字交互技術使傳播者和受眾之間,傳播者和機器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和緊密,這也意味著角色之間的互動和“對話”變得更加重要。但同時,隨著在場感的進一步回歸,情緒表達的進一步豐富,“面具”下的分寸感將愈發難把握。四是角色的數智化。隨著數智技術的發展,傳播者可以借助紛繁多樣的數字工具和軟件來幫助自己扮演角色,并流轉于不同的數字平臺上進行角色展演。這將帶來更多的表現機會和創新思路,但也需要傳播者具備使用數智技術進行創作和展演的能力。數智時代,口語傳播是實現媒介人性化回歸的一種基本策略,“重獲早期技術丟失的、面對面傳播中的元素”。
四、結語
媒介人類學者麗莎·吉特曼認為,新媒介的出現并不總是革命性的,與其說是新媒介與舊的認知論“全然斷裂”,不如說新媒介必須設法去鑲嵌入既有的社會場域中,并持續協商其存在的意義。面對AI等智能化媒體對既有口語傳播秩序的顛覆,“具身性”的回歸與強化為數智時代的口語傳播復興提供了新的可能。以“具身化”整合“口語”與“數智”,既是在技術發展過程中對人為尺度的重申,也是對口語傳播實踐中人本精神的再度呼喚。
作者姚爭系浙江傳媒學院副校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學明系浙江傳媒學院播音主持藝術學院講師
本文系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教學改革項目“基于文化自信導向下的‘以創促學在藝術語言教學中的探索與實踐”(項目編號:jg20220411)、浙江傳媒學院2023年第十二批校級課程教學模式創新實驗區項目“文化自信導向下口語傳播課程數字化創新與探索”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鄧建國.我們何以身臨其境?——人機傳播中社會在場感的建構與挑戰[J].新聞與寫作,2022(10).
[2]譚雪芳.圖形化身、數字孿生與具身性在場:身體-技術關系模式下的傳播新視野[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08).
[3]唐寧,孫延鳳.多元共生:智媒時代融媒體新聞欄目的創新趨勢[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2(01).
[4]彭蘭.智能時代人的數字化生存——可分離的“虛擬實體”、“數字化元件”與不會消失的“具身性”[J].新聞記者,2019(12).
[5]徐學明.語態的轉換:《新聞聯播》抖音號口語傳播研究[D].北京:中國傳媒大學,2022.
[6]張晶,朱時宇.近代中國啟蒙視閾下的媒介變革與知識傳播——以白話報、廣播、電影為中心[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3(09).
[7]強海峰,張超.回溯、鏡像與本真:數字化時代口語傳播的時空擇取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07).
[8]焦寶,張雅雯.從元宇宙到ChatGPT:人際傳播場景的回歸[J].東南學術,2023(03).
[9]張萌,于德山,徐生權.好物的連接:網紅公益直播的動力機制與意義建構——基于口語傳播的研究視角[J].傳媒觀察,2022(08).
【編輯:錢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