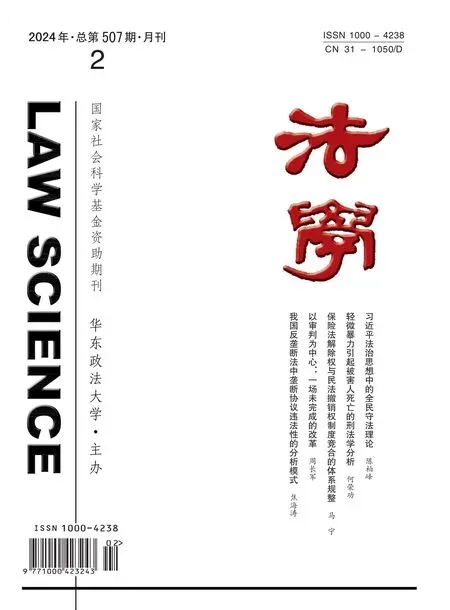我國反壟斷法中壟斷協議違法性的分析模式
●焦海濤
一、問題的提出
壟斷協議是各國反壟斷法明確禁止的壟斷行為之一,是多個獨立經營者通過協議、決定或協同行為等方式聯合實施的壟斷行為。我國《反壟斷法》將壟斷協議定義為“排除、限制競爭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行為”,同時對典型的壟斷協議類型予以列舉。因《反壟斷法》未對“排除、限制競爭”作出解釋,其內涵是指排除、限制競爭的“目的”“效果”抑或其他,學界與實務界的看法并不一致,而且對于明確列舉的壟斷協議類型,亦未規定在個案認定時是否還需要判斷“排除、限制競爭”的要件滿足與否。由于執法機構和法院依據各自的理解來處理案件,導致在壟斷協議認定中產生了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不僅影響到《反壟斷法》的實施效果,亦有損于經營者的合規預期。
2022 年6 月《反壟斷法》完成首修,確定統一的壟斷協議分析模式是修法的重要目標之一。新《反壟斷法》在第18 條“禁止縱向壟斷協議”條款中增加了第2 款,規定對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經營者能夠證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不予禁止”。從表面上看,該規定像是承認了即便是認定《反壟斷法》明確列舉的縱向壟斷協議(轉售價格維持),也要以“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為前提,但同時又指出,“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需由行為人來反證。這實際上是確立了轉售價格維持的違法推定模式。如此規定在學界和實務界引發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立法對壟斷協議“效果要件”的直接承認;另一種觀點認為,當事人的“反證”規定意味著對法律明確列舉的壟斷協議,執法機構或原告無需再證明其具有排斥、限制競爭效果。由此可見,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的爭論,并未因《反壟斷法》的修改得以統一。〔1〕參見蘭磊:《〈反壟斷法〉轉售價格維持條款現階段應維持現狀——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修正草案)〉第17 條第二款》,載《競爭政策研究》2021 年第6 期,第5-6 頁;倪泰、程云帆:《專家熱議反壟斷法(修正草案)亮點與重點》,載《中國市場監管報》2021 年12 月11 日,第003 版。
可以說,壟斷協議違法性的分析模式已成為我國壟斷協議制度中最需要解決但可能又最難形成共識的問題。這里所說的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主要指判斷一項協議是否違反《反壟斷法》的分析思路,側重于分析步驟或分析框架,不涉及個案中判斷某協議是否產生競爭損害及損害大小的具體因素。關于如何合理確立壟斷協議違法性的分析模式,一來需立足實踐,探究執法機構與法院案件處理分歧的產生根源,二來要立足《反壟斷法》文本自身,從法律的規范表達、體系構造及背后邏輯出發,尋求合理、自洽的解釋方法。作為反壟斷法后發國家,我國在立法過程中極大地借鑒和繼受了歐盟競爭法中的相關制度,其中歐盟法中的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也是我國模式選擇的一個重要參考。
基于上述問題及考慮,本文擬先從當前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的主要爭議切入,解析爭議背后的成因,尤其是理論與制度根源,再從規范論和體系化的角度,闡釋新《反壟斷法》框架下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的基本步驟和主要路徑,以消除法律適用上的困境。
二、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的主要爭議
實踐中,反壟斷執法機構和法院對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理解的不一致造成了同種行為不同認定的情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和可預測性。當前我國對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的爭議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爭議一:“排除、限制競爭”指向效果還是其他
我國《反壟斷法》未明晰壟斷協議定義中“排除、限制競爭”的內涵指向的是“目的”“效果”還是其他,而新法第17、18 條(原法第13、14 條)在列舉壟斷協議類型時,明確使用了“禁止”一詞,這使得“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是否屬于壟斷協議的構成要件之一存在爭論。實踐中,反壟斷執法機構在處理大多數壟斷協議案件時,均根據涉案行為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即作出違法性認定,實際上跳過了效果要件的判斷過程,且較少對效果要件是否必要作出說明。對此,有觀點認為,競爭損害并非壟斷協議的必備要件,如“目的或者效果”是壟斷協議的選擇性要件,兩者只要具備其一即可。〔2〕參見王先林:《論我國壟斷協議規制制度的實施與完善——以〈反壟斷法〉修訂為視角》,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1 期,第114 頁。有觀點進一步指出,《反壟斷法》第56 條對尚未實施的壟斷協議也規定了處罰措施,也就肯定了不存在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僅有排除、限制競爭的“目的”的行為仍然屬于壟斷協議,即“證明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并非壟斷協議的“必要條件”,“壟斷協議不一定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3〕張世明:《結果論與目的論:壟斷協議認定的法律原理》,載《政法論叢》2020 年第3 期,第4 頁。
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法院的看法雖略有不同,但總體上大同小異。在“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協會壟斷案”中,一審法院認為,壟斷協議的前提是“排除、限制競爭”,判斷是否構成壟斷協議的基本原則在于協議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目的、效果以及不合理地限制了競爭。這里將“排除、限制競爭”同時理解為“目的”“效果”以及限制競爭的不合理性。而二審判決書則指明,判斷本案行為是否構成壟斷,需要“確定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協會在相關市場是否已經產生了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4〕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55 號民事判決書。又將“排除、限制競爭”理解為“效果”。在“銳邦涌和訴強生公司案”(以下簡稱“強生案”)中,二審法院指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2 年發布的《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2012 年反壟斷法司法解釋”)第7 條,“被訴壟斷行為屬于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壟斷協議的,被告應對該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承擔舉證責任”,此處列明的壟斷協議是競爭者之間達成的橫向壟斷協議,其比縱向壟斷協議具有更強的限制競爭效果,既然橫向壟斷協議都存在效果要件,舉重以明輕,縱向壟斷協議自然也應以“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為構成要件。〔5〕參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滬高民三(知)終字第63 號民事判決書。在此之后的一系列壟斷協議民事訴訟案件中,法院均貫徹了“強生案”的判決思路,一再強調壟斷協議應以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為構成要件。在“韓泰輪胎壟斷案”中,法院還特別強調,《反壟斷法》中的“排除、限制競爭”應當理解為行為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而非“目的”,因為“行為目的的判斷是一種主觀判斷”,真實目的難以通過外在行為而準確探知,加之市場行為的復雜性使得行為的目的動機與實際效果并非完全對應,以行為目的作為合法性判斷標準就顯得過于簡單、隨意了。〔6〕參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滬民終475 號民事判決書。
(二)爭議二:個案中“排除、限制競爭”如何證明
壟斷協議的“排除、限制競爭”要件在個案中如何證明,反壟斷執法機構和法院的看法不盡一致。
反壟斷執法機構在認定壟斷協議的違法性時,基于涉案行為屬于典型的壟斷協議類型還是屬于《反壟斷法》中的“兜底項”,采取了不同的認定思路。在《反壟斷法》之外,反壟斷執法機構此前分析壟斷協議的主要依據是《禁止壟斷協議暫行規定》,其第7~12 條明確列舉了禁止經營者達成的壟斷協議類型,并于第13 條規定“不屬于本規定第七條至第十二條所列情形的其他協議、決定或者協同行為,有證據證明排除、限制競爭的,應當認定為壟斷協議并予以禁止”,同時該條列舉了詳細的認定因素。2023 年修訂頒布的《禁止壟斷協議規定》并未改變上述內容,這就意味著在個案中,僅當涉及《反壟斷法》第17、18 條“兜底項”的壟斷協議時,反壟斷執法機構才會詳細分析涉案協議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
對《反壟斷法》明確列舉的典型壟斷協議,從既往案件的處罰決定書可以看出,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分析重心在于協議的達成與實施、協議的內容等客觀事實,而非詳細分析協議的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僅在部分案件中在描述完行為表現后對競爭損害有粗略的說明。不過2021 年的“揚子江藥業案”是少有的例外:反壟斷執法機構不僅詳細闡釋了本案中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的損害效果,并使用了“固定和限定價格行為嚴重排除、限制了競爭”的表述,且以經濟學分析報告作為支撐。總體而言,本案處罰決定書的分析思路并非以“效果”分析為主,而是更側重“目的”分析。在描述涉案行為的損害后果時,處罰決定書首先表述的是“當事人具有強烈的固定和限定價格目的”;在當事人抗辯“排除、限制競爭是縱向價格壟斷協議的構成要件”時,反壟斷執法機構指出:“經營者與交易相對人達成固定轉售價格和限定最低轉售價格協議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競爭,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影響,對此類協議的適用原則依法為原則禁止加例外豁免。”〔7〕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市監處〔2021〕29 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法院在審理壟斷協議案件時的主要依據是《反壟斷法》及“2012 年反壟斷法司法解釋”。關于個案中“排除、限制競爭”的證明責任,司法解釋第7 條提供了基本依據,即“被訴壟斷行為屬于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壟斷協議的,被告應對該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承擔舉證責任”。這意味著,除了典型橫向壟斷協議外的其他所有壟斷協議,包括轉售價格維持協議、非典型壟斷協議(即《反壟斷法》第17、18 條“兜底項”涉及的壟斷協議),均需要原告證明協議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換言之,在承認“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屬于壟斷協議構成要件的前提下,法院對典型橫向壟斷協議與其他壟斷協議案件中效果要件的證明進行了二分。實踐中,除了“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協會壟斷案”〔8〕本案涉及固定價格協議,但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需要先確認涉案行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55 號民事判決書。外,法院對固定價格等典型的橫向壟斷協議皆依據司法解釋第7 條采取了舉證責任倒置的證明思路,即原告僅需證明行為存在,被告對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承擔舉證責任。對于轉售價格維持協議,法院明確指出,由于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明確規定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因此仍應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原則,由原告對涉案協議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承擔舉證責任。〔9〕參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滬高民三(知)終字第63 號民事判決書。
由上可見,反壟斷執法機構與法院的主要觀點分歧在于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的損害效果如何證明上,在典型橫向壟斷協議及非典型壟斷協議方面,兩者的看法一致。
兩種不同的分析模式在“海南裕泰案”中出現了正面交鋒。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二審中支持了反壟斷執法機構的立場,否定了一審法院和“強生案”等縱向壟斷協議民事訴訟案件中法院的一貫主張,明確了反壟斷執法機構不必對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的排除、限制競爭效果予以證明。〔10〕參見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瓊行終1180 號行政判決書。在再審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對二審法院的觀點予以部分肯認,提出某些協議“一旦形成,必然會產生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后果,對這類協議應采取本身違法原則”,即只要協議“被證實存在,就構成壟斷協議”,并認為轉售價格維持協議“一般情況下本身就屬于壟斷協議”,反壟斷執法機構無須對該協議是否符合“排除、限制競爭”這一構成要件承擔舉證責任。〔1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4675 號行政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未按“強生案”的裁判思路而是支持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分析模式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反壟斷私人訴訟與行政執法的目標不同:前者主要目標在于損害賠償,原告除了要證明行為違法外,還要證明違法行為造成了自身損失,即損害后果是必須證明的事項;而后者的目標在于終止違法行為,不在于索賠,故而無需證明存在損害后果,僅需考察涉案行為是否違反了反壟斷法。目標的差異決定了行為認定標準的差異,進而決定了不同的違法分析路徑。〔12〕同上注。最高人民法院主要從不同機構適用反壟斷法的目標差異來區分審查標準的不同,并未從根本上對兩種分析模式予以統一,甚至一定程度上還認可了反壟斷執法機構與法院可以對壟斷協議的違法性認定采取不同的標準。從理論上看,《反壟斷法》不同實施方式的目標盡管有所差異,但無法為壟斷協議分析模式的二元割裂提供充足理由。同一部法律中的制度,不可能因實施機構的不同,行為認定標準就會存在差異。
(三)爭議三:適用禁止條款時是否需要考慮積極效果
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的第三個爭議在于《反壟斷法》第17、18 條與第20 條(原法第15 條)的適用關系。第17、18 條分別對橫向壟斷協議與縱向壟斷協議進行了列舉,并直接使用了“禁止”一詞,屬于“禁止條款”;第20 條規定,若經營者能夠證明協議具有積極影響并滿足一定條件,則不適用上述兩條的禁止性規定,屬于“豁免條款”。
在歐美反壟斷法中,認定壟斷協議的基本思路都是對其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和促進競爭效果進行衡量,只有凈效果為負的壟斷協議才具有最終的違法性。但問題是,我國《反壟斷法》同時規定了禁止條款和豁免條款,凈效果的判斷究竟應放在第17、18 條的禁止條款中,還是要結合第20 條的豁免條款進行分析呢?對此,有觀點主張,適用禁止條款時,需要對協議可能產生的所有限制競爭效果和促進競爭效果進行全面分析,不能只看競爭損害。〔13〕參見蘭磊:《轉售價格維持違法推定之批判》,載《清華法學》2016 年第2 期,第98 頁;蘭磊:《論我國壟斷協議規制的雙層平衡模式》,載《清華法學》2017 年第5 期,第174-175 頁。相反的觀點則認為,如果禁止條款的適用包含了消極效果和積極效果的所有分析內容,那么相當于變相排除了第20 條的適用。〔14〕參見侯利陽:《轉售價格維持的本土化探析:理論沖突、執法異化與路徑選擇》,載《法學家》2016 年第6 期,第77 頁。
對此,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做法是:在認定典型壟斷協議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后,直接作出初步違法判斷或說明其具有損害效果,很少對協議產生的積極效果進行分析。在少數案件中,經營者會主動依據第20 條提出豁免抗辯。例如,在“揚子江藥業案”中,行為人以行為符合《反壟斷法》第20 條第一款(一)項和(四)項為理由申請豁免,但未被反壟斷執法機構采納。總體上說,就轉售價格維持等典型壟斷協議而言,反壟斷執法機構所采納的違法性分析模式可概括為“原則禁止+例外豁免”,豁免依據主要是第20 條,且豁免分析并不是認定協議違法的必經步驟,而是需由行為人自行主張的例外環節。
法院的分析思路與反壟斷執法機構有所不同。在“強生案”中,法院列舉了認定轉售價格維持違法的四個要件:(1)涉案相關市場競爭不夠充分;(2)經營者具有很強的市場地位;(3)行為動機是為了限制競爭;(4)涉案行為的促進競爭效果低于限制競爭效果。〔15〕參見丁文聯:《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的司法評價》,載《法律適用》2014 年第7 期,第61 頁。法院雖然強調了要對行為的促進競爭效果進行分析,但是似乎并不以行為人提出抗辯為前提,即在行為人未依據《反壟斷法》第20 條提出積極效果抗辯的情況下,法院也可能會積極審查涉案行為是否具有抵消消極效果的積極效果。這相當于“越俎代庖”地替被告進行了法律適用和分析。
三、爭議的根源與我國“兩步走”分析模式的確立
產生上述爭議的表面原因在于兩機構適用的法律依據不同,即除了《反壟斷法》外,反壟斷執法機構主要適用《禁止壟斷協議規定》,而法院則嚴格遵循“2012 年反壟斷法司法解釋”。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其實在于,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不僅對歐盟競爭法中的“目的性限制”存在誤解,還將美國與歐盟競爭法下壟斷協議違法性的不同分析模式混淆并“雜糅”在了一起。
(一)效果要件和效果證明的區分
1.壟斷協議應以“損害效果”為要件
從法理上看,凡違法行為均需以“損害效果”為構成要件。若一行為不存在實質性侵害法益的可能,則為“不能犯”,從而不受法律處罰。我國《反壟斷法》關注的法益侵害為競爭損害,在立法上表述為“排除、限制競爭”,但正如刑法中危險犯與實害犯的區分一樣,競爭損害也分為潛在損害和實際損害兩種。對于潛在損害的預防,是反壟斷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我國《反壟斷法》第1 條規定要“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第56 條規定“尚未實施所達成的壟斷協議的,可以處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第34條規定要禁止“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均體現了反壟斷法不僅要制止已經產生實際損害的壟斷行為,還要預防那些具有潛在損害的壟斷行為。很顯然,效果要件包含實際效果和潛在效果兩種狀態。承認壟斷協議的效果要件,并不等于一定要等實際損害發生才能禁止這類行為,也不是說在個案中反壟斷執法機構或原告必須要證明行為產生了實際損害,而是只要行為具有潛在損害,即具有損害競爭的極大可能性,效果要件就得到了滿足。
2.效果要件的證明可以采用簡化方式
學界之所以對壟斷協議的效果要件存在爭論,特別是提出“排除、限制競爭”不能僅理解為“效果”還包括“目的”,主要是受到歐盟“目的性限制”(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概念的影響。從字面上看,“目的性限制”很容易被理解為當事人基于限制競爭“目的”而達成協議的,也可以認定違法行為成立。換言之,壟斷協議概念中的“排除、限制競爭”并非僅指效果,也可以是目的。基于此,有學者主張,我國《反壟斷法》中壟斷協議的定義應當修改為“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目的或效果”的協議。〔16〕參見王先林:《論我國壟斷協議規制制度的實施與完善——以〈反壟斷法〉修訂為視角》,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1 期,第114 頁。還有觀點認為,這里的“目的”與“效果”應該分別對應行為產生的潛在和實際損害。〔17〕參見劉繼峰:《再論壟斷協議的概念問題》,載《法學家》2020 年第6 期,第148 頁。這些理解實際上都是對歐盟競爭法中“目的性限制”的誤解。
其一,歐盟創設“目的性限制”是為了在實踐中簡化效果要件的證明,提高執法效率,而非代替效果要件。原則上,壟斷協議案件中的原告和反壟斷執法機構均應對協議的競爭損害效果進行證明,但由于市場競爭的復雜性以及出于節省法律實施成本的考慮,各國或地區通常將實踐中處理的那些總是或幾乎總是具有顯著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典型協議(如固定價格、限制產量協議)進行歸納,并事先預設其反競爭效果,從而不必再在個案中進行詳細認定。這類協議在歐盟被稱為“目的性限制”,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s)。〔18〕See Alison Jones, Left Behind by Modernisation—Restrictions by Object Under Article 101(1), 6 Eur.Competition J.649 (2010),p.649, 657.由此可見,“目的性限制”的本質是一種效果要件的推定機制,其創設并不在于否定或替代效果要件,而在于簡化損害效果的證明,即在這類案件中,損害效果已經被假設成立了。〔19〕See Sina Tannebaum, The Concept of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 and Article 101(1)TFEU, 22 Maastricht J.Eur.& Comp.L.138 (2015), p.138.這就意味著,在“目的性限制”案件中,舉證責任的重心不在于行為效果,而在于行為本身,只要證明某些協議屬于“目的性限制”的行為類型,就意味著效果要件得到了證明。反之,如果協議不屬于“目的性限制”,那么反壟斷執法機構或原告必須在個案中證明協議具有限制競爭的實際或潛在效果(“效果性限制”)。所以,在歐盟的壟斷協議規制實踐中,“目的性限制”的證明只是第一步,不屬于“目的性限制”的,需再證明屬于“效果性限制”,兩者雖是選擇適用關系,但本質上都指向行為的競爭損害。〔20〕兩種協議類型的適用關系及其分析過程,可參見歐盟委員會發布的《橫向合作協議指南》(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其二,“目的性限制”中的“目的”不宜被簡單地理解為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我國學界目前傾向于將歐盟的“目的性限制”理解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的協議,即“目的”指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如果是這樣的話,歐盟就失去了創設“目的性限制”的意義,因為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比協議的損害效果還難判斷。正因為“目的性限制”本質上還是一種效果分析方法,所以這里的“目的”主要不是指行為人的主觀因素。歐盟委員會在其《橫向合作協議指南》中將“目的性限制”解釋為,就其性質而言(by their very nature),具有潛在或實際競爭損害的協議。而評估一項協議是否屬于“目的性限制”,則主要考慮協議的內容(content)、協議力求達到的目標(objectives),以及協議形成的經濟和法律背景(the economic and legal context)。該指南還特別指出,當事人的意圖(intention)不是確定協議是否具有反競爭“目的”的必要因素。〔21〕參見歐盟委員會《橫向合作協議指南》(2023 年修訂版)第22、23、29 段。當然,這不是說在“目的性限制”認定中完全不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意圖,而是說不能僅憑主觀意圖就認定“目的性限制”成立,主觀意圖只能作為客觀因素的補充。〔22〕See Case C-67/13 P, Groupement des CartesBancaires v.Commission, ECLI: EU: C: 2014: 2204, para.28.可見,“目的性限制”中的“目的”在實踐中主要指向協議本身的性質及其所追求的客觀目標,而非當事人的主觀意圖,〔23〕在“韓泰輪胎壟斷案”中,法院認為“行為目的判斷是一種主觀判斷”,這實際上就是對“目的性限制”的誤解。參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滬民終475 號民事判決書。前者體現為各種客觀因素,后者則指向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因此,即便當事人具有損害競爭的主觀意圖,若其市場力量很小,或相關市場條件及協議內容使得行為在客觀上對市場競爭產生的消極影響微乎其微,則歐盟競爭法就不會僅憑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去譴責其相關行為。
(二)歐美效果要件證明路徑的差異
雖然在歐盟和美國反壟斷法中,壟斷協議的違法性標準本質上相似,但立法規定的不同導致了兩者認定思路上的較大差異,這也一定程度地影響到我國壟斷協議制度的實施。典型表現就是,我國壟斷協議的立法框架源自歐盟,分析模式卻又受到美國的影響,即以美國的分析思路套歐盟的制度框架,最終導致反壟斷執法機構與法院對同種行為采用不同認定標準的尷尬現狀。
1.歐盟的分析步驟:正負效果“分步衡量”
《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是關于壟斷協議的規定,共有3款。第1款對壟斷協議進行了概括禁止,即“凡影響成員國間貿易”,并具有“排除、限制或扭曲內部市場競爭目的或效果”的協議,均受禁止。該款規定的是壟斷協議的競爭損害,且區分了“目的性限制”和“效果性限制”兩種損害類型。第3款規定的是豁免制度,用于考量協議的促進競爭效果。根據該款,符合第1 款的壟斷協議(已經確定有競爭損害),若同時符合以下四個條件,則不受禁止:一是促進了效率,即“有助于改進產品的生產或分銷,或者有助于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二是消費者能夠分享到這種效率;三是限制競爭的協議對實現上述效率具有必要性;四是市場競爭只是受到限制并未被消除。第2 款則宣布,符合第1 款但不符合第3 款(即凈效果為負)的壟斷協議自動無效。
三個條款各有分工,適用順序也很明確:先適用第1 款(評估消極效果),再適用第3 款(評估積極效果),最后才是第2 款(作出最終的效力認定)。第2 款的效力認定依賴于第1 款和第3 款的適用結果,因此歐盟競爭法下壟斷協議的分析模式實際分為兩個步驟(“兩步走”):第一步是適用第101 條第1 款,分析一項協議是否會產生需要《歐盟運行條約》關注的競爭損害,主要體現為反競爭目的(anticompetitive object)或實際/潛在的反競爭效果(actual or potential anti-competitive eあects);協議經第一步評估具有顯著競爭損害的,進入第二步,適用第101 條第3 款分析協議是否會產生促進競爭效果,以及評估這種積極效果是否大于其產生的消極效果。在歐盟競爭法中,“兩步走”的分析思路非常清晰且分工明確:只有在第一步被認定為限制競爭的協議才有進入第二步的必要,而積極效果的衡量僅限于在第3 款下進行,第1 款的適用不會考慮任何積極效果。〔24〕參見歐盟委員會《橫向合作協議指南》(2023 年修訂版)第18、22 段。
2.美國的分析步驟:正負效果“一攬子評估”
美國《謝爾曼法》第1 條起著《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的作用,但與后者分款規定禁止條款(消極效果)和豁免條款(積極效果)不同,《謝爾曼法》第1 條只有禁止性規定,即直接宣布以合同、聯合、共謀等方式限制州與州之間或者與外國之間貿易的行為違法。如果將所有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都認定違法,那么可能過度干預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為此,美國在司法實踐中發展出認定競爭損害的兩種認定標準:本身違法原則和合理原則。前者指某些行為一經實施必然會產生排除、限制競爭后果且缺乏可抵消的積極效果,因此可直接根據行為本身認定其違法。后者肇始于1911 年“標準石油公司案”,聯邦法院在判決中提出,原則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競爭行為才屬于《謝爾曼法》第1 條的禁止范圍。〔25〕See Standard Oil Co.of New Jersey v.United States, 221 U.S.1 (1911), p.87.適用合理原則需要在個案中詳細分析涉案行為的正負效果,而不是僅看行為本身。
不論本身違法原則還是合理原則的適用,或者是其后在這兩個原則之間發展出來的“快速檢視方法”(quick look)和結構性合理原則(structured rules of reason)等,〔26〕參見[美]歐內斯特·蓋爾霍恩、威廉姆·科瓦契奇、斯蒂芬·卡爾金斯:《反壟斷法與經濟學》(第5 版),任勇等譯,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8-190 頁。都是在檢視一個協議可能具有的所有正負效果,只不過有的簡單、有的復雜。本身違法原則并非不承認效果要件,而是說某些壟斷協議(如價格卡特爾)不大可能產生積極效果,或者只會產生少量的積極效果,不足以抵消其更大的消極損害,因此不必在個案中耗費資源去詳細分析,經典的本身違法原則也不允許當事人抗辯。合理原則的適用則需要原告和法院全面考察涉案協議的積極影響。這些原則都是《謝爾曼法》第1 條的適用方法,其適用過程都需要在該條的禁止性規定下完成。
美國模式與歐盟存在的重要區別在于:《謝爾曼法》第1 條提供了壟斷協議認定的所有規范依據,除此之外并不存在獨立的豁免條款,所以壟斷協議積極效果的衡量也需要在第1 條下完成。這與歐盟既存在壟斷協議的禁止條款,也存在壟斷協議的豁免條款,進而使得消極效果和積極效果的衡量分別擁有獨立的規范依據明顯不同。以“本身違法”和“目的性限制”為例,二者雖然在適用的協議類型上存在重合,但是適用效果有著顯著差異:前者是對協議凈效果為負的認定(認定過程已全部完成,當事人不能再抗辯);后者僅是對協議具有消極效果的推定(僅是認定的第一步,當事人仍可援引豁免條款抗辯,即主張還存在更大的積極效果)。〔27〕在歐盟競爭法中,即便是固定價格、轉售價格維持等“目的性限制”,當事人仍可依據《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3 款提出抗辯,盡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抗辯是當事人的權利,也是壟斷協議違法性認定的重要步驟。這種不同正是歐美壟斷協議分析模式存在差異的制度根源。總的來看,與歐盟壟斷協議認定中消極效果與積極效果的分步衡量不同,美國采用的是典型的“一攬子評估”模式。《謝爾曼法》第1 條衍生出來的合理原則,既有《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款承載的功能,也有第3 款承載的功能。
(三)我國的選擇:“兩步走”分析模式
如上所述,歐盟競爭法下壟斷協議違法性的分步衡量分析模式與其立法規定一脈相承,且體現為高度形式化的環環相扣的法律適用過程。這種分析模式在歐盟委員會頒布的《橫向合作協議指南》《壟斷協議豁免指南》《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縱向限制指南》等一系列配套規定中都有非常明顯的體現。相比之下,美國法院確立的“一攬子評估”模式更加依賴先例和法官的自由心證,這使得《謝爾曼法》第1 條的適用十分靈活。我國《反壟斷法》中的壟斷協議制度主要以歐盟立法為藍本,其第17、18 條的禁止性規定基本對應《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 款,第20 條的豁免規定則對應第101條第3 款,所以,歐盟的分步衡量分析模式更加貼合我國的立法規定。但由于實踐中對美國合理原則的不當引入,導致我國壟斷協議的分析模式實際上處在歐盟模式與美國模式的交織之中,從邏輯上看,這兩種模式其實是互斥的。〔28〕我國《反壟斷法》存在獨立的豁免條款,因此對第17、18 條規定的典型壟斷協議,也允許當事人依據豁免條款提出抗辯,這意味著我國反壟斷法中并不存在本身違法原則。新修訂的《反壟斷法》對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的競爭損害新設了一個當事人的抗辯條款(第18 條第2 款),這更加使得本身違法原則難以與我國現行立法相兼容。
“強生案”的法律適用具有很大的典型性。法院認定應由原告負擔行為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舉證責任,并列出了轉售價格維持的四個分析要件,之后被告進行了三點反駁:(1)涉案行為有利于增強企業內部管理體系和提高企業知名度;(2)涉案行為有利于提高服務質量,防止“搭便車”;(3)涉案行為僅限制品牌內競爭而不影響品牌間競爭。其中前兩點是“積極效果”,屬于豁免條款即第20 條的分析范圍,第三點是“消極效果”,屬于第18 條的分析范圍。但在本案中,無論法院還是當事人,對于行為正負競爭效果的判斷和證明均在第18 條(原法第14 條)下進行,使得本屬于法律適用不同環節的事項被納入了同一環節。這一做法不僅造成了訴訟程序中舉證責任的配置混亂,而且架空了第20 條的適用空間。之所以產生這種錯亂,本質上是因為將美國的合理原則引入我國《反壟斷法》禁止規定(第17 條或第18 條)的適用中,而忽視了《反壟斷法》中還存在獨立的豁免規定(第20 條)——只有豁免規定才是評估壟斷協議積極效果的法律依據。
為了防止壟斷協議案件處理中不適當地將美國法的分析模式套用于歐盟法的制度框架中,我國應在遵循《反壟斷法》文本的基礎上,確立與立法規定相適應的壟斷協議違法性分析模式,即堅持《歐盟運行條約》設置的“兩步走”分析框架:(1)在禁止條款下評估協議的消極效果,以確定一項協議是否屬于反壟斷法所要關注的“壟斷協議”;(2)在豁免條款下評估壟斷協議的積極效果,以確定其是否需要反壟斷法作出最后的違法性認定。
四、適用第17 條或18 條:在禁止條款下評估消極效果
(一)確認是否構成壟斷協議:識別競爭損害
壟斷協議分析的第一步在于確認當事人達成的協議是反壟斷法所關注的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協議,即壟斷協議,而非一般的合作協議或交易合同。企業的市場行為特別是合同很容易產生各種損害,但并非所有的損害都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總的來說,判斷一種協議是否落入《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主要看其是否產生了法律所關注的競爭損害,即是否侵犯了反壟斷法所保護的法益。而根據歐盟判例法,反壟斷法通常只會關注較為嚴重的、人為導致的、本可避免的限制競爭效果。
這一步在歐盟體現為對《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 款的適用,在我國則體現為對《反壟斷法》第17、18 條的適用。盡管這些條款在立法中的表述方式都是禁止性的,但其適用目的僅在于判斷某種協議是否屬于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而非終局意義上的禁止,所以其僅為分析壟斷協議的第一步而非全部,有學者將這種禁止理解為管轄權意義上的禁止,而非真正的禁止。〔29〕參見許光耀:《轉售價格維持的反壟斷法分析》,載《政法論叢》2011 年第4 期,第98 頁。
禁止條款的具體適用,體現為分析涉案協議的消極效果。在歐盟,這又被分解為“目的性限制”和“效果性限制”兩個步驟。《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 款禁止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的協議,從立法上看,目的或效果似乎沒有判斷的先后順序,但根據《橫向合作協議指南》,一旦某項協議的反競爭“目的”確立,就不必再審查其對市場的實際或潛在影響。也就是說,效果審查以不存在限制競爭目的為前提,具有限制競爭目的的協議已可以推定禁止,不必再進一步考察其限制競爭效果。如前所述,這里的“目的性限制”只是一種效果判斷的簡化機制,本質上也是一種效果判斷,只不過采用了推定方式。之所以能夠推定,是基于這類協議限制競爭的固有屬性,也是基于豐富的執法和司法經驗。在歐盟競爭法中,“目的性限制”主要指“核心限制”,即在歐盟各個豁免條例中被列入黑名單(black-listed)的那些限制競爭協議,如固定價格、限制產量、劃分市場等。
如果一項協議不屬于“目的性限制”的范圍,那么就必須詳細考察它是否具有限制競爭效果。效果分析要考慮實際與潛在效果兩個方面。換言之,該協議至少要具備可能的反競爭效果。在競爭法中,反競爭效果主要指協議對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產量、質量、多樣性及創新等方面產生的負面影響。為此,通常需要分析協議的性質和內容、各方單獨或共同擁有的市場力量大小,以及協議在多大程度上會創造、維持或加強相關方的市場力量。〔30〕參見歐盟委員會《橫向合作協議指南》(2023 年修訂版)第30 段。
在我國,對壟斷協議第一步的分析也借鑒了歐盟的“目的”和“效果”兩種方法,即對于《反壟斷法》第17、18 條明文列舉的協議類型,默認其具有反競爭效果,而對于“兜底項”中的協議,則需原告和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協議的消極效果進行證明。但需注意的是,與歐盟“目的性限制”有所不同的是,新修訂的《反壟斷法》對典型橫向壟斷協議和典型縱向壟斷協議采取了有區別的分析方式。在歐盟法下,若協議構成“目的性限制”,其對競爭的消極影響就是不容置疑的(clear beyond doubt),經營者不會被給予機會證明協議沒有損害,“目的性限制”想要避免被禁止,當事人只能依據豁免條款進行抗辯。〔31〕See Case C- 67/13 P, Groupement des cartesbancaires (CB)v.European Commission, ECLI: EU: C: 2014:1958, para.25.但依據新修訂的《反壟斷法》,轉售價格維持的行為人還能夠依據第18 條第2 款證明協議不具有反競爭效果。這意味著,對典型的橫向協議,我國采取了反競爭效果的“絕對推定”,當事人無法抗辯協議沒有損害;對于典型的縱向壟斷協議,我國則采取了反競爭效果的“相對推定”,當事人仍可抗辯協議沒有損害。前者與歐盟的“目的性限制”一致;后者則讓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的當事人在第一步分析中就獲得了一個額外的抗辯機會,即證明協議沒有損害——盡管這種抗辯事實上很難成功。〔32〕縱向壟斷協議一旦達成,基本都會有或大或小的損害效果。歐盟競爭法在判例中確立了一項基本規則,即僅禁止嚴重限制競爭的壟斷協議,而不包括輕微限制競爭的壟斷協議。我國反壟斷立法與實踐中還不存在這項規則,這意味著縱向壟斷協議只要有了損害效果,就符合第18 條第1 款的認定,而較難再依據第2 款作出抗辯。
(二)壟斷協議的排除機制:兩種推定規則
“目的性限制”作為一種反競爭效果的推定機制,雖能節約法律適用成本、提升案件處理效率,但因受限于法律的滯后性和經濟行為的復雜性而不宜擴大適用范圍,所以仍有大量的行為無法通過“目的性限制”來確認其屬于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進而需要進一步分析其限制競爭效果。而效果分析比較復雜,不是單純的法律適用過程,還依賴于經濟分析,其雖可能會減少不當的市場干預,但也會增加法律的實施成本。基于此,為了緩和效果分析不確定性與法律制度可預期性之間的矛盾,歐盟競爭法在實施中基于經驗確立了兩種推定規則,規定符合某些條件的協議,推定其不具有反壟斷法意義上的限制競爭效果,因而不構成“壟斷協議”,不屬于反壟斷法的管轄范圍。
1.定量推定:低影響協議規則
反壟斷法通常只關注對競爭損害較嚴重的行為,這是歐盟競爭法實踐確立的一項重要規則。在1969 年的“V?lk 案”中,歐洲法院認為,如果考慮到相關主體在相關市場上的弱勢地位,該協議對市場僅產生了微不足道的影響,那么其不在歐盟競爭法的禁止范圍內。〔33〕See Case 5-69,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9 July 1969, Franz V?lk v.S.P.R.L.Ets J.Vervaecke, ECLI identifier: ECLI: EU: C: 1969:35, para.7.該案確立了《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 款的適用門檻,即一項協議的限制競爭效果必須達到“顯著”的程度(appreciable restrictive eあects),才被認為是一項“壟斷協議”。
為了更確定地判斷“顯著”與否,2001 年歐盟委員會頒布了《關于影響較小的協議的通告》(簡稱“低影響協議通告”,2014 年該通告重新頒布)。〔34〕See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1)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 Minimis Notice), OJ [2014]C 291/1.根據通告,當協議當事人是實際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即競爭者之間的協議),且在相關市場上的份額總和不超過10%,或者協議當事人不具有競爭關系(即非競爭者之間的協議),且在相關市場上的份額均不超過15%時,該協議通常不會對競爭產生較大限制,因而也就沒有必要認定為《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 款意義上的壟斷協議。若難以分清某一協議是競爭者之間還是非競爭者之間的協議,則適用10%的最小市場份額門檻。“低影響協議通告”確立的是一種“安全港”規則,是歐盟壟斷協議認定中的第一個“安全港”,其背后的原理是只有產生顯著限制競爭損害的行為才具有反壟斷法上的違法性。2004 年歐盟委員會發布的《壟斷協議豁免指南》再次重述了該原理,其中第24 段規定,對一項“效果性限制”來說,其負面效果應當是相當顯著的,當所確認的反競爭效果不顯著時,《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1 款確立的禁止性規則不予適用。“低影響協議通告”正是通過市場份額的量化從反面排除了不大可能影響市場競爭的協議,從而在第一步就排除了第101 條第1 款的適用。當然,即便經營者的市場份額超過了通告中的閾值,也不意味著協議的限制程度必然具備“顯著性”,仍需要進行個案認定。
2.定性推定:附屬性限制規則
“附屬性限制”理論(ancillary restraint doctrine)起源于美國,〔35〕See Gregory J.Werden, The Ancillary Restraints Doctrine after Dagher, 8 Sedona Conf.J.17, p.17.由歐盟法院引入司法實踐,〔36〕歐盟法院在2001 年的“M6 案”中正式解釋了什么是附屬性限制,即與一項主要目標的實現具有直接關聯并且必要的限制。See Case T-112 /99, Métropoletélévision(M6)and others v.Commission, [2001]ECR.II-2459, para.104.并在歐盟委員會發布的《壟斷協議豁免指南》及“與經營者集中直接相關且必要的限制的通告”中被固定下來。在歐盟競爭法中,若一項限制競爭行為具有附屬性,則不為法律所禁止。根據上述指南及通告,附屬限制理論適用于以下情況:限制競爭行為附屬于一個合法的、非限制性的主合同或商業活動,且限制競爭行為對主合同目標的實現具有客觀必要性(objectively necessary)并合乎比例(proportionate)。之所以要進行客觀必要性和比例性分析,是為了確認,如果不施加此類限制,那么具有合法目標的主合同將難以或不可能實現。在此情況下,適度的限制競爭應當被允許。如果這類附屬性限制落入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那么其服務的主合同可能就難以實現,否認這類附屬性限制,就是否認主合同。
附屬性限制規則與“低影響協議通告”的功能相同,即排除反壟斷法中禁止條款的適用,這意味著對涉案協議的分析在第一步就結束了,即推定缺乏反競爭效果進而無需進入第二步的積極效果衡量環節。不過這兩個推定規則在理論基礎與適用標準上存在差異。“低影響協議通告”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通過設置一定的市場份額門檻,識別出那些不大可能具有嚴重排除、限制競爭影響的協議,這些協議因當事人市場份額低,即便具有消極效果,也達不到禁止條款所要求的“顯著”程度。附屬性限制規則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以相關協議具有限制競爭效果為前提,但著眼于協議整體,對那些具有“附屬性”的限制競爭行為排除禁止條款的適用,旨在以較小的犧牲追求更大的目標。
五、適用第20 條:在豁免條款下評估積極效果
(一)豁免條款的功能與性質
在“兩步走”的框架下,第一步(禁止條款的適用)在于劃定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若某項協議被認為具有顯著的限制競爭效果,則進入第二步(豁免條款的適用),對正負效果進行權衡。豁免的性質不是責任阻卻,而是直接認定行為不違法,其功能類似于刑法中的違法阻卻事由。在歐盟及我國反壟斷法中,經禁止條款認定具有競爭損害的協議若符合豁免條件,則不僅不受禁止,當事人還可以繼續實施該協議,其他企業也可在商業活動中效仿。若將豁免條款視為責任阻卻事由,則意味著行為人雖免于承擔不利法律后果,但其行為的法律價值評價為負,其他人也不能效仿——我國反壟斷法中的“寬大制度”就是典型的責任阻卻事由。從此意義上看,壟斷協議的性質認定必須經過“兩步走”的完整分析過程,僅適用禁止條款并不能得出協議是否違法的最終結論。只不過第二步既然是豁免條款的適用,意味著主要由行為人來證明其協議符合豁免條件,實踐中若行為人放棄豁免抗辯,則反壟斷執法機構或法院可省去這一步而直接認定協議違法。
在“兩步走”的分析模式中,積極效果的分析專屬于豁免條款。如果在禁止條款的適用中就要求全面考察協議的消極效果與積極效果,那么無異于廢除了豁免條款。《歐盟運行條約》第101 條第3款對積極效果的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即有助于改進產品的生產或分銷,或者有助于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效果(經濟效率)。相比之下,我國《反壟斷法》第20 條的內容更為豐富,既有經濟效果,也有非經濟效果。《反壟斷法》第20 條列舉了多種豁免情形,其中“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統一產品規格、標準或者實行專業化分工”等屬于典型的經濟效果內容,而“為實現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救災救助等社會公共利益”則屬于典型的非經濟效果內容。
當然,不是只要壟斷協議產生了上述好處就可以得到豁免。根據歐盟和我國反壟斷法的規定,最終能被豁免的協議還需滿足另外幾個條件:第一,協議帶來的好處要大于造成的損害,即凈效果必須為正。這在《歐盟運行條約》中主要體現為“不能消除競爭”,在我國《反壟斷法》中體現為“不會嚴重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如果協議對市場競爭的限制效果非常嚴重,甚至達到了消除競爭的程度,那么其帶來的積極效果就很難抵消這種損害。第二,協議帶來的好處要能傳遞到消費者身上,即不能由行為人獨享而使消費者遭殃。這由反壟斷法維護消費者利益的目標決定,也是在平衡“生產者剩余”與“消費者剩余”的內在沖突。第三,《歐盟運行條約》還規定了一個我國《反壟斷法》中未明確提及的條件,即限制競爭行為在實現上述好處時具有必不可少性,即不存在其他非限制性或限制效果更小的手段能帶來同樣的好處。這個《反壟斷法》中缺失的要件已在《禁止壟斷協議規定》中得到了彌補:其在第20 條指出,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定被調查的壟斷協議是否屬于第20 條規定的情形,應當考慮的因素之一是“協議是否是實現該情形的必要條件”。
從當前的實踐看,反壟斷執法機構和法院似乎對豁免條款的功能存在誤解。如前所述,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壟斷協議的認定主要采取“原則禁止+例外豁免”的分析模式,雖然很少適用豁免條款考慮行為的積極效果,但是由于是否符合豁免規定應由行為人證明,而非執法機構的義務,所以嚴格來說,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認定思路并無明顯錯誤。不過在個別案件中,反壟斷執法機構認為固定價格等協議屬于“本身違法”,〔37〕參見重慶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渝市監經處字〔2019〕第5 號行政處罰決定書。或者表明對這類行為的判斷不適用合理原則,從而不予采納當事人的申辯,〔38〕參見云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云市監競處字〔2022〕01 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這種分析思路實際上忽略了《反壟斷法》中還存在獨立的豁免條款以及積極效果分析步驟的獨立性,對典型的壟斷協議誤用了美國“本身違法”的分析模式。這種誤解在反壟斷民事訴訟領域同樣存在。法院雖然主張需要對壟斷協議的正負競爭效果進行全面評估,但并未嚴格依據《反壟斷法》確立的分析步驟,而是采用了美國的合理原則模式,在適用《反壟斷法》第18 條時就對協議的消極效果與積極效果進行了“一攬子評估”,進而使第20 條喪失了法律規范的意義。此外,在“海南裕泰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有些經營者之間的協議、決定或者協同一致的行為,一旦形成,必然會產生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后果,對這類協議應采取本身違法原則。”這里直接將本身違法原則適用于我國,忽略了我國《反壟斷法》與美國《謝爾曼法》的立法差異。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對原《反壟斷法》第13、14、15 條的性質作了如下解釋:“《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與第十四條分別對橫向壟斷協議及縱向壟斷協議作出規定,同時在第十五條規定了可以不認定為壟斷協議的例外情形。”〔39〕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4675 號行政裁定書。這個表述實際上也混淆了“壟斷協議的認定”與“壟斷協議違法性的認定”這兩個問題,錯置了不同法律條文的功能定位,因為若行為人適用原法第15 條抗辯成功,其法律效果并非不將涉案行為認定為壟斷協議(這是第一步的任務),而是宣布已被認定為壟斷協議的行為不需要禁止(這是第二步的任務)。
(二)推定合法:集體豁免制度
基于豁免條款的適用往往會給行為人帶來較為沉重的舉證負擔,對此歐盟競爭法中發展出了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制度。該制度適用于壟斷協議分析的第二步,功能在于通過量化的市場份額門檻推定某些協議的積極效果大于消極效果,因而無需禁止,從而免去了在個案中對行為促進競爭效果的復雜經濟分析過程。
集體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某些特殊類型的壟斷協議(如大部分縱向協議、競爭之間的研發協議等),一般都能產生明顯的促進競爭效果,并對消費者有利,因此只要其限制競爭效果不太嚴重,其積極效果都能抵消消極效果。所以,為了避免個案中的煩瑣分析過程,可以將這類協議類型化,然后直接予以豁免。只要篩選好適用范圍,設定好豁免條件,將損害效果不太嚴重同時積極效果明顯的那部分壟斷協議識別出來,集體豁免一般不會出現“放縱”違法行為的結果。在各種豁免條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市場份額標準,即只要當事人的市場份額不太高,這類協議的促進競爭效果通常能夠覆蓋其限制競爭效果。以歐盟《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為例,〔40〕歐盟競爭法中的集體豁免條例較多,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1)縱向協議的集體豁免條例,主要是一般性的《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以及適用于特殊領域的《汽車業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2)橫向協議的集體豁免條例,主要是《研發協議集體豁免條例》《專業分工協議集體豁免條例》《班輪運輸聯盟集體豁免條例》《保險業集體豁免條例》(現已失效);(3)既涉及橫向協議也涉及縱向協議的豁免條例,主要是《技術轉讓協議集體豁免條例》。上述條例規定的集體豁免標準主要是市場份額,但不同條例設定的市場份額閾值不同。其規定,就一些縱向壟斷協議來說,當生產商和購買商(即協議的雙方當事人)在相關市場上的份額均不超過30%時,可依本條例直接予以豁免。〔41〕參見歐盟《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2022)第3 條。這是歐盟壟斷協議認定中的第二個“安全港”。
在歐盟競爭法中,集體豁免制度的適用發生在壟斷協議分析的第二步,因此從邏輯上看,其適用前提是相關協議已經經過了第一步的分析,即被證明具有嚴重的競爭損害,進而屬于壟斷協議,落入了禁止條款的范圍內。〔42〕參見歐盟《縱向限制指南》(2022)第23 段。不過在實踐操作中,也可不必經過第一步的損害分析而徑行適用集體豁免制度。〔43〕參見歐盟《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2022)序言第4 段。這并不是對“兩步走”分析框架的突破或背離,而是一種簡便機制,因為即便經過了第一步的分析過程,在第二步適用豁免條款時,只要發現市場份額較低,也可認定協議合法,既然如此,也可以一開始就直接依據相對好判斷的市場份額標準來進行終局性認定。這種簡便的適用方法不僅能大大提升案件的處理效率,也給予了當事人申請集體豁免的更大激勵。
集體豁免制度與“低影響協議通告”都是歐盟壟斷協議認定中的“安全港”機制。二者的形式區別在于“安全”的市場份額標準不同;實質區別則在于兩種制度的性質存在較大差異。“低影響協議通告”適用于壟斷協議分析的第一步,其功能在于推定某項協議不具有反競爭效果,即不屬于“壟斷協議”;集體豁免制度適用于第二步,在涉案協議已構成“壟斷協議”的情況下,通過市場份額推定協議具有更大的積極效果,進而豁免該壟斷協議。這兩項基于市場份額的推定規則,共同構成了歐盟壟斷協議分析中的“安全港”制度。〔44〕集體豁免制度和“低影響協議通告”在歐盟相關指南中均被稱為“安全港”制度。See Guidance on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by object”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which agreements may benefit from the De Minimis Notice, SWD(2014)198 final, p.3.
我國《反壟斷法》中也存在“安全港”制度,2022 年《反壟斷法》修訂前,相關規定體現為《關于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第13 條和《關于汽車業的反壟斷指南》第4 條。修訂后的《反壟斷法》第18 條第3 款也規定了“安全港”,只是當前“安全港”制度的性質較為混亂。在《關于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中,“安全港”的適用效果為“通常不將其達成的涉及知識產權的協議認定為《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六項和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的壟斷協議”,即符合條件的協議不被認定為壟斷協議,這類似于歐盟的第一個“安全港”。在《關于汽車業的反壟斷指南》中,“安全港”的適用效果為“可以推定適用《反壟斷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即符合條件的協議雖然構成本應禁止的壟斷協議,但是推定豁免,這類似于歐盟的第二個“安全港”。在2022 年修訂的《反壟斷法》中,“安全港”的表述是:“經營者能夠證明其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低于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標準,并符合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不予禁止。”從字面上看,這里的“不予禁止”似可理解為包含“不構成壟斷協議”和“雖然構成壟斷協議但符合豁免規定”兩種情形。相比之下,在2021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反壟斷法(修正草案)》中,“安全港”的適用效果被表述為“不適用本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即排除禁止條款的適用,這更像是確認涉案協議沒有消極效果因而不構成壟斷協議。但實際上,由于新法中的“安全港”規定在第18 條即壟斷協議的禁止條款項下,因而從體系解釋的角度看,其性質應當與《關于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和歐盟的“低影響協議通告”相似,即符合條件的協議直接不被認定為壟斷協議。換言之,新法確定的“安全港”規則適用于壟斷協議分析的第一步。
不過,《反壟斷法》確定的“安全港”規則,僅適用于縱向壟斷協議,但同時又將兩類典型縱向協議納入了調整范圍,這與《關于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不同,也與歐盟的兩項“安全港”規則均不適用于“核心限制”存在明顯區別。歐盟之所以將轉售價格維持等核心限制排除在“低影響協議通告”的適用范疇之外,是因為這類協議已經滿足了“顯著”損害競爭的標準。我國《反壟斷法》第17、18 條對明確列舉的典型壟斷協議采取了損害效果的認定或推定模式,說明執法或司法實踐已經承認典型壟斷協議通常會產生較明顯的競爭損害,若轉售價格維持也適用“安全港”規則,則不僅有悖“安全港”制度的性質定位,實踐中也可能使大多的轉售價格維持行為逃脫法律制裁。〔45〕例如,在國家發改委處理的合生元等乳粉企業限制轉售價格壟斷案中,這些乳粉生產商的平均市場份額為11%,通常符合“安全港”規則下的市場份額門檻[2022 年6 月公布的《禁止壟斷協議規定(征求意見稿)》曾將“安全港”的市場份額門檻設定為15%],但由于各大品牌乳粉生產商均實施相同的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累積效果明顯,因而涉案協議不僅對品牌內競爭,也對品牌間競爭產生了較大的限制效果。參見許光耀:《轉售價格維持案件中壟斷行為的識別——兼評新〈反壟斷法〉第18 條》,載《法學評論》2023 年第2 期,第13 頁。2023 年3 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公布了修訂后的《禁止壟斷協議規定》,對“安全港”的適用條件和適用程序都進行了模糊化處理,一定程度上給“安全港”制度的細化留下了更多時間和空間。未來“安全港”規則的適用條件可以考慮兩個方案:一是在市場份額標準上,對轉售價格維持協議和“兜底項”設置不同的閾值;二是設置相同的市場份額閾值,但借助《反壟斷法》第18 條允許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其他條件”,對轉售價格維持協議適用“安全港”時,要求當事人額外證明涉案協議具有“附屬性”,以進一步提高“安全港”規則對轉售價格維持協議的適用門檻。
六、結論
壟斷協議分析模式的確立需立足于法律文本,并厘清多個法律條文背后的邏輯關系。壟斷協議定義中“排除、限制競爭”的本質是行為構成中的效果要件。反壟斷法所禁止的壟斷協議,一定是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協議,否則沒有禁止的理由。如果一項協議事實上不可能產生任何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那么就不屬于反壟斷法的管轄范圍,反壟斷執法機構也就沒有調查之必要。不過,承認效果要件并非要求個案中必須證明產生了實際損害,潛在損害也包含在效果要件之中。換言之,這里的損害效果,既包括實際損害,也包括潛在損害,即只要某項協議具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就符合效果標準,而不是說非要等到損害競爭的實際效果發生才去禁止。歐盟競爭法中雖然存在“目的性限制”的概念,即將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目的”的協議視為壟斷協議,但這里的“目的”并非純粹的當事人的主觀意圖,而是一種效果的推定機制,本質上仍是效果要件。所以,不宜將單純的主觀目的作為壟斷協議的違法性標準。我國新修訂的《反壟斷法》并未增加限制競爭“目的”的表述,是一種更合理的選擇,因為所謂的“目的”不過是競爭損害效果的一種推定方法,增加“目的”的規定反而容易引起不當的誤解。
承認效果要件并不意味著所有壟斷協議案件中的損害效果都由反壟斷執法機構或原告證明。對于典型的協議類型,可推定或直接認定其存在競爭損害。嚴格來說,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認定一般應基于個案,但長期實踐表明,某些協議產生消極效果的可能性極大或限制程度非常明顯,對于這些協議,基于節約執法資源的考慮,可以適用類似歐盟“目的性限制”的分析方法,推定其具有反競爭效果,然后再由行為人反證。美國的本身違法原則與歐盟的“核心限制”規則解決的就是這樣的問題。我國《反壟斷法》第17、18 條兜底項之前的列舉規定,涉及的也是這些協議類型,所以,應將這些明確列舉的協議視為“核心限制”,實踐中只要能夠證明這些協議的存在,就推定其已經符合了壟斷協議的構成要件,即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而不必再作進一步認定。對于列舉規定之外的協議,則需要堅持嚴格的效果分析,即必須證明其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才能認定其屬于壟斷協議。
競爭損害分析只是壟斷協議違法性認定的第一步,對于所有的壟斷協議,包括推定禁止的壟斷協議,都應當允許當事人依據《反壟斷法》第20 條提出豁免抗辯。在我國現行的立法框架下,壟斷協議的違法性認定可以堅持“兩步走”分析模式:《反壟斷法》第17、18 條解決的是壟斷協議的競爭損害問題(第一步),第20 條則提供了分析壟斷協議積極效果的基本方法(第二步)。不過,豁免抗辯是當事人的權利,而不是執法機構的義務,故需要行為人承擔符合豁免情形和豁免條件的證明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