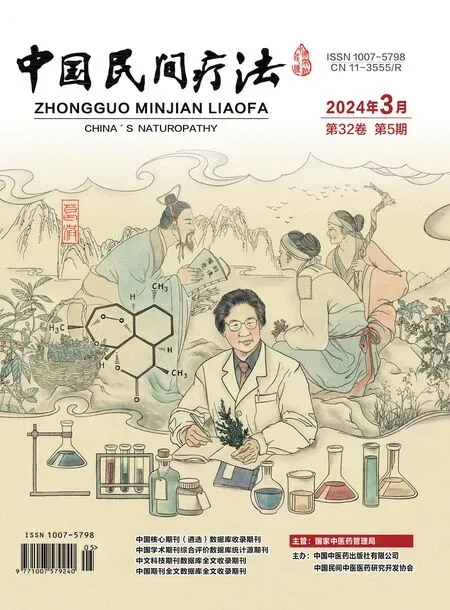除濕消疹一號方內服外洗治療急性、亞急性肛周濕疹的臨床觀察※
陳澤芃,顧慶龍,陳瑞超
(1.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南京 210029;2.江蘇省徐州市中醫院,江蘇徐州 221000)
肛周濕疹是肛腸科常見病之一,是一種非傳染性炎癥性肛周皮膚病,發生于肛門及其周圍皮膚,也可延及臀部及會陰等處。中醫病名有“風濕瘍”“腎囊風”“繡球風”“癢風”“谷道癢”“浸淫瘡”等,主要表現為肛周及會陰潮濕、瘙癢、皮膚丘疹、丘皰疹、浸潤肥厚、皸裂、鱗屑、結痂、苔蘚樣變,多伴有坐立不安等[1]。西醫根據病情的發展可分為急性、亞急性、慢性肛周濕疹,主要采用抗組胺藥及類固醇皮質激素、乳膏類藥物等對癥治療,但停藥后易復發,難以根治[2]。中醫認為肛周濕疹多因風、濕、熱邪侵入機體,飲食偏嗜辛辣刺激、肥甘厚味,導致脾胃功能受損,運化失常,加之肛門不潔,誘發肛周濕疹[3]。目前,中醫治療肛周濕疹方法較多,且療效較好,不易復發。徐州市中醫院肛腸科陳瑞超主任采用自擬除濕消疹一號方內服聯合局部熏洗坐浴治療急性、亞急性肛周濕疹,取得較好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選取徐州市中醫院肛腸科門診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60例急性、亞急性肛周濕疹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每組30 例。對照組男16 例,女14 例;年齡18~60歲,平均(39.1±7.2)歲;病程3~15 d,平均(8.6±1.5)d。治療組男16例,女14例;年齡18~60歲,平均(37.5±8.1)歲;病程4~20 d,平均(7.9±1.1)d。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中相關倫理學要求[4]。
1.2 診斷標準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制定相關診斷標準[5]。①急性肛周濕疹:發病較快,病程較長,初起時皮膚損害有紅斑、丘疹、滲出、糜爛、結痂、脫屑等,一般表現為1種。輕者微癢,重者瘙癢劇烈,難以忍受,呈間歇性或陣發性發作,夜間增劇。②亞急性肛周濕疹:多由急性濕疹遷延不愈而來,病情較緩慢;水皰不多,滲液少,尚可見紅斑、丘疹、鱗屑、痂皮、糜爛等[5]。
1.3 納入標準 符合上述診斷標準;無肛腸病手術史;無肛門功能異常;年齡≥18周歲;患者及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4 排除標準 由結核、梅毒、艾滋病、克羅恩病等引起的特異性肛腸病者;合并有胃腸腫瘤、炎性腸病、慢性潰瘍、直腸息肉等其他嚴重肛門直腸疾病者;妊娠期、哺乳期者;患有血液病、免疫系統疾病者;有嚴重心、肝、腎、腦血管疾病及其他嚴重危及生命的原發性疾病者;局部皮膚有苔蘚樣變者;正在接受其他相關治療者。
2 治療方法
2.1 對照組 口服鹽酸西替利嗪片(UCB Farchim SA,國藥準字HJ20171304,10 mg/片),每次10 mg,每日1次;局部外涂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00454,10 g/支),每日2次。治療2周。
2.2 治療組 ①中藥內服。除濕消疹一號方:苦參15 g,黃柏15 g,地膚子15 g,蛇床子10 g,茯苓20 g,甘草片6 g。脾胃虛寒者,加3片生姜。每日1劑,每劑中藥水煎2次,取藥液150 m L,分早晚2次口服,連服2周。②中藥熏洗及坐浴。除濕消疹一號方先熏洗后坐浴:苦參20 g,黃柏20 g,地膚子20 g,蛇床子20 g,茯苓20 g,甘草片10 g。每劑中藥煎取藥液約400 m L,先熏蒸5 min,再坐浴10 min左右(水溫不要太燙)。每日1次。每日坐浴后瘡面換藥。治療2周。
兩組患者治療期間均保持肛周局部干燥,忌食辛辣刺激、海鮮及其他易導致復發的食物,戒煙酒,不熬夜。
3 療效觀察
3.1 觀察指標 分別記錄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皮損面積和肛門瘙癢、潮濕程度積分,并計算總積分。①肛門瘙癢程度。無瘙癢,計0 分;偶感輕度瘙癢,計2分;中度瘙癢呈間歇性,計4分;重度瘙癢呈持續性、坐臥不寧,計6分。②皮損面積。皮損不明顯,計0分;輕度:≤10 cm2,計2分;中度:>10 cm2且≤20 cm2,計4分;重度:>20 cm2,計6分。③肛門潮濕程度。無滲液,計0分;輕度:紗布有少量分泌物,計2分;中度:分泌物濕透2次紗布,計4分;重度:分泌物濕透3次以上紗布,計6分。
3.2 療效評定標準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制定療效標準[5]。痊愈:癥狀、體征消失,證候積分減少率≥95%;顯效:癥狀、體征明顯改善,證候積分減少率≥70%且<95%;有效:癥狀、體征均有好轉,證候積分減少率≥30%且<70%;無效:癥狀、體征改善不明顯,證候積分減少率<30%。證候積分減少率(尼莫地平法)=(治療前積分-治療后積分)/治療前積分×100%。痊愈、顯效、有效計為總有效。
3.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4 結果
(1)瘙癢、皮損、潮濕積分及總積分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的瘙癢、皮損、潮濕積分及總積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瘙癢、皮損、潮濕積分及總積分均較治療前下降,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急性、亞急性肛周濕疹患者治療前后皮損、瘙癢、潮濕積分及總積分比較(分,±s)

表1 兩組急性、亞急性肛周濕疹患者治療前后皮損、瘙癢、潮濕積分及總積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5。
組別例數時間瘙癢積分皮損積分治療組 30治療前 4.3±1.6 4.2±1.9治療后 0.7±0.3△▲ 0.7±0.3△▲對照組 30治療前 4.6±2.1 4.1±1.7治療后 1.6±0.7△ 1.4±0.5△組別例數時間潮濕積分總積分治療組 30治療前 2.7±1.2 9.6±3.1治療后 0.3±0.1△▲ 1.2±0.5△▲對照組 30治療前 2.5±0.9 8.9±2.7治療后 0.6±0.2△ 3.3±1.3△
(2)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隨訪半年后,治療組復發率為3.3%(1/30),對照組復發率為33.3%(10/30),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兩組急性、亞急性肛周濕疹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4 討論
肛周濕疹主要的自覺癥狀是瘙癢、潮濕。《素問玄機原病式》記載:“人近火氣者,熱微則癢,熱甚則痛。”《丹溪心法》曰:“諸癢為虛,血不榮于肌腠,所以癢也。”《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對本病的癥狀和病因病機也有明確的描述:“此證初起如粟米……隨處可生。由脾胃濕熱,外受風邪,相搏而成。”故本病的病因為風、濕、熱、虛。從肛周濕疹的病程上看,初期病機為濕熱內蘊,后期為氣血虧耗、血虛生風、濕熱內蘊。現代醫學認為,肛周濕疹病因復雜多變,是由多因素綜合致病的結果,一般認為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種,前者原因尚不明確,多認為與變態反應相關,后者常由肛瘺、肛裂、痔瘡等手術后分泌物所致[6]。目前對于肛周濕疹的治療,中醫主要包括中藥口服、熏洗、針灸、耳穴等,西醫主要有口服抗組胺藥、糖皮質激素、抑菌藥膏或洗劑、手術治療及紅光、激光等物理治療[7]。
除濕消疹一號方由苦參、黃柏、地膚子、蛇床子、茯苓、甘草組成。苦參具有清熱祛濕殺蟲的功效,用于治療濕熱下注之帶下、濕疹、濕瘡、瘙癢、疥蘚等癥,為君藥。苦參中的苦參堿類生物堿具有抗炎、抗過敏、鎮靜、抗滴蟲等作用[8]。黃柏具有清熱燥濕、瀉火除蒸、解毒療瘡的功效,具有抗炎作用[9]。地膚子具有清熱利濕、祛風止癢的功效,用于治療陰癢、帶下、風疹、濕疹等癥。地膚子水提物能抑制單核巨噬細胞的吞噬功能及遲發型超敏反應[10]。蛇床子具有燥濕祛風、殺蟲止癢、溫腎壯陽的功效,多用于治療濕疹瘙癢癥。研究顯示,外用蛇床子湯可明顯緩解皮膚病導致的皮膚瘙癢癥狀,減輕皮損,且安全性高[11]。黃柏、地膚子、蛇床子合用為臣藥。茯苓利水滲濕,健脾寧心安神,為佐藥。苦參、黃柏、地膚子、蛇床子均為苦寒之品,多損傷脾胃,且瘙癢多致人心神不安,故用茯苓寧心安神。甘草益氣補中,緩急止痛,緩和藥性,生用可瀉火解毒,為使藥。甘草主要活性成分是三萜皂苷和黃酮類化合物,具有抗潰瘍、抗炎、抗氧化、抗病毒、抗癌、抗抑郁和增強記憶力等藥理作用[12]。六藥合用,共奏清熱解毒、祛濕止癢、消腫止痛之功。
熏洗坐浴法是肛腸科常用的保守治療方法,可使藥效直達病所,配合水溫控制和局部適當通風,改善肛門周圍組織血運,有助于患者病情恢復。臨床上西醫常局部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但停藥后易反復,并有可能使潛在的感染病灶活動和擴散,最終形成慢性肛周濕疹,使治療更加困難[13]。本研究結果顯示,除濕消疹一號方內服加外洗坐浴能有效改善肛周濕疹患者瘙癢、潮濕癥狀,加快皮損愈合,相較于西藥治療,復發率較低。數據挖掘分析結果顯示,苦參、黃柏、白鮮皮、蛇床子、地膚子、蒼術、土茯苓、防風、當歸是中藥熏洗治療肛周濕疹的主要藥物,以清熱祛濕、攻毒殺蟲止癢、解表、利水滲濕、補虛為主[14]。除濕消疹一號方在前人用藥基礎上加以補氣健脾祛濕,可取得較好的療效。本研究納入的樣本量較少且比較單一,此后需要加大樣本量,開展多中心研究,以更全面地評估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