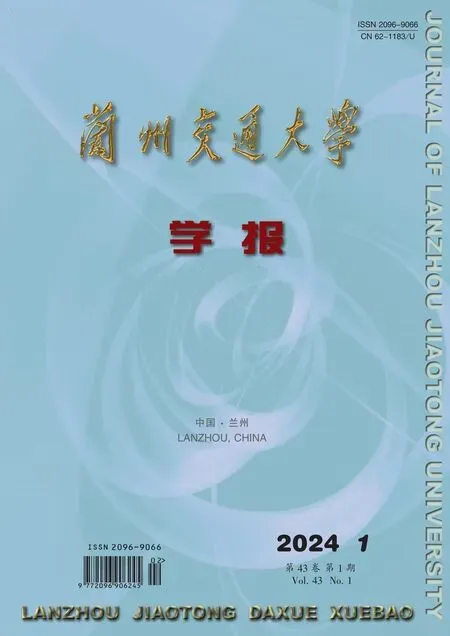數字經濟能夠促進中國服務業發展嗎?
金 梅,雷一鳴
(蘭州交通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蘭州 730070)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亟需以高效的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度重視服務化轉型,以優質高效的服務供給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支撐產業現代化、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實際需求中,核心問題在于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和體制構建,有效地協調和實施經濟發展的多樣化和動態目標(黃群慧等,2023)[1]。2022年,服務業的增加值達到了638 698億元,同比增長2.3%。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服務業所占的比例為52.8%,比第二產業高出12.9個百分點。數據表明,無論從就業機會吸納還是對經濟貢獻的角度來看,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產業,服務業的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這些成就的背后,中國服務業發展也面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服務業受到了“鮑莫爾成本病”的困擾。服務業的不可貿易性、難以實現規模經濟效益以及相對于工業部門,生產率提升較為緩慢等特點,服務業部門可能會將成本轉嫁給其他經濟部門,從而對整體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江小娟,2004)[2]。二是與發達國家在同等發展水平時期相比,中國的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所占比重相對較低,服務業內部結構也存在不合理之處。尤其是高知識、高資本、高技術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比例相對較低,服務業過度偏向“脫實向虛”現象(戴奎早等,2020)[3]。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占比迅速擴大,數字技術已經深入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新興產業、新商業模式和新業態推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黃群慧等,2019)[4],數字經濟已開始在各個產業和領域廣泛融合。“互聯網+”、大數據和智能技術的應用,出現了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興商業模式,加速了服務業的數字化改造。數字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不僅縮短了信息傳遞的時間和空間,增強了不同地區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系,促進了生產要素和產品的自由流動,有效擴大了服務業的服務范圍(袁航和夏杰長,2022)[5],提高了整個服務業的生產力。在新技術革命的背景下,數字技術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歷史機遇。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集群發展,構建高質量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數字經濟,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五輪顛覆性革命浪潮的產物,具備一種全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根據經濟學理論,數字經濟以其高度滲透性和協同性等特點,一方面可能有助于緩解服務業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也可能推動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數據作為生產過程的新要素,對于價值創造產生了根本性的顛覆性影響。相較于制造業,服務業對信息的敏感性更高,數據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可能更大,進而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可能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研究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的總體效應和作用機制,并提出數字經濟與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建議,有助于從理論角度更好地理解服務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提高服務經濟發展理論的深度。
1 文獻綜述
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文獻具體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數字經濟最早的概念是由Tapscott(1996)[6]在他的著作《數字經濟》中提出的,他將美國在“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框架下催生的新經濟形態命名為“數字經濟”。目前數字經濟的定義主要基于三種角度。一是基于技術形態劃分,如OECD在2012年的行動計劃報告中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信息與通訊技術(ICT)轉型升級的產物”(OECD,2012)[7]。二是數字經濟的定義可以基于產出的角度劃分,例如,英國經濟研究院將數字經濟定義為“由以信息通信技術為基礎的生產和銷售工具的投入所帶來的產品和服務產出”(Nathan和Rosso,2017)[8]。三是基于投入、技術和產出等多個因素劃分,美國商務部下屬的經濟分析局將數字經濟定義為“包括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交易和數字經濟用戶創造和訪問的內容”(BEA,2019)[9]。
二是數字經濟的測度方法。李研(2021)使用DEA-Malmquist指數[10],基于全國28個省份和八大經濟區的數據,計算了2005-2017年數字經濟產出效率[11]。魏萍和陳曉文(2020)從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普及狀況和技術應用等三個角度,選取了四個指標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來測度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12]。何宗樾和宋旭光(2022)使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測算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13]。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基于數字經濟測算體系,計算了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與總產值[14]。劉軍等(2020)基于省級面板數據,構建了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從信息化、互聯網和數字交易發展三個維度來研究數字經濟的發展,發現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在空間上呈現“數字經濟鴻溝”的特征[15]。趙濤(2020)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金融普惠兩個維度來測度中國22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16]。
三是數字經濟的影響評價。張勛等(2019)發現與數字經濟深度結合的數字金融服務通過激發居民創業意愿來促進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17]。李帥娜(2021)的實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通過促進經濟效應顯著提升了服務業的生產效率[18]。袁航和夏杰長(2022)提出加強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5]。戴奎早等(2023)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論框架下,探討了數字經濟通過提高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要素效率從而影響服務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和機制[19]。
已有研究文獻關注數字經濟的內涵、測度和影響評價,但鮮有數字經濟賦能服務業發展的理論研究,且作用機制的研究相對較少。基于已有文獻,本文的潛在貢獻可能在于:1) 從時間和空間異質性的方向來研究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為現有研究補充;2) 從技術創新、產業集聚和人力資本的角度,探究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作用機制;3) 在產業結構高質量升級的背景下,為加快服務業數字化進程提供理論依據。
2 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2.1 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作用
假說1:數字經濟能夠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相對于傳統的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勞動力等),數字經濟的特點在于數據首次成為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因素。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實現了各種資源的互通互聯(荊文君和孫寶文,2019)[20]。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數據要素能夠與傳統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和資本)形成增值關系。且數據要素的增殖近乎無限,顯著減輕了傳統生產要素受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制約的問題。數據的投入很可能會提高服務業的效率,為服務業的轉型提供強大支持(劉國武等,2023)[21]。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推動了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極大程度地緩解了傳統經濟條件下服務業的限制,例如非存儲性、不可遠距離貿易、生產和消費同時性等問題。這為服務業賦予了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長尾效應等三個特點(楊秀云等,2023)[22],改變了過去服務業的發展和增長邏輯,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數字經濟加速了要素流通,降低了服務業企業的交易成本。數字化轉型還使服務業企業能夠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現跨地域和異步的服務交易,顯著降低了服務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交易成本。借助不斷擴展和完善的信息網絡、ERP系統、CRM系統以及人工智能等工具,數字經濟還能夠促進服務業企業內部管理模式的改變,提高管理效率,最終加深數字經濟與服務業的融合。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了數字經濟與服務業之間的深度融合,對服務業的提升和創新發揮了關鍵作用。
2.2 數字經濟、技術創新和服務業發展
假說2: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創新活動伴隨著高投入、長周期以及不確定的回報,這導致服務業企業在進行創新活動時必須充分考慮創新成本和潛在風險。數字時代的來臨,數字技術在服務業企業的創新活動中得到廣泛應用。一方面,借助大數據和虛擬算法,數字技術加快了產品的迭代速度,各類商業模式和服務創新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數字孿生等技術的應用允許服務業企業通過數字仿真和情景模擬等方式,模擬實驗在虛擬空間中進行,避免了在物質世界中耗費大量資源的需求。例如,虛擬購物場景和在線體驗的模擬,大幅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成本。數字技術顯著提高了企業的信息獲取能力,尤其是在獲取用戶反饋和了解用戶需求方面。企業可以利用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快速捕捉核心需求和潛在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創新,減少了創新成本,推動了服務業企業的創新活動。
2.3 數字經濟、產業集聚和服務業發展
假說3:數字經濟能夠通過產業集聚對服務業產生影響。
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產業集聚效應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進行分析。
“橫向”角度:服務業與其他產業存在緊密的鏈接關系。例如,計算機等電子產品通常屬于中間制造業,而軟件服務以及信息技術服務則被歸類為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服務業。信息技術服務業通過數字技術實現了與傳統制造業更深入的結合,促進了這兩大行業的協同升級。信息產業具有高人力資本密度、高研發活動頻次和高研發投入強度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時還具備網絡性和滲透性等特點。在服務業與信息產業之間的互動中,知識、技術和創新成果更容易從信息產業部門傳播到非信息技術服務業部門,創造了積極的外部性效應。
“縱向”角度:數字經濟的發展提高了服務業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搜索和運營成本,提升了服務業的跨地區跨平臺的流動效率。這種情況產生的技術創新推動了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特點包括高知識密度、高就業率、高增長率和高輻射性。產業集聚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創新活動的頻率,提高了服務業的產出比重和層次。知識的擴散使得整個服務業的效率得到提升,最終推動了服務行業的發展。
3 實證研究
為評估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本研究擬選取數字經濟指數為核心解釋變量,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為被解釋變量,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從總體和部分對數字經濟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
3.1 模型設定
具體而言,本文設定如下模型:
Serviceit=α0+α1*Digit+α3*CVit+ut+eit
(1)
模型(1)中,變量Service表示地區服務業增加值,為文章的被解釋變量。Dig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為文章的核心解釋變量,CV為一系列控制變量。ut為時間固定效應,下標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
3.2 變量說明和數據來源
考慮到新冠疫情對本研究產生的潛在影響,本文選擇2011-2020年中國30個省(市、區)(不包括西藏)的面板數據,并對個別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補齊。相關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及各省(市、區)的統計年鑒。
1) 被解釋變量(Service)。本文參考汪偉等(2015)的研究,選擇三種度量指標:一是用各省(市、區)每年的服務業增加值衡量服務業發展(Service1);二是用各省(市、區)每年的房地產業、金融業、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增加值衡量生產性服務業發展(Service2);三是用各省(市、區)每年的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增加值衡量生活性服務業發展(Service3)[23]。上述三個指標均以2004年為基期,用消費者價格指數剔除價格因素后作對數化處理進行測算。
2) 核心解釋變量(Dig)。本文借鑒現有研究,構建了數字經濟的指標體系。具體參考了趙濤(2020)的方法,基于五個關鍵維度構建了數字經濟的指標[16]。包括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量、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量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其中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使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合作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郭峰等,2020)[24]。
獲取上述指標之后,本文采用了魯玉秀等(2021)的方法,對這些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運用熵值法來測算各指標的權重[25]。最后,本文通過綜合加權的方式得出了數字經濟的綜合指數。這些具體指標及其分類可在表1中找到。指標體系的構建,能夠更全面地評估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為進一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據。

表1 數字經濟指標構建
3) 控制變量(CV):① 服務業固定資本(Capital)。選取以2004年為基期,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來調整第三產業的固定資本投資額。② 服務業就業(Labor)。選取第三產業從業人數。③ 經濟發展水平(GDP)。本文使用人均GDP進行衡量。④ 外商投資水平(FDI)。選取外商直接投資額作為測算指標。⑤ 城市化水平(Urban)。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來衡量。⑥ 產業結構(Stru)。采用第三產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進行衡量。具體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統計
3.3 回歸結果
表3報告了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得到的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其中,第(1)、第(2)、第(3)欄分別為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進行回歸,為本文的基準回歸,第(4)、第(5)、第(6)欄分別為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進行回歸,且添加了地區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除被解釋變量為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其余回歸結果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明顯促進了服務業發展,部分驗證了H1的正向影響。數字經濟對生活性服務業影響有限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國的該行業目前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特征為主,主要吸收城市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相較于生產性服務業來說,一方面知識密度相對較低,數字經濟高創新性對其影響力有限;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務業的“生產消費同步”、“不可儲存”、“不可貿易”的特征更為顯著,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約束難以通過數字技術進行有效緩解。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3.4 異質性分析
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東部地區的經濟水平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地域間的不平衡差異使得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潛在機遇在不同區位可能存在異質性。本文將樣本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以深入研究數字經濟的影響。表4中呈現了數字經濟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空間異質性回歸結果。第(1)、第(2)和第(3)列分別報告了數字經濟對東部地區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和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的回歸結果;第(4)、第(5)和第(6)列分別報告了數字經濟對中西部地區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和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的回歸結果。

表4 空間異質性分析
分樣本后,數字經濟對中西部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促進作用不再顯著;同時,對東部地區整體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促進作用也顯著減弱。對這一現象可能的解釋如下:在數字化產業方面,相對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仍然以傳統業態為主,高新技術服務業與信息技術產業相關的占比嚴重不足。導致服務業高技術專業人才在中西部地區進行知識融合、交流和學習的機會較為有限,減少了溢出效應的程度。在產業數字化方面,中西部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相對較低。先進技術和信息在服務業中的應用不夠廣泛,服務業對數字技術的吸收效率較低,數字經濟對中西部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不再顯著。
本文進一步將樣本劃分為2015年前和2015年后,探究數字經濟在不同時間段的作用異質性。表5呈現了數字經濟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時間異質性回歸結果。第(1)、第(2)和第(3)列分別報告了2015年前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和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的回歸結果;第(4)、第(5)和第(6)列分別報告了2015年后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和生活性服務業增加值的回歸結果。

表5 時間異質性分析
在2015年前和2015年后,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促進作用都顯著達到了1%水平,但2015年前的系數明顯高于2015年后,表明數字經濟在2015年后的促進作用有所降低。可能有以下解釋:首先,2015年后中國網民數量增長速度明顯放緩,與信息化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逐漸趨于飽和,數字經濟的擴張力度不如2015年前那么強勁。其次,信息通信技術高度發達的美國對中國數字經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外部性影響,2015年后美國“中美脫鉤”計劃的提出,由于涉及政治因素,這種正外部性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3.5 穩健性檢驗
內生性問題主要源于雙向因果、遺漏變量及測量誤差。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的作用可能會受若干因素的干擾,包括資源稟賦、地理位置、財政水平以及政策支持等,這些因素或難以量化,或數據難以收集,研究可能存在遺漏變量的問題。服務業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也是數字經濟發展較好的地方,在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發展作用機制不明晰的情況下,可能存在雙向因果的問題。本文選取工具變量法和替換核心解釋變量作為本文的穩健性檢驗。
1) 工具變量法
工具變量的選取需要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兩個條件。本文借鑒黃群慧等(2019)的做法,選用各個城市1984年的固定電話和郵局數量這兩個歷史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指數的工具變量[4]。根據黃群慧等(2019)的研究,現代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是有傳統通信技術繼承和發展而來的,歷史上固定電話等電信基礎設施完善的地區更容易獲得先發優勢,數字經濟發展也可能較好,滿足了相關性條件。城市固定電話對樣本期間服務業發展幾乎沒有影響,滿足了外生性條件。固定電話數是截面數據,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的研究,以全國互聯網用戶數占總人口的比重與固定電話數相乘,從而構造出工具變量(iv)[16]。模型中所有變量的衡量指標保持不變,回歸結果見表6。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增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的促進作用在5%水平上顯著。

表6 工具變量方法的回歸結果
2)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滯后一期
本文還進行了另外兩組穩健性檢驗,一是通過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測算數字經濟指標權重,綜合加權后得到數字經濟綜合指數(Dig2)并作回歸,二是將控制變量滯后一期,再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其中第(1)、(2)、(3)列為替換解釋變量法的回歸結果,第(4)、(5)、(6)列為控制變量滯后一期的回歸結果。回歸結果均在1%水平上顯著,進一步證明基準回歸的穩健性。

表7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滯后一期的回歸結果
3.6 服務業結構分析
前述分析主要關注了服務業的“規模”方面,但同樣值得深入探討數字經濟對服務業“質量”的影響。中國的服務業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困擾(夏杰長和肖宇,2019),可能導致服務業的發展受到“鮑莫爾成本病”的制約[26]。根據經濟學理論,傳統服務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通常滯后于現代服務業,后者以知識、資本和人才密集為特征。然而,傳統服務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往往會與現代服務業部門同步上升,導致傳統服務業部門在整體服務業中的比重逐漸增加,整體服務業的發展受到制約。
理論上,數字經濟既能推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迅速發展,又能推動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可能對服務業結構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本文此部分通過構造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服務業結構造成的影響。具體參考段文斌等(2016)對現代服務業的定義,采用現代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作為衡量服務業高級化(Serstru)的指標[27]。測算的現代服務業具體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模型設計如下:
Serstruit=β0+β1*Digit+β3*CVit+ut+eit
(2)
模型(2)中被解釋變量替換為服務業高級化(Serstru),解釋變量分別為熵值法計算的數字經濟指數(Dig)和主成分分析法計算的數字經濟指數(Dig2),控制指標均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服務業高級化和數字經濟的回歸結果
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有望推動服務業的高級化結構和結構升級。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為構建服務業產業體系的結構優化注入了新活力。數字技術的應用,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有助于促進數據共享、資源流動和價值共創,從而推動高質量服務業業態的興起,提升整體服務業的質量,優化服務業的結構(戴魁早,2023)[19]。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還推動了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升級,這為服務業結構升級提供了實質支持。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縮小傳統時空距離,降低創新要素的交易成本和集聚成本,尤其是能夠增進高水平人力資本的“網絡集聚”和“云端合作”機會,這為創造有利于集體學習和創新的環境創造了條件。數字基礎設施的升級促進了知識的流動和共享,加速了知識的外溢和擴散,增強了技術創新能力,從而助力了服務業結構的升級(袁航和夏杰長,2022)[5]。高水平的人力資本結構也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化可能影響服務業的要素供給結構,進一步改變服務業的結構(戴魁早等,2020)[3]。
4 結論及政策啟示
在中國經濟邁入“換擋調速”的新常態時期,發展服務業,特別是以生產性服務業,成為實現經濟動能轉換和社會穩定的關鍵驅動力。本文基于省級面板模型,通過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對數字經濟滲透服務業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基礎回歸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在促進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方面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數字經濟對生活性服務業影響不顯著的可能原因是中國生活性服務業目前仍以吸納城市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
第二,在異質性分析中,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存在時間上的異質性。具體來說,數字經濟對東部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區這種作用不明顯;數字經濟對生產性服務業的促進作用在2015年之前更為顯著。
第三,研究進一步指出,數字經濟可以顯著推動服務業的高級化結構和結構升級。數字技術的應用推動高質量服務業業態的興起,提升整體服務業的質量;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升級增進了高水平人力資本的集聚,改善了服務業的結構。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速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的潛力尚未充分挖掘,服務業應積極參與數字化轉型。政府可以通過提供稅收激勵、財政補貼和低息貸款等方式,推動服務業與其他產業的深度整合;加大對小微制造業和私營企業的支持力度,協助它們成功度過數字化轉型期,克服“數字鴻溝”;服務業企業應增加研發資金,積極合作并充分利用社會的創新資源,以促進不斷地創新。
第二,促進不同地區間的數字紅利共享。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的“扶強”特點,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實現區域服務業的差異化發展。東部地區應培育以創新引領、以知識技術密集為特征的數字化服務業企業,為全國建設服務業數字化轉型的樣板。中西部地區則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區域內民族和特色服務業的數字化發展。政府應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加大中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
第三,推動服務業的數字化集聚。在數字經濟時代,更強大的數字網絡和頻繁的人員交流使得知識和創新成果更容易傳播。需建立企業間協同合作的互聯網平臺,增強跨行業企業的合作意識,促進數字資源在服務業內部、服務業與農業、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相互聯通;加速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數字技術和服務經濟在更廣泛領域的協同集聚,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打破數據和信息要素的流動障礙,促進服務業在“橫向”和“縱向”的集聚發展。